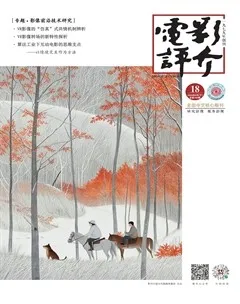國產公路電影中流行音樂的生命敘事與理想建構


【摘 要】本文通過對近年來國產公路電影中流行音樂元素的創新應用進行深度探討,揭示流行音樂從單純的情感渲染逐漸轉向具有承載生命哲思與理想追尋重要符號的新特征。流行音樂通過與敘事動態聯動、豐富影片層次結構以及拓展敘事空間,強化電影情感表達和敘事連貫性。同時,生命敘事在音樂中得以升華,深化角色心境與故事內涵,推動理想建構主題的發展。流行音樂在電影中的運用還展現出本土化的“影音互文”敘事策略,以及獨特的中國式詩性抒情審美,映射出中國社會變遷、地域文化和個體生命體驗。此外,通過進一步論證流行音樂在公路電影中跨越視聽界限,構建獨特的“音樂-敘事”互動結構,從而實現對生命歷程的詩意詮釋與理想愿景的藝術重塑,實現對個體生命經驗的象征性表達與理想追求的精神投射。
【關鍵詞】 國產公路片; 流行音樂; 音樂維度; 電影敘事
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文化運動和文化思潮的影響下,尤其是法國新浪潮的“反叛”精神,旨在打破社會既有規范和傳統道德觀的束縛。《逍遙騎士》(丹尼斯·霍珀,1969)是公路電影的典型范例,美國公路上游蕩的騎士踏上通向夢想和愛的遠方。“在路上”意味著不可調和的文化和社會沖突,如自由與壓制、個人與社會、生與死等問題,用自身“離開”的反叛行為,以自由的宣言丈量著人性的尺度,具有天然的批判性。這種“在路上”的狀態,以空間地理為敘事空間,充滿隱喻和象征的元素,穿過時空的不確定性體驗,追尋的是精神的“回歸”。公路電影借著工業的發展態勢,多元化的類型趨勢嶄露頭角,與其他類型之間的關系,或借鑒模仿,或反思批評,在這種或緊密或游離的關系中,使公路類型化在鞏固與顛覆之間逐漸成熟,如《末日狂花》(雷德利·斯科特,1991)是劇情、犯罪的結合,被黃沙、塵土和巖石包裹的公路成為關鍵角色,預示了另一種烏托邦和人生理想。
國產公路電影中的社會結構和文化語境是人與社會轉型關系,《落葉歸根》(張楊,2007)中“背尸還鄉”的鄉土情結,徐崢“囧”系列的中產階級危機,《無人區》(寧浩,2013)的荒誕喜劇以及韓寒《后會無期》(韓寒,2014)中人與村莊的背離關系等,以“在路上”呈現社會轉型時關于人的故事。近年來,國產公路電影的商業化、類型化運作,有票房和口碑的成功案例,背后深層次的文化邏輯則是后現代性的敘事技巧迎合觀眾的審美需求。
一、流行音樂在國產公路電影中的敘事功能
國產公路電影中,俄羅斯作曲家穆索爾斯基“別再談論藝術界限的問題吧。我根本不相信藝術有什么界限。”[1]當藝術不再設限,就處于全方位、多層次的兼容狀態,因此流行音樂和電影藝術就有著天然的黏性,能夠在必要時加強兩種藝術體裁的“黏合度”。流行音樂與公路電影的故事內核、情節、角色、情感渲染的不斷調適的過程中,延展出更大的影視表述空間,逐漸呈現出跨界融合的“新特征”。電影和音樂以“流”的形式,在流動中構成整體,“電影音樂”有著一般音樂的共性,又有作為電影音樂的特殊性。
(一)音樂文本與電影敘事的動態互動
語言學范疇的“文本”,作為紙面的、口頭的某種語言承載物,隨著敘事學理論的出現,“文本”概念逐漸被文學、音樂領域引用。電影中流行音樂的調性布局、織體形態和音響組織在影片中得到有效恰當的運用,超越純粹的音樂形態,如與劇情緊密交織,推動劇情發展、揭示人物關系的關鍵線索。流行音樂遵循國產公路電影的創作邏輯,音樂文本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電影敘事的不足。文化互融視角下,音樂和電影兩種藝術體裁形成同生共構關系,電影強大敘事功能也賦予音樂文本較強的敘事性。
流行音樂主題與公路電影的敘事內核的動態互動關系,音樂主題以音樂語言、歌詞等,直抵公路電影故事內核,成為敘事主題的音樂化表達,電影對流行音樂有著內容和形式上的需要。音樂用“敘述者”“第二臺詞”視角解讀故事。音樂編曲創作在配合國產公路電影劇情發展需要,是一種不純粹的音樂形態,和聲、調式、節奏等音樂語言,在音樂起承轉合與情節的沖突、高潮、轉折、結局等關鍵節點精確對應。《后會無期》電影情節中對音樂元素的多樣化,就是將經典音樂或歌曲進行流行化改編融入電影的修辭語言。《西游記》(楊潔,1986)中唐僧途經女兒國時的歌曲配樂《女兒情》,在電影中浩漢和劉鶯鶯分離的那場戲里,導演采用《女兒情》的音樂作為敘事的延伸;浩漢和江河告別劉鶯鶯之后就開車離開,行駛在一條仿佛沒有終點的公路上。
在這樣的語境下,《后會無期》等國產公路電影通過對流行音樂文本的精心編織,充分展現音樂作為非言語敘事工具的巨大潛能。影片中的音樂文本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如同故事中的隱形線索,通過其內在的情緒起伏和主題演變,與鏡頭語言、表演藝術以及劇本臺詞共同構筑起立體的故事空間,使音樂文本在國產公路電影中成為無可替代的敘事構件。
(二)音樂結構豐富電影敘事層次
“在音樂審美中,這兩種思維活動都是存在的。最直接的常是形象思維,即人們從音樂中感知、獲得間接的具體形象和情感變化;其次是邏輯思維,即分析、思考音樂的形式、邏輯、結構和布局。”[2]音樂的情感引發,有著音樂情緒誘發機制的前置條件,也離不開從音樂材料的編輯中,獲得的具體音樂形象,在音樂預期中對人的生理喚醒。那么,電影中的音樂結構不再局限于旋律、節奏、調式、和聲等組成要素,而是從電影整體敘事層次中,用不同的音樂風格、樂器、歌詞等對影片內容和精神進行詮釋,根據電影敘事需要對音樂結構的靈活創新運用。
音樂結構具有層次性、邏輯性,深入電影的鏡頭語言、敘事內容等創作肌理中,是音樂想象力與視覺畫面的深度結合,描繪音樂情緒動態,通過雙重敘事的方式,傳達豐富的情感層次和深度。《去大理》是歌手郝云應邀為電影《心花路放》(寧浩,2014)的情節特意創作的歌曲,充滿滄桑感的抒情味道。歌詞以問句的方式一句一句的呈現現實難題,仿佛是在對電影中的男女主人公發出的靈魂叩問。這首歌也在一定程度上給布滿喜劇色彩的電影增加深度:音樂既交代電影敘事的情節線——去向大理,也是黃渤作為過氣歌手這一人物設定的情節需要;與此同時,音樂作為獨立的媒介介入相當于對幾個主要人物這一路的行走和成長給予評價和注解。
《心花路放》中,當阿凡達們演出時,舞臺上播放網絡串燒歌曲。“你是青里透著藍,我是黃色屌絲男”歌詞低俗而直白充滿戲謔和調侃意味,伴隨節奏感強的嘈雜電子音樂;這首歌為電影的該場景特意創作,意指舞臺上正進行著的和電影中此刻發生的雙重敘事情境。國產公路電影與流行音樂的跨界互動,音樂以其超越言語的表意能力,補充并延伸角色的性格塑造和劇情發展,通過音樂結構與視覺畫面的深度耦合,旨在實現更深層次的情感挖掘與敘事建構。音樂的內在邏輯與影片情節發展相互呼應,形成“音畫互文”的藝術表達,增強故事的立體感和主題的深刻性。
(三)音樂想象力拓展電影敘事空間
音樂想象在思維中展開,無形之中又能被具體感知的音樂冥想,以聽覺的抽象形式存在,需要在時間中完整呈現,有著特殊的時空邏輯。電影音樂縫合兩種藝術體裁之間的差異,使抽象的思維行為具體化、可視化,在描繪性音樂、情節性音樂、音響感知與情感體驗等三種不同的音樂欣賞方式中,音樂想象力與電影的敘事空間有著更為緊密的內在關系,共同營造“影像時空環境”。鏡像語言與音樂的動態持續發展,時間上連接了過去、現在和未來三種時態,通過音樂“連所再現”的思維形態結構,依靠音樂想象力在電影敘事空間上進行更為廣延的拓展。
公路和汽車都是空間延伸的想象,人們不斷擴展物質空間,同時又為創造出的新的空間秩序所桎梏。《無人區》中,地上一只被獵殺的鳥的鏡頭以一個吉他泛音配樂;影片正式的片頭音樂隨著汽車行駛而響起,吉他、號子、電子音樂等音色質感描繪黃沙大漠的荒涼景象,緩慢、沉重的鼓點節奏,以音樂想象形式加深對大漠、公路這種影像地理空間的描繪。影片中的大量運用塤這種土質的吹奏樂器,音色拙樸抱素與黃沙大漠有著本質上的相似性,更能襯托荒涼大漠的空間特征。
音樂與視覺影像相互呼應,通過對各類地域音樂風格的細膩表現,深刻揭示并傳達多元的文化內涵與社會景觀,進而將公路電影的敘事空間從直觀的物理旅程延伸至更為寬廣且富含意蘊的精神領地。音樂作品中的象征符號和隱喻運用深化電影的符號學意義,有助于表現角色內在心理變化、時間流逝與空間變遷等多層次的主題。音樂的想象力量在公路電影中顯著拓寬敘事的空間結構,并在觀眾內心創造出充滿情感張力的藝術空間,實現聽覺與視覺藝術的深度融合與高級表達。
二、流行音樂對國產公路電影的有效闡釋
流行音樂在電影語境中,不僅扮演著敘事補充的角色,通過歌詞與旋律的情感投射,深化角色性格塑造與情節推進的內在邏輯。而且在符號層面上,流行音樂作為文化符碼,蘊含時代精神與集體記憶,與影像交織形成復調式詮釋,拓展電影的語境含義與社會批評維度。同時,音樂與視覺藝術的聯覺互動,按照時間性結構編排,實現電影時空構造的藝術升華。此外,流行音樂憑借其普適性與認同感,實現電影文本在大眾傳播層面的有效闡釋與重構。國產公路電影與流行音樂的交叉與融合,跳出歌詞、旋律的藩籬,突破音樂的聽覺限制,配合影像畫面講故事,力圖結合影像畫面進行更深度的詮釋。
(一)音樂元素對生命敘事中的升華
“電影中使用配樂不足為奇,但在公路電影中,音樂就不僅僅是電影的一種構成要素,而是構筑其地理空間必不可少的媒介。音樂,尤其是大量民謠和搖滾樂的插入,對于塑造公路電影的流動性起到了重要作用。這兩種通俗文化的表現形式,與公路電影中途經的地域面貌相結合,能夠強化其空間感,使該地區的特征顯露出來。”[3]國產公路電影中的音樂主題與公路旅程的核心象征物形成象征對應關系。音樂主題通過音樂符號、音樂意象等元素,與公路旅程的地理空間、心理空間、時間流逝等象征意義緊密相連,共同構建電影的象征體系。
公路片擅長表現青春的迷惘、傷痛和對人生意義的追尋;主人公帶著或失意或迷茫的心境踏上一段未知的旅程,開始對人生價值感和自我身份的重新確認或是對生命意義的最終消解。歌曲所代表的是當下充斥在互聯網和現實生活中的人們對視聽暴力和通俗娛樂的追捧——在某種意義上,是崇尚純粹的消費主義、消解意義追求即時滿足的社會生態。
“從音樂中吸取了通過音響世界去獲得的協調與節奏感”。[4]《后會無期》電影開頭《東極島島歌》,曲子來源于2006年的好萊塢喜劇電影《波拉特》的音樂旋律,緊接著敘事內容銜接的卻是三個社會男青年四處游蕩的漫無目的的旅程,電影自動產生一種鮮明的情緒對照,更加突顯人物內在精神的空洞。在主題意義生成的層面上,這是人物在心中的理想和不盡如人意的現實之間愁苦的隱喻。《泰囧》(徐崢,2012)用喜劇的外殼包裹著對家庭、事業、人生的探索與思考,鬧劇過后的冷靜便是對自我的剖析,鋼琴悠揚緩慢的旋律隨著穿林過河越草地回歸自然、本真的狀態,完成對生命敘事的升華。
音樂元素在生命敘事構造中發揮著無可替代的內在化與象征性功能,是對生命情感動力學的一種高度抽象和結構化詮釋。在各類敘事文本如電影、戲劇、文學等范疇內,音樂作為一種獨立且交織的敘事層次,以其獨特的旋律結構、節奏韻律以及和聲轉換,映射并塑造生命經驗的時間性和空間性維度。
(二)流行音樂對理想建構的推動
“尋找”是公路電影的永恒主題,其文化姿態關注內在探索,從“路上”獲得成長,擺脫現實生活帶來的精神困境。“類型電影的環境是一個成規化的場所,不僅是場景更是一個文化社區既提供了發生動作的空間,還通過類型的重復過程形成了一個本身就具有意義的文化領域。”[5]公路電影創作受時間、文化、地點等“場域”的影響,表現特定時期的社會現實問題,而“尋找”的主題仍舊不變。
電影的同名片頭曲《后會無期》(鄧紫棋演唱)改編自美國女歌手琪特·戴維絲1963年發行的The End Of The World,這首略帶感傷的舒緩的鄉村音樂也在訴說離別、愛情的失去和告別之意。韓寒借用并保留原曲目的感情基調和精神內蘊同時以中文填詞,完美契合公路電影的主題:人們夢想逃離故鄉和現實困境,借助現代化的工具或技能去尋求現實到理想的飛躍、封閉到自由的飛躍、陳舊秩序到新的物質領地的跨越。歌曲的感傷基調與公路電影中主人公的迷茫與追尋形成共鳴,借由音樂這一跨文化的語言,揭示影片中角色試圖掙脫既有生活框架,借助公路旅行這一現代象征形式實現自我超越與理想重構的深層寓意。
《心花路放》中流行音樂出現在日常化的場景中——健身的人群,動感的廣場舞,是構建當下環境氛圍的真實感營造出一種瞬間的真實性,也暗指人物的情感和心理真實。電影采用正序與倒敘交叉的雙線敘事模式,最終在“來”與“離”大理時,小提琴、低音提琴交替敘事穿過耿浩與康小雨相識的場面,又回到現在,隨著小、低提琴緊張快速的節奏旋律,推動著人物正面面對自己的人生困境,逐漸明晰自我價值與理想目標,從而推動他們走出現實的荒誕與無奈,走向心靈救贖與理想重構的道路。
流行音樂所代表的摩登氣息和浪漫主義風格會跟人物正經歷的現實的荒誕和無奈狀態形成一種戲劇沖突感,人在矛盾和沖突中推動理想建構的過程。音樂對理想建構過程的一種深度介入與有力推動,揭示角色在公路旅途中不斷找尋、反思和重塑理想的心靈之旅。
三、流行音樂在國產公路電影中的文化映射
國產公路電影并非借著西方的發展經驗就能“拿來用”,在電影工業化進程中逐漸脫離美國經典敘述模式,公路電影的生態環境及創作取向和癥候,受中國文化場域影響,如發展脈絡、文化語境及社會心理中,整體呈現本土化的文化特征和精神取向。國產公路電影與流行音樂的交融互鑒,為本土文化傳承賦予新的藝術表達維度。《人在囧途》《無人區》《心花路放》《后會無期》等國產公路電影在內容與文化象征層面上本土化重構,不僅是物理空間上的移動敘事,更是通過對廣闊地域景觀的展現,深入挖掘并反映中國文化情境下的社會變遷、家庭倫理、民族風情及個體生命體驗等多重主題,構筑區別于西方公路電影的、蘊含深邃東方哲學觀照的獨特敘事框架。
(一)“影音互文”的本土化敘事
國產公路電影聚焦于社會生活的碎片,從微觀視角切入,關注個體命運和人與人關系的現實問題。一個值得品味的問題,對真實情感的需求,對叢林法則的厭惡,對虛偽、丑惡發自內心的擯棄,在“失樂園”中向外出走,尋求心靈的寄托和救贖,表達著一種后現代性的價值判斷。“不安與不確定性”“自由和孤獨”便是公路電影所探討的現代性問題。流行音樂能夠精準地把握并傳達這種深層的心理結構和時代問題,將自身的功能性優勢與電影的空間構建靈活性相結合,最終形成屬于公路電影的抒情表意模式。
“落葉歸根,入土為安”的鄉土情結,使公路電影《落葉歸根》有著濃厚的中國人文情懷。影片中通過聚焦“農民工”老趙與老劉兩個人在路上的經歷,低音提琴、笛子、鋼琴和小提琴的旋律安靜的、平緩的響起,音樂不再成為主要敘事,而是間歇的情感宣泄。跟牛比賽用歡快的鋼琴配樂,帶著戲謔的喜劇色彩。“影音互文”敘事方式以流動的畫面與旋律勾勒出現代社會中老趙“在路上”的苦中作樂,深層的是社會轉型期個人困境,反映出本土文化語境下的獨特人文關懷,其實踐在跨媒介對話中有力地推動了本土文化轉化和發展。
《人在囧途》以“春運”返鄉難成為敘事節點,“三聚氰胺”事件使“要薪”成為“討債”,為電影敘事作引,當公共汽車行駛在鄉村的道路上,吉他輕松愉快的旋律,回蕩在鄉村田間,隨著鏡頭的轉換,音樂旋律與春節的氣氛相得益彰,烘托喜慶又和諧的畫面。然而隨著撞人事件發生,矛盾的升級,緊密的鼓點節奏、快節奏的吉他彈奏配合著畫面語言,還有小提琴、鋼琴的加入,人物間的矛盾開始升級,音樂終止于救人成功。在這個過程中,音樂與公路電影的空間流動性結合,形成對中國社會現實問題進行藝術再現與哲理思考的有效抒情機制。
流行音樂作為電影的重要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其如何精準捕捉和表達現代社會個體心理結構中的復雜矛盾與普遍焦慮,諸如對真實性的人性訴求、對叢林法則的批判性反思,以及對虛假與丑陋現象的道德摒棄。流行音樂與電影空間的深度融合成為一種有效的抒情與哲理性反思機制,透過視聽藝術的獨特力量,對中國社會現實問題進行深度解讀與審美再現。
(二)“中國式”的審美呈現:詩性抒情
“公路電影承載的是不同的文化寓意和時代主題,中國的公路電影雖然在發展之初借鑒好萊塢,在內容與文化寓意上卻具有迥異于好萊塢的旨趣和范式,這種文化跨界中的吸收與變異適應了中國觀眾獨特的欣賞口味并折射出東方文化的審美情趣。”[6]公路電影在中國文化語境中,除了類型電影的制作模式,在儒道思想影響下形成圍繞“離去”“歸來”的敘事模式,在意象的描繪和意境的構建中,表現出國產電影獨有的抒情方式——詩性抒情。
《無人區》作為一部表現中國西部風貌深度剖析人性的另類公路片。電影中的音樂元素運用不多,只有寥寥幾處卻起到點睛的作用。徐崢決定獨自返回二道梁子去救人的情節段落中,音樂在此時像主人公的呼吸和心臟律動般瞬間響起,伴隨著他騎馬在沙漠中昂首前進,構成一次讓人振奮又情緒激動的完整抒情,意味精神“歸來”的完成。音樂取材自羅德里戈的《阿蘭胡埃斯協奏曲》,并在改編中融入金屬搖滾元素,東西方音樂風格的交融與中國公路電影所追求的“詩性抒情”美學理念相得益彰,即在冷靜與殘酷并存的影像敘事中,揭示對于回歸本真、追尋精神歸宿的深切人文關懷。
中國公路電影在儒道等傳統文化底蘊的影響下,建構一種以“離別-回歸”為主線的敘事模式,并在影像表達和意境營造中展現典型的詩性抒情特征。國產公路電影中的音樂策略不僅成功塑造影片獨特的視聽體驗,也進一步凸顯中國公路電影在全球化視野下,通過本土文化的深度挖掘與創新演繹,展現出屬于中國電影的獨特韻味和詩意空間。音樂與電影敘事的有機融合,既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底蘊的當代轉譯,也是對中國公路電影詩性抒情美學的有力實踐。
結語
在國產公路電影這一特定的文化場域中,流行音樂已超越單純聽覺裝飾的范疇,而上升為一種具有深厚哲學意蘊和生命哲思的重要敘事手段。流行音樂以其特有的情感穿透力和象征意味,巧妙地嵌入公路電影的敘事脈絡之中,不僅揭示了角色復雜微妙的心理變化,還在微觀層面生動呈現了個體在面對生活困境與追尋人生理想過程中的心靈歷程,從而構筑一種動態、立體且富含哲理的生命敘事體系。
在未來的國產公路電影創作實踐中,應更深層次地挖掘流行音樂作為敘事元素的潛在價值,通過理論與實踐的緊密結合,不斷探尋音樂敘事與影像敘事相融合的嶄新路徑。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提升國產公路電影在全球化語境下的藝術品質與文化影響力,使流行音樂的生命敘事與理想建構在光影世界中得以更富有深度與廣度的展現,從而推動中國電影藝術邁向更高層次的精神探索與美學追求。
參考文獻:
[1][日]巖崎昶.電影、文學、戲劇[M]//陳犀禾.電影改編理論問題.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8:104.
[2]葉純之.音樂美學十講[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6:1,52.
[3]邵培仁,方玲玲.流動的景觀——媒介地理學視野下公路電影的地理再現[ J ].當代電影,2006(06):98-102.
[4][蘇聯]C.弗雷里赫.論電影美學的特性[M]//陳犀禾.電影改編理論問題.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8:31.
[5]吳瓊.中國電影的類型研究[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15.
[6]張金華.文化跨界中的吸收與變異——中美公路電影比較[ J ].中外文化與文論,2011(01):59-63.
【作者簡介】" "盧致遠,女,江西贛州人,贛南師范大學科技學院音樂系講師;
雷 晴,女,河北秦皇島人,北京科技大學天津學院藝術學院音樂系講師。
【基金項目】" "本文系贛南師范大學科技學院中央蘇區文化教育研究專項課題“音樂中的鄉土記憶一中央蘇區音樂與贛南、閩西等地域文化的雙向影響”(編號:YJZX2024-01)階段性成果,受贛南師范大學科技學院中央蘇區文化教育研究專項課題資助、贛州市社會科學規劃課題“中央蘇區音樂的歷史與文化價值探究”(編號:2024-NDWX03-0994)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