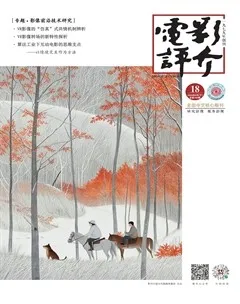日本作者動畫與中國文人動畫互補與共生探賾



【摘 要】 在文明交流互鑒的當下,歸納總結日本作者動畫與中國文人動畫在儒家文化、藝術個性以及東方美學上的相似性,比較分析日本作者動畫與中國文人動畫在藝術風格、情感基調和人性表現上的相異性,探賾這種異質性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而是在相互影響和相互融合中形成的互補共生關系。本研究指出中國動畫必須主敬存誠,不僅要堅守,而且要取法,只有這樣才能實現中國動畫發展新飛躍。
【關鍵詞】 日本作者動畫; 中國文人動畫; 互補與共生; 中國動畫崛起
長期以來,日本動畫以鋪天蓋地的“蝗蟲戰略”占領了開闊而穩定的世界市場,與美國動畫電影形成雙雄對峙格局。作者動畫成為日本動畫的砥柱,影響著世界動畫發展。目前,中國正處于“新動畫中國學派”重建的關鍵時期,曾扛起“開創民族動畫”大旗的文人動畫,仍將擔起重任,砥礪前行。
中日兩國因“物理距離,注定了我們在文化領域有很多共性,不管是東亞的文化基因,還是發展軌跡,甚至作品的相互影響,都完美詮釋了什么叫一衣帶水的鄰里關系”[1]。就此而言,日本作者動畫和中國文人動畫歷來不是獨立發展、相互排斥,而是在相互影響和融合中形成互補共生的關系。兩者在藝術追求、文化觀念以及藝術審美等方面雖有差異性,但更具相近性。日本作者動畫濫觴與發展得益于中國文人動畫的啟蒙,而中國文人動畫的成熟又取法日本作者動畫的啟示與輔弼。無論如何,如今中國由動畫大國正在走向動畫強國,可借鑒日本動畫的成功經驗,進行自我革新與發展。
一、日本作者動畫與中國文人動畫的相似性
日本“作者動畫”由歐洲“作者電影”引申而來。法國電影理論家安德烈·巴贊將電影“作者”確認為導演;亞歷山大·阿斯特呂克主張攝影機要像作家的筆一樣,自由描寫事物,確立導演的地位,強調導演作為藝術創作者的自由表達。①日本作者動畫與歐洲作者電影一樣,關注現實生活,強調創作者的個性表達和影片的客觀真實性,反映創作者對現實生活的獨特思考,批判反思意識強。
中國傳統的文人動畫傳承了中國文人畫的文化精神,以中華美學思想表現詩意人生、家國情懷以及社會思潮等內容,“寓教于樂”,表達中國文人“天下之興、匹夫有責”的社會責任感。21世紀以來,中國現象級動畫電影層出不窮,思想內涵的深度、題材范圍及表現形式革故鼎新,并開啟了具有自省和批判意識的“成人向”動畫之路。這些作品以傳統故事為創作素材,在形式上追求文人情趣,內容上或映射當下中國社會問題和大眾情感,或賡續自“五四”以來的反專制主題,極具“載道”“濟世”的中華文化精神。
就內涵而言,日本作者動畫和中國文人動畫同樣受儒家文化的浸潤,彰顯藝術個性,極富東方美學特色。
(一)儒家文化:思想浸潤,變異創造
日本作者動畫和中國文人動畫同屬漢文化圈,受儒家思想浸潤和正統漢文化觀念以及五服制思想的支配,影響至深。后因西方基督教進入,日本開始去漢化和廢除漢字。盡管如此,隨著東亞的再度崛起,學習漢字文化的優勢再度被審視。
諸子百家中,儒家兼收并蓄,或取之于道家,或取之于法家,或取之于墨家,使自身有容乃大。大和文化亦有著“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日本的“和魂洋才”同中國的“中體西用”一樣,是日本作者動畫的一大特點。如《千與千尋》(宮崎駿,2001)是日本妖怪文化與東方人文倫理的融合,《風之谷》(宮崎駿,1984)中的角色造型是中世紀歐洲游牧民族服飾加上亞洲人的面孔。此外,日本物哀美學是在中國儒家文化和“感興”美學思想基礎上的演化。如《輝夜姬物語》(高畑勛,2013)中風起云涌、山野寂寥的風景描繪,表達了輝夜姬在現實面前的無奈和挫敗;黑暗的景色、微弱的燭光和碎片的碟子表現出輝夜姬的弱小,隱喻著她浪漫而凄美的愛情。
中國文人動畫中儒家思想占據主導地位。如水墨動畫《山水情》(特偉等,1988)中“幾乎每件東西都具有儒家文化特質,音樂旋律中也蘊涵著中國古代文人音樂的精髓。凸顯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是一部如散文詩一樣優美的動畫片”[2]。老琴師與漁家少年之間的關系,正是儒家學說中“有教無類”的思想;少年學琴的刻苦,琴聲穿越四時變換,忘我的彈奏,體現了儒家文化中“學而不厭”的傳統美德;古琴暗示中國傳統“禮樂”文化,是一種文化堅守。動畫電影《姜子牙》(程騰/李煒,2020)“借用儒家思想中孔子的‘天命論’以及孟子的‘民本’思想賦予了‘武王伐紂’以正義性”[3]。
日本作者動畫和中國文人動畫雖受儒家思想浸潤,但均追求在自身傳統文化基礎上的蟬蛻龍變。如宮崎駿動畫電影中的未成年女主人公,葆有新時代的女性觀,旨在號召女性努力尋求自我,獲得社會認可。日本人強調“忠”,強化日本特有的武士道精神。如《風之谷》中娜烏西卡面對多魯美奇亞的“白衣魔女”庫夏娜的大軍、吉貝特人和王蟲之間難以調和的戰爭,她勇敢、鎮靜,甚至犧牲自己,使風之谷免受滅頂之災。日本動畫中的“物哀美”是對中國儒家思想“悲天憫人”的變異表現。中國文人動畫進入21世紀后,在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博弈中構建了新的神話宇宙,對儒家文化是一種創新性的傳承。
(二)藝術個性:批判反思,求新求異
日本作者動畫和中國文人動畫都反映或影射現實生活,表達作者真情實感,旨在啟發人們反思自省,具有批判意識。如宮崎駿作品始終讓觀眾感受到一種“向死而生的悲壯情懷,他展現的人類末日災難帶有藝術家的科幻想象和預設,目的還是著眼于現世。他深深認識到‘人心惟危’,因此稽古振今,目的是警醒世人”[4]。高畑勛作品總能讓觀眾感受到歡樂表層下隱藏的悲憫情懷和現實憂思。諸如此類的中國文人動畫有鞭撻人性貪婪的《九色鹿》(錢家駿等,1981);洞見人性自私的《三個和尚》(徐景達,1980);表達“英雄失路、壯志難酬的情懷”[5]的《山水情》等。21世紀的中國文人動畫更注重當下社會問題,表達真情實感和時代精神。如《哪吒之魔童降世》表達的“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抗爭精神;《長安三萬里》(謝君偉等,2023)的“家國情懷、文人品格與詩意人生,都是中國式人文精神的集中展示”[6]。總之,日本作者動畫和中國文人動畫作為藝術動畫,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內涵和批判意識。
日本作者動畫和中國文人動畫都在形式上求新求異,力圖沖破商業類型片的敘事窠臼。今敏著迷于“元世界”;新海誠追求唯美畫風,擅長營造“空間感”;山田直子偏愛長焦鏡頭、腿部特寫和意象隱喻等手法。而中國的特偉、錢家駿、唐澄把齊白石的水墨畫做成動畫,創作賡續文人畫傳統的水墨畫。美影廠的藝術家將民間藝術形式引入動畫,創作了木偶動畫、剪紙動畫、折紙動畫等。新動畫中國學派承續二維動畫的遺芬剩馥,創作了大量的三維動畫、flash動畫,而且還染舊作新,創造性地把二維角色造型和三維場景合榫合卯地相結合,使作品畫面錯彩鏤金,驚艷觀眾。除了原來的因果線性結構,又學習小說、戲劇、真人電影,創作了綴合式分段結構的集錦片,淡化矛盾沖突的散文式結構動畫片,還有復線結構、網狀結構動畫電影也不斷涌現。日本作者動畫和中國文人動畫均“以百變的形態和無窮的魅力不停地表達與呈現,無限趨近動畫藝術自在、自為、自覺、自由的世界”[7]。
(三)東方美學:人文品格,創新發展
日本作者動畫和中國文人動畫均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倡導內心的平靜和自我提升,彰顯出獨具魅力的人文品格。如宮崎駿動畫以獨特的東方美學思想,在作品中呈現出對森林的崇拜和對“萬物有靈”的信仰,通過“人化自然”和“神化自然”,探索人性的迷失和回歸,反思人與自然應有的關系,如《龍貓》(宮崎駿,1988)中的龍貓、《幽靈公主》中的麒麟獸、樹精等自然神、《千與千尋》中的蘿卜精、河神、湯婆婆等,無不寄予著創作者憂世濟世之心。新海誠用物理距離表現心理距離,旨在反思高速信息發展所引發的情感溝通問題,是對人生存壓力的關懷。中國文人動畫的人文品格體現在對傳統文化的鐘愛,如《天書奇譚》(王樹忱等,1983)盡顯“吳門畫派”的寫意之風;《寶蓮燈》(常光希,1999)呈現出水墨畫的韻味;《白蛇:緣起》(黃家康等,2019)不但保留著水墨畫風的清新淡雅,又用高飽和的紅綠色,營造了唯美恢弘的東方世界。
日本作者動畫和中國文人動畫同屬于東方文化圈,都對傳統美學進行了重新詮釋。如森林意象在日本動畫中并非是彰顯生命的隱喻,而是象征著寂滅與死亡的恐懼。日本動畫中人與自然的關系,并非是二元對立,而是呈現出一種非和諧、非撕裂的超越性,是一種“物哀”式的浪漫和諧。①如《秒速五厘米》(新海誠,2007)中櫻花短暫的花期猶如男女主人公的命運,從相遇時花瓣滿樹,到最終滿地殘瓣。中國文人動畫始終借用中國傳統美學的表達形式,“表現‘以形寫神’‘視點流動’的特點”[8],并不斷地創新發展。如《深海》(田曉鵬,2023)將寫意水墨技法與寫實3D技術相結合,形成“粒子水墨”動畫;《大護法》(不思凡,2017)將傳統水墨與暴力暗黑美學相結合,形成獨特的視覺效果;《白蛇:緣起》(黃家康/趙霽,2019)將中國古典山水畫的意境之美寓于其中,創新性地融入特效,為情節服務。
二、日本作者動畫與中國人文動畫的相異性
中日傳統文化雖然有著深厚的聯系和淵源,但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各自獨特的文化特色,如體味微觀世界與關注宏觀世界、鐘愛陰柔之美與陽剛之美、熱衷強弱對立與善惡對立、張揚武士道精神與俠義精神、表現恥感文化與樂感文化。在日本作者動畫與中國文人動畫上則體現在藝術風格、情感基調、人性表現等方面的相異性。
(一)藝術風格的寫實與寫意
強調寫實性是日本作者動畫的鮮明特征,受迪士尼動畫的影響,是一種比較粗糙的模仿。“日本動畫之父”政岡憲三對寫實的追求貫穿于他的創作始終;“漫畫之神”手冢治蟲的作品注重細節,打造真實的角色和場景;宮崎駿作品多實地取景;大友克洋動畫常常帶有一種真人電影才具有的震撼,押井守和沖浦啟之等人的作品表現鏡頭的寫實性。21世紀10年代,日本新生代作者動畫電影“真實”的轉向,是一種不同于宮崎駿、押井守等人開拓的客觀“寫實”風格,是主觀“寫實”風格。如新海誠的《你的名字》(2016)以時間為節點,創作了被譽為“真實幻象”的動畫。無論是“寫實性”還是“真實性”,善于表現微觀世界精致的日本動畫,與日本“崇小”,追求陰柔之美的傳統文化相一致。受西方理性思維的影響,追求科學的“求真”寫實,不僅是對物體和場景的逼真描繪,更是對人物情感、社會現象和人性問題的深入探索和表達。
中國文人動畫的寫意風格,是現代動畫藝術與中國傳統美學相結合的產物。中國文人動畫的寫意性體現在虛實相生的意境營造、臉譜化角色造型和程式化的表演等。如齊白石“不求形似,但求神似”的水墨畫氣韻在《小蝌蚪找媽媽》(特偉等,1960)中得到了很好表現;《鹿鈴》(唐澄等,1982)達到了“無聲勝有聲”的意境美;《山水情》“將‘以景抒情、情景交融’的筆墨情趣和‘實中帶虛、虛中有實’的詩畫意境融入到每一幅畫面中”②。此外,基于中國傳統戲曲表演的中國動畫,提煉出具有象征意義和表現力的戲曲表演元素,如“云手”“亮相”等程式化的動作,增強了動畫的寫意性。新時代中國文人動畫的意境美不僅追求外在的形似,更注重傳達物象的內在神韻和情感表達,強調基于神話故事構建虛擬時空和大場面,突出歷史感和未來感,這與中國主流文化追求“尚大”的陽剛之美有關。
(二)情感基調的悲觀與樂觀
日本作者動畫大多通過細膩、精致和極具真實感的視聽語言,展現角色的命運,呈現出沉重的悲觀基調。這種基調一方面源自故事本身的悲劇色彩,如《東京教父》(今敏,2003)中流浪漢喝完最后一口酒后,心滿意足地死去。但這種悲觀情緒并不是簡單的消極和絕望,而是一種對人生、社會和人性深刻的思考和感悟,暗含“重生與希望”之意;另一方面是在看似平靜、喜悅故事中內涵的悲劇色彩,宮崎駿的大多數作品歸屬此類,觀眾沉浸在溫情的感動中,忽略了影片的悲情色彩。如當千尋一家人開車從國道20轉入國道21后,父母為了抄近路而失道,隱喻日本走向泡沫經濟一樣地迷失了發展的方向。父母不顧千尋的呼喊,執意進入隧道,影射著現實中年輕人的人生道路被父母“規定”的悲哀和無奈。《千年女優》(今敏,2002)、《秒速五厘米》屬于愛情類悲劇作品,沒有你死我活的場面,而是被一種淡淡的青春感傷充斥著,“無奈”貫穿全片始終。日本作者動畫的悲觀基調受地理條件、宗教觀念等因素的影響,對自然之美的“無常”變化表現出一種“物哀”的悲涼。
中國文人動畫則多是積極向上的樂觀基調。中國文人動畫受意識形態色彩強烈的主旋律電影的影響,主人公一開始都比較脆弱、渺小,經歷磨難,從困境中走出來,曲終奏雅,展現出人性的光輝和力量。勇敢無畏的英雄、聰明伶俐的智者、善良淳樸的普通人基本上都是正面形象,不僅帶給觀眾親切感,而且呈現出昂揚的精神。中國文人動畫受傳統“和美”思想觀念的影響,片中很少出現“毀滅”。模仿美國鬧劇創作的第一部動畫短片《大鬧畫室》(萬氏兄弟,1926)奠定了中國動畫萌芽時期的滑稽性喜劇樂觀風格,并一以貫之。“中國學派”動畫無論是開端之作《驕傲的將軍》(特偉,1956),還是鼎盛時期的《大鬧天宮》(萬籟鳴,1961)、《哪吒鬧海》(王樹忱等,1979)、《三個和尚》《天書奇譚》,以及鰲擲鯨吞的《哪吒之魔童降世》《白蛇2:青蛇劫起》《深海》《長安三萬里》等,都注重“寓教于樂”,以健康的內容引導觀眾。即便是反映現實狀況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的影片,也能呈現出一種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
(三)人性的復雜與單純
日本作者動畫故事取材兼容并包,敘事形式多樣豐富,以立體的圓形人物形象,表現人性在善良與邪惡、堅強與脆弱、理性與感性之間起伏變化的復雜狀態,通過獨白和回憶表現激烈的內心沖突,展現復雜微妙的情感和行為動機。如大友克洋的作品總是展現出人性與科技之間的矛盾;宮崎駿的作品始終在深挖人性的多面性,塑造一個個既迷茫脆弱又善良勇敢的角色。如“《風之谷》中娜烏西卡在戰爭與和平之間尋求平衡,展現出對人性善良與慈悲的堅守;《幽靈公主》阿西達卡在人與神獸的沖突中探尋生存之道,揭示了寬恕與理解的力量。”[9]今敏作品中的角色更是復雜多面,如《紅辣椒》(今敏,2006)中的千葉敦子既善良慈愛,又殘暴好斗。
中國20世紀的文人動畫短片多而長片寥寥,故大多數電影采用因果式線性敘事結構,故事情節相對比較簡單,大都沒有盤根錯節的情感糾葛,人物扁平臉譜化符號化,旨在表現人性的單純整一。如《天書奇譚》《大鬧天宮》《哪吒鬧海》中的主人公,都心懷大愛,反強權反壓迫,無懼無畏,是一種單純“善”的人性表現。進入21世紀之后,隨著動畫電影“成人向”轉型,人性表達亦趨復雜。如詭譎怪誕的《深海》中的參宿,既有懦弱抑郁的一面,也有堅強開心的一面;體大思深的《哪吒之魔童降世》(餃子,2019)中的哪吒,外表桀驁不馴,玩世不恭,但內心卻善良孤獨,渴望解除眾人的偏見,獲得認可。此外,“好萊塢化”大片和巨片趨勢加劇,“合家歡”類型橫空出世,熱衷構建龐大的世界觀,以致角色多面,關系錯綜復雜。不過,與人性恢弘浩繁的日本作者動畫相比,國產文人動畫的人性表現還需轉益多師。
三、共生:日本作者動畫與中國文人動畫的融合性
日本作者動畫和中國文人動畫無論是在內涵上還是形式上,都存在著顯而易見的異質性。但由于鄰邦關系,“中日的‘二次元世界’也有著不可分割的‘羈絆’”[10],這種異質性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而是在相互影響、相互融合中形成的共生關系,尤其是在世界全球化,提倡“命運共同體”,交流互鑒成為常態的當下,二者更應共生共榮,方得祉猷并茂。
(一)持續久遠的相互影響
中國文人動畫對日本作者動畫影響的前塵影事,主要體現在動畫創作者從中國文化中吸取創作靈感。1941年中國創作完成的亞洲第一部長片動畫《鐵扇公主》(萬籟鳴等,1941)一上映便引起轟動,觀者如堵,后來對日本動漫具有補天浴日、斷鰲立極之功的手冢治蟲從此迷上了動畫藝術。作為“日本動漫之父”,手冢治蟲從這部“抗日救亡”影片中捕捉到反對不義戰爭的主題,故事恰恰是他熱衷和執著的東西。影片所營造的神話意蘊和奇幻色彩,更是滿足了他對東方冒險故事的想象。手冢治蟲曾坦言說《我的孫悟空》(手冢治蟲,1952)受到《鐵扇公主》的影響,尤其是寫到“火焰山與牛魔王”的結尾時,這一部卡通的影像更是在他思考中跳躍,揮之不去,逼得他幾近于模仿。①
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中日動畫學術交流活動日益頻繁,旨在加強溝通,尋求融合發展的路徑。1981年,特偉、嚴定憲和段曉萱經文化部批準,帶著《大鬧天宮》《哪吒鬧海》《小蝌蚪找媽媽》等十余部影片在東京展映,高畑勛、宮崎駿和大塚康生借此機會,對中國動畫有了初步的認識,他們攻過箴闕,多持平之論。大塚康生認為中國動畫無法從中國近代歷史的背景中剝離,如果把日本動畫看作是“私人企業”,那么中國動畫則具有“國家性質”,《鐵扇公主》把日本帝國主義比作牛魔王,人民大眾合力戰勝他的政治性隱藏,指出了當時中國動畫的政治因素和無法擺脫的傳統束縛,而日本動畫對外國的注目程度是令人吃驚的;②宮崎駿指出《哪吒鬧海》中哪吒是人類正義力量的象征,充滿了活力和趣味感,認為《哪吒鬧海》并沒有明顯的政治意圖,而是具有亞洲風格的傳統元素。③
高畑勛認為應該在是否有趣的層面上討論影片,而非聚焦于政治含義。宮崎駿對于《小蝌蚪找媽媽》所洋溢的趣味感大加贊賞,認為中國動畫正在逐漸加入中國傳統風格之外的元素,追求塑造具有現實感的人物。高畑勛認為《哪吒鬧海》中民族舞蹈式的運動規律、民族化的美術風格、背景設計都融合得恰到好處。中國動畫將傳統和民族的風格引入,成功建構了作為電影的空間。④他對中國水墨動畫是相當崇拜,尤其喜歡中國水墨畫中的留白,呈現出彩墨畫效果的《輝夜姬物語》《我的鄰居山田家》(高畑勛,1999)可以說是對中國水墨畫的活學活用。
日本作者動畫對中國文人動畫的影響不單表現在故事的建構上,更體現在理念層面上的滲透。如《龍貓》《千與千尋》《懸崖上的金魚公主》、《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宮崎駿,2023)等講述普通人的生活,緊扣時代脈搏,用一個個鮮活的動畫形象,講述了一幕幕治愈人心的童話故事,對中國乃至世界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宮崎駿曾從理念層面對中國動畫作出評價。1981年宮崎駿直言不認同《牧笛》的田園牧歌,認為《牧笛》沒有服務于大眾,而是關注水墨畫動起來,以此表現民族自豪感。1984年宮崎駿和高畑勛訪問上美廠,并贈送了《風之谷》膠片。他們滿懷膜拜之心來到中國,卻失望而歸。宮崎駿對于中國動畫的市場化表示反感,上美影廠的轉變似乎驗證了兩位導演對中國動畫發展的擔憂。資金不足、大眾認知不足、質量不高、審核過于嚴格、外來市場沖擊太大、缺乏原創性等一系列問題是中國動畫不得不面對的問題。針對這一現狀,宮崎駿指出:“中國的‘動畫夢’不在未來,而在重拾過去”[11]。雖然一家之言有所偏頗,但對中國動畫的創作大有裨益。
持永只仁作為中日動畫交流的先驅,出生于日本東京,在中國度過了部分童年時光。1945年后,加入“滿洲映畫協會”,戰后加入東北電影制片廠,參與制作了中國第一部木偶動畫片《皇帝夢》(持永只仁,1947),并執導了多部動畫片,積極協助宣傳中國解放戰爭,同時也將日本動畫技術傳授給中國的同行。20世紀50年代,持永只仁返日,將中國的木偶劇等動畫技術引入日本。
(二)多渠道、多方位的相互融合
中國早期動畫注重人文性的表達,而21世紀之后更關注影片的作者性。進入21世紀,中國動畫刮起了一場顛覆傳統動畫的旋風,相繼出現了《西游記之大圣歸來》(田曉鵬,2015)、《大魚海棠》(梁旋等,2016)、《白蛇:緣起》《姜子牙》以及《哪吒之魔童降世》等內蘊豐富的成人向動畫電影。這些作品雖然沒有脫離中國神話故事,但多部影片的導演兼具編劇,增加了作者性的表達。
中國文人動畫之所以開始關注影片的作者性,與中國文化發展的主導思想有密切關系。新中國成立之后的中國動畫“在文化部電影局的政策引領下更多側重于對民族傳統文化的轉化,而要達成對民族風貌的高度藝術化呈現,離不開創作者的主動探索和積極開創”[12]。新時代之前的中國動畫更關注形式和技術的積極探索,而新時代之后的中國動畫電影不僅注重形式和技術的創新,而且越來越關注現實生活和角色內心的情感刻畫,以此呈現創作者觀念的表達。“新主流動畫的創作專項是在國家政策調整、產業格局重構、作者結構轉型等多種因素共同推動下發生的。”[13]
當然,中國文人動畫的作者性與日本作者動畫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和呼應。如《羅小黑戰記》導演木頭說:“在全球化的信息時代,技巧上的國界其實已經非常模糊,我是看日本動畫長大的,學習和影響也是必然的。”[14]
中日動漫合作早在1947年就已經開始。日本戰敗后,持永只仁(中文名為方明)應邀進入“東北電影制片廠卡通股”,參與創作新中國第一部木偶動畫片《皇帝夢》(1947),導演了《甕中捉鱉》(方明,1947)、《謝謝小花貓》(方明,1950)、《小貓釣魚》(方明,1952)等作品。21世紀之后,中日動畫合作主要出現在電視動畫市場,如《銀發的阿基德》(杉山慶,2006)、《三國演義》(朱敏等,2009)、《藏獒多吉》(小島正幸,2011)。這一時期的中日合作動畫主要以中國資金投入為主,而且出現了內容質量不高的問題。2015年之后,中日合作動畫卻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熱潮,出現了《一人之下》(李豪凌等,2016)、《時空使徒》(陳燁,2016)、《銀之守墓人》(大倉雅彥,2017)等影片,主要以網絡劇的合作為主,這是因為中日動畫都處于一個借助外力尋求突破的時期。就日本動畫而言,海外銷售收入頗為豐厚,拓寬了海外市場,突破傳統動畫制作委員會制度,為業界注入新的活力。從中國動畫來看,中國意識到中日動畫需要深度合作,開始培養自己的動畫產業,繪夢、藝畫開天等動畫公司拔地而起,為中國培養了一批新時代人才,推動了中國動畫2015年之后的井噴式爆發。
此外,日本動畫的中國元素豐富且繁雜,使用頻率比較高的元素有:神獸、虛擬人物和故事、裝束、武術,以及中國城市元素。如《攻殼機動隊》拘奇抉異,以賽博朋克風格展現的上海外灘、園林建筑、香港街景以及九龍城寨貧民窟等混亂的生活場景。
借用天文學術語“星叢”來描述日本作者動畫與中國文人動畫之間十分貼切:“既不支配卻又彼此介入,既松散存在卻又相互鏈接的伙伴關系。”[15]但必須承認,當前中國文人動畫還沒有形成如日本作者動畫一般保泰持盈的態勢。中國文人動畫要想比肩日本作者動畫,要有全球化的眼光和接納包容的心態,虛舟任觸,折中中西,融匯今昔,不斷地學習國外的成功經驗,敬守良箴,方可使之興盛繁榮。
結語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中日兩國動畫的創作亦是同理。日本作者動畫與中國文人動畫的互補共生,可謂影不離燈。中國文人動畫關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弘揚,體現對傳統文化的尊重;而日本作者動畫善于從現實生活中尋找靈感,對影像的逼真描繪,強調個人對現實世界的體悟和人性的挖掘,這種基于文化內涵上的差異性根深蒂固,由此決定了中日動畫的樣貌天然有別。但因日本動畫商業市場化遠早于中國動畫,故中國動畫電影創作者必須主敬存誠,學習日本作者動畫的敘事策略、影像構成、表現形式,以及傳播的成功經驗等。可見,國產動畫不但要堅守中國文化傳統,表現中華民族的精神風貌和流風遺躅,更應采用拿來主義,轉益多師,取法日本動畫的成功經驗,望塵追跡,探尋彎道超車,后來居上之策,使中國由動畫大國盡快走向動畫強國。
參考文獻:
[1]經濟觀察報.后疫情時代,動畫產業如何突破——日本動畫后311時代探索的啟示[EB/OL].(2020-07-02)[2024-08-15].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1097323894802930amp;wfr=spideramp;for=pcamp;searchword.
[2]薛揚.動畫發展史[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11:122.
[3]楊曉明,王敏.從《姜子牙》看國產動畫電影對傳統文化的傳承與重構[ J ].新疆藝術(漢文),2021(02):91-96.
[4]楊曉林.宮崎駿動畫之歷史觀探賾[ J ].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05):57-67.
[5]楊曉林.傳統動畫的“異類”:詩動畫和情殤小品《山水情》新解[ J ].上海文化,2020(10):53-59,126.
[6]楊雯.傳承中華傳統文化展示中國人文精神[N].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2023-08-08(A3).
[7]孫立軍,孫平.中國動畫百年之際的若干思考[ J ].當代動畫,2023(01):6-12.
[8]沈嘉,李璐揚.以中國傳統美學符號構建當代中國敘事——以動畫短片集《中國奇譚》為例[ J ].當代電視,2023(08):100-104.
[9]楊曉林.新世紀以來日本動畫電影的發展趨勢及美學特征[ J ].民族藝術研究,2017(05):55-63.
[10]徐文欣,金旭.從孫悟空到哪吒,中國動畫百年發展史藏著哪些“出海”密碼?[EB/OL].(2022-09-09)[2024-08-15].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3480229989776684amp;wfr=spideramp;for=pc.
[11][12]張一品 從“中國動畫學派”到“新主流動畫”——中國主流動畫藝術流變與創作轉向[ J ].藝術傳播研究,2023(04):80-90.
[13]木頭JJ:《羅小黑戰記》導演木頭微博[EB/OL].(2021-11-18)[2024-08-15].https:weibo.com/mtjj.
[14][15]百惠元.國產動畫宇宙:新世紀中國動畫電影與民族性故事世界[ J ].藝術評論,2022(02):52-67.
【作者簡介】" "張 敏,女,河南駐馬店人,商丘師范學院藝術設計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動畫創作、動畫研究。
【基金項目】" "本文系2023年國家社會科學藝術學基金項目“動畫電影‘講好中國故事’敘事理論創新研究”(編號:23BC051)階段性成果。
①參見:萬柳.日本動畫的森林美學[J].世界文化,2023(10):20-24.
②該觀點歸納自:張敏.筆墨情趣影像呈現:中國水墨動畫的發展歷程、困境及蛻變之策[J].電影評介,2023(19):14-19.
①參見:亞·阿斯特呂克,劉云舟.攝影機——自來水筆,新先鋒派的誕生[J].世界電影,1987(06):22-26.
①參見:動畫學術趴揭秘“漫畫之神”手冢治蟲的中國情結[EB/OL].(2020-10-15)[2024-08-15].https://www.sohu.com/a/424705682_482993.
②③④參見:大塚康生、高畑勛、宮崎駿等暢談中國動畫/史料鉤沉[EB/OL].(2021-05-11)[2024-08-15].https://www.163.com/dy/article/G9M6EV190517EGE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