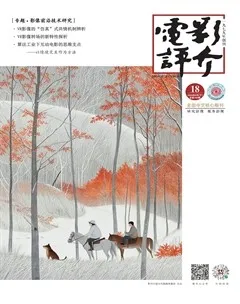20世紀80年代中國探索電影回顧:樸素求新的“另類”書寫者


【摘 要】 《鼓樓情話》是李小瓏1987年改編且獨立執導的第一部故事片,該片聚焦于新時期中國某個逐漸發展演變的侗族山寨,以一個外來采風學生蘇娜的視角,去觀察幾對侗族青年男女間的感情變化,從而引申到對民族生命力存在和延續的思考。1988年《鼓樓情話》卻以“中國電影發行歷史上第一個‘零拷貝’”的新聞而出現在公眾視野;隨后,李小瓏于1989年完成的第二部探索電影《神女夢》(原名《百鳥衣》)僅賣出4份拷貝,成為1990年35毫米國產故事片發行拷貝成績的最末。本次采訪將以李小瓏個人的親歷者視角,重新回顧20世紀80年代中國探索電影近十年的快速變遷與電影觀念的更新,著重探討其“零拷貝”電影的創作過程、環境及探索經驗。李小瓏與他的探索電影,不僅僅是當前中國電影史研究的“空白”,在80年代電影語言的先鋒性探索上,作為同“第五代”有著相似身份話語且一同成長的電影作者,展現出截然不同的道路“命運”,他對西方現代思潮的擁抱態度,嘗試“本土化”探索,推進民族題材電影的思辨創新,對當前代際和區域電影史學研究具有重要的參照意義。
【關鍵詞】 李小瓏; 作者敘事; 思潮本土化; 探索電影
一、回顧:郭寶昌、北京電影學院與“探索電影”熱
王熙成(以下簡稱“王”):聽您說話不像是本地人,能否講講過去您是如何成長并進入電影行業的?
李小瓏(以下簡稱“李”):我是五四年(1954年)生人,出生在北京,三歲就隨父母來了南寧,他們都是山東籍貫。但我周圍也沒有北京的朋友,自己喝邕江水長大,從幼兒園開始一直到工作,都始終在南寧。
我是普通家庭,學校畢業后就把我分到了廣西電影攝制組,搞新聞紀錄片。1971年分配時,剛高中畢業,原來是統一全部上山下鄉,后來多了去工廠這一條出路,那時候人沒有更多選擇。一般去農村的,往往是家庭出身一般;去工廠以及當兵,肯定是工人家庭或者是干部家庭。
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這代人從小便是在一種較為封閉的環境中成長。我記得新中國成立后的學校教育重政治理念。我們這一代人在傳統與西方文化的學習上來說是零起步,當然對于張藝謀、陳凱歌這樣的老三屆,他們的文化教育要比我們完整一些。我們還就停留于當時的小學教育,初中沒上,高中基本混過去了。
王:20世紀70年代以后,當時郭寶昌也調入了廣西廠。
李:我和他相當于一個單位的同事,我們第一次合作是一部新聞紀錄片《光輝的節日》(郭寶昌,1974),由他來擔當編輯,我負責剪輯。后邊還有一部《馬馱醫院》(郭寶昌,1976),也是紀錄片,在廣西隆林我和他繼續合作。
郭寶昌業余時間給南寧當地文化宮排話劇《于無聲處》(1978)時,我就在一旁跟班學習。那個時候也沒什么書看,只能靠有經驗的人言傳身教。他對我印象還不錯,我們的關系也越來越近。
等到他拍第一部故事片《神女峰迷霧》(郭寶昌,1980)的時候,我就是這部影片的剪輯兼導演助理。
王:之后應該就是您去北京電影學院進修的時候,剛好是在80年代初。
李:全稱叫做“少數民族導演進修班”。1982年定向招,面向新疆內蒙古廣西這幾個少數民族地區。進修班就是為了把當時北京電影學院定向招收“表、攝、美、錄”專業本科班他們這一套班底配足(缺導演專業),原來演阿凡提的吐依貢就是我們班的同學。
我能去進修主要是因為郭寶昌,他向宣傳部長力薦,要求電影學院在廣西招生增加一個漢族名額,這樣我才有了機會。這一屆的老師比較有名氣,實力較強比如張暖忻、鄭洞天、詹相持、鄭國恩等。主要負責我們班的,還有韓小磊,美術專業課就是倪震、程永江,攝影專業是鮑蕭然。
進修學制是一年多,上半年是上課,剩下后面半年基本上都是實習,實際上課時間并不長。能看內參片,唯獨是一個“特權”,學校組織去電影資料館,每個禮拜都有。當時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一直推崇的黑澤明電影,《羅生門》(黑澤明,1950)、《蜘蛛巢城》(黑澤明,1957),還有就是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偷自行車的人》(德·西卡,1948),法國新浪潮的《四百下》(特呂弗,1959)等作品。后來離開學校以后,推崇今村昌平的《楢山節考》(今村昌平,1983),還有一個意大利的生活流電影叫《木屐樹》(埃曼諾·奧爾米,1978)。
我記得那時電影學院就很排斥商業片,排斥好萊塢,推崇法國、意大利的影片,包括蘇聯時期的那幾部電影,都屬于學習內容之一。相反好萊塢電影,我印象里幾乎沒看過。安排過的,也就《亂世佳人》(維克多·弗萊明,1939),還有《公民凱恩》(奧森·威爾斯,1940)。
除了看老師推薦有關西方電影理論的那些書,屈指可數。他們(學院教師)幾乎就憑著自己的理解去講意大利新現實主義、法國新浪潮。簡單來說,主要是以歐洲電影為他們的教學中心,也是講授的中心,排斥商業片。
王:您進修結束后,我記得就有了《霧界》(郭寶昌,1984),還有當時“探索電影”熱潮的響應,同樣是“廣西廠”出品,但它遠不如另外兩部為人們熟知。
李:《霧界》基本上是按照他(郭寶昌)的思路去改的,我改的那一版郭寶昌不太認可,于是他自己操刀定稿。
說起這場“電影探索”,1983年至1984年我剛從電影學院進修回來,《一個和八個》(張軍釗,1983)在電影界引起了震撼,第五代導演異軍突起,產生新的電影浪潮,所以他們這一代人就開始接受了(新電影意識)。
郭寶昌也想脫離原來的傳統,想創新。他就按照這個路子拍出現在這么一個《霧界》。很暗的光影,機位基本上沒有什么切換,人的表情也是呆滯的,情節也沒有人為設定的“起承轉合”。實際上那時追求的藝術類電影,也許就是一種紀錄風格。同時正巧趕上《黃土地》(陳凱歌,1984)也出來了。
王:聽您講郭寶昌確實也響應了這個浪潮,為什么《霧界》之后,郭寶昌在《男性公民》(郭寶昌,1986)的一次創作訪談中說是曾經的“教訓”?
李:他試圖參與,但覺悟早,就說“此路不通”。他原話意思是,要在這個行業里面生存下去不能走這條路,今后你要走這條路就沒有機會了。藝術類電影,不圖市場的盈利與回報,但卻比較看重“留名”。
他(郭寶昌)當時也沒有刻意勸過我,僅是那句“此路不通”。到執導《鼓樓情話》(李小瓏,1987)時,我曾把這個導演本(導演劇本)給他看,寄到深圳后他表示認可。他還是提到了“票房”,但是我那個時候迷戀藝術電影,不撞南墻,也不回頭。
王:1984年新中國35周年電影學術討論會有一部分針對電影新觀念的批評,點名《黃土地》《霧界》等探索電影“看不懂”的問題,1986年全國故事片創作會同樣對《獵場扎撒》(田壯壯,1984)、《霧界》走向沙龍、獵奇化而提出批評。能講講當時針對這些電影批評時,您是如何經歷、看待的?
李:后面主要是壯壯那幾部《獵場札撒》、《盜馬賊》(田壯壯,1986)。主要還是在于電影學院這個“中心”,我們上課,包括陳凱歌、張藝謀他們這一屆,包括前輩鄭洞天、謝飛,向我們講授灌輸的,也就是法國新浪潮、意大利新現實主義。一是突破過去中國電影的“不真實”,這個是從西方電影學來的觀念;二是很早發現的“模仿問題”,由于教育、文化熏陶的斷層,面對西方沖擊表現出這種模仿式創作,作為當時的年輕創作者很難從這個“影子”(模仿西方)中走出。
王:從《黃土地》一直到后邊《紅高粱》(張藝謀,1987)斬獲金熊獎,“探索電影”熱潮又迎來新的一波討論,也就是您完成《鼓樓情話》的那一年。
李:這其實是一個“連鎖反應”,《黃土地》是第一步,引起國際影壇的注意。
簡言之,參加國際電影節是成功的第一步,得獎為成功畫句號。當時也講究成本,原來這是一種經營方式,得獎就會有外國發行商去買放映權,幾十萬美元,電影的本錢也有得賺。后來逐漸轉化為名氣吸引投資,提供的便是拍攝成本。相比當時的歐美國家,國內投資成本放在國外就有逆差問題,即使一個拷貝也賣不出去。
那個時候(20世紀80年代中期)大家也默許,因為走向世界,換言之是走向西方電影領域。被西方電影界、文化界接受,包括繪畫音樂一樣。它是一個體系,至少是文化完整的體系。
舉個例子,我在學院學習期間,最喜歡的導演是黑澤明。他作品表現的是純日本的故事,《蜘蛛巢城》(黑澤明,1957)、《亂》(黑澤明,1985)只是借用莎士比亞原作的情節及人物設計。但是他把英國文化的東西完全去除,就是文化決裂的關系。包括后來學院推崇的《楢山節考》(今村昌平,1983),用一種紀實的風格去含蓄表達日本民族,甚至人性、全人類共通的一些思考。很容易聯想到《盜馬賊》、《活著》(張藝謀,1994)這些電影曾試圖走的路子。那就回到我剛才說的,模仿之路難以擺脫,甚至當代也是。
王:當時商業電影與藝術電影的爭辯也很激烈。
李:說穿了,當時我們那幫人,包括我們的上一代人,郭寶昌、鄭洞天他們認為拍功夫片、商業片等于一種自掉身價的行為。你比如《一個和八個》的張軍釗,后來在廣西廠也拍了一部功夫片(《孤獨的謀殺者》(1986),用他的話說,“那是捏著鼻子拍完的”。拍得也還行,拷貝成績很好,但是從心里這種藝術追求角度來講,“被五斗米折腰”,有“屈尊”的意思。
實際上《鼓樓情話》是趕了一個末班車,試圖去投獎,但也沒趕上,后面就再無可能。藝術電影確實投資太大了。
王:郭寶昌還是比較早注意到這些問題。
李:對,他拍完了《霧界》就再也不染指這一類型了,最后還是回到他所熟悉的“套路”,他所接受的那種“套路”,也結合民眾喜歡的“套路”。
二、反叛:“追求真實”與作者寫作
王:我記得在1988年《當代電影》雜志上曾發表過您一篇導演闡述,說《鼓樓情話》是“用生命去表現生命”,以及您提到常看的《百年孤獨》,為何要去提這個“表現生命”的觀點以及馬爾克斯的這部作品呢?
李:應該是在《鼓樓情話》開拍以前寫的一個隨想(《表現生命——寫在lt;鼓樓情話gt;創作之后》,《當代電影》1988年第3期)。《當代電影》后幾期里面還應該有一篇仲呈祥先生的文章,大概也都是圍繞著“表現生命”這個角度去說。
《當代電影》雜志是整個年輕一代影圈的一個陣地。它是中國電影資料館下屬的一個刊物,得天獨厚還享有“內參片”的這么一個特權。網羅了一批所謂的新銳影評家、新導演,在《當代電影》上發表文章,在電影資料館開座談會。包括有人拍出“新的東西”都拿到那里去,請一些專家看。
王:當時是不是都在講“用生命去表現生命”這樣的生命主題。
李:不流行,這個是我在自己作品中提出來的。原因還是在于《百年孤獨》這本書的啟示,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我更傾向“本土文化”,藝術風格本土的那個文化底蘊,在作品里面必須要表達出來,而且讓外人看,你沒有所謂抄襲和借鑒的“影子”。
李:侗族題材故事片是首例,當時沒有任何參照。我意識到要有個切入點,就像《百年孤獨》一樣,切入他們一個村子、部落、家族、生存,歷史生存狀態什么的,就像馬爾克斯曾說他是從小聽外祖母去講他們民族的神話故事長大的。所以,片中穿插了寨老講述這么一些傳說故事的情節。
具體落實到《鼓樓情話》,我本想完全照搬(《百年孤獨》的結構),也不可能,但我還是想用他們本民族文化的東西去表達,在這一點上比較明確,就是說不要用我們漢族人的視角。
一個山里族群的生活狀態,需要規避自己的文化理解,而且必須要去理解他們的文化習俗和生活方式。我選擇寨老、“滾泥田”等情節,一些好像和故事主線沒關系的,旁枝末節的東西;包括古老村寨中出現收音機、玩具這樣很“現代”的東西,實際上就想加厚這個電影的文化成色吧。在我做這些“改動”之前,原劇本還是一種比較傳統的情節套路,一個廣州某知名大學的人類學學者蘇娜,對侗族文化感興趣。然后就去到侗族的這個寨子里,像采風那樣,在與這些人接觸當中,她愛上了這個龍奔(侗族青年),最后與龍奔結成眷屬。
大幅改動原作,是因為那是從正常的角度,從觀眾的角度,從學習受信西方的角度,始終有一條看法:就是我們認為在這之前的電影藝術作品,大部分距離真實的中國老百姓生活太遠,不太真實。從立意、情節、人物設計來講,不太符合電影的“真實”追求。
我的做法就是,她(蘇娜)只是作為一個旁觀者,主要表現侗族內部的這種戀愛婚姻,表現他們自己本身的生活方式,婚喪嫁娶觀和價值方式。談及繁衍生存,但還沒有表現“喪”文化。只是情愛這種東西是全人類共通的,有不同的表現方式和傳說背景。最后結局是因為民族習俗的這么一種阻隔,個人的喜怒哀樂和情仇恩怨,在強大的民族意識面前非常渺小。這就是我想表達的主題。
王:這也是您電影中去看待“生命表現”的一個立場嗎?
李:只是對主人公情感的這么一個看法,用生命表現生命,就是“滾泥田”穿插的這個隱喻。一開始,這個孩子要離開母親的懷抱滾到父親那邊,一共有三次,代表著人生成長。侗族的文化,就是“萬物有靈”,“滾泥田”的場景,就來自于他們民俗志。
我的解釋是:從小有所依靠,直到長大成人,經歷類似成人禮的東西,泥田中滾到對面,當孩子16歲時,對面卻沒有人接應,以后的生活之路你自己走吧。講的就是一個人的生命,從呱呱墜地到獨自行走,這樣一個必經的過程。
當時還有一個觸動,就是去寨子采風,我看到這里的貧窮落后,卻繁衍了上千年。我想追問支撐他們存在的依據是什么?不能從文化的角度去解釋,只能用生命去解釋了,就是創造了生命,那生命就必須發散開,一代一代延續下去,無論困苦與絕望,我想回歸到人原始的狀態。暗示人跟其他所有的生命實際上是同樣的一種歸宿,不要去強調人類是所謂的生命體的最高形式。繁衍子孫,就是生命的最原始動能,所以才會去派遣我們行動。
《神女夢》(李小瓏,1989)就更極端了,原來的框架統統修改,唯一保留的就是一個仙女下凡,要體驗一下人間的云雨之歡,然后相中了凡人小伙,有一種很虛幻的東西,最后就是一場夢。通俗地講就是“做夢娶媳婦”。人有很多很美好的愿景,往往人生又恰巧不如意。
王:《神女夢》您講過是您更極端的作品,我看過一篇對您的批評文章,講的是《神女夢》成為您個人宣泄式的作品,涉及柏格森生命哲學,生命本能沖動(欲望)的解釋。
李:這個倒不認同,談及柏格森,那就可能又把我抬高了。我們這代人老想去走別人沒走過的路子,《百鳥衣》(《神女夢》原作)原來就是過去重復千百次的這么一個情節,跟《天仙配》(石揮,1963)、《劉三姐》(蘇里,1960)、《阿詩瑪》(劉瓊,1964)這些相差不遠,況且延續了那句,“文藝作品不是‘精神鴉片’”,當時并不在意大眾的接受問題。
創作核心還是反叛父母、反叛社會、反世俗與主流意識。這也是從西方新浪潮,現代主義藝術中學到的一種做法。《神女夢》那種神話,談及個人宣泄,我想就是戳破這個神話泡沫吧。就是所謂農民的兒子,得到了天上仙女的青睞,兩人就結成百年之好,從此幸福衣食無憂。
我還想提一點,因為《鼓樓情話》《神女夢》都牽涉到少數民族,須十分謹慎。有很多紅線的地方,所以這兩部作品就不可能表現酣暢淋漓的想法,都是很含蓄。
王:我記得《神女夢》是在1989年年底才上映。
李:這兩部電影都是指令性生產,并不是自己選擇和要求的。其實《神女夢》,延續了《鼓樓情話》的這么一個“影子”,《鼓樓情話》有個寨老,代表這個民族的、習俗的延續與象征,生存價值觀的一種傳遞。《神女夢》出現一個巫師,靈感來自于農村普遍都存在的一個角色,廣西壯族這邊叫道公,占卜算卦,遵循或反抗命運與天命,就是整個中華民族文化中的一個特點。設立這個人物,還是始終想表達民族文化中底層的東西,具象來說就是占卜巫術。《百年孤獨》里面也大量存在著這些巫術的描寫,開拍之前我還把《金枝》硬著頭看了一遍,也不得要領。還看了那本寫日本文化的《菊與刀》。
《神女夢》中比如說算雞卦,五更螞拐舞。我是想借用一些所謂的“準宗教色彩”儀式的表現。聚焦在民族歷史人文這塊,借這些人物的設計、行為和場面的表現,來體現民族同胞在一些日常生活當中,比較典型的狀態。
王:《神女夢》的結局既虛幻又壓抑,您是有意設計這樣富有哲理思考的結尾嗎?
李:我想表達的,歸結到不是個人向往尋求得到的東西,而是另一種我自己的感想。愛情、貧窮、功名利祿,社會不是因為有“你的想象”和“你的需求”而存在的。最終也僅僅是個人的欲求,實際上就是一場夢。表面上,個人的情感、婚姻追求必須要符合“規范”;那深層的表達,就是打破一句古話叫“有情人終成眷屬”,所以《神女夢》中,那個巫師一再地提醒,“這只是一場夢”。因為故事發生前已經設定了一條,“你(仙女)不能下凡,你一旦有了世俗行為,就會灰飛煙滅。”男女主人公則代表了“反叛”,不顧禁令,雙方都是拼死一搏,最后也是“一場空”的結局。但這兩個人都是,也只是完成了他們的一種反抗。就像那句“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臺詞,作為“人”就是這樣無視規范,不停地沖破各種阻撓。
王:從今天的視角去看,您的作品與這樣的創作理念在那個年代少有,但并不被重視,至少在探索電影里,與當時的“第五代”相比較。
李:我記得都是批評的文章,當時我去北京,基本上被他們理論圈子貶得一塌糊涂。記得我當時創造了全國第一份“零拷貝”,一個拷貝都沒賣出去。
我承認從畫面構成、情節推進,可能有許多幼稚、枯燥的東西。探索電影中,我走的這條路就比較狹窄了。
三、思辨:理論借鑒、本土化與電影探索
王:我們再來聊聊當時的這些思潮理論,您剛才也提到了人類學理論的影響啟發。
李:其實不能稱為啟發或者影響,更像“感悟”。就像《鼓樓情話》中用一個人類學學者的視角去看待一個部族文化生命的延續。20世紀80年代文藝界當紅的就是人類學理論和那幾本書。主要的根源都來自于西方的理論學術外加上我們所謂的藝術感悟、藝術感知,還有新浪潮電影。除了之前提到的那些,還包括安東尼奧尼、紀錄學派、《電影手冊》這一幫。日本電影的黑澤明、小津安二郎這些集中在影像感覺方面。還有瑞典電影、德國電影的法斯賓德、施隆多夫,包括費里尼在內的意識流那一套,雖在電影學院看過,論影響基本也是過場。
王:學習的這些理論具體到《鼓樓情話》《神女夢》中是如何表現的?
李:《神女夢》就是先將濃重的政治意味一筆勾銷,就非常“純”地講神話本身,將社會生活對立面、階級沖突的層面去掉。人類學中會講這個巫術、神話、宗教對民族群體的影響,老鬼主就代表了這樣一個東西。
《鼓樓情話》就是從真實的角度,結合人類學理念,用原汁原味的民族歌曲,我想率先嘗試類似于一種“原生態”的理念,尤其在西南少數民族作品中。《鼓樓情話》里邊的民歌,包括蟬歌,都沒有經過任何作曲家按照過去傳統的編排方式將其美化,僅是在音符上稍微潤色,拒絕使用民族大樂隊等。跟《阿詩瑪》《劉三姐》這些作品歌曲可以形成一個對比。歌詞部分從民俗志中抽出,一一對應,找當地的侗族民俗專家譯成慣用的民族語言,讓本地的民歌手來演唱。我拒絕照搬西洋樂隊的編制,包括當時的民族樂隊同樣也是這個模式。
王:包括《鼓樓情話》《神女夢》中的人物造型?
李:一切源于真實,避除北京上海職業演員的那種“大眾明星臉”,就按照地方人的長相來找演員。就像意大利新現實主義,服裝也不經過任何修飾,去除披金戴銀等特別夸張的造型。
王:您的兩部少數民族題材作品,尤其是第二部《神女夢》,除了對神話故事、民族文化等方面的表現,主題闡釋的那種夢境、虛無、個體追求的無意義似乎還有一種西方現代主義哲學的意味。
李:這點我還是更喜歡海德格爾的研究。歸結到一點,實際上《神女夢》中我想表達的并不是“虛幻”,準確來說是對未來的一種不可知。
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會講到“此在”這個專有名詞,我所理解的“此在”就是“物體”每一秒都在發生變化,時間是流動的,那么你所看到的東西就不一定是“真實”的。當時同樣聯想起《羅生門》中所提出的“真實”悖論,每個人都會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敘述案件。我想表達的就是“真實”的不存在,是虛幻的,或者是未來不可知的一種消極和悲觀。另外還有他(海德格爾)書中所提的“向死而生”,這點同樣可以在《鼓樓情話》中去叩問“生命”的意義在哪里,那種注定走向死亡、虛無的“發問”,但《神女夢》中男女主人公依然選擇自己的意愿無視禁令、完成反抗,是一種“本真”的生命,也不單單是因為“欲望”的本能去驅使這樣的行為,所以會有存在主義的意味。
我更認同海德格爾是站在“人的角度”去認識時間、生命,承認生命與死亡都是存在的。部分哲學理論,更多的是一種世俗的抗爭,在名利場上的一種解讀。海德格爾則脫離這個,更抽象又更純粹,但又不是宗教,用一句話講不清楚。
王:海德格爾的書,您是哪年看的?
李:應該是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中文第一版出來,我就買了(第一版《存在與時間》中文版大陸上市時間為1986年)。那個時候還有叔本華的《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薩特的《存在與虛無》,最后才是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
王:到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國內電影體制改革的聲音越來越響,當時陳昊蘇提出了“娛樂片主體論”,嚴肅處理電影上座問題,還有消滅“零拷貝”的口號。我記得那時探索電影的創作者紛紛轉型,您仍然堅持在1989年完成了《神女夢》。
李:中國電影發行公司這邊關注市場的力量,傳統的“聲音”也說中國不能滿屏幕都是“探索電影”“沒有觀眾的電影”。不過當時中國電影發行體系還沒崩潰,還是由中影公司統一確定一部影片,各個省分公司都是服從于中國電影公司這個拷貝的分配量。到了中后期,在多重的壓力之下,陳昊蘇他們還是選擇了娛樂片。不過那時候環境還比較友好,創作界、評論界業內不講這個市場,對藝術片創作者還是較為尊重的。
還有一個最大的沖擊就是電視,為什么強調娛樂電影?因為當時引進這些娛樂片的標準很嚴格,審查標準同樣是。所以電影發行這一塊有些寸步難行。大伙家家都有電視機,也不去電影院了。
王:當時拍攝電影的成本是不是也有所增高?拷貝、膠片也在漲價。
李:成本并不高,就幾十萬元。拷貝、膠片并不像你說的那么上漲,一百萬就是大制作了。那時候五十萬到八十萬就屬于一個正常的制作水準。至于電影體制,商業片是一個全新的片種,要重新學習、重新嘗試,原來所學的東西,全部推倒重來。比如說功夫片類型,當時國內連個功夫班子都搭不起來,動作設計、鏡頭角度、攝影機的升格降格,偏技術的誰都不會。尤其中國香港的片子,很難與其競爭。當時內地國產電影,普遍票房都不好,即使是那時最新銳的第五代,第三代、第四代導演不擅長拍商業片,而且還排斥商業、娛樂電影。
矛盾就在于業內對娛樂片、商業片是不接受的,電影主管部門一直也考慮到電影的生存問題,得找出路,活下去要與電視競爭,但是恰巧研究界普遍認為電影競爭不過電視。
王:我記得電影經濟不景氣,出現了賣廠標等現象。
李:那個時候就改革了,電影公司解體。首先就是中國電影公司下屬省、縣市逐級脫鉤,自謀生路。改革是先從電影發行體系這一邊入手,至于電影制作體系(制片廠),是自生自滅的狀態。之前每一部電影按照計劃生產,交給電影公司發行,不管怎么樣,多少能回點本。
唯獨只要他(電影公司)定拷貝就可以。當時是按拷貝定價,不按票房分成,制片廠跟中影公司的矛盾也很大,就是“我們種地,打下的糧食你們去賣高價”。
流傳一句“用制片廠的水養電影公司的魚”。20世紀80年代末電影經濟困難剛開始,但還沒那么慘,到90年代初負擔壓力就很大,就是那會兒的“中國電影大地震”。我記得90年代制片廠發不起全工資,包括廠長、書記,一個月領200塊錢,按照當地的最低生活標準。我們導演、編劇甚至比其他技術工種的工資還低,那段時間很多人就離開電影制片廠,自尋生路。
至于說“零拷貝”這個事,或許就是當時改革的這個情況,制片廠信任我做了這么一個“探索嘗試”。《鼓樓情話》正好搭上了中國電影不景氣這班車,所以說“零拷貝”能成一個問題,當代就不至于了,“零拷貝”就不是新聞了。
王:不知當時廣西廠受這個經濟沖擊影響大不大,《神女夢》當時的制作環境又是如何的?
李:不好的情況也是在《神女夢》之后,只是因為作品表現得太過壓抑或者所謂“不健康”內容而取消了那年的獻禮片資格。之后,制片廠就開始制作承包了,攝制組、導演和制片要跟廠里簽一個保本協議。攝制組里面也開始分包,壓縮成本。
王:當時廣西廠就不再立項這種“探索片”了嗎?
李:都不搞了,包括西安廠也是。因為改革,各自為政,都為眼前的生存,大家也沒心思。就是郭寶昌的那句話,“此路不通”。
王:詳細一點說,就像實現電影本土化探索的實驗嗎?
李:在當時這就是一個矛盾。你比如說我的模仿,《鼓樓情話》片頭片尾“滾泥田”的音樂就是完全照搬了法國一個先鋒派作曲家的這種風格。因為這個作曲人(《鼓樓情話》作曲),是譚盾的同班同學,叫陳遠林。他們是82屆,受西方現代音樂的影響很深。
當時我通過錄音師(林臨)聯系上他(陳遠林)。他建議本土音樂應該加上現代風格的這么一個類似準宗教色彩的一種組合編曲。確實很新穎、有氣勢,我也認可,由他作曲并負責交響樂、配樂部分。還有影片當中對唱的那個情歌、民俗活動的那些清唱,也是他(陳遠林)負責采風整理過來后進行錄制。交響樂部分,是在北京請的中央交響樂團這一幫年輕樂手,都非常興奮,也包括了這種無伴奏合唱。陳遠林還請了他們指揮系同學邵恩來負責,他(邵恩)對音樂,只要跟西方的東西沾上邊,那絕對是贊不絕口,大家都很狂熱。
所以現在想起來,實際上如果全部按照純民俗的那個原生態路子走,才是對的。不應該照搬模仿。反思起來,覺得還是不夠徹底的生活流,徹底的民俗化、寫實化,那也是一個路子。如果當時能夠考慮到是“零拷貝”,我在創作上就應該會更徹底一些。我確實做了迎合新文化潮流,西方現代派、先鋒派的東西。但是,這個視野只局限在了自己所謂的影視小圈子。但電影畢竟是一種大眾文化,它不是小片兒的文化,也不是一個學術文化。
王:回到20世紀80年代譯介而來的西方思潮、哲學或是藝術作品,部分人基本上保持了不質疑的接受態度。
李:不質疑,因為那個時候大家對西方是一種盲目的推崇。其中走了一個捷徑,就是第一時間復述西方“大牛”的思想。現在看來也不太正常,但這也是必經的一條路,真正在學術法(學科制度)建立起來前,人文學科就有這樣的現象。
當時就十分缺乏對于這種西方思潮的思考、融合,還有變化,升華為自己獨自的學術觀點。也同樣是用西方思路、視角照搬去審視我們自己已經割裂的傳統、民族文化,模仿無法避免,包括我自己的電影也存在局限性。張藝謀或許更崇拜尼采、“超人意志”這類,我的哲學“原點”是海德格爾,當時就想將這種人生哲學的依據,去對應作品里內涵的東西。
王:那電影的這個“探索”到最后其實是失敗的。
李:應該是失敗了,但是這一步又必須要走。因為要突破原來的極端,等到我們這代人正需要接觸這些的時候(指中國傳統文化以及西方思潮發展歷史),恰恰沒有比較和對比。文化知識壓抑引起的反彈,就是80年代的現象。這個過程必須有人做鋪路實驗、墊腳石,后人可以借鑒我們失敗的經驗。所謂失敗,那還是需要到市場上去檢驗,比如這種電影“探索”如果沒有前瞻性,只是一種個人表達,那畢竟還是太有限。
我認為中國電影的探索,“第五代”只是使電影“另起一行”的這么一個作用,脫離原來的傳統表達方式,開辟了另外一條路。因為電影畢竟在過去屬于唯一的、很有限的娛樂品種,所以之前營銷意識也弱,也就依靠于業界、學界這一批的宣傳、評論。
王:就像您在那篇導演闡述中所表述,電影探索確實又是十分矛盾的。
李:我喜歡的作品應該具有永恒性,就不是那種快銷,我以前就比較討厭“爆米花式”的東西。追求永恒,但我也深知永恒是不可能的。
在30年以前,有人問過我,電影導演這一行,最喜歡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說我最喜歡干的就是給我一臺16毫米或者8毫米的攝影機,我自己會把攝影的一套原則去配一個攝影師,兩個人就扒火車也好,跟著貨運司機也好,就拍一個沿途的紀錄片,紀錄片符合我的個人選擇。就是我有時(創作)過度追求真實,弄的人有些“執拗”。
還有一點就是我的人生觀比較悲觀,比較灰色,因為對生命的看法,總是會回到宗教的“生與死”,出生必然走向死亡,這么一個出發點,對人生的看法。但人畢竟是有思想的,能夠調節自己,在里邊尋找光明、尋找閃光點、尋找快樂。回到《鼓樓情話》,“用生命表現生命”,似乎應該有點共通的東西。
【采訪者】" 王熙成,男,山西太原人,廣西藝術學院影視與傳媒學院碩士生;
安 燕,女,貴州沿河人,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電影史、電影理論與批評、少數民族電影研究。
【受訪者】" 李小瓏,漢族,中國內地導演、編劇,1954年出生于北京。1971年李小瓏高中畢業分配至廣西新聞紀錄電影攝制組(廣西電影制片廠前身),從事電影剪接工作,1982年入學北京電影學院少數民族導演進修班,次年7月畢業。代表作品有新聞紀錄電影《光輝的節日》(1974)、《馬馱醫院》(1976),故事片《神女峰迷霧》(1980,擔任剪輯)、《潛影》(1981,副導演)、《霧界》(1984,副導演兼執筆編劇)、《男性公民》(1986,聯合導演)、《鼓樓情話》(1987)、《神女夢》(1989)、《黃金驛站》(2001)等。
【基金項目】"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重大項目“戲劇與影視評論話語體系及創新發展研究”(編號:23ZD07)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