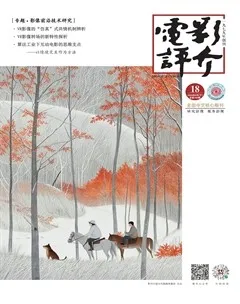從《孔繁森》到《回西藏》:英模形象的重寫與美學升級

【摘 要】" "1996年陳國星、王坪執導的影片《孔繁森》與2022年陳國星、拉華加執導的影片《回西藏》均以孔繁森援藏事跡為原型,兩部影片創作時間跨越26年,在人物形象、敘事與美學方面呈現出不同特點。本文通過比較分析孔繁森藝術形象的嬗變,由卡里斯馬化的超級英雄形象轉變為成長型英雄;以及分別在主旋律電影與新主流電影的框架下分析兩部影片的敘事模式,進一步指出兩部影片從強調“仁愛”思想的“仁義美學”到強調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和合之美”的美學升級。
【關鍵詞】 孔繁森形象; 英模敘事;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1996年由陳國星、王坪聯合執導的影片《孔繁森》上映,影片根據原西藏阿里地區地委書記孔繁森的真實事跡創作改編。孔繁森籍貫山東聊城,1979年主動響應國家號召赴藏工作,先后兩次赴藏,1992年孔繁森被任命為西藏阿里地區地委書記,其在任職期間,積極推動阿里地區的經濟發展,走遍了全區的鄉村、牧區,切實幫助藏民解決問題。不幸的是,1994年,孔繁森在帶領工作組赴新疆考察途中發生車禍,以身殉職。為紀念孔繁森、發揚孔繁森無私奉獻的精神,1995年4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長篇通訊《領導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并發表題為《向孔繁森同志學習》的社論。翌年,影片《孔繁森》(陳國星/王坪,1996)上映,通過平民化視角、散文化情節,塑造了一位克己奉公、無私奉獻的人民公仆形象,將“孔繁森精神”以影像化的方式呈現,該片上映之后,榮獲了第5屆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第2屆電影華表獎最佳影片[1]等多個嘉獎。
時隔20余年,時代語境、中國電影業態、觀眾審美趣味發生了歷史性劇變,傳統主旋律電影與類型電影融合,產生了兼顧思想性與商業性的“新主流電影”,“網生代”成長的觀眾群體對電影有了更高的敘事需求,如何在新的時代語境下繼續講好孔繁森故事,已經有著豐富主旋律電影創作經驗的陳國星導演聯合藏族青年導演拉華加創作了影片《回西藏》(陳國星/拉華加,2022),兩位導演跨越文化、年齡的差異,以全新視角重述孔繁森的故事,對孔繁森精神的當代表述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影片以其創新性的表達,豐厚的美學底蘊入圍第12屆北京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天壇獎,獲得了第36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獎項。[2]
一、“孔繁森”的藝術形象嬗變
影片《孔繁森》講述了孔繁森赴阿里地區擔任書記,切實幫助群眾解決實際困難,將生命奉獻給阿里的感人故事。影片并沒有將孔繁森刻畫為充滿豪言壯語、“高大全”式的教條化英雄人物形象。而是以平民視角、在孔繁森與群眾的日常互動中塑造了一位無私奉獻、為民鞠躬盡瘁的英模形象。孔繁森一路走訪群眾:在學校,當教師說已經幾個月沒有發工資時,孔繁森毫不猶豫地將自己的工資拿出來;在部隊,和軍人一起唱《說句心里話》;在發生雪災時,挨家挨戶為牧民送去了救援物質;沿途遇到說唱詩人,也會將自己的外套給他披上擋風。為了突出孔繁森一心系民的人民公仆形象,影片運用了諸多感人至深的細節,看到病重的曲珍仍然穿著破爛的鞋子,孔繁森解開衣服為她捂腳;不顧病重的妻子在暴風雪中為災民送去物資,孔繁森形象正是卡里斯馬(Charisma)形象的典型。
“卡里斯馬”原為宗教概念,指“神圣的天賦”,后來在現代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等人闡釋下,成為具有特殊的魅力或神賦力量的人。“卡里斯馬”帶著中心價值體系,尤其是承載著社會權威意識形態,其魅力對于社會結構的維護與變化產生著強有力的作用。“一種社會結構是否穩固、富于生命力,根本上取決于它的‘卡里斯馬’是否魅力不衰。‘卡里斯馬’的崩潰必然意味著整個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的混亂。”[3]相反,一個崇高且具有魅力的“卡里斯馬”對維系社會穩定和引領社會意識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作為“卡里斯馬”的孔繁森形象不僅是人民公仆形象,更是20世紀90年代社會結構發展的文藝表征。20世紀90年代中國正處于社會大轉型期,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同時也經歷了社會轉型的陣痛,城鄉結構發生變化,“下海”成為時代熱詞,出現了公務員辭去工作南下經商的現象。在這種背景下,孔繁森成為時代的逆行者,從經濟發達的山東主動前往貧窮落后的西藏,這一行為對于遏制當時社會出現的拜金主義與極端個人主義,感召更多的人進行邊疆建設,加強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無疑有著重要積極的意義。
影片《回西藏》在重述孔繁森故事時候,將故事時間進行了調整,影片一開始標注的時間為“一九七九年,藏歷土羊年,西藏日喀則”,這是孔繁森第一次進藏時間,并非《孔繁森》電影中孔繁森前往阿里地區擔任書記的20世紀90年代,可將該片視為《孔繁森》前傳。在名稱上“老孔”的稱呼代替了“孔繁森”這一所指明晰的稱呼,這一稱呼的轉變祛除掉“孔繁森”所攜帶的象征意義,不僅創作上更加自由,而且對《孔繁森》中完美無缺的英模形象進行了“祛魅”。影片一開始老孔因為高原反應,意識模糊地倒在荒地上,被救后的老孔隨身插著氧氣管,前往藏民家中不知道如何吃糌粑,這位瘦弱的甚至有些窘迫的形象與《孔繁森》中成熟的已經完全融入藏文化的干部形象相反,是對英模形象的“解卡里斯馬化”。影片前半部分幾乎都是在對傳統孔繁森形象的“祛魅”中展開,老孔進藏以后要處理第一件工作就是處理瘟疫羊,老孔提議埋掉病羊拿政府補貼,牧民們并沒有同意老孔的建議;曲珍奶奶病重,老孔要求送她去醫院治療,也只是得到久美“你是好人,但你不懂。”的婉拒。
“解卡里斯馬化,其實是解超卡里斯馬化,即其解構對象主要不是卡里斯馬典型而是超卡里斯馬典型。這是要消解超卡里斯馬典型的超常的神圣性、唯斗爭性,恢復卡里斯馬典型的本來面目。”[4]“老孔”形象的祛魅的實質是要消解孔繁森形象中超常的、非人性的、唯神的形象,要回歸人物本真。1979年,初次入藏的孔繁森進入到與家鄉孔孟之鄉完全不同的西藏,本地藏民對這位“闖入者”一時的不認可也符合歷史現實邏輯。但是,《回西藏》中老孔形象對孔繁森形象的改寫與解碼,并非是要消解孔繁森的英雄形象及其內涵的崇高精神。而是通過對“孔繁森”符號的祛魅進入真正的“孔繁森”精神世界,探索其成為英雄的精神內核,進行“再卡里斯馬化“。面對身體不適與文化沖擊,老孔仍然能兩次進藏之后留在西藏,驅使他留下來的精神動機是什么?影片突破寫實主義手法,增加了“老孔”的內心獨白與寫意化的段落。如夜晚老孔在昏暗的燈光下寫日記,旁白為老孔的內心獨白。尤其是影片結尾,不同于《孔繁森》中結尾孔繁森穿上民族服裝唱起了藏族民歌,緊接著是雪域高原中孔繁森殉職的字幕,將孔繁森悲壯崇高的形象定格。《回西藏》結尾為寫意化的夢境,在夢中,老孔出現在一片絢麗的花叢中,穿過載歌載舞的人群,重新撫摸刻在墻上更敦群培的詩歌“軀體猶如空殼,何時亡亦無憾。智慧如同金子,惋惜一同逝去”,將老孔的生命價值升華為一種美學式的永恒存在,“再卡里斯馬化”后的老孔不再只是克己奉公、為民奉獻的人民公仆形象、而是又有著豐富精神世界以及對西藏摯愛的多元化藝術形象。正如《回西藏》制片人紀煥學所述:“我們更想從一個奔赴邊疆的熱血青年角度,去溯源他成長的心路歷程。他奔赴西藏,除了責任和使命,一定還有對這片土地的熱愛,對這里人民的熱愛。這是《回西藏》故事的靈感源泉,也是影片想要去尋找和表達的東西,我們想探尋一個英雄的精神源泉。”[5]
二、敘事更迭:從“平民化英雄”到“英雄平民化”
《孔繁森》影片的誕生與英模形象的刻畫離不開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電影語境。20世紀80年代末期“突出主旋律,堅持多樣化”的口號的提出。“主旋律”成為90年代中國電影創作的重要使命與內容。以英雄模范為原型的英模電影具有著凝聚時代民族精神,激勵人們奮斗的指向標作用,不僅是主旋律電影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政策重點扶持的題材。因此在20世紀90年代創作出一批以英雄模范為題材的主旋律電影。如《焦裕祿》(王冀邢,1990)、《蔣筑英》(宋江波,1992)、《周恩來》(丁蔭楠,1992)、《離開雷鋒的日子》(雷獻禾/康寧1996)等。影片《孔繁森》貴在塑造以平民化、而非教條化的方式塑造孔繁森形象,但是從根本上并沒有打破自上而下的權威型、說教型的話語體系,典型表現為這一時期英模敘事主體仍然是單一的、具有典型性、榜樣性的英雄模范。
時過境遷,隨著大量同質化英模電影出現,觀眾對這類平面化悲情式的英模形象出現了審美疲勞。在新的時代語境下,如何將英模精神進行有效傳達?新主流電影進行了有益探索。新主流電影將主旋律電影與商業電影相融合,將類型電影的敘事手法融入主旋律電影的意識形態訴求中,尤其是借鑒了好萊塢電影、中國香港電影成熟的類型經驗。如《湄公河行動》(林超賢,2016)、《紅海行動》(林超賢,2018)等影片將香港警匪片的類型模式與主旋律電影的意識形態訴求縫合,創造了符合內地審美與國家形象的新主流電影。在英雄形象刻畫上,新主流電影打破了主旋律電影中單一的英雄形象,往往以群像式英雄形象集體出現,注重刻畫群體英雄為完成某一事件/目標共同努力,以及在這一個過程中建立的群體情誼。如《中國機長》(劉偉強,2019)在講述飛機遇難這一災難性事件時,并沒有將鏡頭全部聚焦于機長劉傳建,而是通過刻畫機長、第二機長、乘務長等群體協作完成迫降。又如《奪冠》(陳可辛,2020)講述中國女排為爭奪奧運金牌全力奮斗、不屈不撓的故事。影片既有對女排總教練郎平成長歷練的講述、也有對女排陪練陳忠和、女排隊員朱婷等人物行為情感的細膩刻畫。在這種群像式的英雄譜寫中,個體與群體、個體與社會實現了高度統一。不同于主旋律的電影中的平民化英雄視角,新主流電影真正正將英雄平民化。影片《回西藏》充分借鑒了新主流電影中“群像英雄”的創作手法。
《回西藏》在人物塑造上以“雙男主”形象代替了《孔繁森》中的“個人英雄”形象。另一位男主人公久美在影片中所占的比例與老孔旗鼓相當。久美形象原型是真實的孔繁森翻譯——阿旺曲尼,阿旺曲美1978年從西藏民族學院畢業進入日喀則地區工作,1979年擔任孔繁森藏語翻譯,在擔任翻譯的兩年期間,阿旺曲美跟隨孔繁森下鄉調研,陪伴在孔繁森周邊。在影片中“久美”這一形象不再僅僅是傳統英雄電影中的“輔助者”,而是與老孔享有同等地位的主體,在片中這一人物形象的設定是貴族的后裔,后來在民主改革之時,莊園被沒收,久美給生產隊放牧,接受再教育。久美不僅輔助老孔深入了解藏民,融入當地生活,除此之外,久美更有著超然于外界的自我精神世界,如家里墻壁上的詩歌,老式留聲機以及為老孔所唱的英文民謠。不同于影片《孔繁森》,在講述孔繁森關懷阿里地區人民時候,一直存在著一條隱線就是他無法照顧家中的母親、妻女,影片《老孔》徹底去除掉這條與現代觀眾審美經驗相悖的敘事線。代之以講述老孔和久美這兩位有著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身份地位的人從剛開始的分歧、理解到精神共鳴,建立如兄弟般的情誼。影片一開始坐著車的老孔與騎著馬的久美相遇在荒原,但是對于老孔的疑問,久美并未予以理會;而隨著兩個人交流的深入,久美輔助老孔理解藏族文化,在久美被圍困時,老孔心有靈犀地去幫助他,在藏學大師更敦群培的詩歌與久美所唱的英語民謠中,兩個人產生了琴瑟和鳴般的友情。
這種“雙男主”的形象脫胎于香港警匪片中的人物設定,在《喋血雙雄》(吳宇森,1989)、《無間道》(劉偉強/麥兆輝,2002)、《線人》(林超賢,2010)等經典警匪片中往往設置兩位立場身份截然不同的警察/匪徒,但就是在打斗過程中產生出超越身份的惺惺相惜的兄弟情,這種警匪片的人物設定豐富與提高了影片的戲劇性與觀賞性。“北上”后港人將這種英雄敘事策略進行內地化調整,林超賢、劉偉強、李仁港等導演在新主流電影中將“雙男主”擴大化為群體英雄,尤其是賦予英雄的“輔佐者”們以同等重要的主體地位。影片《回西藏》借鑒了“北上”香港導演的創作手法,除了老孔與久美的主角地位之外,將曲珍奶奶這一“本土文化持有者”也加入到英雄群像的譜系中。在《孔繁森》中,曲珍奶奶是深受孔繁森恩情的崇拜者與擁護者。但是在《回西藏》中,曲珍奶奶是與老孔平等的主體,甚至長期在西藏生活,曲珍奶奶的話語更具有權威性,對于瘟病羊的處理,牧民們并沒有遵從老孔的建議,而是跟隨曲珍奶奶將瘟疫羊掩埋,曲珍奶奶也沒有接受老孔的建議去醫院,而是順應自然,安然地走向生命的終點。在群像式的書寫中,老孔與久美、曲珍奶奶建立了平等的主體關系,老孔這一英模書寫真正地融入藏民群體書寫中。
影片對老孔形象的建構也充分吸收了新主流電影中英雄的成長敘事。新主流電影中英雄不再是生來就具備英雄品質的高尚形象,而是處于不斷的成長蛻變中。英雄在年幼或者初期階段往往經歷創傷,是一個消極、猶豫、自卑的形象,但是在經歷種種磨煉與嚴峻考驗之后,尤其是克服內心恐懼之后,英雄浴火重生為真正的勇士,如影片《湄公河行動》中緝毒情報員方新武因為女朋友沾染毒品自盡產生的心靈創傷,這種創傷促使他下定決心抓捕毒販,但是也會沖動失去理智,最終方新武的蛻變也體現出一位真正緝毒警察的成長。又如影片《萬里歸途》(饒曉志,2022)中年輕外交官成朗在撤僑行動初始缺乏經驗,在經歷挫折與挑戰之后,成為挺身而出的少年英雄。在影片《回西藏》中,老孔進入日喀則要處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怎么處置瘟疫羊?老孔建議拿政府補貼活埋瘟疫羊,這與村民們理解的生命觀相悖,沒有人聽從他的建議。而在影片后半部分老孔在與村民們修水壩時候埋入了“地藏寶瓶”,高呼“吉祥”化解了來自信仰的阻力,此時的老孔已經成為一位令藏民們信服的成熟干部形象。從傳播效果來看,主旋律電影中單一英雄所攜帶的意識形態話語以及暗含的權威話語模式具有一定的說教性,觀眾成為被教育的客體,也較難與高高在上的英雄產生情感上的共鳴。而新主流電影中的具有瑕疵、不完滿的英雄則容易激發觀眾的“移情”效果,初次抵藏瘦弱的老孔形象比高大威猛的英模形象更具有親和力,在建立“移情”效果之后,觀眾能夠逐漸認同老孔與久美情誼的建立、老孔一心為民的精神,這也是新主流電影對于主旋律電影修辭策略的升級:“從‘說服’到‘認同’的修辭策略轉變是主旋律電影和新主流電影在創作觀念上的根本區別。”[6]
三、美學升級:從“仁義為美”到“和合之美”
作為主旋律電影典范的《孔繁森》,影片正是通過政治倫理化的策略,將意識形態包裹于人情味的道德形象中,通過倫理情感,尤其是“苦情戲”這一傳統家庭倫理電影的手法塑造了一位近乎完美的“仁者”形象。“中國式的家庭倫理片,尤其是‘苦情戲’是中國電影史上橫亙百年的超穩定類型。”[7]英雄模范人物犧牲自我、病倒在工作的崗位上的“苦”自然能生發出崇高感與悲壯感。“‘苦情’之苦,源于英模主人公大公無私、為工作不惜犧牲個人生活的‘自苦’,或者積勞成疾而成的‘病苦’,而支撐這一類故事的精神底色,是儒家文化的道統。”[8]孔繁森這一道德化的英模人物,其精神底蘊正是儒家文化中的“仁愛”思想。支撐孔繁森舍己為民、親民愛民行為的并非是阿里地委書記這一政治身份,而是“愛的最高境界是愛人民”(孔繁森語)這一“仁愛”思想,“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仁者愛人。影片《孔繁森》以儒家倫理中的“仁愛”思想為底蘊,是儒家文化美學中“仁義之愛”的集大成者。
影片《回西藏》不僅講述了“老孔”的愛民思想,如孔繁森用自己的工資為農民買種子等細節的呈現,更為重要的是影片以“和”作為敘事基礎與美學底蘊,在美學上是將《孔繁森》電影中的“仁義為美”升級為“和合之美”。這種“和合之美”體現為電影中將不同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體美學”“天地人合”的家園意識與影片之外的跨民族、跨風格的合作模式。
影片《回西藏》始終貫穿著現代與傳統、漢藏不同民族文化的碰撞,究竟是騎馬快還是開車快?初次進藏的“老孔”時時刻刻遭遇著民族文化沖擊,如久美確認盜馬賊的方式是帶他去寺院前面發誓;在處理藏民糾紛時,老孔的內地經驗與現代性處理方式是失效的,老孔不解酒館老板娘的朝圣行為。但影片并沒有刻意凸顯文化差異來制造戲劇性,更沒有以二元對立的思維、以一種文化代替另一種文化進行敘事,影片以溫和的筆觸將不同的思維方式與民族信仰融入在“對話”式的協商之中,在文化交流協商中融合發展。這種“和”文化正是指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共同體美學。學者饒曙光認為“共同體美學”彰顯的是關聯型思維而非因果型思維,這種思維形態促使“在面對他者時的態度,即‘以和為貴’的精神。‘和’并非對獨斷自我的強調,而是始終從自我與自然、與他者的和諧關系出發來思考問題”[9]。這種“共同體美學”正是影片《回西藏》所要展現的美學宗旨。需要指出的是,“共同體美學”不僅是影片《回西藏》所追求的美學境界,也成為當下少數民族電影創作的重要方向與文化旨歸。如同樣是以20世紀60年代在國家特殊時期“三千孤兒入內蒙”這一歷史事件改編的電影,2010年由寧才導演的《額吉》通過講述草原母親的無私奉獻呈現民族大愛。2022年由爾冬升導演的《海的盡頭是草原》則以尋親為線索,講述了上海孤兒與內蒙古收養家庭中建立了超越血緣民族的深厚情感,這種淳樸的“一家親”從深層次上指向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回西藏》不僅在民族文化、民族情感上體現為“和”的美學,而且突破文化視域,進入更為廣闊的生態視域中的“天地人和”。影片的片名為強調地域特性的《回西藏》,影片中西藏不是高清影像下的藍天白云,以及民族符號堆砌下的“他者”景觀,而是以泛黃的色調呈現出強烈的年代感與懷舊風格,而這種“去景觀化”的西藏內在地與老孔將西藏作為自己家鄉這一精神世界融為一體。片名以“回”這一動詞,而不是影片故事所講述的“去”西藏命名,“回”暗含著家的意味,老孔以“外來者”身份逐漸理解、融入、奉獻西藏的同時,早已將西藏作為自己的精神故鄉,孔繁森的個體意義正是通過“回西藏”這一動作得以實現。“西藏”已并非簡單意義上只是其工作奉獻生命的地方,而是具有更為深層次的家園意識。“‘家園意識’更加意味著人的本真存在的回歸與解放,即人要通過懸擱與超越之路,使心靈與精神回歸到本真的存在與澄明之中。”[10]影片《回西藏》將個體置于家園中,將老孔置于西藏這片土地中,進而實現了整個天地人系統中“大我”意義上的價值。正如影片結尾老孔所說:“時隔多年,俺又回到了西藏,回到俺的另一個家。這里的土地,這里的人民,還有知心的朋友,總是在夢里縈繞著俺,召喚俺回來。還有這里的藍天、白云、雪山、圣湖,也許就是俺的歸宿吧。”
文本之外,1956年出生的陳國星導演曾經執導了《孔繁森》、《橫空出世》(陳國星,1999)、《郭明義》(陳國星/王競,2011)、《鄧小平登黃山》(陳國星,2015)等多部主旋律電影,其電影始終保持著與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同步,呈現出強烈的家國意識。1989年出生的拉華加導演師從萬瑪才旦導演,曾擔任萬瑪才旦影片《塔洛》的執行導演,并且于2018年自編自導了首部長片《旺扎的雨靴》。影片《旺扎的雨靴》講述旺扎渴望擁有一雙雨靴,但是當他拿到夢寐以求的雨靴之后,山雨欲來,村民們請了防雹師做法阻止下雨,影片體現出強烈的作者風格以及能夠從藏族文化的“內視角”講述藏族故事。兩位文化、風格截然不同的導演聯合創作,將作者美學風格與主旋律電影的融合,這種創作模式也不失為一種“和合之美”。
結語
在銀幕上講好英模故事,充分發揚英模精神是英模傳記類電影的重要使命。在新的時代語境下,導演如何突破既往講述的窠臼并進行創新性表達,影片《回西藏》首先在創作模式上進行了革新,陳國星導演聯合年輕的藏族導演拉華加,共同將孔繁森藝術形象進行貼合時代語境的重寫與再塑,在英雄敘事上充分吸收新主流電影的群像式英雄與成長敘事,并且在美學上,從強調孔繁森“仁愛”精神的“仁義美學”到強調不同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和合之美”,《回西藏》為未來電影中的英模形象塑造,尤其是少數民族電影中英模形象塑造提供了一種典范。
參考文獻:
[1]尹鴻,何建平.時世造就品格[ J ].當代電影,2002(05):85-89.
[2]中國文藝網.第36屆中國電影金雞獎獲獎名單公布[EB/OL].(2023-11-04)[2024-08-15].http://www.cflac.org.cn/syhdx/202311/t20231105_1291212.html.
[3]王一川.卡里斯馬典型與文化之鏡(一)——近四十年中國藝術主潮的修辭學闡釋[ J ].文藝爭鳴,1991(01):23-31.
[4]王一川.王一川的藝術修辭學研究——卡里斯馬典型與文化之鏡(二)——近四十年中國藝術主潮的修辭學闡釋[ J ].文藝爭鳴,1991(02):8-16.
[5]齊魯晚報.山東新主流電影煥新,《回西藏》拍出了獨屬銀幕的詩意氣質[EB/OL].(2024-01-12)[2024-08-07].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8760807105805498amp;wfr=spideramp;for=pc.
[6]王真,張海超.從“主旋律”到“新主流”:新主流電影的修辭取向研究[ J ].當代電影,2021(09):158-160.
[7]劉帆.中國電影學派的“苦情”傳統、悲劇感與溫情美[ J ].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22(04):21-29.
[8]田卉群.行走在空中的影像——試析英模傳記片“苦情”式[ J ].中國圖書評論,2009(09):24-25.
[9]饒曙光.實踐探索、理論集成與傳統承繼——再談共同體美學的三個維度[ J ].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02):20-28.
[10]曾繁仁.試論當代生態美學之核心范疇“家園意識”[ J ].溫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03):7-8.
【作者簡介】" "賈學妮,女,山西呂梁人,山西大學文學院講師、碩士生導師,博士,主要從事少數民族電影研究。
【基金項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藏族形象在中西方電影中的敘事建構與話語機制研究”(編號:23YJCZH087)階段性成果、山西省“1331工程”立德樹人提質增效建設計劃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