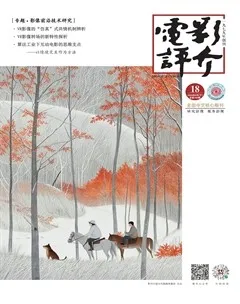新主流電影人民性的影像呈現(xiàn)與意蘊表達



【摘 要】 新主流電影彰顯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實現(xiàn)了人民性與時代性的同頻共振。通過相關文獻梳理與歸納,梳理了人民性文藝理論發(fā)展脈絡,探析新主流電影在人民性層面的具體表現(xiàn),進而提出新主流電影人民性意蘊表達的主要內容。從人民性層面來說,新主流電影是中國價值、中國文化和中國精神的重要表達載體,它可以引領我國觀眾身份認同,進而建構自信開放包容的大國形象。
【關鍵詞】 新主流電影; 人民性; 影像呈現(xiàn); 意蘊表達
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鮮明特點,是人民群眾歷史主體地位的藝術呈現(xiàn)。人民性一直貫穿于新中國文藝的發(fā)展進程之中,引領與指導大眾的思想與文藝實踐活動,并為文藝創(chuàng)作提供深厚的理論支撐。新主流電影將“人民性”作為創(chuàng)作的指導思想,堅持以人民為創(chuàng)作主體,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精神生活的需要,同時在影像呈現(xiàn)與主流價值表達方面聚焦人民性,實現(xiàn)人民性與時代性的同步書寫,開辟了中國電影發(fā)展的新路向。
一、人民性文藝理論的闡釋
人民是歷史發(fā)展的主體,是歷史發(fā)展的主要推動者與實踐者,“人民性”是社會主義文藝發(fā)展的應有之義與根本遵循。文藝與人民之間關系是歷史范疇,隨著歷史的發(fā)展具有不同的時代內容。馬克思指出:“人民歷來就是什么樣的作者‘夠資格’和什么樣的作者‘不夠資格’的唯一判斷者。”[1]列寧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文藝人民性的思想,提出:“藝術屬于人民的。……,它必須為群眾所了解和愛好。”[2]馬克思、列寧的文藝思想鮮明地指出文藝服務的對象是人民,其內容是滿足人民的需要,這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人民性”的初步構建。
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引介中國后,結合中國實際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進行了多方面的實踐,理論內容不斷拓展,逐步從“人民性”演進為“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中國化的“人民性”文藝性理論逐步確立。這其中有個關鍵性事件:兩次文藝座談會的勝利召開。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座談會上發(fā)表了重要講話,旗幟鮮明地提出了中國化的“人民性”理論,即:“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我們的文藝應當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文藝為工農兵服務。”[3]這一論斷明確了社會主義文藝服務對象是群眾,進一步明晰了社會主義文藝“人民性”的屬性與價值指向。
2014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主持召開全國文藝工作者座談會,全面、深度論析了社會主義文藝的地位及作用,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文藝“人民性”思想,提出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創(chuàng)作導向:“只有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真正做到了以人民為中心,文藝才能發(fā)揮最大正能量。以人民為中心,就是要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xiàn)的主體,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文藝工作者的天職。”[4]這一論斷是基于新時代背景下人民精神文化需求變化、社會發(fā)展變革、文藝發(fā)展新態(tài)勢而提出的,為新時代文藝發(fā)展明確了目標、指明了方向。新主流電影以“人民性”理論為參照,精選代表中國社會發(fā)展變化的典型素材,力求滿足廣大人民群眾對文化的新需要,進而實現(xiàn)思想性與藝術性的高度融合,傳遞主流價值觀,更好地弘揚中國精神,展示自信、開放的中國形象。
二、新主流電影人民性的影像呈現(xiàn)
新主流電影以散點透視的方式來展現(xiàn)國家、社會的變遷,把人民群眾的生活、工作、學習等社會實踐活動作為表達內容。這種敘事方式突破了傳統(tǒng)主旋律“高大上”、臉譜化、一元化的人物形象塑造模式,更加關注觀眾審美需要與審美體驗,呈現(xiàn)了多元化、立體化、真實性的人物形象。這些人物形象既有時代變遷主體的平凡人,也有平民化的英雄,更有多元化人物群像。這種影像呈現(xiàn)方式使電影敘事題材更多元,共情能力更強,更加契合時代之變與人民之需,實現(xiàn)了藝術性和人民性的創(chuàng)新性表達。
(一)時代變遷主體的大眾化
新主流電影順應時代發(fā)展,關注點不斷下沉,瞄準社會發(fā)展的主體——普羅大眾。他們是社會、時代發(fā)展的主要推動者,是新主流電影人民性特征的重要體現(xiàn)。他們沒有做出驚天動地的事業(yè),沒有投身邊防一線保家衛(wèi)國,也沒有在危難中逆轉困局。他們默默無聞,但他們熱愛生活,對生活充滿信心,努力工作,盡其所能做好每一件事情,以一己之力為中國發(fā)展貢獻力量,用自己的微光照亮前行之路,為“中國夢”助力。
普羅大眾與受眾之間幾乎不存在溝通障礙,新主流電影讓他們成為主角,更易引發(fā)受眾的情感回應,這能更好地回應受眾的觀影心理需要,更讓受眾感受到被尊重與認可,可以與電影中人物平等溝通交流。因此,他們能夠從真實可親的普羅大眾身上感悟生活、社會之變,體悟質樸又真實的價值觀,親民性、接地氣性厚重,提升人民的獲得感與幸福感,為觀眾追尋人生夢想提供參照。“國慶三部曲”——《我和我的祖國》(陳凱歌等,2019)、《我和我的家鄉(xiāng)》(寧浩等,2020)、《我和我的父輩》(吳京等,2021)都以“我”為敘事主體,即以普通大眾人物來表達與國家、故鄉(xiāng)、父輩之間的關系,以碎片化的敘事形式展示不同主體中群像式的大眾形象,展現(xiàn)這一群體與大時代緊密相連、命運與共的感人場面。如為了研制原子彈被迫與妻子兩地分居的工程師高遠;為了確保開國大典升旗精確無誤的林治遠;自己非常優(yōu)秀卻沒有機會參加紀念抗戰(zhàn)70周年閱兵式的備份飛行員呂瀟然。《我和我的祖國》與《我和我的家鄉(xiāng)》都展現(xiàn)了一位關愛他人、愛崗敬業(yè)的出租車司機張北京的形象:他計劃用買車錢幫表舅看病,把自己奧運門票無償送給汶川孩子。這些平凡人形象的塑造不但全景化展現(xiàn)了中國人民的形象,還從普通群眾視角呈現(xiàn)了百姓生活與社會共同演進的歷程。同時,新主流電影從多個視角展現(xiàn)平民大眾生活,涵蓋不同生活地域、職業(yè)、年齡等層面的人民,使大眾形象更加立體、豐富與具象化。《奇跡·笨小孩》(文牧野,2022)中為了讓妹妹早日手術而克服重重困難創(chuàng)業(yè)的景浩;《一點就到家》(許宏宇,2020)中三個年輕人扎根鄉(xiāng)村,辛苦創(chuàng)業(yè);《我不是藥神》(文牧野,2018)中良心轉變,熱心幫助病人的程勇等。大眾身上奮斗、擔當、積極進取精神,正是當代中國精神的投射,也是激發(fā)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精神動力。
(二)人民英雄塑造平民化
傳統(tǒng)主旋律電影把英雄塑造為文化觀念與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形象符號,承載了教化民眾、傳遞主流價值的功能,但其人民性影像表達不足,政治色彩較為濃重,影響受眾認同與審美需要。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英雄來自人民。隨著時代變化,新主流電影以“人民性”理論為指導,改變了英雄人物扁平化的塑造方式,以陌生化手法使人物現(xiàn)象更加貼近生活,更為立體化、形象化與大眾化。英雄在新主流電影中化為多面性的平民英雄,帶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反映普通民眾的真實生活場景與生活實踐,其在平凡崗位中做出了貢獻,形象更有真實感,更讓普通民眾感到可親、可學。人民英雄的形象與稱號實至名歸。成千上萬的平民英雄化為時代的重要推動者與見證者。新主流電影把平民化英雄作為影像呈現(xiàn)重點,使英雄與時代同頻共振,體現(xiàn)時代特征。電影《中國機長》(劉偉強,2019)源自真實事件,講述一位機長在面對飛機航行中出現(xiàn)的各種險情,冷靜、沉著應對,最終帶領全體人員安全返航的故事。中國機長是一位平民英雄,同時他擁有多重身份:兒子、丈夫、父親。家人期待他平安返航,與家人共享幸福、快樂時光。這樣平民英雄呈現(xiàn)更契合受眾生活的現(xiàn)實境遇,更能提升受眾與英雄的共情性,進而產生全新審美感受。電影《長津湖》(陳凱歌,2022)以長津湖戰(zhàn)役為主線,講述了中國志愿軍在極寒嚴酷自然條件下,以鋼鐵意志與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打敗了美軍,最終贏得勝利的故事。影片中伍萬里本是一個玩世不恭的野孩子,他不僅是在特定時代背景下平民英雄成長代表,也是對那時革命英雄視死如歸,為國捐軀的真情解析。影片以紅領巾為主線,引領故事發(fā)展與演進,勾畫了紅領巾與哥哥的故事以及與好友張小山的關系,推進伍萬里在親情、友情及大無畏革命英雄精神之間做出理性選擇。影片在多重事件對比中表達一個不受約束、任性倔強的孩子成長為革命英雄的心路歷程,英雄成長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接受考驗時戰(zhàn)勝困難逐步成長起來的。偉大的革命事業(yè)需要凡人英雄,凡人在不平凡成長中成為英雄。新主流電影這種表達方式促使“典型英模形象”向“平民英雄形象”轉向,英雄與人民群眾之間的鴻溝被填平,更具人民性基調,引導廣大人民群眾形成學習英雄,崇尚英雄,敬仰英雄的社會良好風尚。
(三)人物群像塑造多元化
新主流電影打造的群像式人物更注重人民群眾主體,體現(xiàn)人民群眾是社會發(fā)展的主導群體,歷史發(fā)展是人民主體合力推動的結果。這與好萊塢的超級英雄有本質的區(qū)分,也與早期主旋律電影把各種優(yōu)點匯集一人之身理想英雄有一定區(qū)別。新主流電影把關注重點內聚于群體人物身上,展現(xiàn)群體中每個個體的個性與優(yōu)秀品質,以多元化的集體群像人物彰顯人民集體力量,形成共情效應,引領大眾感受人民群眾集體的力量。電影《紅海行動》(林超賢,2018)突破“一元化”的人物表達方式,以多視角、群像化的呈現(xiàn)路徑,把集體中的每個人的優(yōu)點從不同方面顯示出來,八位蛟龍小隊成員各有特點:隊長陽剛帥氣,隱忍沉穩(wěn);副隊長徐宏沉著冷靜、英勇無畏與舍生忘死;戰(zhàn)士楊瑞鎮(zhèn)定自若、成熟穩(wěn)重;張?zhí)斓履贻p活潑、單純善良;女“蛟龍”隊員佟莉英勇無畏,是一個十足的女漢子等。他們群體因崗位不同導致分工不同,但他們相互無私幫助,協(xié)同完成任務,是一個團結、積極進取、高效合作的群體。他們展示了中國軍人無私無畏、團結一心、英勇戰(zhàn)斗,不怕犧牲的精神。同時,影片也不刻意遮掩群體中每個成員的性格缺陷。如李董的膽怯猶豫、機槍手石頭緊張時需要吃糖來緩解情緒,化解尷尬;隊長面對壓力也十分焦慮,心神不安。隨著劇情的推進,每個隊員融入團隊后不斷相互扶持成長,不斷彌補缺陷,改正缺點,超越自我,完善自我,如內心恐懼的石頭面對危險時,毫不畏懼,挺身而出為保護團隊犧牲自己;李董不斷成長,克服了膽怯猶豫,成為一名出色的狙擊手;莊羽為了讓突擊小隊保持通訊暢通,冒著槍林彈雨,在生命最后一刻,接通了通訊器。兩名女性隊員的角色設置也各有亮點:佟莉沉著冷靜,但不失女性的柔美形象,記者夏楠不是一個單純無知的少女,內心強大,面對困難毫無畏懼之色。蛟龍隊員各有特色,有血有肉,讓觀眾具有良好的情感體驗。此外,《八佰》(管虎,2020)、《烈火英雄》(陳國輝,2019)、《金剛川》(管虎,2020)與《緊急救援》(林超賢,2020)等新主流電影都以多元群像人物開展敘事模式,使受眾自覺帶入,化為具象化的人物,其現(xiàn)實性的人間煙火氣撲面而來,構建起多種職業(yè)、不同性格的審美認同,人民群體性的作用應然而生,愛與情誼并重,倫理關照自然而然地滲入其中,人間溫情自然流露。
三、新主流電影人民性的意蘊表達
電影的創(chuàng)作與傳播需建構文本與觀眾之間多個認同,如情感認同、價值認同、心理認同、文化認同等,進而使觀眾體悟影視作品意義,實現(xiàn)電影文本的主流價值表達。中國電影無論是主旋律電影與新主流電影都承載著宣講主流意識形態(tài)與中國精神的重要功能,都以弘揚與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核心敘事要義,并隨著時代變遷增添更多的文化內涵與歷史使命。新主流電影在弘揚愛國主題中融入對“小家”的關注,書寫了中國化的社會集體記憶與身份認同,展現(xiàn)了一個自信開放包容的大國形象。
(一)家國情懷的賡續(xù)傳承
早期主旋律電影采取單一、固化的敘事方法,把國家的發(fā)展與強大作為敘事主題,使個體與小家的發(fā)展遵循國家發(fā)展邏輯。在這種宏大敘事視角下,大國的崛起與發(fā)展需要個體與小家犧牲來助推,個人與國家完全割裂,國家地位高于個人,個人命運需順應國家與民族需要,沒有獨立的身份,進而使小家價值無法充分顯現(xiàn),人民主體性地位無法全面闡釋。新主流電影重構家國之間的關系,探尋“大國”和“小家”之間的互融與協(xié)同,重視個體情感與個體價值,從而構建家國情懷賡續(xù)的新模式。這種新模式凸顯家國關系的和諧統(tǒng)一,大國與小家是互動與認同的共同體。如“我”系列電影——《我和我的祖國》《我和我的家鄉(xiāng)》《我和我的父輩》。“我”的成長與祖國、家鄉(xiāng)、父輩相互支撐,相互促動。“我”既是大國崛起與發(fā)展見證者,更是參與者與貢獻者。我愛我的祖國,愛國主義精神賡續(xù)傳承;我愛我家,國家好,家庭更好。由此,家國命運與共,緊密相連。電影《長津湖》中,楊家三兄弟為了保家衛(wèi)國相繼參加抗美援朝戰(zhàn)爭,這既有對國家安全的支持,也體現(xiàn)著對小家幸福安寧生活的維護,也有我國人民愛國、愛家的優(yōu)良精神的傳承,更有“舍家為國”的愛國主義接續(xù)。其后的《長津湖之水門橋》(陳凱歌,2022)更加淋漓盡致地表達家國關系,彰顯愛國主義。余從戎、平河、雷公、伍千里的慷慨犧牲是小家對大國的貢獻,是愛國與愛家的互融。這種敘事主題與敘事方式可以讓觀眾認同中國人民志愿軍的高大形象,使他們熱血沸騰、熱淚盈眶。影片塑造的歷史場景讓觀眾重新認識抗美援朝戰(zhàn)爭,感受家國利益相互依存、密不可分。家國相互支持、相互映襯,是命運共同體,激發(fā)起觀眾愛國、愛家,有效傳達與賡續(xù)家國情懷。
(二)社會集體記憶與身份認同書寫
電影的認同機制是一個以社會的主流性文化為取向、以傳統(tǒng)的民族精神為依據(jù)、以電影的敘事形態(tài)為核心的電影心理問題。[5]新主流電影把觀眾心理認同作為人民性主題表達的重要途徑。如把家國情懷、改革創(chuàng)新精神、愛國主義、國家意志、集體主義、團結友愛等融入電影的表達主題,在電影發(fā)展情節(jié)與細節(jié)中呈現(xiàn)社會現(xiàn)狀、核心價值觀與主流意識形態(tài),使電影表達主題與社會核心問題相融通、觀眾個人審美體驗與社會現(xiàn)實相縫合、觀眾個人想象空間與銀幕形象呈現(xiàn)相一致。電影《奪冠》(陳可辛,2020)描述了女排奪冠的三個重要歷程:1981年獲得首冠,2008年中美北京奧運會女排對決,2016年里約奧運會中巴女排終極對決。影片采取非虛構影像還原中國女排姑娘參賽的比賽場地、激戰(zhàn)場景、受傷及重新上場等激發(fā)人心的畫面,展現(xiàn)觀眾支持女排、期待女排有更好地表現(xiàn)比賽氛圍和女排克服各種困難。不斷拼搏的進取精神。在這種視聽氛圍烘托下,觀眾不自知地被帶入比賽場景之中,享受跌宕起伏的比賽過程,感覺自己就是比賽現(xiàn)場的參與者,更是女排比賽實景的鼓勵者與見證者,完成自己的心理與身份認同。女排奪冠只是中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過程中的一個縮影,是中國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光輝進程,更是人民走上幸福生活的復興之路。其深層含義更含納奮斗、創(chuàng)新、拼搏、團結、愛國等精神力量,引發(fā)了受眾對不同階段女排精彩比賽場面的集體記憶,進而強化國人對自身身份認同,產生強烈的國家歸屬感與民族自豪感。《我和我的家鄉(xiāng)》之《天上掉下個UFO》《神筆馬亮》等篇取景鄉(xiāng)村,讓觀眾從視聽層面感受田園詩歌生活的愜意與美好,激起觀眾的思鄉(xiāng)之情與身份認同,促進個體記憶與國家記憶無縫對接。
(三)自信開放包容的大國形象
“國家形象是國家的內部公眾和外部公眾對一國相對穩(wěn)定的總體評價,是一個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體現(xiàn)。”[6]國家形象建構可以通過具象化的符合進行呈現(xiàn),如國歌、國徽、國旗等,也可以借助影視媒介來呈現(xiàn)。新時代以來,新主流電影化為中國形象與文化自信呈現(xiàn)的重要媒介。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多極化與經濟全球化使中國從東方大國向全球大國躍遷,深度參與到國際事務之中,展現(xiàn)了東方大國擔當與大國形象,此種世情下新主流電影應弘揚中國精神、展現(xiàn)文化軟實力,重塑中國形象,向世界展示自信、開放、包容的良好形象。面對不同的場景,新主流電影把這些內容融入特定空間進行表達。《紅海行動》(林超賢,2018)講述中國撤僑救僑故事。中國公民在世界遇到任何困難,祖國都是其最強的后盾。但中國的救援行動不止步于中國公民的安全撤離,當發(fā)現(xiàn)有“黃餅”危及世界安全時,蛟龍隊果斷采取行動來消除隱患以維護世界和平,保護人類平安幸福,展示開放、包容、自信的中國形象,更是負責任大國的有力佐證;《流浪地球》(郭帆,2020)以地球面臨共同的災難為故事起點,去除了你死我活的相互傾軋場景,而是以開放、包容、自信的心態(tài)團結各種力量,共同拯救人類共有的家園,和地球一起流浪。這其中既有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展現(xiàn),更有中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表達;《我和我的祖國》(陳凱歌,2019)采取全球上映模式,把影片推向歐美市場,讓全球觀眾見證中國變化,感悟中國精神,宣傳自信、開放、包容的中國形象,傳播人類命運共同體美學,使世界認同中國形象。
結語
中國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重要實踐者與創(chuàng)新者。“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理論為影視作品人民性的創(chuàng)新性與創(chuàng)造性表達夯實了理論基礎。以人民為敘事主體的中國故事承擔著堅守中國精神價值的現(xiàn)實任務。[7]新主流電影對文本進行了敘事重構,以人民話語呈現(xiàn)時代變遷下國家、社會發(fā)展的圖景,彰顯家國情懷、書寫社會集體記憶、引領觀眾國族的身份認同,進而建構自信開放包容的大國形象。當下,中國式現(xiàn)代化進程如火如荼,人民需要更多優(yōu)秀影視作品來滿足精神文化需要。“讓中國價值、中國文化、中國精神在影像與聲音的交響中傳遍世界”[8],為文化強國爭光添彩。
參考文獻:
[1][德]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5-196.
[2][蘇聯(lián)]列寧.論文學與藝術[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435.
[3]毛澤東.毛澤東選集 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3,863.
[4]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3-14.
[5]賈磊磊.中國主流電影的認同機制問題[ J ].電影新作,2006(01):41-46.
[6]孫興昌.“一帶一路”視域下的國家形象塑造[ J ].山西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46):13.
[7]王蕊.從平民敘事到人民形象的構建:“講好中國故事”的策略分析——以《人世間》為例[ J ].電影評介,2022(06):85-88.
[8]黃鐘軍.新主流電影“人民性”的表述延伸與審美更新[ J ].中國文藝評論,2022(07):66-76.
【作者簡介】" "孫弋嵐,女,河北石家莊人,河北師范大學匯華學院外語學部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