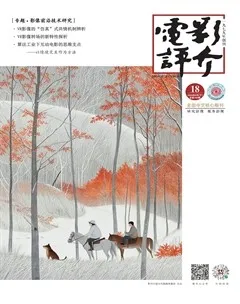芥川龍之介改編電影的媒介置換與人性維度
【摘 要】 本文旨在探討芥川龍之介文學(xué)作品改編電影的多維度主題拓展及其對人性探討的深化。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文本分析與電影媒介理論相結(jié)合的方式,分析芥川龍之介小說改編電影在主題、符號等方面的拓展,以及在多維人性方面的發(fā)掘。本研究不僅在于揭示電影媒介如何在視覺與聽覺層面上拓寬和深化文學(xué)文本的內(nèi)涵,而且著重探討電影如何通過鏡頭語言、光影效果等手段直觀展現(xiàn)人物復(fù)雜的內(nèi)心世界。結(jié)論表明,改編電影在保持甚至拓展芥川龍之介原著主題探討的同時,也通過電影特有的表現(xiàn)手法,進(jìn)一步豐富對人性多面性的表達(dá)。本文旨在為文學(xué)作品的電影改編提供一種新的研究視角,強(qiáng)調(diào)電影媒介在文學(xué)傳播與接受中的獨特價值,為今后的文學(xué)與電影跨媒介研究提供理論參考。
【關(guān)鍵詞】 小說改編電影; 媒介置換; 主題拓展; 復(fù)雜人性; 演繹式外現(xiàn)
芥川龍之介作為日本近代文學(xué)史上的一位杰出小說家,以其精煉而深邃的短篇小說在文壇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自1915年正式踏入文學(xué)世界至1927年悲劇性地結(jié)束生命,芥川龍之介在短短12年間創(chuàng)作了接近150篇短篇小說。他的短篇小說取材視野廣泛、文筆風(fēng)格獨到和文學(xué)形式多樣,小說內(nèi)容往往有著豐富的寓意,能夠反映出作者對于深刻人性的探索。芥川龍之介的作品,被日本文學(xué)研究者宮坂覺形象地比喻為“芥川山脈”[1],充分說明其在日本文學(xué)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對后世作家的深遠(yuǎn)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芥川龍之介的作品不斷被改編成電影。電影和文學(xué)兩種藝術(shù)形式的結(jié)合為彼此提供了更好的解讀和表現(xiàn)形式,也為現(xiàn)代觀眾提供了通過不同媒介體驗經(jīng)典文學(xué)的機(jī)會。在這一過程中,電影制作人通過視覺語言重新解讀和呈現(xiàn)原作故事,賦予經(jīng)典文本新的寓意和人性維度。
本文旨在探討芥川龍之介小說文本在經(jīng)歷媒介轉(zhuǎn)換后,電影影像中蘊(yùn)藏著的豐富寓意以及復(fù)雜人性的多維度顯現(xiàn),從而揭示改編作品如何跨越時空,與當(dāng)代觀眾進(jìn)行對話;通過深入分析這些電影改編的藝術(shù)手法、敘事策略以及對原作的忠實度和創(chuàng)新性,揭示改編電影如何以獨特的視覺和情感語言,拓展和深化了芥川龍之介作品中的寓意與人性探索,進(jìn)一步豐富了讀者與觀者對于經(jīng)典故事的理解與感受。
一、媒介置換下的豐富寓意
(一)小說原作的深厚主題
芥川龍之介生活在日本從明治時代過渡到大正時代的重要歷史時期,這一時期日本社會經(jīng)歷了劇烈的變革,從封建閉關(guān)自守到積極吸收西方文化和技術(shù)。芥川龍之介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不可避免地受到這一時期日本社會矛盾和文化碰撞的深刻影響,作品主題的深度與廣度都展現(xiàn)出較高的復(fù)雜性,可以說,芥川筆下的人物形象與傳統(tǒng)小說中善惡分明的符號化人物截然不同,而是有著一種獨特的復(fù)雜性和不確定性。從《羅生門》(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版)中企圖探討倫理道德的相對性以及真相的難以還原性,到被稱為追求“藝術(shù)至上主義”[2]的《地獄變》(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中反映人性的瞬息多變與明暗交織,芥川龍之介的作品深刻反映了這一時代背景下的社會矛盾和個人掙扎,而作家對于人性的探索與道德及真相的質(zhì)疑,則展現(xiàn)了他對于人類精神困境的關(guān)注。
首先,芥川龍之介作品中一個較為顯著的主題是探討真相以及道德的相對性,在小說《竹林中》(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9年版)中,通過不同人物關(guān)于同一事件的不同敘述,展現(xiàn)了道德和真相在不同人和不同出發(fā)點視角下的偏差。小說《竹林中》中每個人物的敘述都帶有個人的偏見和自我保護(hù)的動機(jī)。例如,小說中,多襄丸的供詞是他在決斗中殺死了武士,并在提及二人決斗了二十三回合時,甚至快活地笑了。多襄丸之所以沒有推脫責(zé)任,而是直接承認(rèn)殺人,是因為多襄丸更在乎自己的英雄聲譽(yù),保留光明磊落,敢作敢當(dāng)?shù)挠⑿坌蜗蟆6嫔案粗氐氖亲约旱淖饑?yán),因此她著重描述自己受到羞辱之后無意識的迷狂狀態(tài)。芥川龍之介巧妙地利用幾人的供詞,展現(xiàn)了人在極端狀態(tài)之下的不同側(cè)重點與選擇,而人性的復(fù)雜也使得“真相”成為一個模糊且多面的概念。在《地獄變》(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中,芥川龍之介通過描繪一個藝術(shù)家在繪制地獄畫卷時的心理變化,展示了人性中善與惡的矛盾共存交織。藝術(shù)家畫師良秀為了完成堀川大公的命令,畫出一幅驚世駭俗的《地獄變》屏風(fēng),卻不惜陰差陽錯犧牲一個生命的悲劇。
除此之外,芥川龍之介作為一代文學(xué)大師,其純熟的文學(xué)技巧也在展現(xiàn)復(fù)雜主題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首先,作者在對話使用上極具匠心,能夠通過簡潔而富有深意的對話展現(xiàn)人物性格和心理狀態(tài),同時推動情節(jié)發(fā)展。在《羅生門》中,不同人物之間關(guān)于事件的對話揭示了他們各自的性格和動機(jī),加深了故事的復(fù)雜性和沖突;其次,作者善用敘述視角切換,以此來展現(xiàn)故事的多重面貌和深層含義。例如,在《羅生門》中,通過改變敘述者來展現(xiàn)同一事件的不同版本,這種技巧不僅增加了故事的懸疑性,也深化了對于真相相對性的探討;此外,象征手法的運用也不可忽視,芥川龍之介在作品中運用了大量的象征手法來增強(qiáng)故事的深度,例如,在《蜘蛛絲》(華夏出版社2008年版)中,蜘蛛絲不僅是救贖和希望的象征,也暗示了主人公內(nèi)心的貪婪和自私,通過這種象征手法表現(xiàn)出人性中的道德選擇和內(nèi)心的沖突。
(二)改編電影的多重拓展
根據(jù)前文所述,芥川龍之介原小說文本本身就具有藝術(shù)魅力,其深厚復(fù)雜的主題與價值探討使文本本身就具有豐富的寓意。而多樣化的電影改編作品無疑與芥川龍之介的原作品形成了一種對話,在多個方面對原小說進(jìn)行拓展與豐富。
芥川龍之介始終將揭露人性中的利己主義放置于首位,但是不同的電影創(chuàng)作者本身具有自主性。一般來說,導(dǎo)演在進(jìn)行小說電影化改編時,遵循著兩種不同的風(fēng)格傾向。其一為再現(xiàn)式改編,旨在完全再現(xiàn)原著的時空背景與情節(jié)脈絡(luò),力求呈現(xiàn)原作的精神內(nèi)核;其二則為寫意式改編,導(dǎo)演在此過程中充分調(diào)動個人智慧,對原作進(jìn)行創(chuàng)造性的重新改造,以獨特的視角和手法詮釋原著的精髓。這兩種改編風(fēng)格各具特色,共同豐富了電影藝術(shù)的表達(dá)形式。[3]在對小說的改編過程中,對原著的增刪,則可以變現(xiàn)出導(dǎo)演的獨特價值觀,以此實現(xiàn)對于芥川龍之介作品的進(jìn)一步豐富。
在電影《羅生門》(黑澤明,1950)中,黑澤明相較于原作《羅生門》和《竹林中》的敘事,引入了一些顯著的新增情節(jié)和改動,這些調(diào)整不僅加深了電影的主題,也增加了作品的復(fù)雜性和深度。首先是開場和結(jié)尾的寺廟場景。電影開頭和結(jié)尾在一個半廢棄的寺廟中展開,三個角色——一個和尚、一個木匠和一個平民——在這里討論發(fā)生在羅生門下的故事。這一設(shè)置是電影的創(chuàng)新,它為整個故事提供了一個旁觀者視角,同時也象征了對于日本社會在戰(zhàn)后的困惑和對于道德與真相的探索;其次是嬰兒的發(fā)現(xiàn),在電影的結(jié)尾處,三人在寺廟中發(fā)現(xiàn)了一個被遺棄的嬰兒。這個情節(jié)是電影相對于原作的重要添加,不僅引發(fā)了角色間對于人性的最終討論,還給觀眾留下了對未來和希望的思考。木匠最終決定收養(yǎng)這個嬰兒,象征著盡管人性中存在負(fù)面和黑暗面,但仍有善良和希望存在。同樣是由日本導(dǎo)演進(jìn)行改編的電影《迷霧》(三枝健起,1997)則通過情節(jié)的設(shè)置,將視野更多地放置于女性角色真砂的身上。《迷霧》增設(shè)了真砂為母復(fù)仇的橋段,因此,真砂在影片中不再與原作相同,是被多襄丸凌辱的對象,而是在發(fā)現(xiàn)多襄丸就是殺母仇人之后主動獻(xiàn)身于他,以此來達(dá)到復(fù)仇的目的。在這部影片中女性的身體不再是被動地被凌辱的對象,而是成為具有自我意識的女性復(fù)仇的工具,因此,改編作品《迷霧》也具有更多女性主義色彩。改編電影《南京的基督》(區(qū)丁平,1995)雖是由日本牽頭企劃,但是該部電影的主創(chuàng)團(tuán)隊,包括攝影與編導(dǎo)等等都由香港班底完成,該部電影具有比原作更加強(qiáng)烈的東西方混雜性。與小說原作相比,電影增加了諸多巧妙的情節(jié),顯示出多重交織的文化屬性,例如身為日本知識分子的岡川教金花書寫漢字;金花在得梅毒之后走投無路吃“人血饅頭”,這處情節(jié)明顯是對于魯迅文學(xué)傳統(tǒng)的繼承。而岡川,其日本特征被淡化,且教授金花書寫漢字,則可視作東方文化的具象表現(xiàn)。
(三)符號化的鏡頭與主題深化
在電影中,鏡頭符號的運用往往具有隱喻和象征的功能,甚至與電影敘事結(jié)構(gòu)有密切關(guān)聯(lián)[4]。通過對特定鏡頭符號的運用,電影能夠創(chuàng)造出富有深意的畫面。在芥川龍之介小說改編的電影中,鏡頭美學(xué)還體現(xiàn)在對符號化元素的運用上。通過對某些物品或場景的反復(fù)拍攝,電影能夠賦予這些元素以特定的象征意義,從而加深故事主題。例如,雨、門、鏡子等元素在電影中不僅是物理對象,也成為表達(dá)人性、真相和幻覺等主題的象征。這種符號化的鏡頭運用,豐富了電影的內(nèi)涵,使得改編作品不僅忠實于原作情節(jié),更深入地探討了原作的主題和寓意。
黑澤明在《羅生門》中的電影語言使用堪稱經(jīng)典,特別是他對黑白攝影、鏡頭運用的精心選擇,為電影增添了深刻的情感和哲學(xué)意味。導(dǎo)演利用黑白攝影對比強(qiáng)烈、陰影深邃的特點,創(chuàng)造了一種懸疑而又充滿張力的視覺風(fēng)格,這不僅加深了故事的神秘感,也象征了事實與虛構(gòu)、善與惡之間模糊的界限。電影中的鏡頭運用極具創(chuàng)意,比如運用傾斜角度和不穩(wěn)定的攝影手法來表現(xiàn)人物的主觀視角,以及通過長鏡頭和近景鏡頭的切換來加強(qiáng)情感表達(dá),使觀眾能更深入地感受角色的心理狀態(tài)和事件的緊張氛圍。由三枝健起導(dǎo)演的《迷霧》對于“羅生門”的故事進(jìn)行了幾乎顛覆性的改編,他將懸疑、愛情以及復(fù)仇等多種元素交織于一體,塑造出一個充斥著不確定性的世界。該片的光影設(shè)計與色彩色調(diào)的選擇在營造神秘又壓抑的氛圍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過多使用逆光映照以及朦朧質(zhì)感的營造,渲染出近乎詩意的光影效果,有助于深化電影的主題。例如,在電影的開頭,真砂與武士在河邊交歡之時,多襄丸利用鏡子的反射光,使得圓形的光亮在真砂身體之上游走,此處光影的介入就暗示著他們?nèi)酥g將會圍繞著情與欲產(chǎn)生糾葛。而在真砂在敘述武士死亡時,特寫鏡頭下從樹上飄落的樹葉配合詩化的陰影,樹葉便有了較強(qiáng)的隱喻性,暗示生命消失的悲愁。電影《南京的基督》通過前后光影的變幻展現(xiàn)人物的內(nèi)心世界,在岡川與金花的前期交往中,往往采用過度曝光的手法,營造出一種如夢似幻的美麗天堂質(zhì)感。而以岡川受到妻子生產(chǎn)的家書為轉(zhuǎn)折點,電影的光影色彩逐漸偏向暗淡,整體基調(diào)以幽暗為主,營造出悲沉的氛圍。前后的視覺對比不僅強(qiáng)調(diào)二人的關(guān)系由親密到疏離的演變,更能夠暗示金花這個本來純潔天真的女性命運的悲劇性走向。
二、復(fù)雜人性的多維顯現(xiàn)
(一)極端環(huán)境下人的抉擇
電影藝術(shù)中的道德沖突不僅僅是對錯的簡單判斷,而是將人放置于特定社會文化背景下,將其困于充斥著矛盾沖突的極端環(huán)境之中,這一場域往往涉及生存、欲望、正義與自我認(rèn)同等基本人性議題,以此來觀測人在極端環(huán)境中的多種可能性。無論是芥川龍之介的小說文本還是多位電影大師對其小說的電影改編,均無一例外地將人放置于極端環(huán)境之下,以此來觀看人性的復(fù)雜之處。
在《羅生門》中,不同人物對同一事件的不同敘述揭示了人性中自私、虛榮和自我保護(hù)的本能。在生死審判的境遇之中,多襄丸將英雄的聲譽(yù)視作超越死亡的介質(zhì),以大無畏姿態(tài)認(rèn)下殺人之罪,這樣的選擇是超越人向生去死的思維慣性的,由此也表現(xiàn)出不同的個體在對待死亡困境時的不同抉擇。
《地獄變》(豐田四郎,1969)中畫師在面對至親死亡之時的情感變化,更是將人性的不確定與難以捉摸展露得淋漓盡致。良秀焚火的橋段無論是在小說還是電影中,都是高潮部分。小說對于這一極端慘烈場景之下良秀的情感變化描繪得極為細(xì)致。首先,在良秀看到被捆綁在牛車上即將被火焚燒的正是自己的女兒時,他好像失去了理智般,突然跳起蹲坐著的身體,兩手前伸,不自覺地跑向車子。而在點火之后,良秀瞪圓的雙眼,扭曲的唇,不斷抽搐的雙頰,將他心中交織的恐懼、悲痛、驚異,異議都寫在了臉上。但是,在看到奇異的火燒景觀之后,良秀的臉上,卻閃耀出一種無法形容的光輝,宛如出神般的法悅的光輝。他的眼中映射著的似乎不是女兒慘死的景象,只有美麗的火焰。
芥川龍之介通過描繪良秀表情的轉(zhuǎn)變,巧妙地表達(dá)自身對于極端情景之下人的復(fù)雜與多變的深度思考。這一場景在由豐田四郎導(dǎo)演的《地獄變》電影版中也得到清晰地呈現(xiàn)。雖然文字與演員的動作肢體表情語言之間有較大的難以通約性,媒介轉(zhuǎn)換之后,讀者的想象變?yōu)橛^者的直接性觀看,但是在場景光影音效等一系列電影技術(shù)的加持之下,良秀在極端場景之下的人性嬗變還是被呈現(xiàn)得異常生動。與上述兩部影片不同的是,《南京的基督》并非將主人公放置于生死絕境之中考驗,而是刻畫出一個道德審判的牢籠,以此來呈現(xiàn)知識分子在人道與非人道的虛偽狀態(tài)之間掙扎的狀態(tài),更多凸顯的是人性的矛盾之處。由中國香港導(dǎo)演區(qū)丁平執(zhí)導(dǎo)的電影《南京的基督》雖然保留了原作的諸多關(guān)鍵情節(jié),但是卻將金花淪落風(fēng)塵的罪因放置于作家岡川身上,正是岡川的罪惡欲念,使得純潔少女墮入風(fēng)塵,由此走上悲慘之路。而染上了惡疾的金花也讓作家岡川的良心遭受了莫大的譴責(zé),岡川在對于家庭的責(zé)任以及對于金花的拯救兩方面產(chǎn)生了矛盾掙扎,電影用較多的筆觸描繪了作家的內(nèi)心煎熬。這一改編在很大程度上擴(kuò)充豐富了原作的探討主旨,小說原作主要側(cè)重于探討信仰的力量及其局限性。金花的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幫助她面對苦難的生活,但是與此同時,信仰又成為她合理化自身行為的恐懼。正如德國哲學(xué)家尼采所言:信仰是盲目的,但并非沒有目的;它有著盲目的力量。[5]金花的故事正是這一觀點的生動注腳,她的信仰既是她面對困境的盾牌,也是她自我逃避的借口,揭示了信仰力量的雙重性。電影將金花與宗教信仰之間的關(guān)系內(nèi)嵌于金花與日本作家的關(guān)系之中,豐盈了知識分子的角色。由此,將文本的主題擴(kuò)充至對于知識分子虛偽性以及人性的矛盾與糾結(jié)的層面。
(二)復(fù)雜心理的直觀演繹
電影作為一種視聽媒介,其獨特性在于能夠直接作用于觀眾的感官,通過圖像、聲音、光影等多種元素的綜合運用,創(chuàng)造出超越文字描述的沉浸式體驗。正如電影理論家安德烈·巴贊所言:“電影是現(xiàn)實的漸近線。”[6]這種直觀性不僅去除了文字?jǐn)⑹龅闹虚g性,還使觀眾能夠更直接地感受到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和內(nèi)心世界的沖突。電影媒介的這一特性,在改編文學(xué)作品時顯得尤為重要,它允許創(chuàng)作者以更加生動和具體的方式展現(xiàn)原作中的復(fù)雜情感和深層主題。也就是說,電影可以通過更為細(xì)膩的視覺呈現(xiàn)和聽覺音效等,直觀展現(xiàn)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和內(nèi)心世界的沖突。通過演員的容貌、服飾、行為、對話乃至表情和眼神,使觀者感受到人物性格的復(fù)雜性和變化。
電影《羅生門》與《迷霧》均是對于芥川龍之介小說《羅生門》《竹林中》的改編,但是黑澤明的《羅生門》與三枝健起的《迷霧》在演員外形與演繹等方面就呈現(xiàn)出迥然的差異。從女性演員的服飾裝扮來說,《羅生門》中的真砂由日本演員京町子飾演,她在影片中的穿著較為樸素,衣物以素色為主,呈現(xiàn)出莊重的女性氣質(zhì)。較為特別的是,在她的面部卻蒙有一層輕柔的面紗,在多襄丸的敘述中,正是風(fēng)吹動了真砂的面紗使得他欲念萌動。而《迷霧》中由天海佑希飾演的真砂在影片中的服飾上便有較多花色,整體形象塑造側(cè)重于表現(xiàn)少女的靈動之美。而與《羅生門》更顯示出較大差異的是,導(dǎo)演在影片開始便安排了真砂與武士的情欲戲碼,而這也成了多襄丸心生歹念的一個動因。
除此之外,《羅生門》中主要演員精確而富有表現(xiàn)力的表情神態(tài)也有助于直觀呈現(xiàn)人物內(nèi)在的復(fù)雜心理。木村功所扮演的樵夫在他講述自己所看到的故事時,其微妙的表情變化和猶豫的語氣深刻描繪了一個既是旁觀者又不得不卷入其中的普通人的心理狀態(tài)。三船敏郎所扮演的強(qiáng)盜多襄丸在其他人揭示各自版本真相時的微妙表情變化,精準(zhǔn)地捕捉了人物的自私、狡猾以及最終的絕望。而京町子則通過她的眼神和肢體語言,傳達(dá)了一個復(fù)雜的女性角色的恐懼和矛盾。《迷霧》中由金城武飾演的武士則展現(xiàn)出與森雅之版的武士在表演上也呈現(xiàn)出諸多不同,金城武的所飾的武士神色始終是多情的,而森雅之的神態(tài)則多顯露其冷酷與殘忍的一面。兩位演員在人物細(xì)節(jié)演繹上的不同與兩部電影希冀傳達(dá)的內(nèi)在意圖有著直接而緊密的關(guān)聯(lián),重視視覺呈現(xiàn)的電影藝術(shù)正是通過這樣直觀化的手法呈現(xiàn)不同情境之人性的復(fù)雜與不可捉摸。
豐田四郎執(zhí)導(dǎo)的《地獄變》在電影作品中更多地突出現(xiàn)實批判意義,電影通過人物服飾與裝扮以及表演等增添了更多日式恐怖元素。主人公畫師良秀的精確演繹以及眾多特寫鏡頭將其內(nèi)心的斗爭與激烈斗爭一一外顯。為了超越追求藝術(shù)上卓越的良秀,開始嘗試禁忌的繪畫技巧,這直接導(dǎo)致了他和周圍人的災(zāi)難。不同于小說中心理描寫的方式,電影利用視覺效果和演員的身體語言,呈現(xiàn)良秀復(fù)雜畸形的心理狀態(tài)。特別是畫師在實踐禁忌技巧時,他的臉部表情和手的動作,以及隨后的恐懼和內(nèi)疚,都通過演員的表演細(xì)膩呈現(xiàn)。同時,與小說相比較,電影加深了畫師與周圍人物關(guān)系的描繪,通過畫師與他人的互動,展現(xiàn)了他道德淪喪的過程對他人的影響。
結(jié)語
芥川龍之介在日本文學(xué)史上有著不可撼動的地位,其作品與個人的文學(xué)理念,對后來的作家,如昭和時代的川端康成、大島正雄等人,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經(jīng)由黑澤明、三枝健起等電影大師改編的作品無疑在多重意義上拓寬了原作的表現(xiàn)邊界,對于電影史也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但是,就當(dāng)下已有的改編電影來看,仍有進(jìn)一步深化的空間。例如,芥川龍之介文學(xué)作品往往具有復(fù)雜的敘事結(jié)構(gòu)和深層次的主題,文學(xué)作品的電影改編,如同美國學(xué)者杰弗里·瓦格納所言:“是對原著的再創(chuàng)造,既是對原著的致敬,也是對新形式的探索”[7]。因此,在改編芥川龍之介的作品時,如何在保持原作精神內(nèi)核的同時,賦予其新的時代意義,是每一位電影創(chuàng)作者必須面對的課題。電影改編需要在有限的時間內(nèi)傳達(dá)這些復(fù)雜性,這可能導(dǎo)致細(xì)節(jié)或深層含義的丟失。除此之外,改編作品往往需要在忠實原著和創(chuàng)新之間找到平衡。電影作品為了迎合觀眾口味或市場需要,可能會對原作進(jìn)行較大改動,偏離原作復(fù)雜深厚的主旨意圖。尤其是2010年以來,芥川電影改編作品難出精品之作,亟需電影創(chuàng)作者為其作品注入新時代的新精神,以求創(chuàng)作出更符合時代面貌的作品。
參考文獻(xiàn):
[1][日]芥川龍之介.點鬼簿(芥川文集·小說全集下)[M].魏大海,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21:3.
[2]邱雅芬編選.芥川龍之介研究文集[M]//外國文學(xué)學(xué)術(shù)史研究.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78.
[3]李晶.魔方:小說電影改編的藝術(shù)[M].北京:電子工業(yè)出版社,2018:45.
[4][蘇聯(lián)]尤里·米哈伊洛維奇·洛特曼.電影符號學(xué)與電影美學(xué)問題[M].凡保軒,譯.北京:中國傳媒大學(xué),2021:55.
[5][德]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M].孫周興,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23:45.
[6][法]安德烈·巴贊.電影是什么?[M].崔君衍,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7:17.
[7][美]約翰·M·德斯蒙德,彼得·霍克斯.改編的藝術(shù):從文學(xué)到電影[M].李升升,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6:5.
【作者簡介】" "韋克利,女,河南鄭州人,河南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講師;
劉艷君,女,河南鄭州人,河南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副教授,主要從事英語教學(xué)研究。
【基金項目】" "本文系河南農(nóng)業(yè)大學(xué)本科教育教學(xué)改革研究與實踐項目(編號:2024XJGLX048)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