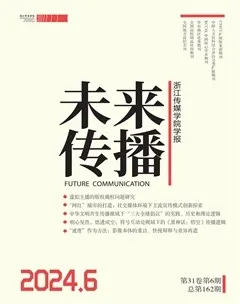數字媒體生態下電影跨媒介實踐的“附改編”現象研究
摘"要:媒體融合大潮之下,電影在與新媒體的交互過程中成了被改編之物,電影改編產品也成了數字時代影像消費的重要內容。電影跨媒介消費的濫觴和參與式文化的勃興推動了電影改編實踐和理論的變革,融合文化場域內的電影改編偏向于科斯塔斯·康斯坦丁尼德斯提出的“附改編”范疇。綜觀融合文化場域中的電影“附改編”現象,媒介殊異性解構了傳統改編模式中源文本與改編文本的從屬關系,以忠誠性為基礎的改編倫理被擱置。媒介殊異性和文本互文性共塑的“附改編”機制催生了“文本—附文本”交雜的改編文本形態,“作者—用戶”共棲的主體性體認,以及“電影—新媒體”共生的融合媒介身份。
關鍵詞:附改編;數字電影;民間創造性;深度媒介化
中圖分類號:J9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6-8418(2024)06-0114-08
隨著數字時代深度媒介化的快速演進,融合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無疑已經成為數字文化生態的核心組成部分。美國電影理論家羅伯特·斯塔姆(Robert Stam)指出,20世紀末以來數字革命的爆發式演進,使得報紙、雜志、小說、電影、電視等傳統大眾媒體被卷入到數字化的洪流之中,以至于數字媒體有可能將以前所有的媒體納入一個龐大、統一的網絡檔案(cyber archive),融合文化因此走向繁榮。[1]電影作為一種多媒體藝術,融合了以戲劇、繪畫、音樂、小說為代表的傳統藝術元素,使得其自誕生之日始便具有內生的融合文化特征。數字媒體發展至今,電影早已在數字空間中被多樣媒體(如短視頻、播客、微博)“再書寫”,實現了貫穿大屏與小屏、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現實場景與虛擬場景的效果。
基于結構主義互文性的理論視角,電影文本(及其要素)在不同文本、語境和媒介的交互現象(如引用、混合甚至反轉)通常被稱為“改編”。當然,跨媒介改編并非電影藝術所獨有。從前現代詩歌、小說、戲劇、繪畫、歌曲、舞蹈之間的故事交換到現代電影、廣播、電視之間的文本傳遞,跨媒介的改編實踐貫穿了人類的文化發展史。[2]傳統電影改編研究關注電影對文學(或藝術)文本的“再書寫”。在以“靈韻”(aura)為代表的原創藝術理想浸潤下,改編研究擱置媒介的殊異性,而將互文性視域下的文本忠誠度視為核心切入點,導致電影改編長期被視為原創文學(或藝術)的附屬品。[3]
媒體融合大潮之下,電影在與新媒體的交互過程中成了被改編之物,電影改編產品也成了數字時代影像消費的重要內容。伴隨著數字媒體的快速擴張和觀眾參與度的顯著提高,融合文化場域內的電影改編獨立性和創造性愈發增強。一方面,數字媒介渠道的擴張要求電影文本自我解構以滿足新媒體環境的消費需求,從而在數字場域內重新對接多元化的觀眾群體;另一方面,觀眾參與度的提高使得電影文本在數字媒體環境中被反復重塑,數字技術賦能的自下而上的改編實踐深刻挑戰電影文本的原初形態。琳達·哈琴(Linda Hutcheon)因此強調,文本和媒介在電影改編研究中同等重要,因為觀眾必須通過媒介感知文本的跨媒介傳遞,乃至參與特定文本內容的改寫;媒介之于改編的重要性不應在以文本為中心的等級窠臼中被忽視,當代電影改編研究面臨“媒介轉向”這一重大課題。[2](xii)
若如此,電影改編在融合文化場域內當被如何重新檢視?其文本和媒介交互機制有何特征?數字媒介賦能的電影改編呈現形式如何?帶著這些問題,本文從電影改編理論的嬗變出發,基于科斯塔斯·康斯坦丁尼德斯(Costas Constandinides)的“附改編”(para-adaptation)理論框架,探索融合文化場域內電影改編的文本和媒介交互問題。本文認為,媒介殊異性解構了傳統改編模式中源文本與改編文本的從屬關系,以忠誠性為基礎的改編倫理被擱置。媒介殊異性和文本互文性共塑的“附改編”機制催生了“文本—附文本”交雜的改編文本形態,“作者—用戶”共棲的主體性體認,以及“電影—新媒體”共生的融合媒介身份。
一、 從“改編”到“附改編”:數字時代電影改編的“文本—媒介”再平衡
據英國改編研究協會(Association of Adaptation Studies)資料顯示,電影改編的系統性研究可追溯至1957年喬治·布魯斯通(George Bluestone)的著作《從小說到電影》(Novels into Film)。然而,對電影改編的討論遠早于此。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當電影語言尚未完全走向成熟之時,活動影像“第七藝術”地位的建構和維系仰賴文學的庇蔭。質言之,對文學作品的改編賦予早期電影這一“新”媒體藝術的嚴肅性和合法性,以克羅德·奧當-拉哈(Claude Autant-Lara)導演的同名小說改編電影《紅與黑》(Le Rouge et Le Noir, 1954)為代表的文學改編作品成為“質量的傳統”(tradition of quality)。[4]
電影和文學藝術地位的等級差異,使得敘事忠誠性成為電影改編價值的重要評價標準。安德烈·巴贊(André Bazin)認為,電影對文學作品的改編主要存在以下兩種模式。[5]一方面,文學作品賦予電影非常詳細的故事梗概,電影不僅需要遵照文學作品的角色塑造和情節設置,而且需要體現出原著的氣氛或詩意;另一方面,電影僅從文學作品中抽取部分人物原型和情節要素,其整體的角色塑造和情節設置與原著相去甚遠,甚至超出文學作品的束縛成為獨立的敘事要素。但無論何種改編模式,敘事忠誠性始終被視為早期電影改編價值的衡量標尺。[2](1-3)
吊詭的是,隨著電影語言的日漸成熟,以敘事忠誠性為核心的電影改編倫理既不能呼應電影藝術對更高獨立性的追求,也不能滿足文學作品捍衛其藝術權威性的需要——電影改編逐漸淪為“不登大雅的權宜之計”。[5](86)就文學領域而言,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早在1926年就批評道,羽翼未豐的電影不可避免地將文學簡化呈現為一種新興的視聽藝術產品,這種簡化使得電影成為僭越文學的“寄生蟲”,而文學則成為被僭越的“犧牲品”。[6]而就電影領域而言,喬治·阿爾特曼(Georges Altmann)贊揚非文學名著改編的《漫游者》(The Tramp,1915)和《總路線》(The General Line,1929),宣稱“這才是電影”。[5](85)及至1958年,法國電影俱樂部聯盟主席、《電影》(Cinéma)期刊編輯皮埃爾·比拉德(Pierre Billard)以《四十個四十歲以下導演》(Forty under Forty)為題,批評20世紀50年代法國電影市場的繁榮完全依賴高投資的歷史小說改編電影和好萊塢商業電影,轉而鼓勵年輕一代導演革新電影美學傳統,以提升電影本身的藝術價值。[2](xxii)可見,文學賦能的改編使得電影在藝術場域內分得一片棲息地之后,語言體系的不斷完善和美學獨立的自覺促使電影藝術重新審視電影改編的價值。
隨著電影藝術地位的逐漸穩固,電影改編中“文學—電影”等級化的身份認知亟待被打破,20世紀中葉(后)結構主義符號學的繁盛恰好為二者關系的“再確認”開辟了道路。(后)結構主義符號學認為,任何文本均由其他文本引用、拼貼而來,文本的存在并不具有絕對的原創性和自主性。當然,此處“文本”指涉羅蘭·巴爾特(Roland Barthes)所謂的“text”而非“work”——前者為開放的意義生成結構,后者為封閉的作品實體。[7]基于新的“文本”概念,(后)結構主義理論框架為20世紀上半葉電影改編的藝術獨立性和依附性爭論成功解圍。
首先,任何文本在一個更為寬泛的互文場域內都是參考和引用其他文本的產物,電影改編中的文學和電影雖有“被引”和“引用”之別,但二者均是其他文本交雜的結果。文本形成機制所自帶的“非原創性”使得電影與文學之間的改編關系并不意味著文學較之于電影擁有“原創”的優越感。基于文本建構機制,“原創”聚焦于符號編碼的獨創性,正如文學作品轉變為電影作品必然經歷由文字符號向視聽符號、文學符碼向視聽符碼的轉變。正是這種編碼的獨創性使得現代改編理論認為,電影改編擁有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謂的“靈韻”特質。其次,電影對文學的改編只是電影文本生成機制的一種,電影美學體系的漸趨成熟使得電影與文學的文本聯系不足以威脅電影藝術的獨立性。更為重要的是,電影的語言體系本身即囊括了多樣的藝術符碼,其與文學或其他藝術的文本聯系具有內生性。正如符號學家克里斯汀·梅茨(Christian Metz)在《心理分析和電影:想象的能指》(Psychoanalysis and Cinema: The Imaginary Signifier)一書中所指出的,電影符號體系分為電影編碼(cinematic codes)和非電影編碼(non-cinematic codes)兩個大類。它們囊括了定義電影所需的特殊編碼(如“攝像機移動”和“連續性剪輯”)、與其他藝術形式共享的編碼(如“小說的敘事”和“繪畫的視覺模擬”)以及社會文化編碼(如“性別角色”)。[8]由此,電影改編從“敘事中心”轉向“文本中心”,“文學—電影”的等級差異被打破,二者在(后)結構主義文本理論體系中實現身份平等。
自20世紀80年代數字媒體崛起和90年代互聯網飛速發展以來,電影的內涵和外延逐漸被數字化所浸染,成為數字時代融合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強調:首先,融合文化并非新媒體取代舊媒體,而是新媒體和舊媒體的共存和相互影響。新舊媒體的交互生成了新的影像文本,并建構了新的影像生產、消費和解讀模式。新媒體成為電影的容器,電影及其要素正是在新舊媒體間的流轉過程中被改編。其次,新舊媒體的交互作用不僅基于媒介本體差異生產新文本,而且影響受眾對文本的生產、使用機制。[9]數字化使得文化生產和參與具有更大的開放性,傳統“作者—讀者”二分的身份認知正在參與式文本消費模式中被挑戰。觀眾(或曰“用戶”)既是電影改編的消費者,又是其參與者。最后,數字化加速了全球資本和文化要素的相互流動,而資本對文化生產、傳播和市場結構的控制愈加緊密。以美國“媒體特許經營權”(media franchising)為代表的資本運作模式,自上而下將跨媒介的文化生產模式標準化、常態化;而更為松散的資本運行模式(如抖音與愛奇藝合作推出的“#抖音二創激勵計劃”)以更為靈活的方式推動電影自下而上的跨媒介改編。
電影改編往往具有跨媒介的特征,但傳統改編研究對文本載體的媒介屬性關照不多。數字時代的到來不斷沖擊著我們對作者身份、媒介與消費者關系、消費者與生產者關系的傳統認知,它推動電影改編突破“文本中心”這一固有模式以回應數字媒體環境下的電影改編新模態。2013年,學者科斯塔斯·康斯坦丁尼德斯提出“附改編”這一基本的話語范式,用以替代傳統改編研究的案例比較研究方法,并處理新媒體所承載的文化交互形式問題。[10]"“附改編”將數字技術賦能的“民間創造性”(vernacular creativity)納入改編范疇,用以觀照高端文化和產業體系掌控下的美學和經濟結構之外的文化實踐,即互聯網時代的參與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參與式文化裹挾著“民間創造性”進入到電影的跨媒介改編,解構了結構主義互文性視域下電影改編理論的文本身份認知。互文性強調文本間的引用關系,鼓吹任何文本都是由其他文本要素拼接而成的“馬賽克式”文本。與之相對,附文本則強調文本間的伴隨關系,指涉非作者主體(如編輯、出版商和觀眾)圍繞特定文本生產的衍生性外圍文本(如標題、題詞、序言、注釋和后記)。參與式的文本生產打破了互文本和附文本之間的界限——以短視頻“電影解說”為代表的電影跨媒介呈現形式不僅“引用”源電影的文本要素(如電影畫面和原聲)以重構電影敘事,而且針對電影文本及其參與主體發表“評論”。可見,互文本和附文本共同形塑了電影“附改編”的文本身份。學者杰弗里·斯康斯(Jeffrey Sconce)將這種用碎片化電影要素進行文本“再書寫”的模式稱為“附電影”(paracinema)——“附電影”雖然吸納了電影原片的文本要素,但因其文本身份和結構的混雜性不再成其為電影,而是基于電影文本生產的跨媒介視聽文化產品。[11]
綜觀電影改編實踐和理論的發展歷程,融合文化場域內的電影改編正在經歷從“文本中心”走向“文本—媒介雙中心”的歷史性轉變,媒介、文本并舉的電影改編理念不僅對傳統電影改編機制進行糾偏,更將矛頭直指數字時代電影在互聯網生態中的跨媒介生產、消費和解讀樣態。
二、重復、再生產及改換意圖:融合文化視域下電影改編的媒介生態和文本構建
電影文本的“附改編”揭示了(后)現代記憶的雙重邏輯:文化記憶被悄無聲息地重復、再生產、改換意圖,以維護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原創性神話和創造力權威。正如文化記憶學者阿斯特莉特·埃爾(Astrid Erll)所指出的那樣,電影在新舊媒體間的流轉即為文化記憶復現的一種方式,它能夠且正在被用于緩解媒介環境變化所帶來的記憶焦慮。[12]然而,“再媒介化”卻不能取代“改編”在探索電影跨媒介呈現模態領域的主導性,前者雖然集中凸顯了電影改編的跨媒介性,但忽略了參與式文化對電影文本的創造性重塑。融合文化場域內的電影改編實踐,其文本的重構和媒介載體的轉換是同時進行的,強行分離媒介和文本有破壞對象認知整體性的風險——“改編”概念的“媒介轉向”因而具有必要性。
那么,融合文化場域內電影“附改編”所服膺的媒介生態具有何種特征?
首先,數字媒介分發機制的專門化、自動化和精確化。數字化浪潮打破了傳統媒體間的壁壘,并使之融合于互聯網這個龐大的數字空間之內。由此,觀眾擁有通過統一的媒介通道同時觸及多樣媒體信息的潛力。然而,“伴隨著智能傳播技術和各類信息平臺的同步繁榮,一個事實變得越來越清晰:更豐富的人際連接并不必然帶來更多元的文化選擇,更多樣的傳播渠道也并不必然意味著更高級的‘用戶自主’”。[13]常江和狄豐琳指出,如今的數字信息生產由高度分散的非專業機構或普通用戶完成,信息分發活動日益與生產活動剝離,最終演變成一種相對獨立的信息實踐。獨立的信息分發體系仰賴于數字技術賦能的大規模收集、處理和使用用戶行為數據的能力,海量數據收集和處理的高門檻不可避免地帶來數字壟斷(或曰霸權),信息生產、流通和消費的功利性傾向也就愈加明顯。與此同時,數字媒介分發機制的專門化進一步仰賴數字工具的深度介入,后者將進一步侵蝕信息制造者和發送者的信息主導權。數字工具深度介入的主要特征是信息分發的自動化:海量信息的處理已非人力所為,只有引入基于機器學習的智能推薦算法才能實現不經人力干預而直接完成對信息的分發和處理工作。“智能推薦算法以海量的數據為依托,能夠超越時間、地域和人口統計學等因素的制約,實現針對個體用戶興趣偏好、消費習慣和生活需求的精準信息分發”。[13]質言之,數字媒介分發機制的專門化早已精準侵入了微觀層面的個體生活,它在數據分發維度引導和控制用戶的信息生產、傳播和消費行為。
其次,信息接收者身份從“大眾”向“用戶”流轉。數字技術的深度介入,使得信息生產、流通和消費全產業鏈趨向平面化;而數字革命所帶來的大眾化浪潮,開啟了數字工具人人可用的新紀元。正是數字技術的賦能使得“大眾”得以參與信息生產、流通和消費等流程,“大眾”成了信息生產者、傳播者和消費者的集合體。此時,“大眾”的內涵超越了經典5W模式和“編碼—解碼”框架的桎梏,成為今天廣為人知的“用戶”。有學者認為,數字媒體場域內“大眾”向“用戶”的轉變,催生了“流行審美的私人化”“社會交往的原子化”和“身份認同的流動化”。[13]在融媒體的智能內容分發網絡之中,每個用戶都能夠接觸到且被束縛于不同的審美趣味社群。此種私人化的審美經驗缺少傳統影視文化的統攝,審美的公共性因此在分散的社群中被解構。基于私人化的審美趣味,“用戶之間‘聯結’的實現則有賴于一致的審美品位,這就導致用戶對視聽文本所做出的情感反應成為(基于審美品位的)趣緣群體形成的基礎”。[14]顯然,“支配這種交往模式的,并不是新的結構化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而是一種被互聯網規則,尤其是流媒體的技術可供性所建構的原子化力量”。[15]盡管趣緣群體的形成依然仰賴成員相近的“品位”,但“前數字時代”群體身份的宏大指示符(如國族、階級、性別、代際等)早已喪失其統治力。審美的私人化和社會交往的原子化強調了高度流動、異質的日常生活經驗和具體的社會歷史語境的重要性,使得數字視聽用戶身份認同的流動性極為突出。
再次,文化資本霸權下產業互文(industrial intertextuality)的濫觴。自電影誕生以來,以廣播、電視、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相繼挑戰電影的市場地位,它們稀釋電影在消費者中的影響力,又迫使電影媒體自我進化以維持其市場主導性。然而,除去電影自身形態的演變,資本在利益的驅使下亦可調和電影與新媒體的相互關系,于媒體形態之外促成視聽文本在多元媒體框架中自由流轉,最終實現新舊媒體的互利共榮。資本的介入出發于版權,落腳于以美國“媒體特許經營權”為代表的壟斷經營模式。以好萊塢為例,特許經營權的介入使得其電影和電視節目中充斥著重復利用的故事、角色、場景;影視畫面、角色也不斷出現在玩具、服裝、新媒體產品等消費模態中。這種受到商業利益驅動,依賴于預先測試成功的材料,通過重復、改造的過程制造新的產品以保障商業利益成功的文化生產方式即為“產業互文”。 [16]“產業互文”的資本運營模式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文化要素在強力資本的支持下得以在不同的媒介、社群、消費場景中流通,一定程度上滿足不同社會群體對多元文化形式的消費需求。另一方面,知識產權保護下的特許經營權賦予特定人士或公司處置特定文化要素的權利,文化生產主體沉迷于對特定文化要素的壟斷經營無法自拔,更為多元的創造力被排除在版權所有者之外。近年來,好萊塢電影的原創性在特許經營權的侵徹下遭受重創,以至于美國電影協會(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不得不出臺“原創性評級”(“O”或“Original”),以鼓勵觀眾和制片方接受和制作更為原創的影視產品。隨著中國文化產業版權意識和執法力度的不斷提升,特許經營權的運營模式同樣影響著文化產品的跨媒介流轉。以抖音“二創”為例,中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協會于2019年1月發布《網絡短視頻平臺管理規范》和《網絡短視頻內容審核標準細則》,要求短視頻平臺履行版權保護責任,不得未經授權自行剪切和改編電影、電視劇、網絡電影、網絡劇等各類視聽文化產品。參見網址: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0110/c1001-30513562.html,2023-10-3。以2022年7月19日“抖愛”(抖音和愛奇藝)合作為代表的跨平臺聯合,為原創影視作品和短視頻“二創”間的鏈接打開了方便之門,但大量的短視頻“二創”仍因版權問題游走于法律法規的灰色地帶。
顯而易見的是,無論數字媒介分發機制的專門化、自動化和精確化,還是文化資本霸權下的產業互文,電影的跨媒介改編已經成為融合文化的核心要素和重要表征。客制化的媒介分發機制細分受眾群體,即使相同的影像產品也需要利用差異化的營銷模式和文本形態滿足異質化的受眾需求;而文化資本霸權下的產業互文則依托版權壟斷地位,將已經取得成功的影像IP通過不同的媒介渠道傳播給多樣的消費者,以期實現利潤的最大化。更為重要的是,信息接收者身份從“大眾”向“用戶”的流轉直接賦予了更為廣大的社會群體進行影像生產的能力,影像文本的生產方式變得更為原子化,影像文本的呈現形態和美學表達則更為私人化。總之,三者均昭示著當今影像文本生產的“用戶中心”原則,正是“用戶”的多元化決定了電影跨媒介改編的快速擴張。
當下融媒體平臺的內容生產早已被UPGC模式所統治,這些融媒體平臺不僅幫助大眾文化進行自上而下的信息傳播,也推動了“民間創造性”自下而上的內容分享。就電影而言,以Youtube、抖音、bilibili乃至微博為代表的流媒體平臺成為電影“附改編”的重要場所。流媒體平臺用戶通常缺乏資本和技術設備,因而無法像專業的影像生產主體(如“好萊塢”)那樣統一地、廣泛地傳播他們所生產的“附電影”產品,但他們創造性的改編活動可以而且經常成為源文本的重要補充。相較傳統電影改編模式,參與式文化孕育的“附改編”作為數字時代電影跨媒介改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數字賦能下“大眾創造性”蓬勃發展的產物。它滿足了當今受眾在新媒體環境中的觀影需求,回應了電影在新媒體生態中拓展其影響力的現實需要,最終將電影的跨媒介改編從亞文化空間帶到了大眾文化場域之內。
三、參與式文化場域中的電影“附改編”實踐:激進的媒介和保守的文本
“附改編”的繁榮揭示了一個基本事實:職業媒體從業者對電影制作及其改編的壟斷權利在數字時代被打破。數字賦能的現代觀眾已經不再滿足于被動接受視聽信息,而是主動參與到視聽文本的創建和重構中去,以將他們的主體性帶入傳統的視聽文本之中。杰弗里·斯康斯認為,“附改編”生產的“附電影”展現了由時尚的觀眾所組成的“游擊隊”與由專業電影從業人員所匯成的“正規軍”之間的文化戰爭。在這場戰爭中,數字技術賦能的“附改編”逐漸成為電影文化中的一股顛覆性力量。[11]與參與主體和媒介載體的劇變相對,舊媒體(電影)內容在數字媒體中被廣為引用和傳播,其跨媒介重復、再生產和改換意圖實踐呈現出明顯的文化記憶復現特征。于是,“激進的媒介”和“保守的文本”共同建構了當今電影“附改編”的基本實踐模式。
基于當下的電影“附改編”實踐,以短視頻、播客和微博為代表的擁有龐大的用戶群體和便捷的數字編輯功能的新媒體平臺是電影“附改編”的主陣地。在差異化的媒體平臺之中,電影被“附改編”為短小精悍的視聽文本、音頻文本以及圖文文本等文化產品,從而為不同應用場景、用戶需求和媒體環境中的受眾群體提供多元的數字影像消費模態。
短視頻是電影“附改編”的核心視聽文本形式。21世紀初,以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為代表的移動互聯網終端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小屏影像消費時代正式到來。2010年,4G網絡標準TD-LTE正式確立,移動互聯網帶寬的革命性提升進一步賦能移動影像消費市場。其中,肇始于2011年的短視頻平臺無疑成為小屏時代大眾影像消費的核心場景之一。職業媒體人和短視頻用戶所建構的UPGC內容生產模式,生產了龐大的“附電影”內容。從2005年自由職業者胡戈的《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到bilibili“鬼畜”專區,再到以抖音平臺“毒舌電影”為代表的短視頻“電影解說”,互聯網場域內的電影“附改編”不僅擺脫了“亞文化”和“叛逆”的標簽,而且進入到大眾影像消費的前沿。
綜觀抖音短視頻平臺的“電影解說”,其本質仍是對電影文本敘事內容和角色設置的“重述”。當電影被縮編成為幾分鐘至十幾分鐘不等的短視頻作品,電影片段或原聲被廣泛引用,多樣的非原片素材被混合嵌入,最終形成了互文本和附文本交織的短視頻“電影解說”形態。與奉文本忠誠性為圭臬的傳統電影改編模式不同,短視頻對電影的“附改編”強行拆解原有的影像編碼結構,使得影像回歸到語言缺失的早期電影狀態。因此,短視頻“電影解說”不得不引入早期電影所依賴的第三方敘事介質——“旁白”,以保證改編影像敘事的連貫性和整體性。以抖音平臺UP主“毒舌電影”改編的《大紅燈籠高高掛》(1991)為例,男聲旁白一邊基于女主角頌蓮的視角介紹電影劇情,一邊分析大宅門里四位太太之間的明爭暗斗。參見網址:https://v.douyin.com/iRKkxcpS/ W@Z.MJ 03/11 mQx:/,2023-12-3。雖然少量電影原聲被引入,但旁白主導著短視頻的敘事節奏。于是,碎片化的影像成為文字視覺化的載體,最終呈現出文字大于影像的特點。可見,短視頻對電影的“附改編”復興了日本“活動弁士”(benshi)和歐美“電影講解員”(film lecturer)提供敘事信息和針對電影故事表達個人見解的傳統,將解說表演與銀幕表演有機結合的早期電影放映(接受)美學重新融入短視頻影像的消費生態之中。[17]
播客是電影“附改編”快速興起的音頻文本形式。相較飛速擴張的短視頻平臺,中國數字“播客”平臺雖然起步較早,但直到2020年才開始快速崛起。“‘播客’(podcast)概念源自廣播(broadcast)和蘋果音樂播放器(i Pod)兩個英文單詞的拆解與重組,是Web 2.0時代下數字技術、音視頻基礎、網絡技術與深度內容融合發展的產物。”[18]"“播客”誕生于2004年,2005年便傳入我國。“直到2015年,荔枝、喜馬拉雅FM、蜻蜓FM等各類音頻App紛紛崛起,中文播客行業初現勃興之態,隨著2020年3月中國第一款獨立播客App‘小宇宙’上線,中文播客元年正式到來。”[19]
學者許加彪和梁少怡認為,中國的數字“播客”既是一種全新的廣播形式,也指涉一種獨特的數字音頻文件。[19]一方面,“播客”基于互聯網、RSS(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架構的數字廣播技術不僅重塑了廣播生態的時空秩序,滿足用戶隨時隨地的收聽需求,而且允許用戶參與到內容制作和聲音發布的流程之中;另一方面,數字時代音頻內容市場細分機制逐漸成熟,“播客”與知識付費、有聲小說、有聲藝術、音頻直播等產品共同形成了龐大的數字音頻內容矩陣。
電影“附改編”是UPGC生產模式下“播客”內容的一種。“播客”平臺的電影“附改編”是短視頻電影解說的音頻版本,它同樣融合旁白和電影原聲,呈現出明顯的文本拼貼特征。以喜馬拉雅平臺UP主“經典國劇精講”對《城南舊事》的改編為例,英子在跨院找到了精神失常的秀貞,發現她正在喃喃自語:“小貴子,你怎么就不要媽媽了?”參見網址:https://xima.tv/1_enRmpA?_sonic=0,2023-10-18。此處,秀貞的獨白引入了電影原聲。參見網址: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7V411775Z/?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amp;vd_source=d84daf8bf877e72005314d342bf278aa, 2023-10-18。從旁白到電影原聲的過渡為觀眾指明了解說文本的拼接架構,揭示了電影敘事和廣播敘事的融合機制,突出了播客電影解說之于電影原片的跨媒介改編特征。
微博是電影“附改編”的重要圖文文本形式。就微博與電影的結合而言,全媒體時代電影的整合營銷和數字賦能的大眾影評是近年來學界關注的焦點。[20]然而,較少學者關注到微博作為一個文字、音頻乃至視頻交叉結合的文本場域,早已為電影的“附改編”埋下了種子。2007年,我國的嘰歪網、飯否網開辟了微博平臺,并推動微博的小眾化傳播;及至新浪微博的快速崛起,微博成為大眾自我記錄的平臺,并以“說說”“狀態”“嘮嘮”“博客”等多樣形式呈現。[21]"“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網絡觸角的無限延伸、網絡受眾的全階層覆蓋,為電影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播映平臺、更大眾的藝術語境、更活躍的商業運作模式。”[21]于是,電影制作者紛紛上網,在微博平臺宣傳電影作品、再造電影文本和延伸電影影響力。
以金馬獎紀錄片導演周浩為例,其于2012年7月6日至2022年9月28日發表了關于其紀錄片作品《大同》的一系列微博,至今可見的微博共計17條。參見網址:https://weibo.com/u/1680894595,2023-10-9。考察微博內容,導演周浩不僅轉發關于《大同》的新聞報道、觀眾反饋和訪談活動,而且上傳了紀錄片影像,并持續追蹤紀錄片中角色(如前大同市市長耿彥波、退休工人老馬)的生活或工作經歷。這些離散的文字、圖片和視頻為紀錄片《大同》提供了豐富的附文本,觀眾不僅可以觸及紀錄片未能呈現的背景故事,而且可以了解到紀錄片完成后特定角色后續的生存經驗。質言之,微博和紀錄片所共有的對現實的記錄特性,使得新的附文本要素(如背景故事和角色經歷)不斷豐富和延展《大同》的核心敘事,它們在微博這一媒體場域內建構了新的文本敘事空間。于是,微博的圖文元素超脫了傳統的宣發和批評功能,這些離散的附文本要素通過對紀錄片影像的改造和延展實現了電影文本的“附改編”。
“激進的媒介”和“保守的文本”的并置凸顯了短視頻、播客和微博等數字媒體的媒介殊異性。特定媒介因其技術特征而具備某些本質屬性,這些特殊屬性植根于其所在的媒介環境,并調節媒介環境與用戶行為之間的互動關系。[15]電影作為一種多媒體視聽文本,可以通過短視頻、播客以及微博等媒體平臺將其視頻、圖像、聲音和文字要素進行拆分和重新整合,以因應不同媒體平臺的技術框架和目標受眾,最終創造出與電影文本緊密相關且符合不同媒介環境需求的跨媒介文化產品。可見,多樣的數字媒體不僅催生了多元的影像文本形態,而且揭示不同媒介環境下受眾群體差異化的媒體使用行為。正是媒介殊異性和電影“附改編”的共棲共榮,凸顯了電影改編媒介轉向的當代價值。
四、結"語
融合文化背景下的電影“附改編”指涉電影改編理論從“文本中心”走向“文本—媒介雙中心”的歷史性轉變,媒介意識成為當今電影“附改編”的關注焦點。無論數字媒介分發機制的專門化、自動化和精確化還是文化資本霸權下產業互文的勃興,都意味著今天的大眾文化生產必須把用戶放在中心位置。而數字時代媒介選擇的多樣性則決定了大眾文化產品必須能夠進行跨媒介呈現,以在不同的媒體終端和使用場景對接異質化的用戶。與此同時,數字賦能的用戶能夠便捷地消費、生產和傳播數字文化產品。隨著數字媒體平臺的爆發式繁榮,參與式文化得以挑戰專業媒體從業者的壟斷地位,“民間創造性”進一步將“附改編”從亞文化空間推向了大眾文化消費的前沿。
融合文化場域內的電影“附改編”平臺至少具有以下兩種核心特質:龐大的用戶群體和便捷的視聽文本編輯功能。數字媒體平臺的零散用戶難以跟大眾媒體平臺比拼優質視聽產品的生產力,但卻可以借由大眾視聽文化產品的“再書寫”實現較高質量視聽文化產品的生產。因此,融合文化場域內的電影“附改編”雖然聚焦于數字媒體這一全新媒體空間,但電影與數字媒體之間直接的內容交換卻昭示著跨媒介內容生產的相對保守性。當然,“附改編”的這一特性無疑引發了版權危機,需要我們理性看待。
參考文獻:
[1] Stam, R.(2005).Introduction: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daptation.In Stam, R.amp; Raengo, A.(eds.).Literature and film:A guid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ilm adaptation.Oxford: Blackwell, 1-52.
[2] Hutcheon, L.(2006).A theory of adaptation.New York amp; London: Routledge.
[3] MacCabe, C.et,al.(2011).True to the spirit:Film adaptation and the question of fidelit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Neupert, R.(2007).A history of the French new wave cinema.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5] [法]安德烈·巴贊.電影是什么[M].崔君衍,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7:85.
[6] Woolf, V.(1926).The movies and reality.New Republic, 47: 309.
[7] Barthes, R.(1977).Image-music-text.Translated by Stephen,H.New York: Hill amp; Wang.
[8] Metz, C.(1982).Psychoanalysis and cinema:The imaginary signifier.London: Palgrave.
[9] Jenkins, H.(2006).Convergence culture: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0] Constandinides, C.(2013).Para-adaptation: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convergence culture.Adaptation, 6(2): 143-157.
[11] Sconce, J.(1995).“Trashing” the academy:Taste, excess and an emerging politics of cinematic style.Screen, 36(4): 371-393.
[12] Erll, A.(2011).Memory in culture.Translated by Sara,B.Young.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3] 常江,狄豐琳.從智能分發到“審美繭房”:數字時代的文化公共性反思[J].中國出版, 2023(14):3-10.
[14] Clough, P.T.(2008).The affective turn:Political economy, biomedia and bodies.Theory, Culture amp; Society, 25(1): 1-22.
[15] 常江,田浩.間性的消逝:流媒體與數字時代的視聽文化生態[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12):137-145.
[16] Herbert, D.(2017).Film remakes and franchises.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7] Gunning, T.(1999).The scene of speaking:Two decades of discovering the film lecturer.Iris, 27: 67-80.
[18] 馮菊香,耿叔豪.人文類博客節目的用戶收聽動機研究——基于喜馬拉雅平臺用戶評論的考察[J].新聞大學,2023(7):101-116,121.
[19] 許加彪,梁少怡.播客復興:聽覺媒介社交化發展的價值優勢與理性反思[J].新媒體, 2023(3): 103-105,112.
[20] 陳旭光,盧茜.論2011—2012賀歲檔影片的“整合營銷”[J].當代電影,2012(4):11-14.
[21] 柴玥.網絡影評新形態——微博影評的特性[J].當代電影,2011(10):152-154.
[責任編輯:華曉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