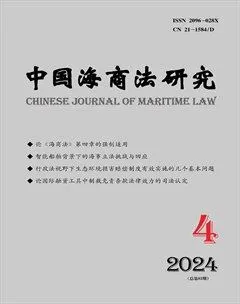海上封鎖法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困境、演進與融合
摘要:以色列與加沙地區存在持久武裝沖突的現實,尤其是“馬維·馬爾馬拉”號事件誘發海上封鎖法在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下的爭論與困境。海上封鎖中交戰團體承認制度的形成、不同歷史時期各國實施海上封鎖的實踐,乃至海上封鎖習慣法的編纂與逐漸發展,昭示著海上封鎖法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順應了武裝沖突法的發展趨勢。第三國能否容忍由于實施海上封鎖導致對海洋航行自由的干涉或阻礙,構成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下實施海上封鎖的關鍵和挑戰。區域化不僅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政治現象,而且成為確保未來的海洋制度達成全球性協議的一種較優路徑。為此,海洋區域主義構建了應對上述挑戰與困境的可行性模式,其實質屬于海上封鎖法在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中的融合性適用。
關鍵詞:海上封鎖;非國際性武裝沖突;“馬維·馬爾馬拉”號事件;交戰團體承認制度;海洋區域主義
中圖分類號:D99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2096-028X(2024)04-0026-11
收稿日期:2024-05-07
基金項目:2018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軍民融合戰略下海上通道安全法治保障研究”(18ZDA155),2022年度浙江省新型重點專業智庫——寧波大學東海戰略研究院自設課題一般項目“海洋安全與海洋合作研究——以海事區域協同為視角”(DHZL22YB03)
作者簡介:周明園,女,法學博士,上海大學期刊社《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編輯,上海大學法學院南方研究中心研究員。
海上封鎖作為一種傳統的海上作戰方式,廣泛地出現在各類不同規模的戰役中。海上封鎖具體表現為一國通過捕獲封鎖區域內的船舶,阻斷封鎖區域內的交通,進而實現控制海權、贏得戰爭的目的。由于封鎖的實施嚴重干擾海上交通和貿易,隨著中立制度的確立和保護中立國通商權利的普遍共識的達成,海上封鎖法在封鎖國主張某種權利和中立國對此表示接受或拒絕的緊張關系下逐步發展起來。【Michael G. Fraunces,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Blockade:New Guiding Principles in Contemporary State Practice,The Yale Law Journal,Vol.101:893,p.893(1992).】1856年的《巴黎會議關于海上若干原則的宣言》(簡稱《巴黎海戰宣言》)作為第一部國際海上武裝沖突法公約,明確了封鎖的實效性原則。【《巴黎海戰宣言》共4條,其中第4條規定,封鎖必須具有實效性,即必須由一支真正足以阻止進入敵國海岸的部隊所維持。】1909年的《倫敦海戰法規宣言》針對封鎖的通知、維持以及實施范圍等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規定。【具體可參見《倫敦海戰法規宣言》第一章“戰時封鎖”中第1條至第21條的規定。】盡管《倫敦海戰法規宣言》最終由于英國的反對并未生效,但其中的主要規則為海上封鎖習慣法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參考。【Ian Kennedy,Practice Makes Custom:A Closer Look at the Traditional Law of Naval Blockade,University of Toronto Faculty of Law Review,Vol.70:10,p.19(2012).】1994年的《圣雷莫海上武裝沖突國際法手冊》(簡稱《圣雷莫手冊》)是當代第一部完整的海上武裝沖突期間軍事行動指南,雖然不具備條約的法律效力,但其中有關海上封鎖的規則很大程度上因已成為國際習慣法而產生普遍的拘束力。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由于國家利益、民族斗爭以及政治分歧等原因,各類規模的武裝沖突依舊活躍,海上封鎖這一作戰方式也同樣未能退出歷史的舞臺。與此同時,海上封鎖的作戰實踐呈現出一種逐漸跨入非國際性武裝沖突門檻的趨勢。由于包括海上封鎖法在內的海戰法規長期被認為是國際武裝沖突法的一部分,現有的規則似乎很難約束游離在國際性武裝沖突之外的實踐。【參見周明園:《海上封鎖國際規則研究》,華東政法大學2021年博士學位論文,第86頁。】然而,目前形成的海戰法律體系并不完全與國際人道法相一致,《日內瓦四公約》
《日內瓦四公約》是指《1949年8月12日關于改善戰地武裝部隊傷者病者境遇之日內瓦公約》《1949年8月12日關于改善海上武裝部隊傷者病者及遇船難者境遇之日內瓦公約》《1949年8月12日關于戰俘待遇之日內瓦公約》《1949年8月12日關于戰時保護平民之日內瓦公約》(簡稱《日內瓦第四公約》)。及其相關議定書主要聚焦國際人道法在非國際性武裝沖突情境下的適用,但是并沒有徹底觸及海上封鎖法如何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的問題。在某種角度上,作為一種作戰手段和措施的海上封鎖,其實施與第三國的海洋航行自由和貿易自由等制度密切相關。故此,就海上封鎖法如何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展開探究,在全球仍存在局部武裝沖突的環境下,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一、海上封鎖法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的困境
(一)“馬維·馬爾馬拉”號事件
周明園:海上封鎖法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困境、演進與融合
為了對哈馬斯政權對以色列領土發動的襲擊實施反擊,2009年1月,以色列公開宣布對加沙地區實施海上封鎖。以色列主張海上封鎖是國際武裝沖突法中允許的一項措施,同時是防止武器、彈藥、恐怖分子和其他物資進入加沙地區的必要手段。【The Public Commission to Examine the Maritime Incident of 31 May 2010,The Turkel Commission,2010,p.53.】2010年5月31日,土耳其籍船只“馬維·馬爾馬拉”號在以色列實施海上封鎖的海域附近航行,意在突破封鎖以向加沙提供幫助。【The Public Commission to Examine the Maritime Incident of 31 May 2010,The Turkel Commission,2010,p.142,278.】由于拒絕聽從以色列方面的警告并拒絕改變航向,以色列國防軍登臨“馬維·馬爾馬拉”號,雙方發生了嚴重的武裝沖突,最終導致“馬維·馬爾馬拉”號一方9人喪生。【The Public Commission to Examine the Maritime Incident of 31 May 2010,The Turkel Commission,2010,p.15-16.】“馬維·馬爾馬拉”號事件引起以色列和土耳其方面的高度重視,兩國分別進行了全面的調查。土耳其和以色列的調查結論存在較大分歧:前者認為封鎖是非法的,以色列國防軍在登船時使用了過度的武力;【Report on the Israeli Attack on the Humanitarian Aid Convoy to Gaza on 31 May 2010,Turkish 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quiry,2011,p.63.】后者則認為封鎖符合國際法的規定。【The Public Commission to Examine the Maritime Incident of 31 May 2010,The Turkel Commission,2010,p.278-279.】在此基礎上,聯合國秘書長組織成立了以新西蘭前總理帕爾默為首的專家小組,就事實和法律問題出具了《帕爾默調查報告》。《帕爾默調查報告》認可以色列實施封鎖的合法性,但同時指出以色列對“馬維·馬爾馬拉”號上的人員使用了過度的武力。【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s Panel of Inquiry on the 31 May 2010 Flotilla Incident,UN,2011,p.4.】“馬維·馬爾馬拉”號事件引發的法律爭議焦點在于以色列針對加沙進行海上封鎖的合法性。就海上封鎖的實施要件看,具體包括以色列是否公告了海上封鎖的實施范圍和時間、海上封鎖是否屬于一種相應的軍事手段、海上封鎖的實施是否對加沙地區的平民產生了不成比例的影響、這一手段是否構成對加沙地區平民的集體懲罰,等等。【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s Panel of Inquiry on the 31 May 2010 Flotilla Incident,UN,2011,p.44.】此外,鑒于加沙特殊的法律地位,有關雙方武裝沖突的法律性質,即能否認為以色列和加沙之間存在國際性武裝沖突存在較大爭議,這也引發了有關海上封鎖法能否及如何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中的爭鳴。
(二)以色列與加沙的武裝沖突:海上封鎖法是否得以適用?
以色列與加沙之間的武裝沖突是否能夠適用海上封鎖法,受制于武裝沖突的定性。
1.事實性武裝沖突之存在
首先應予以明確的是,以色列和加沙之間存在事實上的武裝沖突。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在“塔迪奇案”中指出:“每當國家間訴諸武力或政府當局與有組織的武裝團體之間或一國境內此類團體之間長期發生武裝暴力時,就存在武裝沖突。”【Prosecutor v. Dusko Tadic a/k/a“DULE”,Decision on the Defence Motion for Interlocutory Appeal on Jurisdiction,IT-94-1-AR72,2 October 1995,para.70.】這在此后成為衡量武裝沖突存在與否的權威論斷。鑒于加沙缺乏構成主權國家的要件,加之二者之間的沖突并未發生在一國國境之內,以色列和加沙的敵對行為是否構成武裝沖突,取決于哈馬斯是否構成有組織的武裝團體以及二者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的武裝暴力。一方面,哈馬斯是一個有組織的武裝團體,能夠組織大規模的武器運送并一直試圖擴大其軍事勢力范圍。另一方面,以色列與加沙之間敵對行為的強度和持續性滿足長期武裝暴力的要件。根據以色列的數據,2005年至2009年哈馬斯持續向以色列發動炮彈和火箭彈襲擊,僅2008年就高達3 278次。【The Public Commission to Examine the Maritime Incident of 31 May 2010,The Turkel Commission,2010,p.92.】數十萬以色列平民生活在受襲擊地區,人員傷亡及物質損失慘重。【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s Panel of Inquiry on the 31 May 2010 Flotilla Incident,UN,2011,p.39-40.】可見,以色列和加沙的武裝暴力行為完全構成事實上的武裝沖突。
2.武裝沖突性質之爭議
以色列和加沙之間的武裝沖突構成國際性武裝沖突,抑或非國際性武裝沖突?這是令人困惑的問題。
以色列最高法院主張應將沖突定性為國際性武裝沖突進而適用國際人道法、海上封鎖法的相關規定,【The Public Commission to Examine the Maritime Incident of 31 May 2010,The Turkel Commission,2010,p.47-48.】而土耳其則指責以色列一貫否認巴勒斯坦在國際法上的任何權利但卻根據國際武裝沖突法中的交戰權為其自身實施的海上封鎖進行辯護。【Report on the Israeli Attack on the Humanitarian Aid Convoy to Gaza on 31 May 2010,Turkish 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quiry,2011,p.62-63.】根據《日內瓦四公約》共同第2條的規定,公約適用于兩個或兩個以上締約國間所發生的一切經過宣戰的戰爭或任何其他武裝沖突,加沙并未構成國家實體的客觀事實是其與以色列的沖突構成國際性武裝沖突的最大障礙。
然而,也有評論者認為,該沖突屬于國際性武裝沖突,主要依據如下。其一,跨越邊境。以色列認為由于武裝沖突發生在以色列邊境以外,因而根據以色列最高法院的以往判例主張將此定性為國際性武裝沖突,【The Public Commission to Examine the Maritime Incident of 31 May 2010,The Turkel Commission,2010,p.47-48.】但鑒于以色列將其與黎巴嫩真主黨在黎巴嫩境內發生的武裝沖突默認為非國際性武裝沖突,【The Public Commission to Examine the Maritime Incident of 31 May 2010,The Turkel Commission,2010,p.49.】這影響了以該因素衡量武裝沖突性質的說服力。此外,美國國防部的《戰爭法手冊》認為非國際性武裝沖突應僅根據當事方的地位被歸類,即使有時未發生在一國內,也僅僅是范圍上的國際性武裝沖突,而不是性質上的國際性沖突,【Law of War Manual,Department of Defens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23,p.1041.】即武裝沖突的定性應取決于性質而非范圍。誠然,根據《日內瓦四公約》共同第2條及《1949年8月12日日內瓦四公約關于保護非國際性武裝沖突受難者的附加議定書(第二議定書)》[簡稱《日內瓦四公約附加議定書(第二議定書)》]第1條第1款,【《日內瓦四公約附加議定書(第二議定書)》第1條第1款規定:“本議定書……應適用于為《1949年8月12日日內瓦四公約關于保護國際性武裝沖突受難者的附加議定書(第一議定書)》所未包括、而在締約一方領土內發生的該方武裝部隊和在負責統率下對該方一部分領土行使控制權,從而使其能進行持久而協調的軍事行動并執行本議定書的持不同政見的武裝部隊或其他有組織的武裝集團之間的一切武裝沖突。”】必須承認對國際性與非國際性武裝沖突概念上的區分包含了領土的因素,但僅憑這一因素并不足以界定武裝沖突的性質。在辨明武裝沖突性質的問題上,其實質不在于沖突發生的地理位置,而在于沖突方的身份。【Douglas Guilfoyle,The Mavi Marmara Incident and Blockade in Armed Conflict,The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Vol.81:171,p.186(2011).】其二,占領。占領應發生在兩國之間,以色列對加沙的長期有效控制的狀態使二者的沖突被劃入國際性武裝沖突的范疇。但是,加沙是否仍被以色列占領是一個值得懷疑的問題。一方面,土耳其認為以色列對加沙領土邊界的控制使以色列沒有喪失或放棄其有效控制加沙的各種核心要素,具體包括人員和貨物從加沙進出以色列,人口登記、貨幣制度、稅收和海關安排以及郵電通信等方面的管控。【Report on the Israeli Attack on the Humanitarian Aid Convoy to Gaza on 31 May 2010,Turkish 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quiry,2011,p.42.】此外,以色列最高法院承認,基于武裝沖突的現實情勢,以色列有義務向加沙提供燃料、電力等補給,保障平民生存所需的糧食和基本的人道主義物資,【The Public Commission to Examine the Maritime Incident of 31 May 2010,The Turkel Commission,2010,p.50.】這也成為土耳其主張以色列占領加沙的有力佐證。另一方面,由于以色列已經失去對加沙的永久軍事權力及對民選政府的控制,更為普遍的觀點認為以色列已經不再是加沙的占領國。【The Public Commission to Examine the Maritime Incident of 31 May 2010,The Turkel Commission,2010,p.47-48.】以色列最高法院指出:“自2005年9月以來,以色列不再有效控制加沙地帶的局勢。過去在這一領土上實行的軍事統治因政府的一項決定而結束,以色列士兵不再長期駐扎在該領土上,他們也不再負責那里發生的一切。”【The Public Commission to Examine the Maritime Incident of 31 May 2010,The Turkel Commission,2010,p.50-53.】《陸戰法規和慣例章程》第42條規定:“領土如實際上被置于敵軍當局的權力之下,即被視作被占領土。占領只適用于該當局建立并行使其權力的地域。”據此,筆者認為,由于“外國軍事力量存在于被占領土”這一要件已不再具備,以色列不再為加沙的占領國。事實上,即便存在占領,占領國與非國家武裝行為者之間的沖突也不等于國際性武裝沖突。《日內瓦第四公約》第6條表明,可將國際性武裝沖突視為始于軍事占領之時,但對于軍事行動全面結束后仍可以持續實施的軍事占領,該條款的核心在于明確占領期間公約的適用。【《日內瓦第四公約》第6條規定:“本公約應于第2條所述之任何沖突或占領開始時適用。在沖突各方之領土內,本公約之適用,于軍事行動全面結束時應即停止。本公約在占領地內之適用,于軍事行動全面結束后一年應即停止;惟占領國于占領期間在該國于占領地內行使政府職權之限度內,應受本公約下列各條規定之拘束:……”】可見,軍事占領后的敵對行動并不必然引發國際性武裝沖突,【Douglas Guilfoyle,The Mavi Marmara Incident and Blockade in Armed Conflict,The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Vol.81:171,p.184(2011).】占領也并非構成國際性武裝沖突的充分條件。由此,跨越邊境和占領兩個要素,均不能成為衡量以色列與加沙是否存在國際性武裝沖突的有效論據。
3.能否適用海上封鎖法之爭議
傳統海上封鎖法能否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存在爭議。就“馬維·馬爾馬拉”號事件中海上封鎖法的適用而言,土耳其和以色列兩方同樣未能達成一致立場。土耳其方面否認了《圣雷莫手冊》的適用,主張《圣雷莫手冊》旨在適用于國際性武裝沖突,尤其在那些允許實施海上封鎖等可能影響第三方國家海上行動的規則方面,《圣雷莫手冊》僅僅體現出針對國家間武裝沖突的被視為國際習慣法的條約或慣例。因此,《圣雷莫手冊》中授權在公海上實施海上封鎖等規則,如捕獲中立船只的相關規定等,不能被視為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的國際習慣法。【Report on the Israeli Attack on the Humanitarian Aid Convoy to Gaza on 31 May 2010,Turkish 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quiry,2011,p.61.】與之相對的是,以色列方面提交的報告在假設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的沖突具有國際性質的基礎上,審查了對加沙實施和執行海上封鎖的條件。以色列認為其與哈馬斯的沖突難以分類,因而在以色列的軍方行動中,遵守國際人道法應屬重要準則。鑒于哈馬斯對加沙的實際控制程度,其構成的重大安全威脅,以及其企圖通過海上等途徑進口武器、彈藥和其他軍事用品,即使以色列和加沙之間的沖突被視為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以色列方面也會考慮適用有關實施和執行海上封鎖的規則。【The Public Commission to Examine the Maritime Incident of 31 May 2010,The Turkel Commission,2010,p.49-50.
】與此同時,《帕爾默調查報告》指出,加沙作為一個獨特的案例,不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重復。“馬維·馬爾馬拉”號事件中,雖然以色列和加沙之間存在事實上的武裝沖突行為,但對這一行為的定性存在爭議。盡管如此,考慮到哈馬斯對加沙的有效控制以及對以色列事實上的威脅,很難將二者之間的沖突定義為純粹的國內事務,雙方的沖突具有國際性武裝沖突的全部特征。鑒于海上封鎖通常是在存在國際性武裝沖突的情況下實施的,因此,就海上封鎖法的適用而言,應將其視為國際性武裝沖突。【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s Panel of Inquiry on the 31 May 2010 Flotilla Incident,UN,2011,p.41.】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海上封鎖法能否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未有明確定論。鑒于針對雙方武裝沖突法律性質的界定缺乏共識,海上封鎖合法性的認定仍然以以《巴黎海戰宣言》為基礎形成的海上封鎖相關規則為依據。在當代國家實踐中,就能否以海上封鎖作為國家內部制裁手段這一問題并沒有形成一致的立場。【James Farrant,The Gaza Flotilla and the Modern Law of Blockade,Naval War College Review,Vol.66:81,p.94(2013).】就以色列方面的結論和《帕爾默調查報告》的措辭而言,二者均是在考慮了武裝沖突規模的情況下適用海上封鎖法,這并不等同于得出非國際性武裝沖突必然可以適用海上封鎖法的結論。可見,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中海上封鎖法的適用面臨困境。
二、海上封鎖法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的演進:從國家實踐到習慣法的編纂
(一)理論淵源與早期實踐:海上封鎖措施中交戰團體承認制度的形成
交戰團體承認制度為國際武裝沖突法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提供了理論淵源,并在海上封鎖的典型實踐中得到印證。
1.交戰團體承認制度的理論淵源
通常而言,針對武裝沖突的不同程度,非國際性武裝沖突往往被劃分為叛亂、暴動、交戰三個層級。【Rob McLaughlin,The Law Applicable to Naval Mine Warfare in a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 Series,Vol.90:475,p.481(2014).】叛亂是指一國內部武裝分子短期、輕微的暴動,是針對合法政府的一種零星的挑戰。【Anthony Cullen,Key Developments Affecting the Scope of Internal Armed Conflict i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Military Law Review,Vol.183:66,p.69(2005).】由于叛亂規模較小,叛亂團體很難獲得交戰團體的地位,此類沖突理應由國內刑法予以管轄,并不會涉及主權國家在國際法上的權利和義務問題。與叛亂相比,暴動的程度更加嚴重,是嚴重威脅政府穩定、危害社會秩序的有組織武裝暴力,【James G. Randall,Constitutional Problems Under Lincol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51,p.60.】這種程度的沖突會導致其他國家在界定其與暴動團體的關系時享有一定自由。對暴動團體的承認創造了一種事實關系,即暴動者與外部國家之間的法律權利和義務只有在基于方便、人道和經濟利益而明確承認和商定的情況下才存在。【Rob McLaughlin,The Law Applicable to Naval Mine Warfare in a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 Series,Vol.90:475,p.482(2014).】因此,暴動也成為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三個層級中法律性質最為模糊的一種沖突形式。交戰則是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下規模最大、級別最高的表現形式。客觀而言,被承認為交戰團體應該滿足以下幾個條件:一是國家內部必須存在著內戰和普遍敵對行為的狀態;二是非國家武裝行為者占領并在某種程度上有秩序地管理著相當大的一部分國家領土;三是非國家武裝行為者應當在一個負責當局指揮之下有組織地實施敵對行為并遵守作戰規則;四是必須存在使外部國家通過承認交戰團體的方式明確其態度的必要性條件。【Hersch Lauterpacht,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47,p.176.】可見,武裝暴力的嚴重程度及非國家武裝行為者的性質是決定交戰團體是否獲得承認的主要因素。倘若非國家武裝行為者實際占領部分領土、能夠在客觀上遵守戰爭法規則、沖突雙方具備相當的武裝實力彼此抗衡,【Konstantinos Mastorodimos,Belligerency Recognition:Past,Present and Future,Connecti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29:301,p.303-304(2014).】交戰團體承認制度的意義即是賦予此種事實上的武裝沖突狀態相應的法律地位。此時,沖突雙方的交戰權利得到其他國家的普遍認可,國際武裝沖突法也得以適用。
2.海上封鎖實踐中交戰團體承認制度的證成與流變
交戰團體承認制度的實踐源自美國內戰中的海上封鎖行動,交戰團體承認制度也正是在這一實踐中得到了國際法學界的普遍認可和重視。1861年4月19日,美國總統林肯宣布封鎖所有美國南方的港口。這一海上封鎖措施的實施不可避免地嚴重影響到英國等國家的海洋利益。于是,英國政府通過中立聲明承認美國南方地區的交戰團體地位。受此影響,很多歐洲國家紛紛效仿英國宣布了中立政策。一些權威的國際法學者認為,英國和其他歐陸國家的行動獲得了國際法的認可和支持,因此,對交戰團體的承認是合法有效的。【Wyndham Legh Walker,Recognition of Belligerency and Grant of Belligerent Rights,Transactions of the Grotius Society,Vol.23:177,p.187(1937).】與此同時,盡管聯邦海軍力量的稀缺和海岸線的廣闊所帶來的挑戰令人質疑封鎖的有效性,但是,從一個更加務實的角度考慮,歐洲的中立國家仍然認可了聯邦海軍實施封鎖的合法性。【James Kraska,Rule Selection in the Case of Israel’s Naval Blockade of Gaza:Law of Naval Warfare or Law of the Sea?,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Vol.13:367,p.389(2010).】這是海上封鎖行動中交戰團體承認制度的雛形。在實踐的證成下,該制度成為包括海上封鎖法在內的國際武裝沖突法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的重要切入點。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禁止使用武力及武力威脅成為國際法基本原則,也為國際武裝沖突法重新書寫范式。盡管非國際性武裝沖突時有發生,但交戰團體承認制度的應用逐漸式微,原因如下。一是交戰團體承認制度的應用缺陷。“作為國家的公共行為,承認是一種選擇性的政治行為,在這方面不存在任何法律義務。”【[英]伊恩·布朗利:《國際公法原理》,曾令良、余敏友等譯,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81頁。】可見,即便滿足客觀要件,是否給予承認也完全取決于母國或外部國家的自愿,這就導致這一制度在實踐中的應用并非基于客觀標準,而是取決于外部國家出于政治立場、外交戰略、國際局勢等因素作出的主觀選擇。這必然會影響法律適用的準確性和公正性。【對此的典型實踐是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內戰。對比其他國家在美國內戰中的克制,針對西班牙內戰中外國商船在地中海遭受攻擊的事實,英國、法國等國家并未允許“西班牙紛爭的任何一方行使交戰權利或干涉商船在公海上的航行”。參見《尼翁協定》前言。】二是《日內瓦四公約》體系的影響。《日內瓦四公約》是最早明確國際武裝沖突法能夠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的國際條約。【《日內瓦四公約》共同第3條規定:“在一締約國領土內發生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之場合,沖突之各方最低限度應遵守下列規定:……”】《日內瓦四公約》體系的形成使得國際武裝沖突法直接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成為可能,考慮到其作為習慣國際人道法的普遍適用性,以及《日內瓦四公約附加議定書(第二議定書)》相較于交戰團體承認制度所具有的較低的適用門檻,國際武裝沖突法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法的規范模式被極大地改變了,導致交戰團體承認制度在戰后衰退。三是受限于《聯合國憲章》的制約。《聯合國憲章》下的不干涉內政原則作為國際法基本原則,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尊重。故此,由于不滿足客觀事實情況下的承認可能構成對發生內亂的國家的內政的非法干涉,國家實踐往往更傾向于通過放棄對交戰團體的承認來踐行不干涉內政原則。此外,在禁止使用武力及武力威脅原則的加持下,交戰團體的承認將國際法未加禁止的非國際性武裝沖突與戰爭狀態聯系在一起,也極易引起國際社會的強烈反應,觸發國家政治、外交上的巨大風波。上述原因共同導致交戰團體承認制度的適用銳減。
有鑒于此,有學者認為交戰團體承認制度在當代已不再是一個有效的法律概念。【Douglas Guilfoyle,The Mavi Marmara Incident and Blockade in Armed Conflict,The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Vol.81:171,p.191-194(2011).】然而,各國不愿意將承認交戰團體的法律后果付諸實踐,并不意味著交戰團體承認制度失去了其生命力。【Wolff Heintschel von Heinegg,Methods and Means of Naval Warfare in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Israel Yearbook on Human Rights,Vol.42:55,p.77-78(2012).】一方面,《日內瓦四公約》體系與交戰團體承認制度是并行不悖的。后者的存在是“處理與國際性武裝沖突更為密切相關的罕見內戰的獨特手段”。【Yair M. Lotsteen,The Concept of Belligerency in International Law,Military Law Review,Vol.166:109,p.123-124(2000).】由于承認的標準非常嚴格,在此類罕見的情況下,應向交戰團體提供國際法所允許的最大保護。另一方面,海上封鎖法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的主要障礙在于不能明確非國家武裝行為者是否有權利干擾中立船的航行自由,而外部國家對交戰團體的承認則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路徑。換言之,在“除非中立國明示或暗示交戰權,否則非國家武裝行為者不能干預中立船舶”的理念下,【Phillip J. Drew,The Law of Maritime Blockade:Past,Present and Fu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116.】交戰團體承認制度的適用仍然是當代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中海上封鎖合法化的重要理由。【Konstantinos Mastorodimos,Belligerency Recognition:Past,Present and Future,Connecti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29:301,p.316(2013).】總結而言,在現有的國際法框架下,盡管交戰團體承認制度在實踐中應用較少,但這一傳統理論淵源為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中海上封鎖的實施者設置了基本的門檻,確保叛亂分子不得以發動戰爭為借口實施叛國和海盜等違法行為,同時為潛在的交戰團體提供了與武裝沖突程度相稱的交戰權利以及獲取外部國家認可的可能途徑,仍具有相當的現實意義。
(二)逐漸發展:海上封鎖法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的習慣法編纂
早在1584年,荷蘭聯合政府對西班牙港口實施了海上封鎖。西方海洋強國先后實施了“虛擬封鎖”“巡洋艦封鎖”“全行程禁區”以及“船舶安全區”等海上封鎖措施。1856年《巴黎海戰宣言》確立了海上封鎖時效性原則,直至1899年的第一次海牙和平會議,海洋大國開始對海戰方法、海戰秩序以及海戰中的人道主義保護問題進行法律編纂。【參見馬得懿:《海洋法律秩序生成:歷史脈絡、法治困境與海洋法權》,載《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第4頁。】晚近以來,國際社會開始關注海上封鎖法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的習慣法的編纂。這是因為,國際社會日益意識到,國際性與非國際性武裝沖突的劃分不應該成為海上封鎖能否予以適用的唯一標準。從根本上說,劃分兩類武裝沖突的原因是為了避免給予非國家武裝行為者任何公認的地位,爭議的焦點往往在于是否給予反叛分子戰俘地位,能否使反叛分子免于國內的刑事起訴等。【Norm Lubell,Extraterritorial Use of Force Against Non-State Acto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103.】然而,就海上封鎖的實施而言,劃分兩類武裝沖突的意義體現得并不明顯。“馬維·馬爾馬拉”號事件中,各方均未對以色列與加沙之間的武裝沖突進行明確的定性,但這并不妨礙海上封鎖法的適用。事實上,“馬維·馬爾馬拉”號事件表明,在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中適用海上封鎖法可以免去分析加沙法律地位這一問題的困擾。盡管海上封鎖起源于國際性武裝沖突,但海上封鎖的適用、國家實踐和法律確信都導致了其向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中的遷移。【James Kraska,Rule Selection in the Case of Israel’s Naval Blockade of Gaza:Law of Naval Warfare or Law of the Sea?,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Vol.13:367,p.392(2010).】
將海上封鎖法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的國家實踐存在先例。20世紀中葉以來,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中的海上封鎖行動并不罕見。除“馬維·馬爾馬拉”號事件外,1954年至1962年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戰爭期間,法國在地中海建立了廣泛的封鎖區。【Wolff Heintschel von Heinegg,Methods and Means of Naval Warfare in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Israel Yearbook on Human Rights,Vol.42:55,p.60(2012).】1983年至2009年斯里蘭卡內戰期間,斯里蘭卡政府軍針對泰米爾伊拉姆猛虎組織部署了相當規模的海上封鎖。【Wolff Heintschel von Heinegg,Methods and Means of Naval Warfare in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Israel Yearbook on Human Rights,Vol.42:55,p.61(2012).】2006年,以色列在與黎巴嫩真主黨發生武裝沖突期間同樣實施了海上封鎖。2015年至今,也門內部持續發生武裝沖突,引發了沙特聯軍實施的封鎖行動。【Yemeni Civil War,Britannica,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Yemeni-Civil-War.】上述一系列海上封鎖措施均被視為實施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中。
有鑒于此,作為國際海上武裝沖突法中習慣法的重要載體,《圣雷莫手冊》十分重視海上封鎖法的編纂,尤其關注新時期海上封鎖法的發展。《圣雷莫手冊》非常重視吸收《聯合國憲章》的基本精神,對交戰國能否對中立國船舶采取海上封鎖等手段給予關注。盡管《圣雷莫手冊》在編纂中存在不足,諸如其沒有明確非國際性武裝沖突情境下的法律適用問題,然而,通過對《圣雷莫手冊》相關條文的目的性解釋,《圣雷莫手冊》的編纂者考慮并寄希望于該手冊下的海上封鎖相關規則能夠在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中得到貫徹和實施。《圣雷莫手冊》并未完全排除海上封鎖法在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中的適用。《圣雷莫手冊》第1條規定,海上沖突各方從動用武力之時起就受國際人道法原則和規章的約束。同時,《圣雷莫手冊》對“海上沖突各方”的界定為其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的情境留下空間。對此,《圣雷莫手冊》的權威性解釋文本補充強調,從使用任何武力的那一刻起,適用法律的目的是確保限制敵對行動的進行,雖然該手冊的規定主要是為了適用于海上國際性武裝沖突,但第1條中故意沒有明確指出這一點,這可以避免在涉及海軍行動的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中阻止這些規則的執行。【Louise Doswald-Beck ed.,San Remo Manual on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to Armed Conflicts at Se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73.】在“馬維·馬爾馬拉”號事件中,以色列也認為《圣雷莫手冊》的規定邁出了有益的一步。【The Public Commission to Examine the Maritime Incident of 31 May 2010,The Turkel Commission,2010,p.48-49.】不僅如此,《圣雷莫手冊》也吸收了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簡稱《海洋法公約》)所創設的海洋區域主義路徑立法精神,提出“軍事禁區”等概念,【參見邢廣梅:《國際海上武裝沖突法的歷史演進——從1856年〈巴黎海戰宣言〉到1994年〈圣雷莫手冊〉》,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54頁。】這也為當前武裝沖突局勢下更為廣義的海上封鎖行動制定了規則。
從規則的適用角度考慮,在條約未能充分調整非國際性武裝沖突的情況下,國際習慣法應該發展為能夠指導諸多實踐的具體規則。“塔迪奇案”中法庭指出:“不可否認的是,習慣規則已發展成為管理內部沖突的規則。”【Prosecutor v. Dusko Tadic a/k/a “DULE”,Decision on the Defence Motion for Interlocutory Appeal on Jurisdiction,IT-94-1-AR72,2 October 1995,para.127.】在戰爭手段和方法方面,有關國際戰爭的規則和原則正逐步擴大適用于國內武裝沖突。此外,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在2005年發表的《習慣國際人道法研究》的報告中認為,幾乎所有的規則都適用于國際性和非國際性武裝沖突:“這項研究提供了證據,表明國際習慣法的許多規則適用于國際性和非國際性武裝沖突;國家實踐已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現有的條約法,擴大了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的規則。”【Jean-Marie Henckaerts amp; Louise Doswald-Beck eds.,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xxxv.】具體而言,從國際人道法角度考慮,當一國試圖鎮壓本國國民在本國領土上的叛亂時,允許其使用在國家間武裝沖突中被禁止使用的武器是十分荒謬的。【Prosecutor v. Dusko Tadic a/k/a “DULE”,Decision on the Defence Motion for Interlocutory Appeal on Jurisdiction,IT-94-1-AR72,2 October 1995,para.119.】在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中,遵守與戰俘有關的法律也有利于戰后恢復和平統一。【Yair M. Lotsteen,The Concept of Belligerency in International Law,Military Law Review,Vol.166:109,p.125(2000).】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國際性武裝沖突規則與非國際性武裝沖突規則之間的隔閡已經不再明顯。海上封鎖法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的演進進一步印證了上述論斷。
三、海上封鎖法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挑戰與應對
由此觀之,海上封鎖法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順應了國際武裝沖突法的發展趨勢。在某種意義上,國際性和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之間的法律差別已逐漸縮小。關鍵的問題并不是武裝沖突究竟是國際性,抑或是國內性,而是武裝沖突本身是否存在。【James G. Stewart,Towards a Single Definition of Armed Conflict i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A Critique of Internationalized Armed Conflict,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Vol.85:313,p.344(2003).】對于武裝沖突的事實而言,其規模程度、波及范圍、復雜性以及持續性等因素難免會影響法律的適用。海上封鎖法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的發展愈發呈現融合的趨向,這也是應對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中實施海上封鎖措施的必然選擇。
(一)海上封鎖與第三國的容忍度
就海上封鎖法在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交戰方之間的適用而言,一方面,由于存在交戰團體獲得承認的實踐的支持,一國政府宣布實施封鎖本身就暗含著對交戰團體的承認,海上封鎖法的適用并無太多障礙。此時,實施合法的封鎖應滿足公認的條件。這要求實施封鎖的一方有必要對所有的外國船只采取一定的強制措施;封鎖的實施還應該考慮人道主義精神,封鎖的唯一目的不是使平民忍受饑餓,實施封鎖對平民造成的傷害不應超過所預期的軍事效益。【San Remo Manual on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to Armed Conflicts at Sea,ICC Legal Tools Database(11 October 2008),https://www.legal-tools.org/doc/118957/pdf.】另一方面,作為合法的戰爭手段,非國家武裝行為者實施的封鎖同樣會引發海上封鎖法的適用。一旦非國家武裝行為者在其參與的海戰中控制了海岸線,表明其有能力對敵方建立和維持有效封鎖,就沒有理由認為這種事實上的能力是非法的。【Phillip Drew,The Law of Maritime Blockade:Past,Present,and Fu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119.】
海上封鎖法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并非完全等同于國際人道法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由此,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下海上封鎖法的適用仍舊面臨挑戰。其中,由于海上封鎖的實施極易對海洋秩序造成干擾,第三國(外部國家)對此的容忍度存在著不確定性,這是當前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下適用海上封鎖法的主要挑戰。實施海上封鎖時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下的第三國非常關注由此引發的海洋航行自由問題,進而衍生出如何協調海上封鎖導致的海洋航行自由障礙與第三國容忍度的問題。實踐表明,絕大多數國家都沒有承認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下交戰方干擾第三國航行自由的權利。歷史上,西班牙內戰背景下的《尼翁協定》明確表明其他國家不允許內戰雙方干涉航行自由的立場。面對其他內戰中所實施的海上封鎖措施,多數國家也基本持反對立場。故此,即便是非國家武裝行為者根據海上封鎖法建立了有效的封鎖,第三國對于非國家武裝行為者對海洋航行自由的干涉或阻礙的容忍度,亦成為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下海上封鎖的關鍵及挑戰。
(二)區域主義應對: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下海上封鎖與海洋航行自由的協調
區域化正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政治現象。承認海洋中特殊的區域性利益不僅合理,而且也是確保未來的海洋制度達成全球性協議的唯一可行辦法。【Lewis M. Alexander,Regionalism and the Law of the Sea:The Case of Semi-Enclosed Seas,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Vol.2:151,p.153(1974).】《海洋法公約》追求以“海洋區域主義”為理念的平時海洋合作體制。【參見鄭凡:《半閉海的海洋區域合作》,廈門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50頁。】為此,《海洋法公約》構建內水、領海、毗鄰區、用于國際航行的海峽、群島海道、專屬經濟區以及公海等區域。《圣雷莫手冊》十分重視利用《海洋法公約》對不同法律地位海域的界定展開“作戰區域”的編纂。對此,《圣雷莫手冊》的起草者們承認海上武裝沖突各方在許多場合、相關海域或空域建立了不同類型的區域,并據此拒絕或限制非交戰方的航行權和飛越權。這些區域被冠以“禁區”“軍事區”“隔離區”“戰區”或“行動區”等不同名稱。盡管有關海戰法的條約沒有系統討論過區域問題,但多數學者認為區域的存在是一個事實,應該對相關規則予以完善。【參見《圣雷莫海上武裝沖突國際法手冊》,任筱鋒、楊曉青譯,海潮出版社2003年版,第200-201頁。】
事實上,在充分吸收《海洋法公約》在海洋治理上的國際法治經驗與成就的基礎上,可以嘗試構建區域主義應對模式,以解決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下海上封鎖與第三國航行自由的沖突問題。區域主義應對模式應當充分顧及傳統武裝沖突法與作為平時海洋法的《海洋法公約》的相互融合與互動趨向,將海上封鎖法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引發的交戰方與第三國海洋航行自由利益的沖突,分別按照不同海洋區域予以協調。對于第三國而言,封鎖的實施的確妨礙了公認的海洋自由原則以及中立國的通商自由。然而,當平時和戰時的海洋自由以及中立國通商自由為國際社會所承認時,封鎖的例外限制也同時被視為是合法的。【參見[英]勞特派特修訂:《奧本海國際法》(下卷第二分冊),王鐵崖、陳鐵強譯,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251頁。】此時,戰時的海上封鎖法與平時的海洋法均會對封鎖的實施產生影響。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下海上封鎖與海洋航行自由之間沖突的區域主義應對,可以存在如下情境。
1.沿海國行使主權、主權權利以及特定事項管轄權的海域
根據《海洋法公約》,這類海域通常指內水、領海和毗連區以及專屬經濟區。專屬經濟區一向被認為是“自成一體”的海域,且《海洋法公約》對專屬經濟區的設定主要在于其經濟屬性,故此,專屬經濟區暫不予討論。通過對《海洋法公約》的適用和解釋,非國際性武裝沖突的敵對方在一國內水或領海實施封鎖并沒有太大的法律障礙。由于武裝沖突雙方的敵對行為發生在內水或領海,屬于一國主權所涉及的海域,因此,沖突各方并未被禁止在該國內水和領海內進行敵對行動。只要沖突各方不干涉其他國家的航行自由,就可以在這些海域針對對手采取海戰的方法和手段,包括實施海上封鎖措施。
非國際性武裝沖突的存在無疑構成干涉外國船舶在領海自由航行的正當理由。在此種情境下,第三國是否享有無害通過的權利?無論是條約法或是國家實踐都沒有跡象表明,一旦發生非國際性武裝沖突,無害通過權即自動中止。相反,一般的規則應繼續予以適用。非國際性武裝沖突的存在無疑對沿海國的安全構成威脅。根據《海洋法公約》第25條第3款,沿海國可暫時停止外國船舶在其領海的特定區域內的無害通過,只要這種暫停被正式公布。在這方面可以看出,對《海洋法公約》第25條第3款中提到的“武器演習”可作廣義理解。因此,沿海國當局有權暫停無害通過權,以防止外國船只在沖突地區附近航行。在確定暫停無害通過權是否對保護其安全至關重要時,沿海國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海洋法公約》第25條第3款規定:“如為保護國家安全包括武器演習在內而有必要,沿海國可在對外國船舶之間在形式上或事實上不加歧視的條件下,在其領海的特定區域內暫時停止外國船舶的無害通過。這種停止僅應在正式公布后發生效力。”】鑒于缺乏確鑿的國家實踐,尚不清楚是否可以在整個領海海域暫停無害通過。雖然這與《海洋法公約》第25條第3款“特定區域”的措辭相悖,但在特定的非國際性武裝沖突的情況下,政府可能認為有必要封鎖整個領海海域以維護海洋安全進而保障第三國的海域航行自由的權利。盡管如此,如果敵對行動僅發生于某一特定區域,政府就很難為其在遠離該區域的沿海海域暫停無害通過的行為辯護。此外,在當前實踐中,有關國家政府有權在其領海內實施海上攔截行動。在符合《海洋法公約》第33條的條件下,行動的范圍可擴至毗連區。例如,斯里蘭卡政府軍于1984年建立并實施的“海軍特別監視區”以及針對向泰米爾伊拉姆猛虎組織走私武器和物資的外國船只所采取的措施,在斯里蘭卡基線24海里范圍內所享有的普通海關和治安權力下被認為是合理的。【Douglas Guilfoyle,The Mavi Marmara Incident and Blockade in Armed Conflict,The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Vol.81:171,p.193(2011);Wolff Heintschel von Heinegg,Methods and Means of Naval Warfare in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Israel Yearbook on Human Rights,Vol.42:55,p.64(2012).】可見,在內水、領海乃至毗連區的海域內,平時國際法與戰時國際法的規定對實施封鎖的制約并無太大沖突。
2.國家管轄范圍以外的海域
典型的國家管轄范圍以外的海域當屬公海。此外,盡管專屬經濟區不屬于國家管轄范圍以外的海域,但由于《海洋法公約》對專屬經濟區的規制多體現為經濟方面的專有權利,若不考慮經濟屬性,從武裝沖突期間海上封鎖與海洋航行自由角度考慮,可以將專屬經濟區與公海一并討論。就公海和專屬經濟區而言,《海洋法公約》規定所有船舶在和平時期享有在公海和專屬經濟區的航行自由權。【參見《海洋法公約》第58條和第87條。】然而在武裝沖突期間,海戰法規則應該被置于和平時期的海洋法規則之上。【James Kraska,Rule Selection in the Case of Israel’s Naval Blockade of Gaza:Law of Naval Warfare or Law of the Sea?,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Vol.13:367,p.373(2010).】當然,即使存在國際性武裝沖突,根據《海洋法公約》的規定,沖突各方也有一項積極的義務,即適當顧及第三國所享有的海洋航行自由的權利。同時,禁止沖突各方破壞并非專門為沖突一方服務的海底電纜和管道。【San Remo Manual on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to Armed Conflicts at Sea,ICC Legal Tools Database(11 October 2008),https://www.legal-tools.org/doc/118957/pdf.】此外,如果在另一國的專屬經濟區內采取敵對行動,應尊重《海洋法公約》對沿海國經濟性權利的保障,海戰法和海洋法可以同時適用。
雖然國際武裝沖突法沒有禁止在此類海域內的敵對行動,但這能否同樣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則令人懷疑。對此,現有的國家實踐已經充分表明,沒有習慣國際法禁止非國際性武裝沖突當事方在公海和專屬經濟區內的敵對行為。顯然,就國家管轄范圍以外的海域而言,海上封鎖法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的主要問題是,即使有效的封鎖得以建立,第三國是否能夠容忍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中的敵對方對公海和專屬經濟區航行自由的干擾。筆者認為,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第三國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尊重武裝沖突規模的事實。與交戰團體承認制度的基本原則一樣,第三國僅限于在沖突程度已達到某種強度時,才有可能容忍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中的敵對方對航行自由的干涉。【Douglas Guilfoyle,The Mavi Marmara Incident and Blockade in Armed Conflict,The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Vol.81:171,p.194(2011).】
換言之,海上封鎖法能否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并非取決于沖突雙方的法律地位,而應取決于武裝沖突規模的事實。
3.容易實施海上封鎖的特殊海域
從實施海上封鎖措施的多發海域角度看,用于國際航行的海峽和群島水域屬于容易實施海上封鎖的特殊海域。用于國際航行的海峽和群島水域在武裝沖突中占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值得高度關注。根據《海洋法公約》的立法目的,很容易推斷出無論是沿海國,還是非國家武裝行為者,都無權干涉用于國際航行的海峽和群島水域的過境通行權和群島海道通行權。《圣雷莫手冊》認為,即使在國際性武裝沖突期間,交戰各方也有義務維持這些通行權利。【San Remo Manual on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to Armed Conflicts at Sea,ICC Legal Tools Database(11 October 2008),https://www.legal-tools.org/doc/118957/pdf.】在國家實踐中也沒有跡象表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的存在,將導致海峽沿岸國政府有權通過超越《海洋法公約》允許范圍的有關通行的法律和條例。尤其是,縱然非國際性武裝沖突情境之下存在導致航行或飛越有危險的局面,過境通行也不應予以停止。但是,海峽沿岸國或群島國的當局有義務妥為公布對航行或飛越有危險的任何情況。【參見《海洋法公約》第44條。】這隱含著就容易實施海上封鎖措施的特殊海域而言,海上封鎖法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的前提在于,其應該尊重《海洋法公約》框架下用于國際航行的海峽通行制度和群島海道通行制度,這實質上是一種海上封鎖法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的融合趨向。
四、結語
一方面,事實上,對于卷入武裝沖突的各當事方而言,要求其考慮行為可能產生的不同法律效果略顯荒謬。因為內部的動亂和國家間的沖突極有可能會迅速地互相轉換。【Ian Whitelaw,Internationalisation of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Perth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Vol.1:30,p.41(2016).】有鑒于此,海上封鎖法在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中的適用同樣應該基于封鎖的事實。當前國家實踐中,不可否認的是,一國可以對同該國發生武裝沖突的非國家武裝行為者實施封鎖。在這種情況下,海上封鎖法可以很好地平衡該國政府、非國家武裝行為者以及第三國的權利。
另一方面,非國際性武裝沖突的當事方沒有義務將武裝敵對行動局限于國家的主權范圍內,也可以使用包括海上封鎖在內的公認的海戰方法和手段。只要采取的措施對國際海上通道的航行自由和航空自由沒有不利影響,在海戰法和平時海洋法的框架下就沒有太大的法律障礙。可見,海上封鎖法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時,任何一方都無權干涉海洋航行自由和航空自由。面對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下海上封鎖引發第三國的容忍度問題,在《海洋法公約》奠定的國際海洋法治經驗基礎上,結合相關海戰習慣法的編纂和國家實踐,可以嘗試從海洋區域主義的角度來靈活應對。
國際法的本質是為了維護和平。在當前國際社會局部地區武裝沖突頻發的態勢下,國際武裝沖突法在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中的適用,核心意義不在于對國際性抑或非國際性武裝沖突的識別,而在于解決事實性武裝沖突爭端問題,并在殘酷戰爭面前盡可能地表達人道主義的立場,進而最終促進全人類的共同福祉。【參見劉春一、陳敬根:《〈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十一部分對國家責任規則的發展及中國因應》,載《中國海商法研究》2023年第3期,第34頁。】
The Law of Naval Blockade Applicable to the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
Dilemma,Evolution and Integration
ZHOU Mingyuan
(Periodicals Agency,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China)
Abstract:Naval blockade, as a traditional method of maritime warfare,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various battles of different scales.
Due to the serious disruption of maritime traffic and trade caused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lockade,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utral system and the general consensus on protecting the trade rights of neutral countries, the law of naval blockade gradually developed under the te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locking country’s claim of certain rights and the neutral country’s acceptance or rejection of them.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law of naval warfare, including the law of naval blockade, has long been considered a part of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 law, the existing rules seem to be difficult to constrain practices that operate outside of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 As for the current regulation of armed conflicts, more and more signs indicate that the gap between the rules of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 and that of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 is declining. In the context of frequent armed conflicts in certain reg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core significance of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 law in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 lies not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 but in the universality of resolving factual armed conflict disputes. Recently, the reality of the persistent armed conflict between Israel and Gaza, especially the “Mavi Marmara” incident, has triggered the controversy and dilemma of the law of naval blockade under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 The formation of the recognition system of belligerency in naval blockade, the practice of naval blockade implemented by various countri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the compilation and gradual development of the customary law of naval blockade, indicate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w of naval blockade to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 conforms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armed conflict law. On the one hand, in current national practice, parties to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 are not obliged to limit armed hostilities to the sovereignty of the state, and they may also use recognized naval warfare methods and means, including naval blockade. On the other hand, a country can impose naval blockade on non-state armed actors engaged in armed conflicts with that country. In this situation, the law of naval blockade can effectively balance the rights of the home country government, non-state armed actors, and third countries. The key and challenge of naval blockade under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 is whether the third country can tolerate the interference or obstruction of maritime navigation freedom caused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val blockade. Recently, regionalization has not only become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political phenomenon, but also a preferred path to ensure global agreements on future maritime systems. Therefore, maritime regionalism has constructed a feasible model to address the aforementioned challenges and dilemmas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which essentially belongs to the integration of the law of naval blockade applicable to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 Marine regionalism can be applied to specific situations, that is, in the waters of internal waters, territorial waters, and even adjacent areas, the provisions of the law of the sea and the law of naval warfare do not have much conflict regarding the constraint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blockades. In water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the law of naval warfare may be given priority in application, while in special sea area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law of the sea and the law of naval warfare should be respected simultaneously.
Key words:naval blockade;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Mavi Marmara” incident;recognition system of belligerency;marine region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