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妮亞和她的草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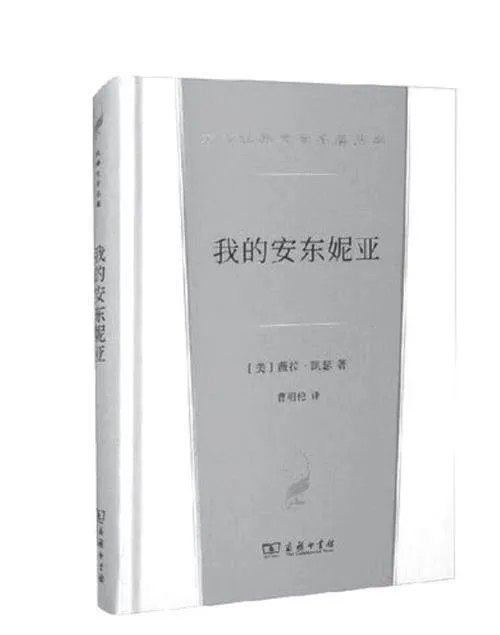
《我的安東妮亞》是美國著名女性作家薇拉·凱瑟的代表作之一。本文從生態批評和生態女性主義的角度對女主人公與自然的關系不斷變換的四個重要階段進行分析,從而揭示人與自然之間的緊密聯系,以便更加全面透徹地理解這部小說傳遞的生態思想。
薇拉·凱瑟是一位蜚聲美國文壇的女性作家,其創作生涯中的多部小說都受到讀者的廣泛歡迎和喜愛,其中以其本人所熟知的內布拉斯加州的大草原為背景的拓荒小說最為聞名。這些拓荒小說的女主人公們通常具有一種野性自然之美,她們深愛著自然,并能與之產生一種發自心底的共鳴。《我的安東妮亞》可謂凱瑟拓荒小說的集大成之作,充分展現了她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深刻思考。凱瑟在這部小說中濃墨重彩地描繪了主人公生長和生活的環境,淋漓盡致地展現了西部草原的大氣與柔美,她將主人公安東妮亞與她所生活和依戀的草原置于一張聯系緊密、生生不息的網中。在這張網中,安東妮亞和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響。安東妮亞生來便是大地之女,她在歷經滄桑后,最終回到了大地母親的懷抱,在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中實現了人生價值。
生態批評發端于20世紀70年代。1974年,美國學者密克爾撰寫的《幸存的喜劇:文學的生態學研究》一書中提出了“文學的生態學”這一術語,主張文學批評應當反映“人類與其他物種之間的關系”。生態批評是“在生態主義、特別是生態整體主義思想指導下探討文學與自然之關系的文學批評”,旨在批判二元對立和人類中心主義,意圖弘揚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在生態批評的基礎之上,生態女性主義自20世紀80年代應運而生。生態女性主義學者稱:“正如女性在父權社會里被統治和壓迫一樣,自然同樣在文明化和工業化的過程中遭受人類的侵害。女性和自然有許多共同點,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她們都有生產的能力。”女性通過哺育后代,自然通過繁育果實來維持整個地球的發展。同時,生態女性主義學者指出,造成這種壓迫的根源是以將事物分為自我和他者的二元模式的男性中心論。婦女之所以遭受壓迫是因為她們是之于男性的“他者”,自然之所以遭到貶斥是因為她是之于人類的“他者”。自然被女性化的同時,女性也在被自然化著。土地和女性的身體開始逐漸變為彼此的影像。女性和自然聯系的本質便是“女性化的他者”。生態女性主義者主張終結一切形式的壓迫,并強調如果不以人的力量去解放自然,一切為女性解放而付出的努力也將付之東流。
在《我的安東妮亞》中,自然環境發揮了重要作用——對安東妮亞產生影響并與之互動。安東妮亞的成長歷程形成了一個“自然—城鎮—自然”的軌跡。自始至終,她都與生于斯長于斯的草原有著深深的羈絆。這部小說中的大自然并不僅是故事發展的背景,更是女主人公不可或缺的精神動力的源泉。當安東妮亞生活在草原上,并與萬物和諧相處時,生活輕松而自由;一旦她對自然的態度發生轉變甚至遠離自然,不幸和挫折便會接踵而至。
本文將從生態女性主義的角度分析安東妮亞在人生各個階段與自然的關系,探討凱瑟在小說中體現出的生態整體意識和生態女性主義意識,并在一定程度上證實女性與自然的密切聯系,或從更深的層面上來看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密切聯系。
一、生于自然
凱瑟對安東妮亞這一形象的塑造是對其生態思想的生動詮釋。安東妮亞是與自然同體共生的“大地之女”,她“眼睛大而熱情,光閃閃的,就像陽光照射在樹林中兩口棕色的池塘上。她的皮膚也是棕色的,兩邊臉蛋上有一層深而濃的紅暈。她那棕色的頭發卷曲而看上去有點蓬亂”。安東妮亞的眼睛、皮膚和頭發都是棕色的,而棕色正是大地的代表色。這種微妙的聯系使安東妮亞成為大地女兒的化身。安東妮亞深深地愛著她所生活的土地,在她眼里,這片草原不僅是她的棲息地,更是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吉姆、安東妮亞以及她的妹妹一同來到溝壑的邊緣玩耍時,“風大得我不得不抓住頭上的帽子,吹得那兩個小姑娘的裙子前面翻了起來。安東妮亞似乎很喜歡這樣……她望著我,因為有些事她想說而不會說,急得眼睛閃閃發光。”自然給安東妮亞帶來了身心的愉悅,也賦予了她對生活的激情和對未來的向往。
安東妮亞與自然的相處方式生動地詮釋了凱瑟的生命共同體意識,在草原上,安東妮亞的“小我”和自然的“大我”融為一體,和諧共生。她珍視和深愛草原上的一切,無論是獾子、野兔還是獵狗,甚至一只小小的昆蟲。一天下午,當吉姆和安東尼亞躺在暖烘烘的崖壁上小憩時,一只螞蚱意外而至。她“合攏雙手給它做了溫暖的窩,用波希米亞語高高興興地愛撫地同它說話”。太陽落山時,由于擔心這個弱不禁風的小生命無法抵御襲來的寒氣,安東尼亞“小心翼翼地把這只綠色的蟲子放在她的頭發里,把她的大手帕松松地系在她的卷發上”。
與自然的相生相惜讓安東妮亞得以遠離外界干擾,促進了安東妮亞獨立自主的品格和健全人格的形成。在自然之中,父權社會的傳統和所謂的文明的影響相對微弱,這對安東妮亞形成正確的自我意識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她把自己看作一個獨立自主的人,而非“他者”。正因如此,她才成長為一個自尊且獨立的女人。大自然與安東妮亞在此階段相融相助,彼此成就。在自然之中,眾生平等,皆能找到歸屬。
二、“征服”自然
圣誕節后,不幸降臨到了雪默爾達一家:雪默爾達先生因無法忍受思鄉之苦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之后,生活的重擔落到了小安東妮亞肩上,她必須和哥哥一起下地干農活,安東妮亞周身散發著一種更加粗獷的氣息,原本柔和的野性之美已經蕩然無存。她穿戴著爸爸的靴子和皮帽,試圖使自己變得更加陽剛。“她整天把袖子高高卷起,她的兩臂和喉嚨口曬得黑黑的。她的頸子從兩肩之間茁壯地聳出來,猶如草根泥上戳出來的一根樹干。”她似乎并不滿足于做一個獨立的女孩兒,忽視自己身為女性的巨大力量,總是想憑著自己偽裝出的陽剛之氣與男人一決高下。與吉姆一見面,安東妮亞便帶著驕傲的神情向吉姆炫耀自己的勞動成果。
海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遜堅決反對人類征服和統治自然,她認為:“在自然這個大系統里,人類只是一個部分,是巨大生命鏈條中的一個環節。”與此同時,她指出:“我們還使用‘征服’這個詞。我們還沒有成熟到懂得我們只是巨大不可思議的宇宙的一個小小的部分。只有很少人意識到認識自然的一部分,意識到征服自然的最終代價就是毀滅人類自己。”對生態女性主義學者來說,女性特征和男性特征一樣重要,不得小覷。而此時的安東妮亞儼然成為一位充滿男性特征的女拓荒者,對自然的征服不僅會導致潛在的生態危機,更會將之輻射至人與人的關系之中,化身為“階級之間的征服控制,性別之間的征服控制,國家之間的征服控制和文化宗教之間的征服控制”。
安東妮亞對自然的態度也在這個時期發生了變化。她失去了往日對自然的尊重和保護,忽視了與自然之間的互動:她無暇欣賞自然的秀美,傾注力量在拓荒耕地之上;她急于征服和控制這片土地,正如男人急于壓迫與征服女人一樣。生態學者西格德·奧森堅稱:“與大自然之間關系的惡化所引發的不僅僅是物質與肉體上的傷害,它還可以導致人們自我意識的喪失和生活意義的迷失。”生態女性主義認為女性的命運與自然的命運息息相關,女性摒棄與自然的交流與互動便是摒棄了自身的幸福。
三、脫離自然
吉姆和祖父母移民到黑鷹鎮后,安東妮亞也來到了鎮上,成為哈林家的幫工姑娘。如此一來,安東妮亞遠離了自然,并與自然斷聯。起初,城鎮中的一切讓安東妮亞感到新鮮和刺激,熱鬧繁忙的生活讓她如同置身天堂一般快樂,甚至天真地認為她可以在這個新天地中獨立且快樂地度過自己的余生。
盡管黑鷹鎮如此之小,但傳統意識和觀念對它施加的影響卻大得驚人。與草原上截然不同,小鎮有著嚴格的等級劃分,男性占據絕對的主導地位。哈林一家是父權制社會的鮮明寫照,生動地詮釋了男性支配一切的局面。在家中,哈林先生儼然是俯視眾生的“國王”。“哈林先生那一套有點專制和唯我獨尊的味道。他走路也好,談話、戴手套、握手也好,總像一個感到自己有權有勢的人。”在這個以男性為中心的等級社會中,女性不可能被平等對待,更不可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和獨立。“城市和農村會造就不同類型的典型人格:城市會令人彰顯男性特征最壞的一面,使人變得自私自利并充滿攻擊性。”作為被小鎮視為“異類”的幫工姑娘,安東妮亞被哈林先生嚴禁參加舞會,險些被惡棍卡特暗算,甚至在懷上多諾萬的孩子之后,又慘遭他的欺騙和遺棄。
在這個遠離自然的小鎮,安東妮亞在男人的統治之下,陷入卑微與困頓的境地。
四、回歸自然
生態女性主義的觀點認為:“男性中心主義意識導致自然生態的失衡和環境的破壞,導致女性地位的卑微與生存的困境。人類必須走出這樣的困境,改變原有的對抗、征服的關系,才能重新建構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男女兩性之間的關系以及人際和諧的關系,重建一個倡導多樣性、整體性、以‘關愛倫理’為基礎的和諧社會。”在城鎮歷經種種不幸,安東妮亞意識到自己和草原的關系密不可分,認識到自己精神的支柱和力量的源泉正是包容萬物的自然。從城鎮回到草原,安東妮亞恢復了與自然的互動。在草原上,安東妮亞汲取力量并自我療愈,完成了社會化自我與自然自我的融合,為進一步的自我實現奠定了基礎。
凱瑟在小說中對二元對立和男性中心論進行了解構,在草原上,東妮嫁給了一個溫柔寬厚的男人,并先后哺育了十個孩子。與父權社會的典型婚姻不同,他們的婚姻建立在互相尊重和相互獨立的基礎之上。在家中,安東妮亞是果敢的“領航者”,是溫柔的妻子,也是優秀的母親。在與自然的良性互動中,安東妮亞重獲自由,在與自然的和諧共存和與丈夫的互尊互愛中實現了自我價值。多年后,吉姆到安東妮亞家拜訪,他發現安東妮亞已不再年輕美麗,但她身上仍有一種東西可以激發人的想象與激情。只要安東妮亞生活在這片她深愛的草原上,她的能量和熱情便會源源不斷、永不消失。作為一位母親,安東妮亞對自然有了更深的理解。和吉姆在果園散步時,她停在一棵蘋果樹前,摩挲著樹干說:“我愛它們,就好比它們是人一樣,我們剛來的時候,這兒一棵樹都沒有。一棵一棵全是我們種的,我們在田里干了一整天活兒以后,還經常提水來澆。”在安東妮亞眼里,這些果樹不僅僅是植物,更是與人類擁有同等地位的生命。人和自然和諧相處的極致便是如此。
重回自然懷抱,大地兒女終于獲得了幸福。正如安東妮亞對吉姆所說:“我在城市總是感到痛苦。我會寂寞地死去。我喜歡住在每一堆谷物、每一棵樹我都熟悉,每一寸土地都是親切友好的地方。”
五、結語
《我的安東尼婭》闡釋了兩個重要主題,其一是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其二是女性的自我實現。通過安東尼婭這一人物的塑造,凱瑟解構了二元對立中的人類中心主義和男性中心主義意識,實現了人與自然、男性與女性之間和諧共生的美好境界,折射出了凱瑟生態思想的光輝。安東妮亞在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中最終獲得獨立,實現了自我價值,這也正是生態批判所期望實現的理想境界。
作者簡介:范曉琳(1987—),女,漢族,河南焦作人,河南警察學院助教,研究方向為現當代英美文學、英語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