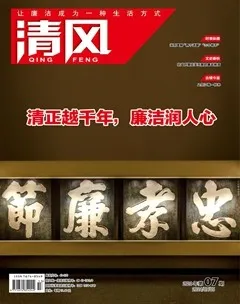陶澍:經世能臣的成長之路

陶澍是晚清經世派主要代表人物,為官清廉,政聲卓著,且其思想對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湘軍領袖影響頗深。張佩綸、張之洞在一起品評人物時指出:“道光以來人才,當以陶文毅(陶澍謚號)為第一。”
1779 年1 月17 日, 陶澍在湖南省安化縣小淹鄉陶家溪出生。與多數受母親影響成長起來的湖南籍歷史人物不同,陶澍受父親陶必銓影響至深。
陶必銓一輩子除了教書,沒干過別的行當。雖然蝸居在閉塞湖南、偏遠安化的一個深山老林的土房子里,一生也沒走出過湖南,但陶老先生野心不小,這從他給陶澍的取名可以看出來。陶澍,名澍,字子霖,號云汀。澍,即“及時雨”,霖,《左傳》解釋:“霖以救旱。”。汀,即“水邊綠洲”。
陶澍名字的來由與用意,陶必銓本人曾做過詳細解釋:“天下能蘇萬物者,莫如雨。戊戌之夏大旱,冬,谷驟貴,而長子適生,因命之曰:澍,字以子霖,蓋其有以澤蒼生也。”顯然,陶必銓寄望于陶澍將來做一個恩惠天下百姓的人物。
陶父其人
古話說,有其父,有其子。
陶必銓本人是個怎樣的人?
陶澍日后這樣描述父親:家君身材高大,英俊瀟灑。性格光明磊落,遇事有主見,無論利誘還是威逼,都不能動搖。他心地很坦誠,沒有城府,從不當面奉承人,一旦他人有過失,他一定會當面說出來,并且加上一頓痛罵,也不管對方權勢有多大。但罵完之后,就不記得了。他平時愛喝酒,喝得差不多了,必豪情滿懷,放言天下,聲震鄰居屋瓦。
寄望兒子將來能恩惠天下百姓,陶必銓當然希望自己早能如此。所以雖居窮鄉僻壤,陶必銓依然自強不息,孜孜追求功名,以期出人頭地。他讀起書來方法十分特別:同時擺開幾桌子書,一本一本全部翻開,將每本書的內容全部貫通起來,讀后做批語,“多前人所未發”。
陶必銓桌上擺的都是些什么書呢?經學。
經學泛指先秦各家學說要義。漢代獨尊儒術后,特指儒家經典,包括儒學十三經:《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谷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這是一種解釋字面意義、闡明蘊含義理的學問。
宋明兩朝,流行程朱理學、陽明心學。但“滿清異族”鐵騎入關,將沉醉于“修煉心性”的漢族讀書人打醒了。億萬華夏子民,竟然亡于只有幾十萬鐵騎的清朝異族,湖南鄉民心有不服。
蝸居安化小淹,山高皇帝遠的陶必銓,在痛苦中總結大明政權滅亡原因,結論是:“程朱理學”教中國士人“空談理心,不理實政”,導致明朝最終亡國。
他的這種看法,其時是一種比較流行的觀點。清朝初年,顧炎武也以思想家的眼界,一針見血地指出:“舍經學無理學。”
亡國之恥,理學之痛,讓陶必銓讀起經學。他是民間教書匠,散民一個,居地偏遠,自由生長,朝廷風氣力不能及。他每天繼續讀著經學,說著大話,懷著野心,也沒有人來管。當時的官員哪里有空去理會深山老林里一個常年連飯都吃不飽的窮教書先生的口出狂言呢?
父子求學
陶必銓自由自在地沉醉在經學的海洋里,他對“雜書”有著狂熱的興趣、瘋狂的追求。他將經學所追求的經國濟世的抱負,同時寄托到自己與兒子身上。懷著望子成龍的偉大夢想,陶澍七歲那年,陶必銓便帶上他,跋山涉水,來到岳麓書院求學。
作為一家之主,教書先生本就家徒四壁,陶必銓舍下父母、老婆,帶兒子背井離鄉求學,壓力可想而知。而且,當時陶家家底已經稀薄。讀書人家碰上盛世,平民百姓家庭有足夠的財力學文化,私塾先生自然衣食無憂;但國家經濟一旦衰落,平民百姓自身朝不保夕,私塾先生衣食往往無告,生計成為頭等大事。岳麓書院作為精英學府,學生讀書需自己帶米,書院每月補貼十錢銀子做蔬菜費。這點補貼,養不活父子倆。
但岳麓書院同時還有獎學金制度,每月由巡撫或學政來主持一次月考,考進前三名者,就能拿到獎學金。對陶必銓來說,獎學金就是求學金。為了能在岳麓書院這座讀書人的圣殿里待下來,他不管嚴寒酷暑,每天堅持讀到深夜,因此總能拿到獎學金。
求學機會來之不易,課余時間,陶必銓也不浪費,他與學友在岳麓山中找塊地方,坐下來對酒縱談,指點天下。小陶澍在邊上聽,似懂非懂。這樣堅持不到一年,因經濟實在過于窘迫,家庭難以維持,陶必銓被迫帶陶澍回到老家。但陶必銓已經心滿意足了,畢竟帶兒子去了長沙,見了回大世面,感受到了千年學府的讀書氛圍。想想看,偌大一個湖南省,多少鄉下讀書人畢生想進也進不去,而父子倆均實現夢想,不由做夢都覺得此生再無遺憾。
帶兒子回到陶家溪,陶必銓重新操起老本行,繼續教私塾。清朝辦私塾分兩種:在自家設館,叫私塾;上門去教,叫坐館。陶必銓人品好,又在岳麓書院深造過,當地有錢人家都爭著搶著聘請他去坐館。他每次坐館,都對東家特別要求要帶上兒子陶澍。
1790 年,陶必銓應邀到安化縣城(今梅城鎮)主持修復南寶塔,陶澍跟隨父親,到安化學宮讀書。十二歲那年,陶必銓開始教陶澍做八股文。也許是從七歲起每天耳濡目染,僅學一個月,陶澍便能做得一手漂亮文章。1792 年,陶必銓到益陽曾潤攀家中設館教書,陶澍仍跟隨在側讀書,前后長達四年。
陶必銓本人讀書從不迷信經典,不盲從權威,他只相信“開卷有益”。在父親這一觀念的影響下,陶澍讀到許多雜書,包括算學、測量學等技術書籍。這些書籍,為他以后精通經濟打下了基礎。
科舉入仕
十八歲那年,陶澍參加童試,以院試第二名的成績考取秀才。這年,陶必銓在離家三里遠的一個叫“水月庵”的破棚子邊帶兒子住下來,專心教兒子讀書。因為一心要將兒子培養成“惠及蒼生”的人物,他不再設館,也不準兒子設館,更不讓兒子干農活。就這樣,每天聆聽資江河畔澎湃的濤聲,父子倆對著江中巨大的“印心石”,埋頭發奮勤讀。
1800 年,二十一歲的陶澍與父親一同到長沙參加湖南鄉試。陶澍一舉考取第三十名舉人。意外的是,父親陶必銓卻落榜了,這讓他多少有點難堪。1801 年,陶澍第一次離家赴京,參加會試,但這次名落孫山。他遵從父親囑咐,留京溫習功課,準備來年再試。
1802 年,二十三歲的陶澍參加壬戌科會試,這次考了全國第二名,考官申報陶澍為一甲榜眼。但還來不及慶祝,霉運跟著就來。殿試照例由嘉慶皇帝親自主考,陶澍不知何故,在“策”內遺漏了一個字,讀起來有點不大順口。關鍵時刻怎能出錯?嘉慶皇帝讀卷,感覺像魚翅里吃出了頭發,眉頭一皺,陶澍被拋進二甲第十五名。
在全國考生中依然排十八名,已經是很不錯的成績。陶澍由此成為安化縣有史以來第一個科考進士。父親在鄉接報,喜極而泣。寄望兒子將來“恩惠蒼生”的夢想,已經邁出最為關鍵的一步。
1805 年,陶澍如愿出任翰林院編修。但就在這年閏六月,陶必銓在老家遙念在京的兒子,安然病逝。
父親是兒子人生的第一個導師。正是在安化窮鄉僻壤、草野民間積蓄了士人清氣,陶澍在人格養成的關鍵時期,才奠定了畢生的理想情懷。
經世能臣
陶澍改革經濟所具備的霹靂手段,則主要受梅山地域文化的熏陶。梅山并不是一座山,而是泛指湘中山區。農耕之余,梅山人還以輔以打漁、狩獵為生,這種古老又原始的生存方式,逐漸演進成一種文化,叫作梅山文化。因為漁獵充滿了風險,漁民、獵人尤重祭祀,它浸透了原始巫術的因子。梅山文化的另一特色是崇尚武術,因為自然環境惡劣,濕氣過重,在長期的狩獵生活中,梅山人觀禽技、仿獸姿,發明了一套梅山武術,用以防身、健體。武術鍛煉了梅山人強健的筋骨,也磨礪出他們勇猛的性格。
巫文化重情,祭祀文化重義,尚武者有膽,這就是湖南俗話說的“霸蠻”。霸蠻是梅山文化之魂,表現于外的基本特征,是勇于擔當。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因有霸蠻、擔當的梅山文化做底襯,情、義是陶澍一生理想情懷的根,膽是陶澍改革家行動之魂。
梅山當地至今仍流傳陶澍一則小故事,可見地域性格對他的影響之深:十歲那年,碰上鄉人油榨作坊開業,籌備者請人寫副大紅對聯志慶,連找了幾位秀才,大家看后直搖頭。陶澍自薦,提筆寫下兩句:“榨響如雷,驚動滿天星斗;油光似月,照亮萬里乾坤。” 這副對聯,勇猛、果敢、大氣,頗見武人氣魄。
陶澍作為踐行士人情懷的一代改革家,入仕后無論遭遇多大阻力,他的理想信念始終不滅,從其童年的成長中也可以找到原因。
鮮為人知的是,陶澍不但是湖南安化第一個進士,也是清朝第一位官至兩江總督的湖南籍高官。
湖南為古來四塞之國,自然、自由的土地,率性、真實。直到宋朝,此地遠離皇權,一直是片處女地。賢士存諸野,禮失求諸野,山水自然清氣,讓讀書人比士族、書香門第子弟更容易信仰儒家文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面對家國天下,內心單純的士子更容易生出一股“書生意氣”,而沒有官場文化滲透后的那種精明、算計、油滑。一身清氣的陶澍,內心始終簡單。梅山地域文化重情義,讓他特別重知遇之恩。儒家信仰與忠君報國,是他畢生的信條。
入仕為官后,對道光皇帝信任有加的逾格提拔,他由衷感激:“臣楚南下士,才識疏庸,蒙皇上特達之知,由道員薦蒞封疆。十載江南,兢兢奉職,毫無報稱。乃復渥荷恩綸,畀茲巨任。臣自顧何人?篤邀高厚。受恩愈重,圖報愈難。”
陶澍在湖南安化出生時,王船山去世已有八十七年。陶澍私讀過他的作品,仰慕有加。至今,王船山故居(湘西草堂)仍掛著那副陶澍撰寫的對聯:“天下士非一鄉之士,人倫師亦百世之師。”對先賢至高評價的背后,可見出船山先生對陶澍的影響之深。
王船山去世一百多年后,陶澍帶著書童,肩挑手提,穿過梅山,走出洞庭湖。如果說王船山用思想影響到湖南人,給予后世以思想的骨架與文化的血肉,陶澍則打破了湖南歷史的千年靜寂,明確為后來者指明前進的方向、行動的指南,兩人前后接力,共同改寫了其后湖南籍士人的命運。
(作者系著名作家,國內左宗棠研究領軍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