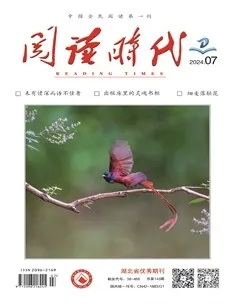漢語是怎么造新詞的
早在萬年之前中國語言就已經產生,遠遠超過文字產生的時間。漢字是表意文字,每個新事物產生之初始,就被予以命名和定義,是先有的義和音結合,后來才有的文字。由初始的義和音,古人通過不斷地變音來豐富和衍生發展出5萬多個不同的文字,甚至更多,但還不足表達人們的思想。與其他歷史悠久文明的語言發展規律一樣,漢語語音的歷史不斷變化。有其發展的內在規律才有所謂的源遠流長,漢語溯源亟須被解決,音就是內在的遺傳基因。
漢字中形聲字占很大比例,據統計,《說文解字》中的形聲字就占82%以上。形聲字是由義符和聲符兩部分構成的合體字。從某種意義講,聲旁是被人忽略的漢字拼音密碼,漢字拼音的形式遠遠大于象形形式。古人沒有真正的注音系統,無法規范地標注和認讀文字的發音,字到底怎么念呢?漢魏以前,漢字注音一般都是采取打比方的方法,即“譬況”,還有其他“讀若”“直音法”等等,但都不能準確注音,直到東漢佛經傳入。當時人們需要在漢語中尋找具有同等發音的漢字來“音譯”佛經,印度來的高僧也需要學習漢語,在梵文拼音方法的啟發和影響下,古人創造了反切法的注音方式,雖然差強人意,但從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音韻作為一門學科的發展。
歷史是一條長河,今天的漢字與早期的甲骨文相比有很大的變化,語音更是不斷發展演變。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大一統的語音,即使是同一時期,因地域方言不同,同樣的字詞發音也各不相同,今日有些地區方言十里已是不同音。由于古今音變,明清不懂唐詩宋詞之韻,唐宋不識詩經漢賦之音。古代典籍大量被誤讀,甚至我們生活中的語言許多不知其本源和真實意思,存在大量的錯誤解釋。
漢代人寫出《釋名》,但那時人們沒有語音學知識,研究成果不能用。中國文人清末才開始認真研究漢語語音學,可惜他們不從自己的方言入手,只從古文的押韻入手,結果研究到清末,可用成果不多。1910年瑞典人高本漢來到中國,在兩年時間里調查、記錄了33個方言點,奠定了有科學意義的漢語語音學。1940年,高本漢把研究成果《漢語詞族》以字典的形式寫進《古漢語字典》,這是漢語開天辟地的研究成果。
語音學、方言學、音韻學,進而訓詁,這是漢語探源釋源的方法路徑。我的父親曾光平1985年成為漢語方言學會會員,1986年成為音韻學研究會會員,1988年成為中國語言學會會員,1989年成為訓詁學研究會會員,語言研究學界少有能集四個協會會員于一身的學者。父親1965年就開始為編寫《漢語釋源大字典》學習植物學、動物學,甚至醫學;研究解決艸頭牛旁骨部肉月部的字的源;1990年起就從十三經和諸子著作中剪書證,家中滿地都是他剪的書證紙條。
父親數十年韜光逐藪,含章未曜,孜孜以求,做漢字的釋源工作并且分類,像達爾文的物種進化,將漢字來源系譜化,編纂了800余萬字的《漢語釋源大字典》。1993年,中國語言學泰斗——北大中文系周祖謨教授,看到《漢語釋源大字典》的幺部字頭和理論體系,欣然題寫書名并作序。語言學家李玲璞等也給予父親鼓勵和支持,書稿在他手中已完成近90%。
父親不但精通英語、印尼語、荷蘭語、日語、朝鮮語,更是精通幾十種漢語方言,到處都是老鄉,他的專屬天賦是:隨處換方言,處處有鄉音。一看就是和藹可親的“鄉親”,隨時與“知音”屈膝細聊。實地調研是方言學研究的生命,但也極其艱苦與枯燥,令許多研究者望而卻步。
語言天賦和學術突破,是建立在大量田間地頭實地的語言調研資料上取得的。父親1934年5月生于福建平潭島,1940年隨父母移居印度尼西亞,5歲時爺爺就用福建口音教他讀《論語》。他天資聰穎,從小連續跳級,中學畢業時作為優秀學生代表畢業生上臺接受校長表彰,23歲回國前在印度尼西亞和其他閩廣子弟一起上學,閩廣諸方言都基本掌握。回國后弄清廣州、潮州、廈門、客家幾種方言,父親自己的方言是福州方言。父親自福建師范大學外語系畢業后,1972年補了上海話。1977年調洛陽,受各地方方言志編委會的委托,寫了洛陽等5個方言志。1984年調河南大學中文系教音韻學。父親利用所有的寒假暑假等節假日,墊上所有積蓄,自費走遍中國南北,錄音和記錄了100多個方言點的實地調查,包括藏語,獲取了中國方言的大量一手資料。
父親熟悉中國七大方言體系,比較并系統整理了各區域之間聲、韻、調的不同,并對日語音讀、漢越語、朝鮮漢字也做了《方言對照調查字表》,從方言延伸到亞洲語系,父親在探源研究中游刃有余,最終摸索出了漢語語音的發展規律。悟出漢語是通過改變聲母、改變韻母、改變聲調或改變寫法造區別詞、造新詞。《漢語釋源大字典》的《漢語語音知識》章節從方言出發,把音韻學講了,也把詞源講了,更好幫助讀者理解《文選》章節中的注釋,有紅爐點雪,醍醐灌頂的作用。
在詞源研究的道路上,父親風趣地說自己開辟了蹊徑。用老舊那一套就像沒有舵的船,很難駛到彼岸。詞源研究需要突破陳陳相因,需要探索與爭鳴,需要旗幟鮮明、剛正不阿的學術風骨,需要敢于突破學科藩籬、學術求真、嚴謹治學、敢于質疑的科學精神。
父親在學術權威面前不畏門派,不拜權威,不立偶像。他認為中國歷史上從沒有出現過全國一致的語音,構擬的上古音不但沒有實用價值,還封殺了漢語音韻研究和詞源探討。
語言學者陳衛恒教授曾這樣評價父親:感念曾光平老師的治學之路,由外而中、由今而古、由流而源,由音理而求義理,并兼顧形理。漢字形、音、義之生發、變化之理,也即編、變碼之理據,由是彰顯,作為單音節語的典型,特立于世界語言之林。“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先生由愛國而愛民族語言,探求漢語源之奇人獨徑,之執著精神,永存。
(源自“閱讀公社”,有刪節)
責編:馬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