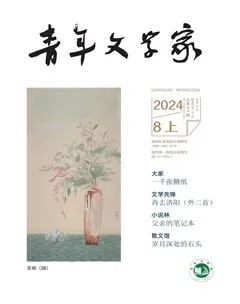如魚在水
也許,從某種角度看,人如魚一樣,本質就是孤獨的,一無所有地來,一無所有地去。然而,人始終是一種社會性動物,我們始終依賴社會與族群的紐帶。
魚在水里生存,一群群地游來游去。然而,它們的身體肌膚所感知的,只是環繞在身體四周的水的觸感。這一瞬間,魚感覺到自己是真實存在的。關于是魚先于水而存在,還是水容納了魚群,這已然是自然界中一個深奧的謎題。不過,我們可以確認的是,水在容納魚的同時,也賦予了它們與生俱來的獨立性。它們彼此相望、相嬉,緊緊相依,卻又不得融合,保持著自己的獨特性。
但人與魚并非完全相同,而是存在本質的區別,至少人不一定要與水共存。我在這個世界度過了人生的十八個春秋,自覺還是不通人情世故,與世隔絕一般。那些明星花旦,對我來說,自始至終仿佛字典上的抽象名詞,觸不可及,他們不知道我的存在,我的世界也沒有他們的存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曾多次遭遇轉折和變故。我痛苦地發現這個世界無論是我們的靈魂還是身體,都在以不可想象的速度暴風驟雨般地改變著。即便再年幼的人,也會試著反思過去發生的一切。
當我們真正去體會,會發現這個世界的繁華與落寞背后,隱藏著深深的憂傷。
一條魚在棲息的時候,為人的精神突圍提供了一種可能的啟示。萍水相逢,在古代有“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的自在與暢快。再遠溯,《論語》中有關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描繪,正是表達了當志同道合的朋友從遠方來訪時,內心的喜悅與暢快。這些描述,都源自人們身處困境,如魚涸澤,痛苦不已,而當見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才喟然慨嘆。古人重萍水相逢,正是他們身邊無友的真實寫照。然而,在現代社會,“萍水相逢”這個詞卻更多地被賦予了艷遇的意味。
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面墻,它在保護我們免受外界傷害的同時,也無形中封閉了我們真實的存在。因此,我們無法真正看到別人的存在,而是在自己的墻內謙遜著,也自大著、驕傲著,甚至痛苦著。我們向外好奇地張望,卻又因為內心深處的自戀和防備,不敢輕易跨越那道無形的界限。這也許是我們在人際交往中,尤其是在萍水相逢時,所面臨的最大困境。
與其說我們不夠勇敢,倒不如說我們抵觸改變。我們不知道別人進入我們的世界將會發生什么翻天覆地的變化,擔憂他人的介入會打破我們現有世界的平衡。因此很多看似花前月下、風花雪月的萍水相逢都無疾而終。于是,很多人一度相信自己的心成了只有一把鑰匙可以打開的獨門獨院,而那把鑰匙在人生蹉跎和機緣巧合中悄然遺失了。所以,我們一直相信愛情,相信我們曾經愛過,而且刻骨銘心,以致我們愿意將余生所有的愛都給那個愛夠了的人。然而,又如所有的凡人一樣,當面對不可避免的遺憾時,我們往往選擇逃避,試圖重新開始。
等到一種思念在我們的回憶里發酵得越發醇香,我們已開始變老,開始回憶當初是否會選擇轟轟烈烈地談一場學生時代的戀愛,而不是畏首畏尾地龜縮在假想的錦繡前程里,只與書本和試卷為伴,對那份真摯的情感視而不見,置若罔聞。
王小波在《黃金時代》中寫道:“我始終盼著陳清揚來看我,但陳清揚始終沒有來。她來的時候,我沒有盼著她來。”我沒有想過,會有一個女生愿意和我談論西方文藝史的奧妙。我一直覺得,那種學術話題對于年輕女孩子而言可能稍顯枯燥,她們是不感興趣的。曾經有女孩聽到我關于歐陽修《朋黨論》的見解,我被她評價是世界上最無聊的人。為此,我受到不少人的敵對。我在我的道路上踽踽獨行,而君煢煢獨立。
你曾提起英國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這部作品為我們描繪了一個理想化的社會藍圖,其中財產公有、人人平等,這與《格列佛游記》中那些奇異的異國他鄉見聞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我們受到的傳統教育說,《烏托邦》不僅揭露了私有制的種種弊端,更是對共產主義美好社會的一種早期憧憬和倡導。但在我看來,這更多是對童心的呼喚。通過成人世界現實的黑暗和人性中渴望真善美的本性之間的對立,提出對理想社會的看法。但由于這個愿望幾乎不可能實現,使得它淪為空想社會主義,其本身提出的時候應不在此范疇。
我沒有看過托馬斯·莫爾的作品,我讀過《柏拉圖全集》《理想國》里有關于烏托邦的描述,著重從精神層面解釋它的構成,后面半章論述到有關精神戀愛—烏托邦式愛情就是對其的補充說明。柏拉圖是一位長于想象和善于形象思維的作家。然而,他這種才華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受到了抽象邏輯思維的極大限制。盡管如此,他仍致力于通過寓言和道德說教的形式,創作出富有意味的作品。他渴望通過敘述爭論的形式,希冀藝術具有改變混亂現實、引導道德風尚的職能。烏托邦,實質上是柏拉圖的夢,只是一個夢,經過無數的斟酌反思,卻本質不變。他更多地沉溺于道德追求,而并非道德說教。所以,說他抨擊萬惡的私有制,實際上是言過其實的……
昨日之言,猶在耳邊;今日人面,不知何處。何日一杯酒,重與君細論文?愁人的萍水相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