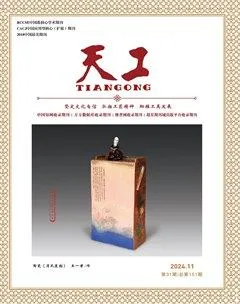商代豕磬相關問題探討
[摘 要]銅磬是商代打擊樂器的一種,主要集中出現在長江流域,從已發現的商代豕形銅磬來看,其遵循了石磬的形制和音樂性能設計,有著越文物的典型特點,器身上的乳釘紋飾非單純記音符號,器身整體造型與紋飾反映了商周時期南方地區人們的圖騰崇拜。銅磬是適應南方環境而生,跟南方大鐃一樣,有著祭祀娛神功能,充實了南方音樂文物發展脈絡,而因自身局限,最終消失在向樂器發展的道路上。
[關 鍵 詞]音樂文物;娛神禮器;圖騰崇拜;豕磬;音樂性能
[中圖分類號]J526.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7556(2024)31-0012-03
文獻著錄格式:袁鑫,尹衡炎.商代豕磬相關問題探討[J].天工,2024(31):12-14.
一、類型學分析
上海博物館收藏有2件銅磬(簡稱上博磬,見圖1),傳為1989年湖南湘陰縣城關鎮出土。兩件銅磬的形制、紋飾基本相同。一件長56.3厘米,高28.5厘米,重17千克。另一件長50厘米,高26厘米,重13.55千克。整體造型為野豬形象,口微張,吻部上卷,腹下部有兩曲踞狀足,弧背上飾鳥狀脊,脊下有一長方形穿孔。磬身飾乳釘10個,臣字眼部位飾1個乳釘,磬身中部的乳釘外飾火紋,乳釘之間有陰線云雷紋,磬身兩面乳釘個數相同、紋飾相同。
現藏于湖北長陽博物館的銅磬(簡稱長陽磬,見圖2),1992年在湖北長陽土家族自治縣磨市鎮官家沖村白廟山坡下土層中出土。通長46.4厘米、高25.3厘米、上部厚2.8厘米、頸厚2.2厘米、下部厚1.5厘米,重9.1千克。整體作板狀,呈野豬造型,嘴微張,唇上翹,尾短,弧背飾一組似豬鬃的鳳鳥扉棱。磬身兩面各有10個乳釘,臣字眼部位飾1個乳釘,中間1個較大乳釘周圍飾火紋,其余9個略小,兩面乳釘數量一致、位置不對稱。弧背上部有一長方形穿孔,下飾呈卷云紋的足,后足斷缺,器身滿飾陰線云雷紋。
湖南博物院收藏的銅磬(簡稱汨羅磬,見圖3),2012年于汨羅市白塘鄉曹家村出土。通長52厘米,高28厘米,厚1.5厘米,重13.05千克。通體呈匍匐狀,嘴微張,上吻部上卷,弧背上飾一組似豬鬃的鳳鳥扉棱,背脊下有一供穿繩的圓形穿孔,短尾下弧。腹部飾9個乳釘,中間乳釘外飾一周火紋,腹中部飾魚鱗紋,吻部及肩、下腹環飾回紋、云雷紋。腹下中間有巨大的三角形生殖器室,兩側置卷云狀扉棱的屈足。
除了已發現的實物,文獻另有記載同類型銅磬,如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王黼編寫的《宣和博古圖》,記錄了宋王宮宣和殿珍藏的4件銅磬:“周雷磬”2件、“周琥磬”1件、“周云雷磬”1件。馬今洪在其《青銅磬瑣論》一文中對這4件銅磬的形制、紋飾有具體介紹,并將尺寸換算,進行了對比,這里不再贅述。
二、音樂性能分析

磬是我國古老的打擊樂器。早期石磬多為特磬,即單件的大型磬。1950年,安陽武官村大墓出土的虎紋特磬,現藏于故宮博物院,該器制作精致,紋飾精美,是商王朝重要的禮樂器。出土于安陽殷墟的一套石編磬,尚存3件,其上皆有銘文,分別為“永啟”“永余”“天余”,每件可出一音,3件的音階結構相當于今天bE調的sol、la、do。
同樣作為樂器,銅磬的音樂性能如何?以汨羅磬測音數據為例,以倨孔下方即磬身正中所刻火紋處的乳釘為起點,以逆時針的方向審視豕磬各乳釘的音高數據,可見整個音高呈由低到高的排布(見圖4)。該磬的最低音為倨孔下方,即磬身正中所刻火紋處的乳釘,音高為“#G3+3音分”,最高音為磬的下半部分,從左往右數第1個乳釘,音高為“#C5-4音分”。從各個乳釘處所測音高來看,各個重復音的音高具有很大的統一性,同一八度內的重復音之間的音高差值最大為5音分,而5音分的差值人耳很難分辨,故可忽略不計。由此看來,豕磬的音高在鑄造時有主觀布局的可能性。
以豕磬倨孔的位置為中線,將其分為前后兩部分,左側(即頭部一側)的面積相較于右側(即尾部一側)較小。故此,其懸掛演奏時應該是尾部一側下垂,頭部上揚。按照石磬的演奏習慣來看,應是敲擊下垂一側(即豕磬尾部一側)。尾部一側的乳釘數量較多且排布較之于頭部一側更為分散,音響效果應好于較密集的排布,也更方便敲擊。再從其各部分音高數據來看,其下垂一側的乳釘的音高多為小字組和小字一組,在實際的演奏中也更加實用,磬身正中所刻火紋中心處的乳釘也與尾部一側幾個乳釘的音高一致。如果按照磬身比例將豕磬和石磬的比例進行比較的話,其身子到尾部應對應“鼓部”,最右側的兩個乳釘也對應鼓上角和鼓下角,而從一般石磬的測音結果來看,也是鼓上角和鼓下角的音最高。故此可以推測豕磬雖形制特殊,但其整體形制比例和音高設計仍遵循著石磬的設計思路。
從五個乳釘的頻譜來看,能看出敲擊同一個乳釘會有兩個相對較強的音高先后出現,聽起來也很雜,音高不明確,故可以確認下面的乳釘應該是沒有作為一個記音符號使用。目前來看,乳釘的目的可能更多還是用于消除雜音,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認它可以作為不同敲擊點的標記,因為不同位置音響的變化也可能具有不同的含義。

商代的磬還沒有完全定型,并沒有形成我們今天所認知的設計和布局。磬上的乳釘是否和鐘上的枚一樣起到消除高頻振動的作用是有待商榷的,因為從石磬的聲學分析實驗來看,更為平滑的表面更適合板塊的振動,具體可參見《編磬音時程特性的分析》①②。
在馬今洪的文章中,上博磬的測音數據相較于汨羅磬和長陽磬較為獨特,其文中的測音數據均為音樂學記法,即#c1 = #C4,其音域為:e2-c4。汨羅磬和長陽磬的測音數據均采用的是物理學記法,筆者嘗試將上博磬的數據轉寫為物理學記法,并將三者一起比較,結果如下表。

從表1可以發現,上博磬的音域比汨羅磬和長陽磬至少高了一個八度,而從馬今洪文中給出的形制數據(青銅磬形制數據)來看,上博磬無論是長、高、厚還是重量,都是三者中最大的一件,其音高應該也是三者中最低的。從這一角度看,其形制數據與測音數據并不匹配。此外,從汨羅磬和長陽磬的形制數據與測音數據的比較來看,兩者都遵循了板塊狀振動體音高變化的基本原理,即通過調整磬體的長度、厚度來調整其音高,簡單來說就是長度越長,音高越低;厚度越薄,音高越低。
三、造型與功能
湖南地區出土了大量的商周時期的動物造型青銅器,最有名的如豕尊、象尊、牛尊等,這些動物造型的青銅器反映出商周時期湖南先民對自然神靈的崇拜。對比湖南湘潭出土的豕尊,以及器身上的鳥紋和魚鱗紋,汨羅磬的造型恰如湘潭出土的豕尊的“側面照”。毋庸置疑,豕磬雖非旋律樂器,仍具有一定的樂用功能,是用于某種特殊祭祀場合的禮樂器。觀察銅磬上的乳釘紋飾,很難將其定位為記音符號,其所發音高是不能構成音階的。那么,這類型銅磬上的乳釘既與音頻無關,其如此規律的布局,又有何寓意?
據《史記》《尚書》等文獻記載,后羿射日的故事發生在夏商之際,與豕形磬所屬年代相近。豕磬上有10個乳釘,中間的乳釘居中,外一周的火紋即代表著太陽光芒,另外9個乳釘圍繞其排列,與后羿射日的故事有著相似性。
甲骨文中有關于殷商時期養豕的記載:“陳豕于室,合家而祀。”豕很早就被家庭飼養,同時是祭祀的主要物品。與銅鐃通過敲擊發出聲音溝通天地一樣,動物造型(豕)的青銅樂器,同樣可以達到溝通天地的作用。
越人視鳥為保護神,越地有鳥田的傳說,《越絕書·記地傳》記載:“大越海濱之民,獨以鳥田,小大有差,進退有行。”越人對鳥的崇拜,表現為越地銅器上的鳥飾扉棱、豕尊上的立鳥紋飾,以及肩部的鳥飾等。
近年來,在汨羅地區出土的一件觥形器,其造型之精美,顯示出擁有者地位的不一般,顯然是適用于較為重要的場合。其與豕形銅磬發現地相距不遠,說明汨羅地區在商周時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文化中心,豕磬和觥形器顯然同樣用于重要祭祀場合。
總之,銅磬的整體造型和乳釘紋飾,以及器身上的鳥飾扉棱與越文化的太陽崇拜、鳥崇拜和豕崇拜似有聯系,是越地獨有的太陽、鳥、豬圖騰崇拜的三位一體。
四、源與流
銅磬的年代為商晚期至西周早期,其形制受到了中原石磬的影響,紋飾上又有著南方青銅器的典型特征。兩種質地的磬是否有聯系?
出土資料顯示,早期石磬多分布于黃河流域,造型扁長,通體打制,整體難以看出具體為何種動物。石磬多在大墓中發現,且還出土有其他類型的樂器;同時期的南方,石磬發現數量很少,僅在湖南石門皂市商代遺址、四川巫山大昌鎮雙堰塘遺址出土了石磬。與此同時,既具有殷墟文化特點又有本地元素的銅磬在長江流域多有發現,且無一例顯示有具體的出土環境與共存器物。出現這種不同,或許跟兩者的功能有關,北方石磬更多是承擔祭祀功能,是權力的象征,南方銅磬則更多的是祭祀、娛神功能。
晚商時期,石磬仍占多數,同時出現了成組的編磬,石磬的功能逐漸由僅承擔打擊任務的節奏形樂器向可以演奏的旋律性樂器發展,其音樂表現力進一步增強。銅磬從目前出土實物和文獻資料來看,似乎很難成編。目前可以肯定的是,銅磬算不上旋律樂器,其音質較為嘈雜,延音也很短,從整體測音數據來看也不足以構成音階。從汨羅磬的測音數據來看,其音高有一定的規律性,結合其他豕磬的數據來看,這種規律也不具有普遍性。商朝出現的銅磬,也用于祭祀,可能是與其他樂器共同使用,承擔伴奏的作用,非主旋律樂器,且以往的金石樂器也多是起這樣的作用。
石磬材質多為石灰巖,而石灰巖又微溶于水,因此石磬在南方無法長期保存。且早期石磬可能無法兼顧音高、紋飾和耐用度這些因素。此時銅磬就應運而生,其更適應于南方環境。從音樂學角度看,其音域和音色過于短,更適合室內祭祀。它與鐃同用時,音高一致,使得兩者可以輪替或同時敲擊。此外,銅磬雖同銅鐃一樣,多單獨發現,但發現地點并不是在山河湖畔,可能與銅鐃置于天地間祭祀自然神靈有關,銅磬較銅鐃輕便,能適應不同祭祀場合所需。
值得注意的是,汨羅磬上只有9個乳釘,另一個靠肩部的穿孔,非常規整,所見為圓角方形而不是圓形,穿孔的直徑和乳釘的直徑大小接近。有可能是當時工匠忘了鑄造器身的穿孔,臨時將其中一個乳釘改制成了穿孔,與早期的石磬的圓形穿孔形制似有聯系。
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銅磬跟不上音樂實踐的發展,單面的敲擊不能發出和聲和雙音,音色、音高、音長都滿足不了需要,進一步樂器化難度較大,因此最終消失在向樂器發展的道路上。
參考文獻:
[1]李純一.中國上古出土樂器綜論[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2]李純一,方建軍.考古發現先商磬初研[J].中國音樂學,1989(1):82-89.
[3]王子初.石磬的音樂考古學斷代[J].中國音樂學,2004(2):5-18,2.
[4]方建軍.西周磬與《考工記·磬氏》磬制[J].樂器,1989(2):2-4.
[5]王子初.中國青銅樂鐘的音樂學斷代:鐘磬的音樂考古學斷代之二[J].中國音樂學,2007(1):5-36.
[6]高蕾.中國早期石磬述論[D].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2002.
[7]王安潮.石磬形態通考[D].上海:上海音樂學院,2003.
[8]王秀萍.樂器學視域下的考古出土商代樂器研究[J].南京:南京藝術學院,2014.
[9]郭正忠.三至十四世紀中國的權衡度量[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298.
[10]丘光明.中國歷代度量衡考[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2:462.
[11]馬今洪.青銅磬瑣論[J].湖南省博物館館刊,2016(00):16-26.
(編輯:王旭平)
注 釋:① 徐雪仙、馮光生、褚梅娟:《編磬音時程特性的分析》,《樂器》1984年第3期,第1-3頁。
② 徐雪仙、馮光生、褚梅娟:《編磬音時程特性的分析(續)》,《樂器》1984年第4期,第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