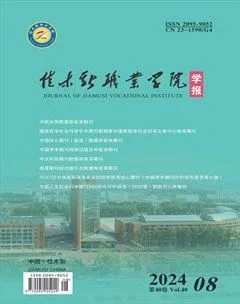生態(tài)翻譯學(xué)研究解讀
摘 要:清華大學(xué)的胡庚申教授提出了著名的生態(tài)翻譯學(xué)(eco-translatology)。生態(tài)翻譯學(xué)是我國(guó)專家學(xué)者所需要的新型翻譯指導(dǎo)理論,其涉及生態(tài)學(xué)(ecology)和翻譯學(xué)(translatology)這兩個(gè)學(xué)科,是二者的有機(jī)統(tǒng)一結(jié)合。本文擬借助生態(tài)學(xué)和翻譯學(xué)的基本定義,探究生態(tài)翻譯學(xué)的基本內(nèi)涵,研究該理論所誕生的國(guó)內(nèi)外背景(全球性的生態(tài)思潮,中國(guó)古代的生態(tài)智慧,生態(tài)取向的翻譯研究),厘清譯者中心、適應(yīng)與選擇、三維轉(zhuǎn)換這些生態(tài)翻譯學(xué)中的核心概念,并借助中國(guó)知網(wǎng)平臺(tái)對(duì)該理論的國(guó)內(nèi)研究現(xiàn)狀展開多個(gè)維度層面的分析,以期幫助廣大學(xué)者能夠快速了解生態(tài)翻譯學(xué),進(jìn)而對(duì)生態(tài)翻譯學(xué)展開更高質(zhì)量的理論研究和實(shí)踐應(yīng)用。
關(guān)鍵詞:胡庚申;生態(tài)翻譯學(xué);生態(tài)學(xué);翻譯學(xué)
中圖分類號(hào):H315.9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文章編號(hào):2095-9052(2024)08-0037-03
引言
長(zhǎng)期以來(lái),我國(guó)的專家學(xué)者普遍接受的是西方的翻譯理論思想,這就導(dǎo)致我們不自覺地就會(huì)按照西方的那一套研究模式來(lái)推進(jìn)我國(guó)翻譯學(xué)的發(fā)展[1]。往小了說(shuō),這不利于我國(guó)翻譯學(xué)的長(zhǎng)遠(yuǎn)健康發(fā)展;往大了說(shuō),在“四個(gè)自信”當(dāng)中,最根本的就當(dāng)屬“文化自信”,這一現(xiàn)象顯然不利于我們堅(jiān)定文化自信,實(shí)現(xiàn)到2035年要建成文化強(qiáng)國(guó)的遠(yuǎn)景目標(biāo)。清華大學(xué)教授胡庚申提出了著名的生態(tài)翻譯學(xué),可以這么說(shuō),生態(tài)翻譯學(xué)的誕生是如今我國(guó)專家學(xué)者從事翻譯研究所需要的新型指導(dǎo)理論。用我們自發(fā)的翻譯理論,來(lái)指導(dǎo)我國(guó)的翻譯實(shí)踐,無(wú)疑是如魚得水、如虎添翼。
一、生態(tài)翻譯學(xué)的基本內(nèi)涵
生態(tài)翻譯學(xué)涉及生態(tài)學(xué)和翻譯學(xué),是兩者的有機(jī)統(tǒng)一結(jié)合。生態(tài)學(xué),英文名為ecology,研究的是生物有機(jī)體及其周遭環(huán)境之間關(guān)系的一門學(xué)科,是生物學(xué)的下屬學(xué)科之一。起初研究的是生物和環(huán)境之間的關(guān)系,后來(lái)則擴(kuò)展到研究人與自然之間的關(guān)系。在人類發(fā)展的歷程中,一系列自然災(zāi)害的頻發(fā),使得人們?cè)絹?lái)越重視人與自然的辯證關(guān)系。現(xiàn)如今,生態(tài)已經(jīng)是一個(gè)整體性的概念,更是用來(lái)泛指和諧共生、平衡。至于翻譯學(xué),翻譯學(xué)科的學(xué)科名稱五花八門,也頗具爭(zhēng)議。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xué)文學(xué)系教授詹姆斯·霍姆斯建議采用translation studies這一術(shù)語(yǔ),國(guó)內(nèi)外專家學(xué)者也有使用合成詞translatology的。2008年,胡庚申教授在《中國(guó)翻譯》期刊上發(fā)表《生態(tài)翻譯學(xué)解讀》一文。在闡明翻譯學(xué)的概念時(shí),他使用的術(shù)語(yǔ)是translatology,生態(tài)翻譯學(xué)被其翻譯成eco-translatology。但其談及翻譯研究時(shí),也使用了translation studies這一表達(dá)[2]。不管使用什么術(shù)語(yǔ),翻譯學(xué)始終研究的是翻譯的規(guī)律、翻譯的藝術(shù),在翻譯過程中所涉及的理論就是翻譯理論。
生態(tài)翻譯學(xué)的根基是“翻譯適應(yīng)選擇論”,這一理念來(lái)自生物進(jìn)化論中的“物競(jìng)天擇”“適者生存”“自然選擇”等概念。可以看出,生態(tài)翻譯學(xué)是一個(gè)交叉學(xué)科,其以生態(tài)學(xué)為哲學(xué)依據(jù),以翻譯學(xué)為理論依托,近年來(lái)得到蓬勃發(fā)展[3]。創(chuàng)始人胡庚申曾指出,生態(tài)翻譯學(xué)就是一種以生態(tài)學(xué)為途徑或視角的翻譯研究。
二、生態(tài)翻譯學(xué)的產(chǎn)生背景
(一)全球性的生態(tài)思潮
1962年,蕾切爾·卡遜發(fā)表了作品《寂靜的春天》,其是美國(guó)著名的海洋生物學(xué)者,該書的出版為美國(guó)和世界各國(guó)的環(huán)保運(yùn)動(dòng)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作者筆下,為提高農(nóng)業(yè)的產(chǎn)量,人們無(wú)節(jié)制使用各種農(nóng)藥化肥,造成了大規(guī)模的環(huán)境污染和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嚴(yán)重破壞。她警示人類思考近代污染對(duì)生態(tài)的影響以及人與社會(huì)的發(fā)展問題。蕾切爾·卡遜是生態(tài)文學(xué)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寂靜的春天》問世之后,一系列生態(tài)文學(xué)作品如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出來(lái)。1972年,聯(lián)合國(guó)人類環(huán)境會(huì)議于6月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中國(guó)也出席了此次會(huì)議。大會(huì)通過了《人類環(huán)境宣言》,這是一項(xiàng)劃時(shí)代性質(zhì)的歷史文件。1982年,為了紀(jì)念聯(lián)合國(guó)人類環(huán)境會(huì)議10周年,國(guó)際社會(huì)成員國(guó)于5月在內(nèi)羅畢召開了人類環(huán)境特別會(huì)議,針對(duì)世界環(huán)境的新問題,提出了各國(guó)應(yīng)該遵守的原則。1992年6月,聯(lián)合國(guó)環(huán)境與發(fā)展大會(huì)在巴西里約熱內(nèi)盧舉行。這次會(huì)議提升了大家對(duì)環(huán)境問題認(rèn)識(shí)的廣度深度,并且把環(huán)境問題與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發(fā)展相結(jié)合,會(huì)上通過了一系列文件,如《里約環(huán)境與發(fā)展宣言》《二十一世紀(jì)議程》《關(guān)于森林問題的原則聲明》《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會(huì)議之后,我國(guó)政府組織制定了《中國(guó)21世紀(jì)議程——中國(guó)21世紀(jì)人口、環(huán)境與發(fā)展白皮書》,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進(jìn)程由此開啟。2003年,時(shí)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錦濤同志,提出了科學(xué)發(fā)展觀這一重大戰(zhàn)略思想。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長(zhǎng)期被廣大專家學(xué)者忽略的“生態(tài)”維度進(jìn)入了各個(gè)學(xué)科領(lǐng)域。
(二)中國(guó)古代的生態(tài)智慧
上下五千年,中華文化源遠(yuǎn)流長(zhǎng)、博大精深。眾多古代先賢的論述中都閃耀著生態(tài)的智慧光芒。就拿“天人合一”這一哲學(xué)思想來(lái)說(shuō),儒家、道家、釋家等諸子百家都進(jìn)行過論述。國(guó)際東方學(xué)大師季羨林曾指出,天人合一是人與自然的和諧統(tǒng)一。人其實(shí)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們與大自然和諧相處,方可達(dá)到心與天地相通的境界。人類應(yīng)尊重自然規(guī)律,遵循大自然的發(fā)展節(jié)奏。客觀規(guī)律性和人的主觀能動(dòng)性的辯證統(tǒng)一規(guī)律告訴我們,我們要承認(rèn)自然規(guī)律的客觀性,規(guī)律的客觀性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人類充分發(fā)揮自身的主觀能動(dòng)性,必須以尊重客觀規(guī)律為前提和基礎(chǔ)。我們想要在開發(fā)利用自然上少走彎路,必須尊重自然、順應(yīng)自然、保護(hù)自然。人類一旦傷害自然、破壞自然,就會(huì)被大自然所反噬,會(huì)反過來(lái)?yè)p害自身的利益。不僅如此,季羨林所解讀的天人合一思想還涉及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統(tǒng)一、人與自己的和諧統(tǒng)一。的確,燈紅酒綠的現(xiàn)代社會(huì)處在一個(gè)很快的發(fā)展節(jié)奏當(dāng)中,人們很少有時(shí)間停下來(lái)去審視自己與自然、與他人、與自身的關(guān)系。季羨林大師不僅在理論層面幫助我們深度理解天人合一思想,還給予我們具體的實(shí)踐方法,其呼吁我們擁抱自然,感受自然,注重與他人的溝通交流,建立良好的人際關(guān)系,關(guān)注自我需求,實(shí)現(xiàn)自我的全面發(fā)展。此外,《莊子·齊物論》中強(qiáng)調(diào),若是把整個(gè)天下縮小到比動(dòng)物秋天換的新毛的毛尖還要小,那么泰山也是小的了;若是把整個(gè)天下最長(zhǎng)的壽命縮短到比早早夭亡的小孩還要短,那么相傳活了八百歲的壽星彭祖也是短命的了。天地與我并生,萬(wàn)物與我合一。可見,萬(wàn)事萬(wàn)物,和諧共生,平等共存。
(三)生態(tài)取向的翻譯研究
1988年,彼得·紐馬克在《翻譯教程》一書中將文化所指分為了五個(gè)類型,分別是:生態(tài)文化,物質(zhì)文化(飲食、服裝、家居、交通),社會(huì)文化(工作、休閑),組織、習(xí)俗、活動(dòng)、程序、概念,體態(tài)、習(xí)慣[4]。可以看出,這五大類型當(dāng)中首當(dāng)其沖的就是生態(tài)文化。彼得·紐馬克強(qiáng)調(diào),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地理屬性會(huì)有所區(qū)別。就拿大家耳熟能詳?shù)挠?guó)浪漫主義詩(shī)人珀西·比希·雪萊的《西風(fēng)頌》中的西風(fēng)舉例,對(duì)于英國(guó)人而言,西風(fēng)是可愛的,充滿著生機(jī)的,西風(fēng)象征的是革命力量,是希望。但對(duì)于中國(guó)人來(lái)說(shuō),西風(fēng)是刺骨的,無(wú)生機(jī)的。地處歐洲西部的英國(guó),位于大西洋東岸,氣候是溫帶海洋性的,西風(fēng)帶給英國(guó)人溫和濕潤(rùn)的感覺。在英國(guó),西風(fēng)是暖風(fēng),西風(fēng)掠過,萬(wàn)物滋長(zhǎng),一片生機(jī)。中國(guó)的東南部臨海,西北部深居內(nèi)陸,氣候主體上是季風(fēng)氣候。秋季盛行西北風(fēng),西北風(fēng)寒冷刺骨,西部地區(qū)又是一片荒涼,西風(fēng)給國(guó)人一種凄涼、殘敗之感。1999年,大衛(wèi)·卡坦對(duì)翻譯生態(tài)文化進(jìn)行了細(xì)化分類,其指出,翻譯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包括物理和政治環(huán)境、氣候、空間、服飾、食品、嗅覺、臨時(shí)場(chǎng)景、所構(gòu)建的環(huán)境等。2003年,在《翻譯與全球化》一書中,米歇爾·克羅尼恩表達(dá)了對(duì)語(yǔ)種翻譯生態(tài)這一問題的重視,其希望譯者在各個(gè)語(yǔ)言的翻譯之間致力于達(dá)到一種健康平衡的狀態(tài)。
在國(guó)內(nèi),北京大學(xué)外國(guó)語(yǔ)學(xué)院世界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導(dǎo)辜正坤在《中西文化比較》一課中,所提出的人類文化演變的九大定律中首當(dāng)其沖的就是“生態(tài)環(huán)境橫向決定論”,這足以看出生態(tài)環(huán)境對(duì)于人類歷史的重要性。學(xué)者張明權(quán)、季羨林、崔啟亮等人也都曾借用翻譯生態(tài)的相關(guān)概念對(duì)翻譯問題進(jìn)行研究討論。
三、生態(tài)翻譯學(xué)的核心概念
(一)譯者中心
生態(tài)翻譯學(xué)指出,譯者是翻譯過程之中一切矛盾的總和,這大大彰顯了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無(wú)論是以原語(yǔ)、原文為中心,還是以目的語(yǔ)、譯文為中心,都顯得片面、極端[5]。萬(wàn)事萬(wàn)物講究平衡,翻譯也如同生態(tài)一般,有其規(guī)律性,譯者應(yīng)掌握翻譯的生態(tài)規(guī)律,在原文和譯文之間追求一定程度的平衡。人具有主觀能動(dòng)性,有目的、有計(jì)劃、有創(chuàng)造性,譯者也是如此。譯文的創(chuàng)作過程其實(shí)就是譯員充分發(fā)揮自身主觀能動(dòng)性的過程。用“譯者中心”這一翻譯理論指導(dǎo)翻譯實(shí)踐,要求譯員進(jìn)一步提升自身的翻譯水平和能力,樹立終身學(xué)習(xí)的理念,保持自律,積極完善自我。將翻譯作品與譯員緊密掛鉤,某種程度上也賦予社會(huì)一定的權(quán)力督促譯員的成長(zhǎng)。社會(huì)也可以出臺(tái)一系列的政策,獎(jiǎng)勵(lì)優(yōu)秀的譯員,適時(shí)淘汰那些躺平的譯員。
(二)適應(yīng)與選擇
生態(tài)翻譯學(xué)的理論根基是“翻譯適應(yīng)選擇論”,這要求譯者要在適應(yīng)中選擇,在選擇中適應(yīng)。原文、原語(yǔ)、譯語(yǔ)共同構(gòu)成了翻譯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所謂“適應(yīng)”就是指譯者要對(duì)這樣的翻譯生態(tài)環(huán)境進(jìn)行適應(yīng)。所謂“選擇”,則指的是作為翻譯生態(tài)環(huán)境適應(yīng)者的譯員要以這樣的身份對(duì)自己的譯文做出選擇。胡庚申教授曾經(jīng)指出,翻譯過程即為一種適應(yīng)加上兩種選擇,一種適應(yīng)就是翻譯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適應(yīng),兩種選擇就是譯者對(duì)翻譯生態(tài)環(huán)境適應(yīng)程度多少的選擇和最終呈現(xiàn)出什么樣譯本的選擇。
(三)三維轉(zhuǎn)換
生態(tài)翻譯學(xué)的基礎(chǔ)理論將翻譯方法簡(jiǎn)單概括為語(yǔ)言維、文化維、交際維的“三維轉(zhuǎn)換”。胡庚申教授曾指出,譯者需要在多維度適應(yīng)與適應(yīng)性選擇的大原則之下,來(lái)保持原文和譯文在這三個(gè)生態(tài)維度意義上的平衡、和諧。在語(yǔ)言維度上,譯者要通過選擇和適應(yīng)致力于保持不同方面、不同層次上語(yǔ)言形式的平衡,這些平衡包括詞義、句意、文風(fēng)、傳神達(dá)意、實(shí)用美學(xué)等等。在文化維度上,譯者要關(guān)注雙語(yǔ)文化的差異,關(guān)注雙語(yǔ)文化內(nèi)涵的傳遞和闡釋,要致力于掃除文化交流上的障礙。最后,在交際維度上,譯者要注重原文的交際意圖在譯文中的合理體現(xiàn),要讓目的語(yǔ)國(guó)家的讀者充分了解原文所表達(dá)的真正含義。中國(guó)譯協(xié)常務(wù)副會(huì)長(zhǎng)黃友義曾指出,我們中譯外有三大難點(diǎn),分別是:語(yǔ)言元素、思維元素、文化元素,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說(shuō)明生態(tài)翻譯學(xué)“三維轉(zhuǎn)換”這一翻譯方法的合理性。
四、生態(tài)翻譯學(xué)的國(guó)內(nèi)研究分析
截至2024年3月6日,打開中國(guó)知網(wǎng)網(wǎng)頁(yè)版,以“生態(tài)翻譯學(xué)”為主題在中文庫(kù)中進(jìn)行搜索,得到了4066條結(jié)果。在這4066條結(jié)果中,學(xué)術(shù)期刊達(dá)到2339條,占比57.5%,學(xué)位論文也達(dá)到了1261條,占比31%。在這些學(xué)位論文中,主體部分是清一色的碩士論文,只檢索到兩篇博士論文,分別是北京外國(guó)語(yǔ)大學(xué)郭長(zhǎng)譽(yù)的論文和南京中醫(yī)藥大學(xué)楊樂的論文。
以這4066條結(jié)果為數(shù)據(jù),我們結(jié)合發(fā)表年度和發(fā)文量,做出如下統(tǒng)計(jì)分析(根據(jù)知網(wǎng)):2008年1篇,2009年7篇,2010年21篇,2011年82篇,2012年131篇,2013年191篇,2014年273篇,2015年230篇,2016年268篇,2017年261篇,2018年298篇,2019年381篇,2020年427篇,2021年505篇,2022年516篇,2023年447篇。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2008年和2009年的發(fā)文量還只是個(gè)位數(shù),2014年至2018年,發(fā)文量都是200開頭。到了2022年,達(dá)到了峰值516篇。再拿具體的年份2008年來(lái)說(shuō),生態(tài)翻譯學(xué)的創(chuàng)始人胡庚申先生在《中國(guó)翻譯》上發(fā)表文章,對(duì)生態(tài)翻譯學(xué)做出了比較全面的解讀,學(xué)界更是對(duì)他本人做出了高度評(píng)價(jià),稱其是開發(fā)本土學(xué)術(shù)資源的一面旗幟。作為后來(lái)者,我們十分感謝胡庚申先生對(duì)該理論所作出的原創(chuàng)性貢獻(xiàn)。
針對(duì)文獻(xiàn)來(lái)源分布,我們也做出了結(jié)果分析(來(lái)源知網(wǎng)):海外英語(yǔ)265篇,英語(yǔ)廣場(chǎng)146篇,校園英語(yǔ)96篇,西安外國(guó)語(yǔ)大學(xué)42篇,作家天地41篇,開封教育學(xué)院學(xué)報(bào)40篇,北京外國(guó)語(yǔ)大學(xué)39篇,漢字文化36篇,上海翻譯35篇……可以看到海外英語(yǔ)、英語(yǔ)廣場(chǎng)、校園英語(yǔ)雜志以較大優(yōu)勢(shì)分別占據(jù)前三。這三本期刊都是比較基礎(chǔ)性的,對(duì)于學(xué)術(shù)初學(xué)者比較友好。而對(duì)于雙核期刊上海翻譯來(lái)說(shuō),其排名就略顯靠后。這也反映出國(guó)內(nèi)學(xué)者要多下功夫,繼續(xù)努力,生產(chǎn)出更高質(zhì)量的生態(tài)翻譯學(xué)論文,推動(dòng)生態(tài)翻譯學(xué)的長(zhǎng)遠(yuǎn)健康發(fā)展。
最后,我們還針對(duì)機(jī)構(gòu)分布,進(jìn)行了分析(來(lái)源知網(wǎng)):西安外國(guó)語(yǔ)大學(xué)59篇,鄭州大學(xué)58篇,天津大學(xué)51篇,北京外國(guó)語(yǔ)大學(xué)45篇,福建師范大學(xué)44篇,昆明理工大學(xué)43篇,廣西科技大學(xué)42篇,哈爾濱理工大學(xué)42篇……排在第一的是西安外國(guó)語(yǔ)大學(xué),其是新中國(guó)最早建立的四所外語(yǔ)院校之一。作為專業(yè)院校,其對(duì)生態(tài)翻譯學(xué)展開了較多研究也并不意外。此外,211、雙一流高校北京外國(guó)語(yǔ)大學(xué)也排在前四,雖然不見其他外國(guó)語(yǔ)專業(yè)院校的身影,但這兩個(gè)知名外語(yǔ)高校的上榜,也足以看出部分專業(yè)院校對(duì)生態(tài)翻譯學(xué)研究的重視。此外,211、雙一流院校鄭州大學(xué)摘得榜眼,985、雙一流院校天津大學(xué)也奪得探花頭銜。
結(jié)語(yǔ)
立足于本土的生態(tài)翻譯學(xué)是我們從事翻譯研究的新型范式。本文闡明了生態(tài)翻譯學(xué)的基本內(nèi)涵,梳理了生態(tài)翻譯學(xué)所誕生的國(guó)內(nèi)外背景,介紹了該理論中的核心概念。與此同時(shí),借助CNKI,本文也對(duì)該理論的國(guó)內(nèi)研究現(xiàn)狀展開了分析。筆者認(rèn)為,生態(tài)翻譯學(xué)為我們從事翻譯研究提供了新視野,廣大專家學(xué)者應(yīng)進(jìn)一步加大對(duì)生態(tài)翻譯學(xué)理論研究和實(shí)踐應(yīng)用的廣度深度。
參考文獻(xiàn):
[1]張?jiān)亞矗塘x明.生態(tài)翻譯學(xué)視角下中央文獻(xiàn)英譯策略研究[J].南方論刊,2023(11):85-86.
[2]胡庚申.生態(tài)翻譯學(xué)解讀[J].中國(guó)翻譯,2008(6):11-15.
[3]張杏玲,郭秋宏.生態(tài)翻譯學(xué)研究評(píng)述[J].英語(yǔ)廣場(chǎng),2018(08):41-42.
[4]段春錦.英譯漢過程中的文化所指現(xiàn)象及翻譯策略初探[J].云南財(cái)貿(mào)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7(02):147-148.
[5]張可欣.生態(tài)翻譯學(xué)視角下譯者中心研究——以芷江受降紀(jì)念館為例[J].文教資料,2021(10):4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