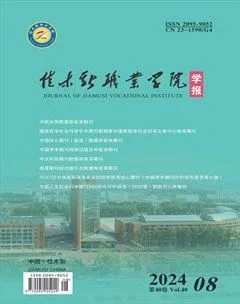《紅高粱家族》的隱喻翻譯研究
摘 要:近些年,中國文學作品中的隱喻翻譯問題,引起了翻譯界及學術界的熱議。實際上,隱喻翻譯在某些方面能夠影響到目的語讀者對文學作品的理解以及文本翻譯的質量。《紅高粱家族》自出版以來便被翻譯成法語、英語等多種語言。翻譯界對該小說的研究普遍局限在譯者主體性、語言風格、文化負載詞等層面上,而原文中的隱喻內涵、文化意蘊卻沒有得到廣泛的重視。本文以葛浩文譯本《紅高粱家族》為例,結合隱喻翻譯的內涵與概念,分析中國文學作品對隱喻翻譯的要求,探究葛浩文在此譯本中所運用到的隱喻翻譯策略。
關鍵詞:《紅高粱家族》;隱喻翻譯;葛浩文;譯本
中圖分類號:I046;H31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9052(2024)08-0046-03
引言
葛浩文是美國地位最高的中國翻譯家,已經翻譯了60多部中國文學作品,主要著作包括蕭紅的《馬伯樂》《生死場》《呼蘭河傳》,莫言的《酒國》《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勞》,王朔的《千萬別把我當人》《玩的就是心跳》,以及老舍、賈平凹、阿萊、李銳、王一安等作家的代表作品[1]。葛浩文翻譯的《紅高粱家族》,并非是對原始文本的直接轉移,而是從跨文化交際的維度出發,實現意義層面上的優化與轉換,通過注釋、刪除、轉換、說明等方法,讓莫言蘊含在隱喻中的思想內涵,人文理念,能夠以西方人能理解的形式呈現出來。換言之,葛浩文可以通過巧妙地隱喻翻譯,實現對一種文化向另一種文化形態的轉化,提高文本翻譯的感染力、影響力。
一、隱喻翻譯的概念與內涵
隱喻作為常見的修辭手法,一般被應用在文學作品的創作中,Newmark在《翻譯教程》中提到隱喻有“認知功能”與“美育功能”兩種。其中,“認知功能”主要指幫助讀者深層次、多維度地理解語句的內涵、意義及引申含義,可以豐富語句的思想內涵,強化文本的意象特征;而美育功能主要指將兩種不相干或聯系不大的“意象”銜接起來,整合起來。通過意象整合,重構語境意境,突出語篇文本的“藝術特征”,給人以審美功能及效果。約翰遜與萊考夫在《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中指出概念隱喻這一理念,讓隱喻研究“重心”逐漸從“修辭功能”轉變為“認知功能”,并且將隱喻的本質界定為:用一種經驗來理解另一種經驗的過程,是幫助人們更好地認知事物、強化意象認知的抓手。所以我們可以將隱喻作為一種輔助人們理解“事物”或“概念”的載體。而我國學者則認為隱喻是利用形象生動的“意象”,來闡釋抽象、復雜、多元概念的過程。是通過尋找兩種事物之間的相似性及關聯性,將具體、鮮明、形象的“意象體”,投射到模糊、抽象的概念域的過程,能夠幫助讀者輕松、自由、愉悅地獲得更深層次的體驗,正確自身的審美感受。而通過深層次地理解及探究,萊考特還將隱喻劃分實體隱喻、擬人隱喻、空間隱喻三種類型。其中實體隱喻主要指利用物質或實體來解釋經驗世界的過程;擬人隱喻則指通過人們自己的動機、目標、行動、特征,來理解事物本質及內涵的過程。至于方位隱喻是指通過空間概念。總而言之,“隱喻”是通過一種事物解釋另一種事物或概念的過程,可以更有效、更全面地幫助讀者了解作者所隱含的復雜思想,讓模糊的概念變得更加清晰、具體、生動,提高讀者對文本的認知深度及理解程度。
二、中國文學作品翻譯中隱喻翻譯的要求
在中國文學作品創作中,隱喻修辭的“價值指向”是幫助讀者更深程度、更全面、更有效地理解文本所蘊含的思想內涵,豐富文本的表現形式,強化讀者的閱讀體驗。而文學翻譯中,翻譯者對隱喻文本的翻譯,不應局限在文本意義的轉換上,要結合隱喻修辭的作用,通過刪除隱喻、將隱喻轉為釋義、用明喻翻譯隱喻以及“保留 原文 意象”等現實,強化讀者對原始文本的理解[2]。但由于隱喻修辭擁有較強的認知作用,所以翻譯人員可以從跨文化交際的維度,對原始文本進行靈活處理,使其蘊含的意識更明確、更直接,更能發揮隱喻修辭所擁有的審美作用,提高讀者的“閱讀感受”。
首先是深化理解。中國文學作品特別是小說和詩歌作品,能夠以“象征”“隱喻”“暗喻”等方式,將作者意象、思想鮮明而生動地呈現在讀者面前,使讀者更深層地理解作品所蘊含的人文意蘊。但要想幫助西方讀者理解文中的意蘊、理念、思想,不僅要從跨文化的角度出發,對文本內容進行優化、強化、轉變,還要結合目的語讀者的審美特征、認知特點、行為方式及思維習慣,進行語言方面的轉化。譬如將“你的命好大”,翻譯為“smiled on you”。能夠表達出“你真幸運,這種狀況下,還能安然無恙”的意蘊。由于“命”在我國古代哲學思想中擁有“命理”的意蘊,代表人的命運、壽命。如果進行直接翻譯,便會使西方讀者感到一頭霧水。而引入“上帝”的概念,將“上帝的微笑”與西方俚語結合起來,可以在跨文化的視域下,深化讀者對原文意蘊的理解。
其次是強化閱讀體驗。隱喻翻譯可以讓讀者在理解文本意蘊、思想、理念的前提下,獲得全新的審美體驗。使譯文作品擁有新的審美特征。特別在刪減不利于西方讀者認知的篇章內容后,翻譯者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和思考,再造一種新的意蘊與語境,使原始文本擁有新的文學特征。這種語境再造是通過再修飾、再加工的過程來完成的,可以讓翻譯文本在不影響原文意思的前提下,貼合西方讀者的文化背景,審美特點、思維方式,為其帶來全新的閱讀體驗。換言之,就通過“重新加工”“修飾文本”“語句重構”的方式,為西方讀者帶來適應其語言閱讀習慣的新語境。
三、《紅高粱家族》葛浩文譯本的翻譯策略解讀
文學作品是弘揚中國人文思想、民族情感及文化哲理的重要載體,在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小說《紅高粱家族》中,莫言通過運用多種隱喻、象征、暗喻等手法,將高密人和紅高粱緊密地連接起來,讓讀者體會到高密人強大的生命力與鮮明的性格。作者通過賦予紅高粱人性化的特點,以憤怒、驕傲、吟唱、歡笑等特點,讓紅高粱成為高密人的代表。葛浩文通過隱喻翻譯的方式,讓莫言賦予紅高粱的鮮明特點、特征、特性,更加直觀、更加鮮活、更加生動地呈現在西方讀者面前,使其以本民族文化的思維、情感、性格,感受、體悟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但要想靈活應用“隱喻翻譯”實現對兩種文化的充分融合,還需要翻譯者擁有較高的文學素養,不僅要深入理解原文所表達的思想,還要熟稔兩種文化體系、掌握豐富的翻譯技巧,通過明確文字表達的側重點,讓中國文學作品更易于被西方讀者所理解。
(一)直接翻譯
隱喻翻譯可以讓讀者更鮮明、更清晰地明確抽象而模糊的概念,深化對文學作品的理解與認知。但要想達到該效果,還需要翻譯者在深入理解原文語意的前提下,強化對語言意蘊、意境及思想的文化轉化。但更多時候,翻譯者需要直觀地呈現作者的思想意蘊,以直接翻譯的方式,呈現文學作品中的“喻體”及“氛圍”。譬如在《紅高粱家族》中“望著在他腳下的水汪汪里,野生著一枝綠荷,一枝瘦小潔白的野荷花,又望著對面火紅四射的高粱,吐口高唱:‘高粱紅了,東洋鬼子來了,國破了,家亡了……’”,葛浩文將其翻譯為:“ big tooth gazed at" THE WATERY WATER,THERE IS A GREEN LOTUS, A THIN WHITE WILD LOTUS, AND LOOKING AT THE FIERY SORGHUM OPPOSITE, HE SPITS AND SINGS: \"THE SORGHUM IS RED, THE JAPANESE DEVILS ARE COMING, THE COUNTRY IS BROKEN, AND THE FAMILY IS DEAD ...”在這里,翻譯者完整保留了野荷花的意象,指出他雖然生在臭水溝里,但葉子依舊是綠色的,花朵依然是潔白的。然而在翻譯腳下時,作者將“腳下”翻譯為“gazed down”[3]。這個動詞充分表達了莫言在《紅高粱家族》中所蘊含的意蘊,即紅高粱的地位,要比野荷花高。間接地表達出紅高粱更受人尊敬的含義。而結合全文語境能發現,通過暗喻手法寫野荷花,還能直觀地闡釋出余大年在面臨處決前“以死贖罪”“臨危不懼”的英雄氣概。如果在此處采用意義或省略等翻譯手法,便會導致莫言對野荷花、紅高粱、余大年三者的態度,以及三種意象所具體表達的涵義,很難得到呈現。
(二)確定“焦點”
隱喻翻譯的價值主要包括“修辭功能”與“認知功能”兩方面。其中認知主要指“通過讀者所能理解的事物來詮釋抽象而模糊的事物”,以生動形象的“喻體”,讓讀者更深層次、更有效地理解原文作者蘊含在文學作品中的思想、情感、意蘊。所以,如何明確作者主要表達的思想或意思,是隱喻翻譯的前提條件。譬如在“眾百姓在汽車周圍狼吞虎咽,沒有筷子、一路用手抓”中,葛浩文將“狼吞虎咽”翻譯為“wolfing down their food”,通過準確而鮮活的翻譯,表達了莫言的寫作意圖,強化了讀者對作品的理解。如果在這里,作者采用直接翻譯的手法,就會呈現出“狼”和“虎”兩種意象,難以將“狼吞虎咽”中“吃東西的人很餓”的意蘊,表達出來。所以,葛浩文通過“down their food”,將“意義表達”的重心聚焦于“食物”,強化了原文的主題和情感。又例如將“風利颼有力,高粱前推后擁,一波一波地動。路一側的高粱把頭伸到路中間,向我奶奶彎腰致敬。”翻譯為“The wind whizzed strongly, and the sorghum pushed forward and backed, moving in waves. The sorghum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reached its head into the middle of the road, bowing to my grandma.”在原句中,葛浩文將“高粱前推后擁”的動作描繪得淋漓盡致,賦予了“紅高粱”人的思想和情感[4]。然而在具體翻譯中卻聚焦于“高粱”擬人化的動作上,并沒有完全照搬原文語句的字面意思。譬如在翻譯“彎腰致敬”中,翻譯者通過巧妙用詞、選詞,凸顯出高粱對“我奶奶臨危不亂、膽識過人的氣度”的認可,體現出莫言蘊含在原文中的思想和情感。綜上所述,葛浩文在《紅高粱家族》隱喻翻譯中,首先明確的是莫言所表達的重點、內涵及思想,然后通過聚焦“意象”或“情感”的方式,讓文章語義和思想更加鮮明。
(三)語句重塑
在《紅高粱家族》中出現了很多諸如《水滸傳》《三國演義》等古典文學作品,以及經典語句,這些語句,蘊含著豐富的傳統文化思想,如果通過直接翻譯的方式對其進行處理,不僅難以幫助英語讀者理解其代表的含義,還容易讓翻譯者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吃力不討好[5]。并且還很難呈現原文作者的表達意圖。但如果刪除掉原文中的相關語句,不對其進行解釋的話,又會使讀者出現誤讀或理解不當的現象。葛浩文在翻譯《紅高粱家族》時,除了刪除了大量英語讀者難以理解的段落、語句,還對其進行重新架構與修飾。譬如將“我從小就看《水滸》《三國》,揣摩出一個道理,折騰來折騰去,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天下歸總還要落在一個皇帝手里……”翻譯為:“I've figured it out: struggles come and go, dragon. The split period precedes unity, and the long-term unity period precedes unity. Divided, but the country always falls into the hands of an emperor.”在這里葛浩文結合西方俚語、俗語以及認知習慣,刪除了原文中的古典名句,用西方人能夠理解的方式,重塑了語言意境。但莫言在原文中所表達的思想,得到了“保留”和“強化”。而為更好地詮釋中華傳統文化,葛浩文在結合英語讀者的認知規律、審美特點的前提下,對語句進行了補充和優化。譬如將“你簡直是魯班門前掄大斧……”翻譯為“You are simply the axe at the door of Luban, a famous carpenter in China”。即通過添加“木匠”這一身份,不僅能讓讀者理解原文意思,還能強化、突出中國古典元素。總之,葛浩文結合中西方文化差異,從讀者的視角對各種意象及詞匯進行優化,讓隱喻語句更加淺顯易懂,能夠被西方讀者所理解,進而為中國文學作品的海外傳播,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及支持。
結語
中國現代小說家莫言,他的作品在西方國家擁有較高的影響力及接受程度,不僅能被海外讀者所理解和接受,更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國際化傳播及發展,奠定了基礎。之所以,莫言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績,則歸功于葛浩文的隱喻翻譯。葛浩文在翻譯《紅高粱家族》的過程中,大量應用了各種隱喻翻譯手法、手段,讓中國文學作品中的文化思想、理念及意蘊,更好地呈現在西方讀者面前,從而使莫言的作品擁有了更廣泛地市場,同時為后世文學創作及翻譯,提供了可靠的借鑒及依托。
參考文獻:
[1]李已堯.論莫言小說與《史記》之關系——以《紅高粱家族》《檀香刑》《豐乳肥臀》中的英雄人物塑造為例[J].散文百家(理論),2022(04):40-42+46.
[2]孫若圣.作為事件的《紅高粱家族》日譯——以日本的中國新時期文學相關資料為線索[J].新文學評論,2022,11(01):82-89.
[3]胥瑾.作者、譯者、原文、譯文——莫言《紅高粱家族》中英版本對比研究(英文)[J].譯苑新譚,2021,2(02):11-25.
[4]陸雨薇,盧小雪,戈玲玲.從初始規范視角探析《紅高粱家族》中本源概念的英譯策略[J].海外英語,2021(04):55-56+78.
[5]鄭貞,郝麗華,來夢露.《紅高粱家族》英譯文中分敘事研究[J].連云港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20,33(02):4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