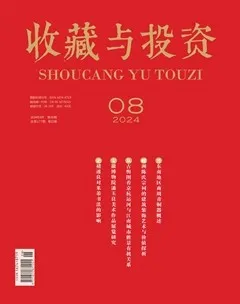1937—1949年蘇區紅色版畫藝術解讀
摘要:江西作為紅色文化的發源地,承載著革命期間濃厚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這些珍貴的物質文化通過圖像和文字的方式記錄和描寫了當時歷史的真實的抗爭樣貌和革命精神,同時也是當時地域性、時代性和民族性的完美融合。紅色版畫在1937—1949年期間蓬勃發展,這一時期的紅色版畫真實地還原了抗日戰爭時期社會的真實樣貌,記錄了革命英雄無畏的抗戰決心,通過黑白木刻極強的視覺沖擊力,吸引人們深思其藝術特征并解讀其精神價值。
關鍵詞:藝術特征;紅色精神;價值
江西是中國紅色文化的搖籃,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蘇區精神在江西廣為流傳。在這片土地上,出現了大批以刻刀形式記錄革命時期社會面貌的版畫家,他們將手中的刻刀作為戰斗的武器,以藝術宣傳的方式激勵革命戰士,喚起他們浴血奮戰的熱情,為中國革命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趙延年、張樂平、王琦、余白墅、梁永泰和吳忠翰等都是這一時期杰出的人物。筆者從這些藝術家的代表作品入手分析江西紅色版畫藝術的獨特魅力,感受當時江西紅色版畫帶給人民、軍隊的力量,分析他們是以怎樣的審美特征來詮釋作品的感染力。
一、紅色版畫的形式語言
版畫是一種通過印刷技術創作出來的藝術形式。版畫有許多種類,其中四種常見的印刷方式是凸版、凹版、平版和孔版。版畫藝術家通過使用刻刀或化學工具來創作各種圖案,材料包括木頭、石頭、橡膠、金屬、鉛、鋅等。他們將這些圖案轉換為可供觀賞的圖像,并將其印制到圖紙上。這種藝術形式不僅展現了作品的外觀,還反映了作品的內涵。馬克思曾經說過:“形式是內容的橋梁,它是內容的依托,沒有形式就沒有內容。”版畫是藝術家通過合適的物質材料將自己的思想物化,以圖畫的方式表達和傳遞,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生活觀念形態,真實地展現了底層人民的貧困和殘酷處境以及他們是如何被壓迫的。紅色版畫是一種藝術形式,它將革命斗爭與人民大眾緊密結合,展現了藝術家的創造力和想象力。
1937—1949年的紅色版畫旨在為人民大眾提供服務,其藝術形式以刻刀為抗日戰爭的戰斗武器,印出來的圖像則具有教化和宣傳的功能,與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思想緊密相連,同時也是民族性和生命力的體現。1931年,在魯迅的領導下,版畫家們積極探索符合當時國情和需求的文藝作品,無論是思想內容還是創作技法,這一時期中國的版畫都處于萌芽階段,需要向歐洲學習,特別是德國和蘇聯。1937年到1949年,抗日戰爭進入了快速發展的階段,成為紅色版畫發展的第一個高峰。紅色版畫是以人為主體的繪畫語言,它體現了人民的民族性,反映了當時人民在戰爭中的殘酷境遇以及革命將士不屈不撓、誓死保衛家國的堅定信念和信仰,是一種功能性的藝術形式。
二、江西紅色版畫的精湛技法
如果說內容是基本手段,那么技法則是使物化的語言轉化為精神的基本手段,能使作品以特定的語言和面貌呈現在觀眾眼前。在黑白木刻版畫中,最具挑戰性的技巧之一便是如何呈現灰色調。在木刻藝術中,黑白兩種極端顏色被視為基礎,但是通過運用多種刀具,如單獨使用或組合使用,可以將它們分割成各種不同的形狀,在大小、疏密度和寬度上有所變化,從而創作出豐富多彩的點、線、面。黑白木刻版畫的制作過程非常復雜,因為它需要高超的技藝才能夠準確地呈現物品的外觀和內部結構。如果版畫師的技術水平不高,那么他們就無法精確地完成任務,只能通過重新設計來彌補這一缺陷。因為每個人的主觀感受和看待藝術的方式都不同,所以我們無須拘泥于單調乏味的技巧,而是能夠輕松展示自己內心深處絢爛奪目的世界。呈現出完美的視覺效果需要版畫師根據客觀形象,結合各種因素精心安排,這樣每一個細節都能夠被完美地呈現出來。
三、江西紅色版畫的審美特征
(一)版畫的顏色之美
老子的“五色令人目盲”和莊子的“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這兩句話有深刻的哲理思想。《末一顆子彈》(圖1)是一幅充滿變化和節奏韻律的作品,它以黑白木刻的形式形成鮮明對比,帶給觀者強烈的視覺沖擊,給人以快感。在畫面中,一位勇士站在殘敗的樹干上,向敵人發射最后一顆子彈,煙霧繚繞,炮聲隆隆,戰場氣勢恢宏,令人震撼。盡管作品以黑白對比的方式呈現,但卻并不缺少戰斗的精神動力。當時的藝術家用黑色和白色對比來表達當時的心境,當最后的子彈被射出時,他們決心永遠活著,因為這代表了他們生命的最終意義。
(二)木刻的刀法之美
黑白木刻版畫的獨特魅力在于它的刀感,這種感覺來自刻刀與板材的摩擦,它展現了木刻版畫的藝術魅力。《搜索殘敵》(圖2)是一幅充滿情感色彩的木刻作品,其精湛的工藝和獨特的風格在當時很少見。刀法犀利而有力,黑白對比的節奏使作品充滿力量。雕刻者通過充分展現物體的特征,突出它的木質氣息。運用“留黑”的技巧,我們能夠精心地塑造獨具魅力的版畫造型;運用刻版水印技術,我們可以使大型陽刻作品具有鮮明的藝術感;采用精心設計的布局,將富麗堂皇、蕭瑟清新的風格融入其中,讓刻刀作品擁有獨特的藝術魅力;改變刀法,如刀的方向、力度、形狀、尺寸,可以為作品增添多種視覺沖擊,讓它們呈現完全不同的視覺效果。這不僅證明了實際戰斗生活的體驗是創作的靈感來源,并且體現了作品的犀利、生動、有力和感人,超越了歷史現實的題材,令人難以想象。
四、江西紅色版畫在當時社會環境中的價值體現
隨著木刻藝術的崛起,紅色版畫應運而生,并在中國近代藝術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為獨立的繪畫語言,也是當時真實的歷史資料,不僅有極強的功能性和政治性,更具有強烈的藝術性。因此,從紅色版畫的內涵和形式出發,進一步探尋其藝術價值,會發現江西紅色版畫是集歷史價值、精神價值和藝術價值于一體的歷史圖像。
(一)歷史價值

20世紀40年代,日軍大規模侵略中國,一大批愛國畫家為抗日救援,紛紛南下來到贛州,迅速和本地畫家組建了一支宣傳抗日、支援前線、抵抗戰爭的美術工作隊伍,這里的版畫題材以抗日戰爭時期的戰斗場面以及人民苦難的生活場景為主,這群版畫家去往前線,深度觀察、體驗和感受并形成思考。創作的紅色版畫以其獨特的視角和風格,真實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斗爭面貌,展現出英勇的革命戰士形象、普通民眾的生活場景以及當時的社會環境,它們不僅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而且還將革命歷史以圖像的形式呈現出來,令人深刻地感受到當時的精神氣質。通過觀察現實,我們選擇描繪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真實事件和場景,同時反映當時的民俗、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等多個方面。通過創作紅色版畫,我們可以捕捉當下的社會和文化特點,并且具有重要的歷史記錄意義。它們見證了新中國藝術的發展與演進,并且擁有寶貴的歷史資料。這些研究成果為我們了解中國藝術的發展歷程、革命進程以及國家建設提供了重要的參考。紅色版畫不僅是對中國革命歷史的一種紀念和贊美,而且在當今社會也是一種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工具。
(二)精神價值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應該從根本上探索一個民族的文化底蘊,把它們融入歷史悠久的文化傳統之中,從而實現對這種文化的基因測序。在這一時期,版畫作品展現了強大的藝術魅力。它們把民族精神融合在一起,讓人驚嘆不已。這些精神來自對祖國和人民的熱愛,以及對敵人的憎惡。1942年毛澤東發表了《講話》,引導我們發掘并繼承中國的傳統文化遺產,并走上了藝術大眾化的道路。雖然紅色版畫已經存在了半個多世紀,但版畫仍然展現了對民族性藝術的追求和時代精神。它們的核心價值在于提高人們的精神境界,引人深思。深入探索中國革命歷史,感受英雄人物的偉大精神,是一種非常有趣且直觀的方式。這種藝術形式不只是通過簡單的描述來展示中國革命歷史上的人物和事件,還通過藝術的方式來表達某些內容,從而喚醒公眾的愛國精神和道德意識。通過創作紅色版畫,我們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國的革命歷史,激發愛國熱情,增強歷史責任意識。創作紅色版畫,不只是為了捕捉人物和事件,而是希望通過它傳遞一種能夠激勵人們成長和成功的精神力量。
(三)藝術價值
紅色版畫是一種具有深遠影響力的藝術形式,它通過對歷史的反思、對現實的描繪,展現人們對于傳統文化的熱愛與尊重。“剛健”“質樸”的獨特之處在于它的創新性,它不僅是一種現代藝術形式,還是一種超越了傳統的審美體驗。“剛健”“質樸”不僅擁有令人驚嘆的美學氣息,而且擁有簡潔而有力的形式。其色彩對比鮮明,整體造型力度強大,令人嘆為觀止。通過學習紅色版畫,我們可以創造一種簡潔而富有裝飾性的作品,這種作品呈現出鮮明的對比度和張力,是傳統繪畫方式無法達到的效果,就像“以刀代筆”和“有力之美”一樣;紅色版畫巧妙地營造了鮮明的對比和和諧的漸變,展現了豐富多彩的世界;通過獨特的手法和技巧,我們創造了一種與傳統版畫截然不同的藝術形式,它既不是簡單的模仿,也不是簡單的復制。紅色版畫以單純的藝術手法表現了豐富的歷史社會生活內容,其表現內容是通過一定藝術加工后的藝術真實,貼近生活又不拘泥于現實的表象。雖然其創作帶有明確的政治性目的,但是總體上未忽視藝術的自律性,創作方式也符合藝術規律,既關注社會性又不忽視藝術性。
五、結語
江西是紅軍長征后的一個重要根據地,革命文化盛行,紅色意識形態在當地深入人心,這也為江西紅色版畫的涌現、傳播打下了基礎。1937年至1949年這一時期,江西在贛州、信豐、宜春、上饒等多地開展了以版畫為抗日宣傳工具的活動。江西版畫在語言表達上可以說是一種獨特的藝術形式,它既體現了作者的藝術理念,也展示了作品的內涵,從而展現出蘇區的獨特魅力。紅色版畫是解放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致力于推動新的思想觀念的發展,并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

作者簡介
李長英,女,漢族,四川廣元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術學理論。
參考文獻
[1]尚輝.人民的藝術:中國革命美術史[M].石家莊:河北美術出版社,2019.
[2]馮婉婉.版畫家江克安研究[D].南昌:江西師范大學,2021.
[3]龔寶香.江西紅色文化題材美術創作研究[D].南昌:江西師范大學,2014.
[4]陳璐璐.紅色版畫的藝術特征及其流變研究[D].無錫:江南大學,2020.
[5]汪洋.論中國“紅色版畫”的概念及其研究范疇[J].美術大觀,2006(6):10-11.
[6]汪洋,楊德忠.論紅色版畫在新中國成立初期(1949—1966)的發展境遇[J].美與時代(下),2012(5):84-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