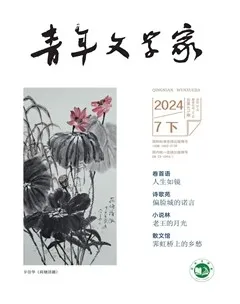一種情懷,兩套筆墨
李長之在《魯迅批判》一文寫道:“單以文字的技巧論,在十七年來的新文學(xué)的歷史中,實(shí)在找不出第二個(gè)可以與之比肩的人。”魯迅作為堅(jiān)定、冷峻的新文化戰(zhàn)斗者,將一腔幾欲噴薄而出的家國情懷與極高的藝術(shù)技巧相融匯,以文言和白話兩套筆墨,提筆書寫,執(zhí)筆救國。
一、主體的分裂:文言與白話表現(xiàn)初析
蘇聯(lián)漢學(xué)家謝曼諾夫在《魯迅的創(chuàng)新》中指出:“魯迅有許多言論以及他的創(chuàng)作實(shí)踐是同他對(duì)本國小說徹底否定的態(tài)度相反的。”“另一位美國漢學(xué)家威廉·萊爾也指出魯迅的語言風(fēng)格‘既受外國文學(xué)的強(qiáng)烈影響,又從中國古典文學(xué)得益不少。這些古典文學(xué)使他的語言極為簡練。這一點(diǎn)似乎難以解釋,因?yàn)檫@古典詞匯正是提倡白話的文學(xué)革命想要丟棄的東西’。”(廖高會(huì)、吳德利《在白話與文言之間:魯迅小說語言詩化邏輯探析》)縱觀魯迅的作品,不難發(fā)現(xiàn)他在文章創(chuàng)作過程中往往運(yùn)用白話文體系進(jìn)行寫作,《狂人日記》《阿Q正傳》《故鄉(xiāng)》等膾炙人口的篇目都是以白話寫成,即使在今天讀起來也朗朗上口、毫不費(fèi)力,這也極符合魯迅提倡白話文的新文化戰(zhàn)斗者身份,是魯迅以筆尖鑿破“黑屋子”的“第一錘”,為當(dāng)時(shí)黑暗愚昧的社會(huì)拉響了警笛。
盡管在文學(xué)改良運(yùn)動(dòng)中,魯迅堅(jiān)定高舉“提倡文言,反對(duì)白話”的旗幟,在《二十四孝圖》中公開表明對(duì)文言的反叛:“我總要上下四方尋求,得到一種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來詛咒一切反對(duì)白話,妨害白話者。”他也曾在《現(xiàn)在的屠殺者》中把支持、固守文言者視作“現(xiàn)在的屠殺者”。但值得關(guān)注的是,自1912年刊行的《〈古小說鉤沉〉序》,到《唐宋傳奇集》的序言和《稗邊小綴》,直至他逝世的前一年為上海聯(lián)華書局作《小說舊聞鈔》的再版序言,魯迅一生中為校勘古籍所作的三十五篇序跋均為文言形式。他在學(xué)術(shù)研究方面的著述亦以文言為載體,如對(duì)后世影響頗為深遠(yuǎn)的《漢文學(xué)史綱要》,在寫作時(shí)用詞擬句極為考究,雖短小精悍,卻注重對(duì)偶排比、煉字?jǐn)嗑洌Z言接近四六駢儷之文,華美鏗鏘,情感飽滿。魯迅在《寫在〈墳〉后面》承認(rèn)自己曾看過許多舊書,“因此耳濡目染,影響到所做的白話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體格來。但自己卻正苦于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shí)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這“古老的鬼魂”正是文言傳統(tǒng),它是魯迅在白話文運(yùn)動(dòng)中力圖擺脫而在創(chuàng)作實(shí)踐中難以擺脫的文化因子。他亦曾提到“協(xié)其同,偶其詞,使讀者易于上口,則殆猶古之道也”(《漢文學(xué)史綱要》),文言筆墨的運(yùn)用亦是他寫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隨著新文學(xué)創(chuàng)作實(shí)踐的深入發(fā)展,魯迅等白話文倡導(dǎo)者們對(duì)于語言的理解也越發(fā)深入,其態(tài)度發(fā)生了一定轉(zhuǎn)變,魯迅也不例外。1928年,他在《革命與文藝》中已經(jīng)開始強(qiáng)調(diào)文藝的審美價(jià)值,對(duì)文言文和文學(xué)遺產(chǎn)也主張“拿來”,批判地繼承民族遺產(chǎn)。1934年4月,他在《致魏猛克》信中所說的“新的藝術(shù),沒有一種是無根無蒂,突然發(fā)生的,總承受著先前的遺產(chǎn)”,更是印證了這種態(tài)度。
二、創(chuàng)傷的療愈:文言與白話緣由再探
那么,對(duì)于魯迅兩套截然相異筆墨的運(yùn)用,我們應(yīng)如何看待呢?對(duì)此,魯迅曾對(duì)學(xué)術(shù)著述使用文言話語系統(tǒng)親自進(jìn)行過說明,他在由北京大學(xué)新潮社出版的《中國小說史略》序言中提到:“又慮鈔者之勞也,乃復(fù)縮為文言。”節(jié)省版面、慮“鈔者之勞”自然可以作為一個(gè)理由,但不免流于表面。
究其深處,魯迅作為一名清醒而富有遠(yuǎn)見卓識(shí)的革命者,對(duì)文言和古文化本身并無偏見,只是反對(duì)其中的糟粕和所謂的“正統(tǒng)”。魯迅曾在《隨感錄四十七》中提到:“古典是古人的時(shí)事,要曉得那時(shí)候的事,所以免不了翻著古典。”他年輕時(shí)大量閱讀古文古籍,在進(jìn)入三味書屋前便已讀完“四書”,進(jìn)入學(xué)堂后接著閱讀《詩經(jīng)》《書經(jīng)》《易經(jīng)》《左傳》和《禮記》等。可以說,作為古典文化土壤中成長起來的新文化巨人,魯迅本身就已深深打上古典文化的烙印,古文根底早已植入他的血脈之中。他主張解放個(gè)人、改造國民性,才能拯救中國,這當(dāng)然是振聾發(fā)聵的新生吶喊,但其中蘊(yùn)含著的個(gè)體完善意義,與古代儒家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這也體現(xiàn)了魯迅對(duì)古典文化的認(rèn)同和延續(xù)。我們將他對(duì)文言的看法與對(duì)醫(yī)學(xué)的態(tài)度相比較便不難理解了,魯迅的父親曾被中醫(yī)誤診致死,導(dǎo)致學(xué)醫(yī)出身的他從此對(duì)中醫(yī)深惡痛絕。然而,他怨恨的真的是中醫(yī)醫(yī)術(shù)本身嗎?非也,他所深切憎惡的是那些照本宣科、不懂裝懂的醫(yī)生,是文言話語系統(tǒng)中那些死板教條、阻礙思想解放的糟粕罷了。魯迅在新文化建設(shè)中所做的工作,樁樁件件無不是經(jīng)過慎重思索與謀劃的。雖偶有激憤之言辭,容易使人們誤解誤讀,但其目的終是將陳腐的枷鎖以雷霆之力狠狠打破,為思想解放鋪路。他說:“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里開一個(gè)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huì)來調(diào)和,愿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時(shí)白話文之得以通行,就因?yàn)橛袕U掉中國字而用羅馬字母的議論的緣故。”(《無聲的中國》)在這種情境下,極端偏激的引導(dǎo)方式只是一種應(yīng)對(duì)當(dāng)時(shí)國內(nèi)局勢(shì)的策略。實(shí)際上,在魯迅的語言視野里,文言文和文言傳統(tǒng)絕非僵死的廢物。由此可見,魯迅并非極端地選擇非黑即白,他在古典與現(xiàn)代、文言與白話的巧妙應(yīng)用上,有自己適當(dāng)?shù)某叨群涂剂俊?/p>
其次,學(xué)術(shù)研究著作以及序跋的特殊性決定了以文言形式進(jìn)行寫作較白話更為適合。正如他自己所說:“沒有相宜的白話,寧可引用古語,希望總有人會(huì)懂,只有自己懂得或連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來的字句,是不大用的。”(《我怎么做起小說來》)對(duì)于中國古籍和中國古典小說的評(píng)述來說,文言能在某些特定的語境下發(fā)揮獨(dú)有的作用,那種細(xì)微的、意境上無法言喻的貼切是白話所不能替代的。例如,1932年7月出版的,用駢儷文作成的《〈淑姿的信〉序》一般,面對(duì)一些中國風(fēng)、中國情調(diào)較強(qiáng)且具有濃郁民族特色的評(píng)說對(duì)象,魯迅也常用文言。他對(duì)于古籍整理后的序跋寫作和文字校注,也往往以文言出之,更能與原作銜接融洽。另外,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xué)史綱要》兩部文學(xué)史著作皆以文言寫成。究其原因,除了某些特定的文言學(xué)術(shù)性詞匯還未在白話文中找到相對(duì)應(yīng)的表達(dá)方式外,便是他想借中國古典文藝?yán)碚撝ΓㄔO(shè)中國現(xiàn)代文藝批評(píng)話語系統(tǒng)。綜上,文言語體的應(yīng)用是魯迅基于評(píng)說對(duì)象、論述形式及寫作目的等綜合考量下的自覺選擇。
再次,文言與白話發(fā)展的不平衡也是其原因之一。語言是社會(huì)的一面鏡子,在魯迅那個(gè)時(shí)代,白話處于萌芽后蓬勃發(fā)展的階段,尚有不完善之處。但文言作為先秦后統(tǒng)一的書面語言,已成為社會(huì)上約定俗成的通用語言系統(tǒng),積淀著民族精神文化傳統(tǒng),受眾極為廣泛,具有一定的穩(wěn)固性和保守性。而且,文言具有簡潔凝練、含蓄蘊(yùn)藉等白話所不具備的特點(diǎn),用以寫作能夠帶給讀者獨(dú)特的審美感受,是一種藝術(shù)和美的體現(xiàn)。另外,文言在近代文化交流的激烈碰撞下獲得巨大發(fā)展,早已不可同日而語,它的敘事能力和表達(dá)能力都具有大幅度的提升。近代社會(huì)中,嚴(yán)復(fù)和林紓等人的翻譯,已經(jīng)顯示了文言在表達(dá)現(xiàn)代事物時(shí)的容量與彈性。在經(jīng)歷了嚴(yán)復(fù)和林紓的翻譯之后,很難說存在著文言不能表達(dá)的現(xiàn)代事物或者內(nèi)容。文言的美感和重要性,使它即使在“五四”時(shí)期白話文成為語言正宗后,也并未徹底退出歷史舞臺(tái)。此外,瞿秋白曾對(duì)“五四”后的白話文進(jìn)行批評(píng):“造成一種風(fēng)氣:完全不顧口頭上的中國言語的習(xí)慣,而采用許多古文文法、歐洲文的文法、日本文的文法,寫成一種讀不出來的所謂白話,即使讀得出來,也是聽不懂的所謂白話。”(《大眾文藝的問題》)由此可見,當(dāng)時(shí)的白話確實(shí)發(fā)展得不夠完善,日常書寫、文字交流尚且會(huì)造成“四不像”文字,更何況是知識(shí)性、綜合性極強(qiáng)的學(xué)術(shù)研究著作和序跋呢?
此外,想要發(fā)展白話文,必然從文言之中提取養(yǎng)料,尋求新舊之間的持續(xù)性。魯迅在論及現(xiàn)代語文建設(shè)時(shí)曾有這樣的言論:“至于對(duì)于現(xiàn)在人民的語言的窮乏欠缺,如何救濟(jì),使他豐富起來,那也是一個(gè)很大的問題,或者也須在舊文中取得若干資料,以供使役。”(《寫在〈墳〉后面》)以文言為基礎(chǔ),豐富和發(fā)展白話文,是傳統(tǒng)語言邁向現(xiàn)代的必經(jīng)階段。那么,對(duì)文言的探索寫作,便是不可或缺的過程。
三、靈魂的指引:文言與白話相輔相成
在魯迅創(chuàng)作的話語系統(tǒng)中,文言與白話是無法完全割裂的。二者相互作用、相輔相成,共同造就了魯迅特有的語言風(fēng)格,即文言式白話或白話式文言,這亦可看作是語言的一種過渡形態(tài)特征。
一方面,魯迅的白話中摻雜著文言因子,帶有古雅的特點(diǎn)。普實(shí)克指出:“對(duì)于優(yōu)秀的現(xiàn)代中國短篇小說,例如魯迅的短篇小說,如果要在中國舊文學(xué)中追溯它們的根源,那么這根源不在于古代中國散文而在于詩歌。”(《普實(shí)克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論文集》)這實(shí)際上點(diǎn)明了魯迅小說語言詩化的根本原因,即所謂民族的詩性精神。他在《為了忘卻的記念》中是這樣寫的:“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huì)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shí)候的。”簡單一段話,頻繁使用“但”“即使”等虛詞曲盡其妙,造成迂回曲折的閱讀感受,符合魯迅敏捷而富有戰(zhàn)斗性的思維邏輯。此外,在《準(zhǔn)風(fēng)月談·談蝙蝠》中,有一段這樣的論述:“道士要羽化,皇帝想飛升,有情的愿作比翼鳥兒,受苦的恨不得插翅飛去。想到老虎添翼,便毛骨悚然,然而青蚨飛來,則眉眼莞爾。”雖是白話文,卻將兩兩相對(duì)的駢句融合其中,“毛骨悚然”“眉眼莞爾”等詞語更是用得巧妙妥帖,汲取了古典文化的靈氣,具有獨(dú)特的古雅之美。魯迅欣賞莊子逍遙自在的浪漫抒情精神,他曾說自己的白話文除了“字句、體格”外,“就是思想上,也何嘗不中些莊周韓非的毒,時(shí)而很隨便,時(shí)而很峻急”(《寫在〈墳〉后面》)。他亦推崇魏晉風(fēng)度的清峻、通脫、華麗、壯大,贊美屈原的“雖懷內(nèi)美,重以修能,正道直行”(許壽裳《屈原和魯迅》)。這些美學(xué)訴求與人格導(dǎo)向,與魯迅吶喊、反抗的詩性精神一致,在他的作品中有著淋漓盡致的體現(xiàn)。
另一方面,魯迅的文言中夾雜著白話元素,具有一定的創(chuàng)新性。魯迅主張“我們要說現(xiàn)代的,自己的話;用活著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無聲的中國》)。在“五四”啟蒙文化語境中,魯迅始終認(rèn)為語言變革是改造國民思想的關(guān)鍵,因而提倡使用口語白話寫作。正所謂“造詞心理是文化心理”的反映,在那個(g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大環(huán)境下,即使是運(yùn)用文言進(jìn)行書寫,也免不了受到歐化語言等形式的影響。例如,他在《文化偏至論》中提出了“意力”一詞,這是將叔本華和尼采在哲學(xué)上的“意志”觀念與中國古典儒學(xué)的“內(nèi)省諸己”等進(jìn)行了融匯嫁接。與嚴(yán)復(fù)的“民力”相類似,魯迅對(duì)“力”進(jìn)行了著重的強(qiáng)調(diào),注入了符合中國實(shí)際情況的社會(huì)效用,旨在為國民輸入剛健之力,從而改造國民性。又如《摩羅詩力說》中的“神思”起源于古希臘的神話故事,指“神的思索”,魯迅以“拿來主義”將他應(yīng)用到自己的創(chuàng)作中,單指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這些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詞,不僅體現(xiàn)著魯迅極高的學(xué)術(shù)造詣,更體現(xiàn)著時(shí)代作用下國民獨(dú)特的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此外,魯迅還大量借鑒外國文學(xué)中的浪漫主義表現(xiàn)手法。在創(chuàng)作《斯巴達(dá)之魂》時(shí),魯迅便將浪漫主義和傳奇色彩融入其中,推崇拜倫、雪萊、萊蒙托夫等人“動(dòng)吭一呼,聞?wù)吲d起,爭天拒俗,而精神復(fù)深感后世人心,綿延至于無已”的戰(zhàn)斗力量。
魯迅始終胸懷家國,以改造國民性、拯救愚昧麻木的人們?yōu)榧喝危尾【热耍瑥囊欢K;以兩套筆墨作為武器,以筆痕寫心跡,為槍為刃,戰(zhàn)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