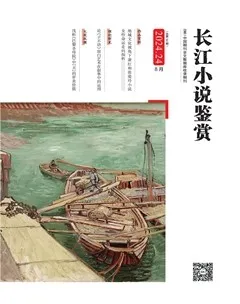被建構的“瘋女人”
[摘" 要] 《白鹿原》是陳忠實歷時六年完成的長篇小說,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里程碑。在這部小說中作者塑造了許多經典的悲劇女性形象,其中掙扎在情欲與倫理間的“瘋女人”冷秋月便是其中之一,本文將圍繞冷秋月這一“瘋女人”形象展開研究。陳忠實在小說中詳細地講述了在白鹿原這個封閉大環境下,冷秋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瘋癲悲劇的,同時向我們證明了“瘋女人”并非生而瘋癲,而是后天形成的。“瘋女人”的形成不僅是父權制社會下對女性的壓抑與規訓的產物,同樣是在“三從四德”傳統思想道德下,女性地位低下喪失話語權的結果。此外“瘋女人”的“瘋癲”所表現出來的并非只是表面上的病理性特征,它還是“失語”女性向壓迫她們的父權社會所做出的抗爭與發聲。
[關鍵詞] 《白鹿原》" 冷秋月" 父權" 瘋女人
一、引言
《白鹿原》塑造了許多悲劇女性的形象與命運,陳忠實曾經說過,他在白鹿原的縣志里發現二十多卷縣志中有四五卷都在記錄“貞潔烈婦”,他在閱讀后大受震撼,因此在小說中許多女性的命運其實就是歷史中的還原。在那個“男尊女卑”的時代下,女性的瘋癲為我們展示了她們在特殊時代里的創口。
本文對白鹿原上的女性形象冷秋月做了詳細的描述與分析,對于她瘋癲的原因與過程做出了分析與解讀,結合白鹿原時代下的大背景分別從父權制、女性的“失語”等角度分析她瘋癲表象背后的要素與原因,并且展現了那個時代下女性生存所受到的冰冷殘酷的對待與作為抗爭者的女性們悲慘的結局。同時,本文將“瘋女人”的“瘋”進行了一定的歸類,對“瘋女人”本身的含義做了一定的解讀,對“瘋女人”問題背后所隱藏的文化話語與深層原因進行了探究。
二、《白鹿原》中的女性命運
1.白鹿原的女性
提到《白鹿原》小說中的女性形象,或許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具有強烈反叛精神的田小娥,她美麗堅強且質樸,不顧封建禮教的壓力,與黑娃私奔。在吃人的封建禮教下,燃燒而又反叛的田小娥就像一把熱烈的大火,投身于這片深不見底的淤泥,最終化為烏有。
在白鹿原,另有一位女性同樣反叛,她是白鹿原第一位不纏小腳并且進入私塾讀書的奇女子——白靈。她是婦女解放的象征,是正義的化身[1]。但就算像這樣的新時代女性也逃脫不了舊時代的魔爪,她沒有像英雄一樣英勇地犧牲在戰場上,卻被活埋在了自己人的肅反運動中。她是深受自由思想熏陶的靈魂,卻被舊時代的厚厚烏云扼殺在了這片黃土地里。
在白鹿原,封建禮教下對人的束縛使人的正常欲望得不到發泄,使人的思想逐漸扭曲。本文主要介紹的對象——冷秋月,便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生長起來的。冷秋月在白鹿原的中醫世家作為長女出生,在冷先生的精心培育下,成長為十里八鄉有名的冷大小姐,成了父親最出色的作品。她的父親將她打造成了舊時代下最完美的賢妻良母,讓她如機械般地執行著封建禮教的程序。但即使如此,冷秋月最終也沒有逃離寒冬臘月獨自慘死的命運。
2.冷秋月的悲劇與瘋癲
“無性也無情”的包辦婚姻注定不幸。鹿兆鵬不接受傳統,卻被父親強行送進洞房。冷秋月期待丈夫會和她生兒育女,和她一起撫養孩子,但鹿兆鵬卻選擇出走。丈夫的消失讓她陷入疑心和恐懼之中,丈夫的不辭而別、公婆的搪塞及父親的冷漠讓冷秋月內心備受折磨。
丈夫重新回到白鹿原,但他的冷漠與客氣讓她徹底心寒。冷秋月因為丈夫的拒絕和公婆的謊言而意識到他不會給她愛,最終導致她對愛的渴望徹底落空,心中最后一根支柱轟然倒塌。同時,冷秋月只有洞房時的性體驗,在長時間的壓抑中,她開始做夢,夢里與身邊的男人顫抖,但她也渴望著隱秘。她無法宣泄與傳統思想相抵觸的罪惡感和對性的欲望,這些進一步折磨著她的內心。
冷秋月的公公鹿子霖在外面喝酒晚歸,她幫他開門時被當成了自己的老婆輕薄,這讓她感到非常憤怒和羞辱。她選擇用麥草放在飯里來報復公公,但公公只是默默地吃著飯,讓她感到既期待又恐懼。在欲望和倫理的折磨中,她決定向公公示好,并說希望他在家里喝酒而不去別的村。這讓鹿子霖感到震驚,他設計讓兒媳吃下麥草后羞辱道:“你才是吃草的畜生!”,最終把冷秋月的尊嚴踩在了腳下。
鹿子霖并沒有意識到這成了壓倒冷秋月的最后一根稻草。她失去了禮教,對愛與性的渴望被否定,終于瘋了。她在忍耐中爆發,大喊:“俺跟俺爹好!俺跟俺爹好!”[2]奔跑和狂叫,傾訴心中的憤怒與不甘,父親的藥換來更加瘋癲的冷秋月。她悲傷大吼:“我有男人跟沒男人一樣守寡,我沒有男人守寡還能掙個貞節牌坊,我有男人守活寡圖個啥,他兒子不上我的炕,他爸愛上!”[3]
冷先生開了一劑“猛藥”毒啞了自己的女兒,她變得一言不發。“三天兩天不進一口飯食,爬到水缸前用水瓢舀涼水喝,隨后日漸消瘦,形同一具骷髏,冬至交九那天夜里死在了炕上。”冷秋月的死是丈夫的拒絕,是父親的冷漠,也是公公的輕蔑,她徹徹底底地死在了父權制社會的荼毒里,壓死在了封建禮教這座大山之下。
三、冷秋月瘋癲的原因
1.父權制下的規訓
冷秋月的父親冷先生是白鹿原上有名的醫生,深受鄰里鄉親的尊敬。他對女兒的教育非常重視,希望將她培養成一個知書達理的大家閨秀。冷先生向她灌輸“在家從父,出嫁從夫”的三從四德扎根于她的大腦,也為她加入鹿家后因為性的缺失逐漸走向壓抑與瘋狂埋下了重要的導火線。從福柯的觀念來說,冷先生的做法是一種將規訓與懲罰的手段運用到了極致的表現,冷先生通過控制女兒的一言一行,對女兒行為舉止的規范制定了嚴格的標準,是一種從上而下的監視與凝視,在這種極度的高壓之下他迫使女兒不得不遵循這樣的賢妻良母準則,最后通過這套價值準則讓女兒心甘情愿地約束自己、規范自己,最后徹底喪失對自我的管制,成為男權社會下對女性要求的典范。
中國傳統社會對女性有一套極為嚴格的標準對女性行為進行道德規范,在這套價值體系的背后是父權社會下對女性的規訓與迫害,它使女性逐漸失去對個體的控制走向了人道主義的反面,使女性在成長的過程中面臨著極為沉重的壓力以及對七情六欲等正常生理需求的被壓抑與被扭曲。在這種由上而下的監督監視體系下,女性最終被馴服、被同化成為加害者如白趙氏[4],被扭曲走向崩潰與毀滅如冷秋月。
正如福柯提到的微觀權力理論,對于白鹿原的女性來說,白鹿原就是一個巨大的監獄,每一個女性都是它監獄場里關押的囚犯,它通過人們日常的話語、行為規范來約束著每一個個體,使女性在成為受害者的同時而不自知,且用這套封建綱常來束縛壓抑著自己與他人的本我,最終成為父權制下的犧牲品。
2.女性的“失語”
白鹿原白鹿村正發生從傳統到革新的歷史大變革,這時的白鹿原出現了像白靈、鹿兆鵬等進步青年,但同時更多的則是祖祖輩輩扎根于這里的封建大家族,在這樣的現實下,即使是有著報國熱情與進步思想的白靈也無法逃脫以白嘉軒為首的封建大家長的控制。在傳統的父權社會體系里女人的作用就是傳宗接代,這也是為什么文章的開篇寫道“白嘉軒這輩子最引以為豪的事情就是娶了七房女人”,這樣的男尊女卑社會導致了對女性的輕賤,斷絕了女性的地位,使女性永遠依賴男性而存在。
女性作為工具與物品,她的訴求與聲音不會被任何人重視,即使是一輩子勤勤懇懇為白家生兒育女相夫教子的白趙氏也逃不了悲慘的結局。白趙氏在死前想見自己女兒最后一面,也被白嘉軒用謊言欺騙了。就像西蒙·波伏娃在著名的《第二性》中講到:“一個女人之所以成為女人,與其說是天生的,不如說是后天形成的”[5],在白鹿原里我們能看到的只有女而沒有人,在小說中除了像田小娥、白靈這樣的女性,小說中更多時候向我們呈現的是如白趙氏、鹿冷氏、黑牡丹、白牡丹、大姐兒、二姐兒這樣的女性角色,她們遵循“三從四德”,最后卻連自己的名字都沒有。她們出嫁前是父親家的客人,出嫁后又成了夫家的生育機器,個別更甚者只有一個代號來叫喚自己,是丈夫旁邊的無名人士,是子孫出生后的保姆,沒人知道她們的名字、也從沒人聽到過她們的需求[6]。一個“透明人”沒有話語權,她們就這樣默默地活在白鹿原上,死在白鹿原里。
冷秋月的生理性需求被壓抑、被禁忌,同時她的情感需求同樣得不到滿足,這種畸形的婚姻使她在一天天的被忽視中逐漸被壓抑、被扭曲,最后當它到達一個再也無法承受的臨界點時,冷秋月只能通過“瘋癲”的方式將自己被雪藏、被變形的情感大聲地傾訴出來,此刻她將女性內心的憤怒與不甘以暴風般的“瘋癲”大聲宣講,讓在場每一位男性的丑陋與陰暗無處可逃,她的話語如響亮的巴掌打紅了男人的臉,撕開了白鹿原男性可笑的遮羞布,但同樣使她被冠上了“瘋子”的枷鎖,最終,作為被社會邊緣化的“瘋女人”,她的話語、她的歇斯底里都在世人異樣的眼神里化作對“瘋子”的恐懼與避讓。
四、被建構的“瘋女人”
1.病理學概念下的“瘋女人”
通常我們在談到“瘋女人”時更多地想到的是行為舉止異常的“瘋人”,她們會出現與常人不同的行為,或是情緒不能自控,或是重復完成同一個相同的動作,對他人或自己展現出攻擊欲望等特征。“危險”“混亂”是我們對于這些“瘋人”的第一印象,因此可以說,文學意義上的“瘋”與病理學意義上的“瘋”或多或少是有部分貼切的。
同時我們在說到病理學概念上的“瘋”時,我們可以用更準確的醫學概念來定義,即“精神障礙”也就是“精神疾病”,它主要表現為意識清醒、無反應、精神錯亂、狂躁癥、出現幻覺、行為不受自己控制等癥狀[7]。因此,病理學概念下的“瘋女人”一般是指受到過巨大的痛苦或者沖擊導致其出現了“精神障礙”相關疾病癥狀的角色。
這樣的角色更能使人清晰地直面感受到女性內心所遭受的巨大不幸與黑暗,如《祝福》中的祥林嫂,在受到丈夫去世被婆婆賣給別人做老婆以及阿毛被狼叼走的巨大打擊后,使她難以承受,逐漸癡傻成為世人眼中的瘋女人,在同村人的耳邊一遍遍的重復著阿毛的悲慘經歷。同樣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有吉爾曼《黃色墻紙》中的“我”,在“我”產后抑郁以后丈夫不聽從“我”的訴求,用自己的方式將“我”囚禁在精致的房間里,以至于“我”的精神狀態越來越差,同時,“我”逐漸自我意識模糊在黃色墻紙里看到想要逃離的女人,最終在房間里徹底陷入瘋癲,在房間里四肢爬行并且撕碎所有的墻紙,將進入房間的丈夫嚇暈。可以看到病理學下的“瘋女人”更多的是向我們展示女性在男權社會下受到的冷酷對待與不公平的境遇。
2.文化意義下的“瘋女人”
在福柯的《瘋癲與文明》中我們可以看到,“瘋癲”一詞從古至今人們對待它的態度是不大相同的。在17世紀以前人們往往認為瘋子是受到了上天的某種啟發的人,如著名的柏拉圖提出的“迷狂說”,直至中世紀以后人們仍然認為“瘋癲”與“拯救”相關,也就是說17世紀以前的人們認為“瘋癲”是一種獨特的象征;17世紀后,麻風病人的出現使當時出現了許多隔離醫院,那些醫院后被用來關精神病人,此時人們看待“瘋子”的態度開始發生轉變,認為他們是獸性的且非理性的。而現代社會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因此,“瘋癲”逐漸成了人們排斥的對象。對于“瘋女人”這樣的形象我們更應該看到她背后的隱喻。
“瘋癲”的態度轉變讓我們想到女性群體的“失語”,父權制角度下有兩種女性,一種是完全順應男性指定的規則下的順從的、乖巧的、無害的、為男性服務的“天使”;另一種則是不符合男性喜好、叛逆獨立、不遵循父權制規則下的“瘋女人”[8]。
在《白鹿原》中,我們可以看到冷秋月發瘋后被毒啞的原因是她的“瘋話”觸及了鹿子霖和冷先生所代表的封建倫理綱常的權威,同時在讀者看來自由果斷的白靈,當她真的違背到了父權制的威嚴時,白嘉軒也會毫不猶豫地將他這個女兒掃地出門。因此,在文化意義里談到的“瘋女人”更多的是不符合父權制度下規訓標準的女性。
所謂“瘋女人”就是女性開始對不合理的父權制度提出反對與抗爭時,受到的來自父權制度的強烈打壓與排斥,成為他人眼中的“特殊群體”。如白鹿原的冷秋月、閣樓上的伯莎,由于壓抑與迫害受到常人所不能及之折磨,使她們貼上了病理學特征的瘋女人標簽。不論是在孤獨中發瘋的冷秋月還是被羅切斯特以各種堂而皇之的理由束之高閣的伯莎,被邊緣化的她們逐漸被男權社會“孤立”“流放”,以瘋病為理由徹底剝奪了她們的話語權[9],將她們一切的訴求打成瘋病的“罪行”。
正如吉爾伯特在書中所言:“寫作使得瘋女人、一個瘋狂而又憤怒的女人獲得了解放,獲得了言說的權利”。[10]伯莎與冷秋月的遭遇最終都化作了歇斯底里的“瘋癲”式的吶喊與反抗,理性的外表承載不下她們真實的面孔,她們只能通過“瘋癲”表達抒發出內心里最強烈的欲望與憤怒。“瘋女人”是時代下女性不幸命運的化身,同時也是對權威發出反抗的“挑戰者”。
五、結語
在陳忠實的筆下的“瘋女人”們,如白鹿原上的田小娥、白靈、冷秋月這樣的女性,她們為爭取自身的權利付出了近乎慘烈的代價,她們是時代下女性真實的命運與悲歌,同時也是作者大膽地揭示封建禮教下慘無人道的悲劇,是對她們處境的同情以及對封建禮教的唾棄。這樣的性別悲劇,不是時代的,是永恒的。同樣,在文化作品里的“瘋女人”們,她們既是對現實社會里女性殘酷境地的訴說者,同時也是尋求女性自我,突破男權文化束縛的反抗者。
參考文獻
[1] 劉晨晨.《白鹿原》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分析[J].文化學刊,2022(1).
[2] 楊一鐸.“女性”的在場“女人”的缺席——《白鹿原》女性形象解讀[J].廣西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nbsp;版),2014(1).
[3] 陳忠實.《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
[4] 王鳳秋.女性物化的悲歌——《白鹿原》女性形象悲劇意蘊探析[J].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07(1).
[5] 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第二性》[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
[6] 尹季.《白鹿原》中三類女性形象的文化內涵[J].船山學刊,2003(2).
[7] 孫振曉.精神病理學[M].西安:陜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
[8] 程錫麟.天使與魔鬼——談《閣樓上的瘋女人》[J].外國文學,2001(1).
[9] Ellen,E,Berry.The Mad woman Can’t Speak,or,Why Insanity is Not Subversive(review)[J].Mfs Modern Fiction Studies,1999.
[10] GILBERT SANDRA M.amp; GUBAR SUSAN and APPIGNANESI LISA.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M].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20.
(特約編輯 楊" 艷)
作者簡介:劉若涵,西北大學現代學院文學院,研究方向為漢語言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