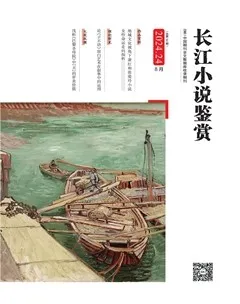地域文化視角下蕭紅和張愛玲小說女性命運走向探析
[摘" 要] 地域文化研究中引入女性、文學研究是一種新模式。通過地域文化視角,對比分析蕭紅、張愛玲筆下的女性命運走向的異同,發(fā)現(xiàn)東北地域的女性在寒冷、漠視、抗爭中走向艱難、悲慘與無奈,而滬港地域的女性在逼仄環(huán)境、悲慘時代、戰(zhàn)亂城市中走向沉默、痛苦、蒼涼的結局。進一步分析發(fā)現(xiàn),自然環(huán)境與文化形態(tài)中都分別直接或間接影響女性命運走向,但蕭紅筆下的女性命運受自然環(huán)境影響更大,更有可視性,更富有抗爭精神,張愛玲筆下的女性則更多因文化而扭曲,命運結局朦朧,更妥協(xié)軟弱。
[關鍵詞] 地域文化" 蕭紅" 張愛玲" 女性命運走向
地域文化研究屬于文化研究領域,近年來逐漸成了學術熱點。在地域文化研究中引入女性、文學研究是一種新模式,目前已有部分研究者選擇使用。縱觀蕭紅、張愛玲的文學作品,一方面她們都塑造了大量具有地域特色的典型女性形象,另一方面她們的性格特征與創(chuàng)作思維都透過地域空間描寫而清晰展現(xiàn),本文選擇從地域文化視角對蕭紅、張愛玲小說展開研究。
目前相關的研究中,對蕭紅小說中的東北地域文化探討較為豐富,研究者普遍認同蕭紅小說中女性的命運同地域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而對張愛玲小說中的滬港地域文化與女性命運的探討則偏少。此外,從地域文化視角分析,對比蕭紅、張愛玲小說中的女性命運的相同點與不同點也是一個少有涉及的研究角度。
本文中涉及的女性命運走向是一個操作性定義,指的是女性在一個地域下的生命結局及其走到結局過程中命運的趨向變化。本文試圖探討蕭紅、張愛玲小說中東北、滬港兩個地域文化與女性命運走向之間的關系,并對比二者的相同點與不同點,以期挖掘蕭、張小說中女性命運走向同地域文化的新關聯(lián)。
一、東北地域文化視角下蕭紅小說中的女性命運走向
蕭紅小說多發(fā)生在東北地域,塑造了一個以黑龍江呼蘭縣為原型的,以“呼蘭河鎮(zhèn)”為主的地域文化空間。在這一空間中,她書寫出多種多樣的女性角色,走向艱難、悲慘、無奈的結局。
1.寒冷中女性走向艱難人生
東北,這片位于中國最北端、最偏遠的區(qū)域,夏天短暫而溫暖、冬天寒冷而漫長,以其極端的、大部分時間并不宜居的氣候條件為生活賦予了荒涼而艱難的主旋律。長期以來的地廣人稀、植被稀疏、景色蒼涼,加之歷史上限制糧食生產(chǎn)的政策、“嚴禁屯墾”導致的物資匱乏共同編織了一幅女性生存艱難的背景圖。
在這種環(huán)境下,女性的生存格外艱難,在身體和精神上都承受了由寒冷帶來的痛苦后果。一方面,寒冷在日常生活上對身體產(chǎn)生損害,使得女性的生命體驗荒涼。如《生死場》中,在肅殺的冬日里,王婆仍要“用冷水洗著凍冰的魚”[1],洗得“兩只手像個胡蘿卜樣”,鼻子上也生出斑點;月英最終在“大樹號叫,風雪向小房遮蒙下來”的寒冷冬日里悲慘死去。另一方面,寒冷深刻殘害了女性的精神。東北的冬天過于寒冷,女人們只能縮在屋子里討論著各種隱私話題;孩子們跑出去玩凍裂手腳,媽媽們并不關注他們的身體狀態(tài),只是以暴怒、瘋狂的心情去摧殘孩子,她們“永久瘋狂著”,精神上極度壓抑孤獨。地獄般的寒冷加劇了女性命運的悲慘性,讓女性在身體和精神上更加艱難而痛苦。
2.漠視中女性走向悲慘結局
特定時期的東北地區(qū)的文化形態(tài)注定了女性的生命是不被重視的,一步一步走向悲慘的結局。
“十年前村中的山,山下的小河,而今依舊似十年前”[1],近乎凝固的時間帶來的是東北地區(qū)民俗、文化的落后與野蠻。由于文化閉塞、地域偏遠,20世紀時東北地區(qū)流行著薩滿教。這類宗教重視原始的求生本能,信仰“農家無論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過人的價值”[1]。人們重視莊稼、牲畜的價值遠遠大過女性,女性幾乎沒有獨立個體的人格和價值,只被視作家庭中的生育工具,只能不停地懷孕生子,永久體驗不到靈魂。愚昧的思想為懷孕的女性帶來了沉重的死亡風險。《呼蘭河傳》中的王大姑娘因為第二胎難產(chǎn)死去;《王阿嫂的死》中的王阿嫂因生育而“發(fā)出她最后沉重的嚎聲”,最后自己和新生的孩子相繼死去;《生死場》中月英因為生育而變成了癱瘓;五姑姑的姐姐在生育時“苦痛得臉色灰白”,赤身著一點都不能爬動,幾近死去。生育的痛楚也不被伸張,五姑姑的姐姐在難產(chǎn)時被醉酒的丈夫用冷水潑醒,并“一點聲音不許她哼叫”,她痛苦到“身邊若有毒藥,她將吞下去”的境地。生育為彼時的東北女性帶來了非人的痛苦與折磨,但這卻是當時她們存在的唯一價值。
東北地區(qū)無邊的寒冷與偏僻也賦予了東北男人極大的野性,使得女性承受了性方面的苦難。男性作為“性”行為的主導者,并不在乎女性的身份、年齡或精神狀態(tài),粗暴地在女性的身上釋放自己的欲望。性的發(fā)生場所多種多樣,時間也毫無限制,如《生死場》中的成業(yè)在高粱地、墻角的灰堆、炕上等各種地方占有金枝;在金枝快要生產(chǎn)時,成業(yè)仍然不管不顧發(fā)泄自己的獸欲,導致金枝直接承受了生產(chǎn)時極大的痛苦。這種身體里流淌的野性讓男性無法控制住自己的欲望,隨意地對女性施暴,而女性也因此備受摧殘。飽受性與生育苦難的女性在這樣的文化形態(tài)中被嚴重漠視,逐漸走向悲慘的結局。
3.抗爭中女性走向無奈命運
在東北地域里,土匪盛行,“人們崇羨著土匪的力量和威懾”[2],許多人民身上存在著一種匪氣。在東北女性的生命中,這種匪氣表現(xiàn)為流淌著的剛強血液,她們敢于抗爭,但最后仍然無奈地走向人生的悲劇。
東北女性的身體、精神都是剛強的,她們曾奮起反抗。她們有著健壯的身體與剛硬的性格,如《呼蘭河傳》中“脾氣大”[3]的王大姑娘、高大結實的小團圓媳婦等等,動不動就說“要回家”,和欺壓她們的人廝打;她們敢于反抗欺壓、敢于表達,精神上異常堅韌,如《生死場》中的勇敢抗爭的王婆。她跟隨趙三,但從不低眉順眼,在趙三提到家中賣掉的青牛時不耐煩地說“人家的了,就別提了”,展現(xiàn)出不服從、不應和的生存狀態(tài)。
但這些奮起反抗的女性最終也會走向無奈的結局。《小城三月》中的翠姨曾突破桎梏,生長于傳統(tǒng)封建家庭的她“萌發(fā)了愛情的憧憬”[4],愛上了才華橫溢的堂兄,在精神上完成了對封建包辦婚姻的超越。但她終究無法突破禮教的束縛,不能違抗父母的命令,對愛情、自由的渴望只能永遠藏在心中。這種矛盾的痛苦使得她“只盼望趕快死,拼命地糟蹋自己的身體,想死得越快一點兒越好”[5],最后在無奈中郁郁而終。《生死場》中的金枝在丈夫死后,為養(yǎng)活自己進城打工卻慘遭侮辱。于是她奮起反抗,打算“做尼姑去”,遠離讓她痛苦的過往。卻因為連年的戰(zhàn)亂,“廟庵早已空了”,終究只能走向無奈的悲劇結局。
二、滬港地域文化視角下張愛玲小說中的女性命運走向
張愛玲小說多發(fā)生在滬港地域,以上海、香港兩座都市為基本空間,塑造了多種多樣的女性角色,走向沉默、痛苦、蒼涼的結局。
1.逼仄世界內走向沉默
滬港地區(qū)氣候溫暖濕潤,幾乎沒有冬天,非常宜居。由于臨海的優(yōu)越地理位置加之一些重大歷史因素的影響,上海、香港成了國際化的“都市”,異常繁華。都市人口密集,高樓聳立,形成了龐大的小市民階級群體,但是人的生存空間狹小,生活環(huán)境逼仄。小說中都市中的女性的活動空間多為家庭住所[6],如《傾城之戀》中白流蘇一家居住的白公館;或是“公寓”,如《心經(jīng)》中許小寒一家住的公寓。在這樣的逼仄壓抑的空間中,女性逐漸變得沉默,逐漸失去對未來、對自我的追求。
逼仄的世界讓女性被限定在家庭內,女性無力再追求自我。《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的丁阿小作為哥兒達家中的仆人,她生活在像個蒸籠一般的“亭子間”中,日復一日地忙碌著。早上她帶著兒子百順前往主人家,照顧他吃飯上學后,繼續(xù)在緊小的廚房中收拾做飯,替主人接電話,直到為主人鋪完床才能離去回家。她雖然內心渴望成為“都市女性”,卻沒有時間和金錢打扮自己、追尋自我,不得不用自己微薄的收入肩負起維持家庭生活的責任。
在兩個狹小、擁擠的空間中重復地工作、生活,阿小逐漸變得沉默。面對自私無能的丈夫的請求,她淡然應允;面對主人要求出門前提前鋪床,卻沒告知出門時間的無理任務,她只應聲去做,即使自己與百順因大雨而不能回家,勉強把棉被鋪在菜板上入睡也毫無怨言;面對骯臟的樓下,她也不再想替人“掃掃掉”,而只漠然地一瞥,想著“好在不是在她的范圍內”[7]后便不再理會。被生活所迫的她不能再做成為都市女人的夢,只能過著一潭死水般的生活,慢慢走向無盡的沉默。
2.悲慘時代里走向痛苦
20世紀初,世界列強將香港作為殖民地、在上海設立租界以傳播西方文化,同時也使得上海、香港建設起了高樓聳立的城市景觀。中西方文化在城市中激烈地交織碰撞,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思潮在同一空間中同時產(chǎn)生影響。時代浪潮中,無論女性追求什么樣的道路,都無可避免地走向痛苦。
部分女性接受新式教育,追求解放與平等,開始自我覺醒、自我救贖,但結局依然痛苦。《半生緣》里的顧曼楨受過新式教育,在辦公室中做打字員營生。她堅持“家里的開銷由我拿出來”[8],心疼為養(yǎng)活家人做舞女的姐姐,在姐姐嫁給了祝鴻才之后,她用自己的雙手奮斗著,“在下班以后多做兩個鐘頭事情”以維持家中的開支。她熱烈地愛著沈世鈞,卻被祝鴻才卑鄙的手段所脅迫,不得不離開自己的愛人。即使歷經(jīng)非人的折磨,她仍然保留著強烈的自我意識,從沒有放棄過逃離的希望。在她的努力下,她逃離了祝鴻才,重新見到了沈世鈞,完成了對自我愛情的救贖。但結局卻是異常悲涼的:沈世鈞早已結婚。“他們回不去了”,她在痛苦時所思索的、期盼的一切卻還是“永別了,清清楚楚,就跟死了的一樣”。曼楨拼盡全力地自我救贖卻還是走向了痛苦。
而部分女性卻被浮華裹挾,瘋狂于世俗的金錢與愛欲,同樣也墜入了蒼白的深淵。《金鎖記》中的曹七巧本身性格純良溫柔,但在曹家這一封建家庭中,父母早亡的她備受欺凌。她被自己的哥哥賣給姜家換取錢財;丈夫身患疾病,這具“沒有生命的肉體”[9]讓她在姜家也毫無地位。她精神上無法得到滿足,唯一支撐她的便是“黃金欲”[10],即對錢財?shù)目是蟆7旨乙院螅X財盡數(shù)落空,她重燃了對愛情的期待,愛姜季澤到“迸得全身的筋骨與牙根都酸楚了”,但姜季澤為人懦弱又只會算計,讓七巧心里對情感的渴望又一次落空。她變得瘋狂,轉而對自己的女兒長安和兒子長白展開了報復。她阻撓長白的婚姻,逼死了兩個兒媳,讓長白“不敢再娶了,只在妓院里走走”;她無法接受長安獲得幸福,對女兒的愛情淡薄冷漠,向童世舫講述女兒曾吸食鴉片的過去,讓長安也“早就斷了結婚的念頭”。最終她被所有人痛恨,“戴著黃金的枷鎖”,最終痛苦地死去。
3.戰(zhàn)亂城市中走向蒼涼
基于高樓林立的都市樣貌,滬港地區(qū)生發(fā)出一種獨特的文化形態(tài),即為市民文化。生活在滬港地區(qū)的小市民們只注重世俗,只追求自我的欲望的滿足而漠視他人的生存境遇。20世紀40年代,中國正經(jīng)歷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戰(zhàn)火紛飛、生靈涂炭;香港早已被瓜分,上海從“孤島”變成“淪陷區(qū)”,兩地建立起的都市景觀都遭遇了一定程度的沖擊。盡管遭受侵略,已然形成的市民文化并未遭到根本的破壞。女性作為弱勢群體,同時面臨著市民文化的延續(xù)與戰(zhàn)火紛飛的局勢,在生存和精神上都困境重重,走向了蒼涼的結局。
生存上,市民文化使得女性關切世俗的自我,末世氛圍逼迫女性重視生活的際遇。女性渴求滿足自我的欲望,但又難以自我謀生,不得已依附男性而生活。《傾城之戀》中的白流蘇離婚后被家人冷嘲熱諷,世俗的流言蜚語讓她“決定用她的前途來下注”,把握住范柳原以滿足自己被他人艷羨的欲望。白流蘇曾想過與范柳原分開,但“家庭的壓力”、年華的老去讓她自甘“下賤”,追隨范柳原來到了香港。連天的戰(zhàn)火讓白流蘇發(fā)覺“他若是死了,若是殘廢了,她的處境更是不堪設想”,她無法離開范柳原獨自生存了。最終白流蘇得償所愿,和范柳原結了婚,回到了上海。但她卻“有點悵惘”,從此她真的能夠幸福嗎?她和范柳原并沒有真切的愛情,正如結尾所說,這只能是一個“說不盡的蒼涼的故事”。
精神上,市民文化導致女性之間相互欺凌,末世氛圍讓她們精神不斷崩潰,唱出蒼涼的悲歌。《小艾》中的席家的五太太生活在戰(zhàn)亂年代的上海。雖然身處封建家庭,但她身上卻有著小市民階級的特征:欺軟怕硬。她仗著自己是姨太太便欺負身為仆人的小艾,使喚她在深夜掃地,罵她是“丫頭胚子懶骨頭”[11]。但面對三太太的欺壓,她只是“怔了一怔”,卻不敢加以反駁;甚至害怕強硬的奴仆陶媽。她從沒有被人重視過,萬分痛苦。但在戰(zhàn)火紛飛的上海,她沒有獨自生存的能力,不能離開家庭,只能“怪她娘家,怪她婆家的人,現(xiàn)在又怪上了小艾”,她將所有痛苦、憤怒都釋放在小艾身上。戰(zhàn)亂中,她的丈夫欠債逃走,她依附于丈夫的財產(chǎn)也被全部收走,她大病一場,性格也變得陰沉、愛計較,精神已經(jīng)游走在崩潰的邊緣。最終她病重,得知丈夫早已死去,自己“拖到第二天晚上就死了”。在戰(zhàn)亂中猶如浮萍的她本身已經(jīng)精神慘痛,丈夫的身死更是成了壓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終她的結局也分外蒼涼。
三、兩者對比
1.相同點
蕭紅和張愛玲筆下的女性命運走向存在一定的共同點。在地域文化的影響下,女性所處環(huán)境都是極其艱苦的,命運走向都具有悲劇性。蕭紅所寫的東北地域寒冷異常、文化落后,不斷蠶食著女性的身體和精神,最終一步步走向悲劇的結局;張愛玲塑造的滬港地區(qū)戰(zhàn)爭頻發(fā)、環(huán)境逼仄,女性無法謀生、無路可走,最終只能走向無可挽回的悲劇。
此外,東北、滬港地域文化中的自然環(huán)境都對女性命運產(chǎn)生了直接影響。東北地區(qū)漫長寒冷的冬季直接摧殘了女性的軀體,諸如王婆等人手鼻被凍紅凍僵,甚至在風雪呼號中死去;滬港地區(qū)高樓林立的城市景觀直接壓縮了女性的生活范圍,像生存在逼仄狹小的空間中的丁阿小一樣,失去全部的生命熱情,走向痛苦蒼涼的未來。
兩個地域的文化形態(tài)對女性命運產(chǎn)生的影響則都具有間接性。文化形態(tài)對女性的戕害并非直接顯現(xiàn)的,而是通過潛移默化影響身居高位的“施暴者”即男性或被同化的女性而實現(xiàn)的。蕭紅筆下的東北地域盛行落后愚昧的薩滿教,男性及被同化的女性切實地對女性施加精神上的貶低與價值上的漠視。正如《呼蘭河傳》中小團圓媳婦被丈夫、婆婆扔進熱水中“驅鬼”,最后悲慘死去一樣,導致東北女性悲劇的命運的正是這些文化形態(tài)中身居高位的施暴者。張愛玲筆下的滬港地域受西方思潮的影響,金錢與愛欲成了部分女性追求的真諦。欲望并不會摧毀女性,但被欲望纏身的“上位者”女性會施暴而摧毀其他女性的命運,《金鎖記》中日漸瘋狂的曹七巧壓迫女兒長安使其命運蒼涼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2.不同點
蕭紅和張愛玲筆下的女性命運走向也存在一些差異。蕭紅塑造的女性生命結局具有強烈的明確性,女性只有兩條路可以選擇:要么如奮力抗爭的金枝、王婆等在痛苦中繼續(xù)茍活,要么像被滾水燙死的小團圓媳婦和因生產(chǎn)癱瘓、死在冬日里的月英一樣走向死亡的結局。張愛玲所創(chuàng)作的女性生命結局則具有較大的開放性與朦朧性。同曹七巧、五太太一樣死亡的女性并不多,大部分女性在戰(zhàn)亂中仍然存活著,像是迷惘悵然的白流蘇、失去希望的顧曼楨,帶著無法磨滅的痛苦,走向蒼涼的人生。張愛玲不曾交代明確的生或死,這些女性的命運就仿佛一條沒有盡頭的道路,無法用絕對的語言來描述,永遠是朦朧、開放的。盡管生命結局都偏向悲劇,但蕭紅筆下的女性人物身上流淌著東北的“匪氣”,懷有強烈的反抗精神,比如在身體上對男人的性壓迫做出了抗爭的金枝、在精神上反抗了封建婚姻制度的翠姨;張愛玲筆下的女性則充斥著市民階級的軟弱,少有反抗的思想,這些“五太太”“顧曼璐”們只會對強大的男性妥協(xié),轉而壓迫比自己弱小的女性。
此外,二者的地域文化為女性帶來的苦難側重點也不相同。蕭紅筆下的女性苦難多來自東北地域艱苦的自然環(huán)境。偏僻的地域導致人民信奉愚昧的薩滿教,寒冷的氣候帶來身體的痛苦、精神的殘暴,自然環(huán)境使得東北女性承受著無邊的痛苦與絕望。張愛玲筆下的女性苦難則多來自滬港地域壓抑的文化形態(tài)。連年的戰(zhàn)亂讓女性失去了自我謀生的能力,世俗的市民文化讓女性相互殘害,受到精神的重創(chuàng)。混亂的文化形態(tài)扭曲了女性的人格,讓她們沉溺于蒼涼與苦痛中。
四、結語
蕭紅筆下的女性在東北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和封閉的文化形態(tài)中飽受折磨,在寒冷中走向艱難、在漠視中走向悲慘、在抗爭中走向無奈。張愛玲筆下的女性在滬港浮華的都市環(huán)境和混亂的文化形態(tài)中痛苦掙扎,在逼仄世界里走向沉默,在悲慘時代中走向痛苦,在戰(zhàn)亂城市內走向蒼涼。她們塑造的女性都受到自然環(huán)境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身體、精神上都受到寒冷或逼仄帶來的傷害;都受到彼時文化形態(tài)對女性深重的影響,而走向消極或悲慘的人生結局。不同的是,蕭紅筆下的女性更多因自然環(huán)境而產(chǎn)生苦難,生死結局更加明確,女性只能痛苦地茍活或者悲慘地死去,但也具有一定的抗爭精神。反觀張愛玲,她筆下的女性則多是因文化形態(tài)而扭曲,結局生死不明、充斥著朦朧之感,大多以軟弱、妥協(xié)的態(tài)度去面對人生的悲歌。
綜上所述,本文觀察、總結了蕭紅、張愛玲小說中女性的生存環(huán)境和條件,揭示了在不同的地域環(huán)境下女性的生命體驗及結局,對比了蕭、張筆下的女性命運走向的相同之處和不同之處,豐富了從地域文化視角分析、對比人物命運走向的研究內容,在一定程度上為研究地域文化對女性命運的影響提供了可參考的資料。
參考文獻
[1] 蕭紅.生死場[M].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
[2] 喬晶.論東北作家群筆下的地域寫作[D].哈爾濱師范大學,2017.
[3] 蕭紅.呼蘭河傳[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
[4] 梁馨予.蕭紅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分析[D].東北師范大學,2018.
[5] 蕭紅.小城三月[M].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16.
[6] 張妍.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小說中的都市空間[D].吉林大學,2014.
[7] 張愛玲.紅玫瑰白玫瑰[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
[8] 張愛玲.半生緣[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
[9] 張愛玲.傾城之戀[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
[10] 傅雷、傅敏.傅雷文集·文學卷[M].安徽: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
[11] 張愛玲.怨女[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
[12] 齊彩虹.論蕭紅小說的女性意識[D].河北師范大學,2013.
[13] 齊秀娟.地域文化視野中的蕭紅小說及其創(chuàng)作心理研究[D].東北師范大學,2006.
[14] 李思琪.張愛玲小說的戰(zhàn)爭敘事研究(20世紀40—70年代)[D].暨南大學,2016.
[15] 范雨,錢華.張愛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解析[J].今古文創(chuàng),2022,(31).
[16] 段緒懿.論張愛玲《金鎖記》中的曹七巧形象[J].名作欣賞,2009(17).
(特約編輯 范" 聰)
作者簡介:連若涵,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院,研究方向為近現(xiàn)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