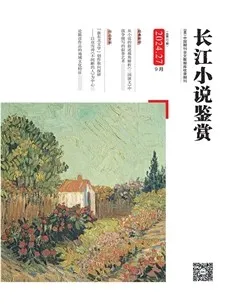生命的堅忍
[摘 "要] 余華的小說《活著》中蘊含著極為深刻的生命哲理,以時間為軸,表現了在極端困境中,生命展現出的驚人的韌性與堅持,反思了生命的意義與價值,體現時間的無情與生命的有限。同樣,小說更是以巧妙的設計,展現了人性中的善良與溫暖,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也不放棄對希望的追尋,最終強調活著本身就是對生命最大的尊重與熱愛,無論遭遇何種苦難,都應珍惜并堅持活下去。
[關鍵詞] 余華 "生命 "命運 "哲理
[中圖分類號] I10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27-0007-04
在當代文學作品中,余華的《活著》無疑是一部引人深思的著作,不僅照亮了人性的幽暗角落,更深刻揭示了生命在逆境中的堅韌與光輝。《活著》是中國當代作家余華創作的一部長篇小說,小說借助主人公福貴跌宕起伏的一生,展現了命運的無常與人在苦難中的抗爭精神,揭示了個人命運與社會變遷的交織,以及帶來的深刻痛楚,深刻揭示了在大時代背景下普通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態與人性光輝。《活著》中的福貴從富家少爺淪為貧苦農民,經歷了內戰、土地改革、“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社會變革,目睹并親身經歷了家庭成員相繼離世的巨大悲痛。然而,在無盡的苦難面前,福貴依然選擇堅強地活下去,展現了生命的頑強與堅韌。這部作品誕生于世紀之交,正值中國社會經歷巨大變遷之際,余華以其獨特的筆觸,將個體命運與歷史洪流緊密相連,展現了一幅幅生離死別、悲歡離合的生動圖景。《活著》的影響力跨越國界,不僅在國內引起了廣泛共鳴,也在國際上贏得了諸多殊榮,成為當代文學的經典之作。它觸動了無數讀者的心弦,讓人們重新審視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書中主人公福貴的一生,雖飽受苦難,卻始終堅韌不拔,用實際行動詮釋了“向死而生”的生命哲理,即在直面死亡威脅時,依然選擇堅強地活下去,尋找生活中的微光與希望。這部作品不僅是對個體命運的深刻剖析,更是對生命力量的崇高頌歌。
一、生死交響:抗爭命運的樂章
在小說《活著》中,余華以細膩的筆觸和冷峻的敘述,構建了一幅幅生與死交織的畫卷,其中,“向死而生”的精神成了貫穿全書的生死交響的主旋律,奏響了命運與抗爭的壯麗樂章。
《活著》開篇便以一種近乎殘酷的方式,將讀者拉入了一個充滿苦難的世界。福貴,這個曾經擁有百畝良田、家境殷實的地主之子,因賭博而一朝之間傾家蕩產,從此踏上了命運的坎坷之路。他的生活,就像一部不斷加速下墜的悲劇,每一次似乎都觸及了谷底,卻又總有新的不幸接踵而至。兒子有慶因獻血過多而死,女兒鳳霞難產而亡,妻子家珍積勞成疾,女婿二喜意外身亡,外孫苦根也因吃豆子過多撐死……[1]尤其是福貴背著因獻血過多而死的兒子有慶的尸身,邁動著沉重的步履一步一步走在回家的路上,那個情節該是多么的悲愴,時間仿佛凝固了,那被拉長的福貴的身影是那樣的孤獨無助。一個曾經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浪蕩不羈的少爺,在成為一個失去了兒子的可憐父親的時候,同樣是那樣的心酸至極。富貴沉重而緩慢的腳步,每一步都是踩到了自己的心窩里,從心里滴出的血,只有自己能夠聽得到。他也許在回憶兒子有慶出生、成長到離世的點點滴滴,想念給他帶來許多歡樂和期望的活潑可愛的孩子。他也許在回憶自己曾經經歷的每一道磨難,詢問著自己的人生歷程。每一個親人的離世,都是對生命脆弱性的直接展示,也是對福貴心靈的一次重擊。余華用冷峻而真實的筆觸,將這些苦難一一呈現,沒有絲毫的渲染與夸張,卻讓人感受到一種直擊心靈的震撼。這種敘述方式,正如命運的交響樂章,每一個音符都沉重而深刻,它們共同構成了福貴生命樂章中最為悲愴的旋律。
然而,在這無盡的苦難與失去之中,福貴并未選擇放棄,而是以一種近乎倔強的姿態,繼續前行。他的“活著”,既是為了生存本身,也是一種對命運的抗爭,一種向死而生的堅韌。在每一次親人離世后,福貴都經歷了短暫的崩潰,但他總能從絕望中找到一絲生存的希望,繼續前行。這種力量,源自他對過去的悔恨、對家人的懷念,以及對生活最樸素的渴望。
福貴的“活著”,是對生命尊嚴的堅守,即使面對生活的重壓,他也一直從未放棄作為一個人的尊嚴和責任。在小說中,福貴曾說:“做人還是平常點好,爭這個爭那個,爭來爭去賠了自己的命。”[2]這句話,既是對他過去所經歷的放縱生活的深刻反思,也是對生活真諦的一種樸素理解。在余華的筆下,福貴的“活著”,成了一種對生命意義的深刻探索,一種在絕望中尋找希望的勇氣。
《活著》之所以能夠觸動人心,激起眾多讀者內心的共鳴,不僅在于它對苦難的真實描繪,更在于它對生命哲學的深刻挖掘。在這部小說中,生與死不再是簡單的對立面,而是相互交織、相互映襯的復雜存在。福貴的一生,就像一首宏大的生死交響樂,其中既有死亡的陰郁旋律,也有生存的堅韌強音。這兩股力量,在福貴的生命樂章中不斷碰撞、交織,最終達到了一種奇異的和諧。
福貴的“活著”,是對死亡的最好回應。他的每一次堅持,都是對生命價值的肯定,是對命運不公的抗爭。正如尼采所言:“那些沒有殺死你的,終會使你變得更強大。”福貴的一生,正是對這一哲理的生動詮釋[3]。在無盡的苦難中,他不僅沒有被擊垮,反而以一種更加堅韌的姿態,證明了生命的頑強與不屈。
二、苦難敘事:生命韌性的藝術展現
《活著》中的主人公福貴,其一生仿佛是由一連串的苦難編織而成的長卷。從家道中落的無奈,到戰亂中的流離失所,再到親人相繼離世的悲痛,每一次命運的打擊都如同沉重的錘擊,落在他的心頭。然而,正是這些看似無法承受之重,構成了福貴生命的底色,也成了小說苦難敘事的核心。余華沒有回避生活的殘酷,反而以一種近乎冷峻的筆觸,將這些苦難一一呈現,讓讀者在震撼之余,也不得不思考:在如此重壓之下,生命何以延續,韌性從何而來?
苦難在《活著》中,不僅僅是人物命運的注腳,更是對生命韌性的一種藝術化呈現。余華通過密集而頻繁的苦難敘事,構建了一個又一個令人窒息的情境,讓讀者在跟隨福貴的腳步走過這段漫長而艱辛的旅程時,深刻體會到生命的脆弱與堅韌并存。這種敘事策略,不僅增強了小說的悲劇色彩,更重要的是,它讓每一次苦難都成了一次對生命韌性的錘煉和證明。
例如,當福貴面對家破人亡,幾近絕望之際,他依然選擇“活著”,每次的苦難,都讓他悲痛欲絕,但他依然要面對生活,繼續活下去。這種在苦難中堅守的信念和表現出來的強大力量,讓每一位讀者都會產生對生命至誠至深的敬畏。
活著,有時候不僅僅是一種狀態,更是一種勇氣和信念。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活著。用一雙布滿老繭的手,繼續耕耘著那片貧瘠的土地。這一場景,是余華對生命韌性最為直觀的描繪。在這里,苦難不再是簡單的情節推進器,而是成為凸顯生命力量的背景板,讓福貴那看似微不足道卻堅韌不拔的生存意志,得以最大化地展現。
《活著》之所以能夠觸動人心,不僅僅在于它對苦難的深刻描繪,更在于它在苦難之中,依然點亮了希望之光。福貴的一生,雖然充滿了失去,但他從未放棄對生活的渴望,對“活著”本身的堅持。這種堅持,是對生命價值的深刻認同,也是余華想要傳達的生命哲理:即便面對無盡的苦難,生命本身仍值得珍視,因為活著,就有希望。
小說結尾,福貴與老牛相依為命的場景,是對這一生命哲理的最佳詮釋。在經歷了所有的悲歡離合之后,福貴依然選擇“活著”,這份堅持,是對生命韌性的最高頌歌,也是對“向死而生”哲學命題的深刻實踐。在這里,苦難不再是生命的終點,而是通往更深層次生命理解的橋梁。
由此能看出,《活著》通過其獨特的苦難敘事,不僅展現了一個普通人在極端困境中的生存狀態,更深刻揭示了生命在逆境中的堅韌與頑強。余華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和深邃的筆觸,將苦難轉化為一種藝術化的表達,讓讀者在感受生命之重的同時,也領悟到了生命之輕——那是一種超越物質與苦難,直抵靈魂深處的對生命的熱愛與敬畏。《活著》不僅是一部關于個人命運的小說,更是一部關于生命哲理的深刻探討,其讓讀者認識到無論生活給予人生多少苦難,只要心中有光、有希望,就能在這無盡的黑暗中,找到屬于自己的那一抹亮色,繼續前行。正如福貴所展現的,活著,就是最美好的開始,也是最深沉的結束,本身包含了生命所有的可能性與不可能,是對生命韌性最真摯的禮贊。
三、時間之河:生命流程的深刻反思
在余華的力作《活著》中,時間不僅是一條流淌不息的河流,它還承載著生命的悲歡離合,見證了主人公福貴及其家庭從繁華到衰敗的滄桑巨變。小說通過時間的流逝,深刻地展示了生命的短暫與無常,同時也讓人物在時間的洗禮下逐漸領悟到生命的真諦。從時間的維度出發,讀者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活著》這部小說,以及它對讀者生命觀念的深刻反思。
時間,作為貫穿《活著》的重要線索,它無情地推動著故事的進程。從福貴的年輕浪蕩,到家道中落,再到家庭的破碎和親人的相繼離世,每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都由時間來標記。余華巧妙地運用時間的流轉,將福貴的一生編織成一幅跌宕起伏的生命畫卷。在這幅畫卷中,讀者可以看到時間的殘酷與公正,它不會因為任何人的祈求而停留,也不會因為任何人的痛苦而加速。時間,就這樣靜靜地流淌,將生命的每一個瞬間都鐫刻成永恒。
在時間的流逝中,生命的短暫與無常得到了最深刻的體現。福貴的一生,可以說是充滿了變數。他從一個富有的地主家的兒子,淪落到身無分文的貧民,再經歷家庭的破碎和親人的死亡,最終只剩下自己孤獨地活著。這一系列的變故,都發生在時間的流轉之中。時間,就像一個無情的判官,它不斷地提醒著福貴和讀者,生命是如此的短暫和無常。人永遠無法預知明天會發生什么,也無法阻止生命的流逝。
然而,正是在時間的洗禮下,福貴逐漸領悟到了生命的真諦。他開始明白,生命的意義并不在于物質的豐富或社會地位的高低,而在于對生活的熱愛和對家人的珍惜。當他的親人一個個離他而去時,他才意識到,那些曾經被他忽視的日常瞬間,那些與家人共度的平凡時光,才是生命中最寶貴的財富。時間,雖然帶走了他的一切,但也讓他學會了珍惜和感恩。他明白了,活著,就是為了記住那些逝去的人,為了繼續他們的生命而活下去。
余華通過福貴的生命歷程,向讀者展示了一個人在時間面前的渺小與偉大。渺小,是因為人無法抗拒時間的流逝和生命的無常;偉大,是因為人們可以在時間的洗禮下,逐漸領悟到生命的真諦,并學會珍惜和感恩。這種對生命的深刻反思,不僅讓福貴這個角色更加立體和飽滿,也讓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對自己的生命觀念進行了深刻的審視。
余華借助《活著》這部小說,從時間維度展示了生命的韌性和人類不屈的精神。盡管福貴經歷了無數的痛苦和磨難,但他從未放棄過對生活的熱愛和對家人的思念。他的生命,就像那條時間之河一樣,雖然經歷了無數的曲折和波折,但依然堅韌地流淌著。這種生命的韌性和人類不屈的精神,不僅讓福貴這個角色更加感人至深,也讓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感受到了生命的偉大和人類的堅強。
四、生存哲學:活著本身的意義追尋
在余華的力作《活著》中,一句簡單卻擲地有聲的話語反復回響:“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這句話如同一道穿透歲月的光芒,照亮了主人公福貴坎坷多舛的一生,也深刻地觸動了每一個讀者的心靈。這不僅僅是一種生存的宣言,更是一種關于生命本質的哲學思考,引領讀者深入探討活著本身的意義與價值,以及這一生存哲學對當代人生存觀念的啟示與影響。
在《活著》這部小說中,福貴的一生仿佛是一幅波瀾壯闊又悲情四溢的畫卷,他經歷了家道中落、戰亂流離、親人相繼離世等一系列幾乎難以承受的苦難。然而,正是在這無盡的苦難之中,福貴對于“活著”的理解逐漸升華,超越了物質財富的積累和社會地位的提升,轉而聚焦于生命本身的體驗與感受。他學會了在饑餓中品味一碗稀粥的甘甜,在失去中珍惜每一份溫情的回憶,即使面對生活的殘酷,也依然堅持著“活著”的信念。
作者借助福貴的經歷,向讀者展示了生命的全面體驗——不僅僅是快樂與成功,更有痛苦與失敗。正如小說中所描繪的,無論是戰亂時期的顛沛流離,還是和平年代的家庭變故,福貴都以一種近乎頑強的姿態去接納、去經歷。活著不在于刻意地追求人活著的意義,只關注“活著”本身。作者在小說中以大膽的筆觸向讀者重復描寫死亡,以福貴所經歷的苦難和磨礪提醒讀者在面對生活的遭際時,不要低迷于苦難的漩渦而頹廢沉淪,而是要堅韌地活下來。這種對生命酸甜苦辣的全面擁抱,是對“活著”最深刻的詮釋。它告訴讀者,生命的價值不在于逃避苦難,而在于如何在苦難中尋找到生活的光亮,如何在逆境中依然能夠感受到生命的溫度。
此外,在《活著》中,愛與被愛構成了生命意義的另一重要維度。無論是福貴對家人的深情厚愛,還是家人之間相互扶持的溫暖,都是支撐他們渡過難關、堅持活下去的重要力量。愛,讓福貴在絕望中看到了希望,在黑暗中找到了光明,這證明了即便是在最艱難的時刻,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紐帶也能成為生命中最寶貴的財富,賦予“活著”以深沉的意義。
小說深刻揭示了對于“苦難”這一主題的把握以及取向,真正的生命意義往往是在苦難中被發掘和塑造的[4]。福貴的一生,是對“向死而生”這一生存哲學的生動演繹。面對生命中一次次的打擊,他沒有選擇放棄,而是以一種近乎超脫的態度,繼續前行。這種在苦難中不斷尋找生命意義的過程,是對人類生存韌性的最高致敬,也啟示讀者思考生命的價值不在于其長度,而在于如何在有限的時間里,探索、體驗、感悟,并最終找到屬于自己的生命意義。
在當代社會,物質主義的盛行往往讓人們忽略了“活著”本身的意義,追求外在的成功與認可成為許多人生活的全部。然而,《活著》這部作品中有著對苦難獨特而富有深度的闡釋[5],它提醒讀者,他們的真正的幸福與滿足并非來源于物質的堆砌,而是源自內心的平和與對生活的深刻體悟。它鼓勵讀者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態度,學會在快節奏、高壓力的生活中尋找片刻的寧靜,學會珍惜眼前人,學會在平凡中發現不凡。
五、結語
《活著》是一部充滿苦難與絕望的小說,但同時也是一部充滿生命力量與希望的作品。小說以生活中普通、樸實的故事情節,講述了富貴在急劇變革的時代中所遇到的不幸和遭遇,記敘了富貴極為坎坷的命運。作者以冷靜的筆觸、細膩的語言和深刻的洞察力,為讀者展現了生命的意義所在,向讀者解釋了存在的價值,揭示了命運的無奈與生活的不可捉摸,向讀者展示了一個普通人在極端困境中的生存狀態和對生命意義的深刻探索。它讓讀者看到,即便是在最黑暗的時刻,生命依然能夠綻放出耀眼的光芒,而這份光芒,正是源自我們內心深處對活著本身的堅守和尊重。通過這部小說,余華不僅向我們展示了一個普通人的一生悲歡離合,更向我們揭示了一個深刻的生命哲理:活著本身就是一種意義和價值所在。
參考文獻
[1] 吳向寧.為活著而活[J].大眾文藝,2019(11).
[2] 姜安祈.淺談余華《活著》中人生觀的兩面性[J].戲劇之家,2019(5).
[3] 孔晶瑩.苦難之下的“生”與“死”——《安琪拉的灰燼》與《活著》的苦難主題探析[J].文教資料,2016(4).
[4] 黃宇.如何“活著”——論余華長篇小說人物對“苦難”的抗爭意識[J].青年文學家,2012(4).
[5] 周序華.對苦難的不同闡釋——試比較張煒、李銳文學作品中的苦難意識[J].語文學刊,2006(9).
(特約編輯 范 "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