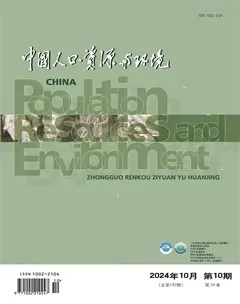中國三大糧食作物生產績效及其要素源泉








摘要 在新一輪千億斤糧食產能提升背景下,揭示主要糧食作物生產績效演進規律并深入挖掘糧食生產績效的要素源泉,對于確保糧食產量可持續增長和推進糧食產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該研究聚焦稻谷、小麥和玉米三大糧食作物,在數據包絡分析框架下構建SBM方向距離函數模型,利用Luenberger生產率指標測度了2002—2021年中國糧食生產績效,并從要素分解角度探究中國三大糧食作物生產績效的源泉。研究結果表明:①樣本期內,三大糧食作物生產績效均呈現顯著提升態勢,主產區的糧食生產績效改善最為明顯。稻谷、小麥和玉米生產率分別累積增長21. 86%、24. 35%和18. 68%。②三大糧食作物生產績效的增長主要源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勞動生產率增速放緩是生產績效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③技術進步是推動三大糧食作物生產績效改善的主要動力,樣本期內稻谷生產的技術進步始終依賴于勞動,小麥生產的技術進步源泉由土地轉向勞動,玉米生產的技術進步源泉由勞動轉向資本。面向新一輪糧食產能提升目標,通過激發種糧農民的積極性、加快農業科技創新、提高耕地質量等措施,切實提升生產要素績效及總體績效,為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建設農業強國提供重要支撐。
關鍵詞 糧食安全;產能提升;生產績效;Luenberger生產率
中圖分類號 F323. 11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24)10-0187-09 DOI:10. 12062/cpre. 20240503
糧食產量穩定供給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建設農業強國的重要基礎。2022年12月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啟動新一輪千億斤糧食產能提升行動,提出“到2030年實現新增糧食產能千億斤以上,全國糧食綜合生產能力進一步增強”。2024年3月,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新一輪千億斤糧食產能提升行動方案(2024—2030年)》,再次強調“提升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然而,必須清醒地看到,近年來中國糧食產量已到達較高位,糧食產量的增速不斷降緩,糧食產量持續性增長的難度越來越大。如果再考慮資源環境約束、“雙碳”目標、旱澇等自然災害影響,新一輪千億斤糧食產能提升目標實則面臨較大挑戰。糧食生產績效能夠體現糧食生產過程中要素投入的整體質量和效率,提升糧食生產績效可帶來更高的邊際產出[1]。從長期來看,提升糧食生產績效不僅是確保糧食產量可持續增長、實現新一輪千億斤糧食產能目標的根本途徑,也是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糧食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現有文獻主要關注糧食生產績效在總體層面上的變動,從效率改進和技術進步的角度對糧食生產績效進行分解,然而基于要素分解視角對糧食生產績效進行源泉探究的較少。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就是要大力提升投入要素優化組合而形成的生產績效。因此,作為糧食生產的最基本載體,勞動、資本、土地等投入要素的績效是糧食生產整體績效的深層源泉。如果可以從投入要素的角度,探索糧食生產績效的要素增長源泉,則有助于厘清糧食生產績效的內部結構,并進一步揭示中國糧食生產績效提升的動因。
1 文獻綜述
全要素生產率是衡量生產績效水平的重要指標,眾多文獻利用全要素生產率對糧食生產的總體績效水平開展研究[2-4]。從糧食作物品種的選取來看,目前研究往往選擇某單一糧食品種或直接從糧食生產總量的角度進行分析[5-6]。從糧食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方法來看,已有文獻主要采用了隨機前沿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與數據包絡分析(data envelope analysis,DEA)兩種方法。其中,DEA方法憑借不需要提前設定生產函數、靈活處理多投入多產出情況、可以對全要素生產率進行分解等優勢,在糧食生產績效的研究中得到了廣泛應用。如方福前等[7] 和閔銳等[8] 分別運用DEA 的Malmquist 和Malmquist?Luenberger 指數測算了中國糧食全要素生產率。從糧食生產績效的增長源泉來看,絕大多數文獻從效率改進和技術進步層面進行識別[9]。如高鳴等[10]基于1978—2013年中國糧食生產數據,測算了中國各省的糧食全要素生產率,并將其分解為技術變化和效率變化,發現技術進步是糧食生產績效提高的主要動力。還有部分文獻在規模報酬可變的情形下,從技術水平、規模效率、純技術效率層面來探究糧食生產績效的變動來源[11-12]。以上文獻為本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但仍存在一定的拓展空間:一是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糧食整體或某單一作物的生產績效,對于三大主要糧食作物生產績效的研究較少。二是現有研究主要采用Malmquist 指數或Malmquist?Luenberger指數對糧食全要素生產率總體水平進行評價,忽視了對投入要素生產率的評價,從而無法揭示糧食生產過程中投入要素的績效水平。三是目前研究主要從技術進步與效率變化角度探討了糧食生產績效的增長源泉,而基于要素分解視角對糧食全要素生產率進行更精細化的研究較少,從而難以揭示全要素生產率的內部結構,也難以進一步探索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具體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