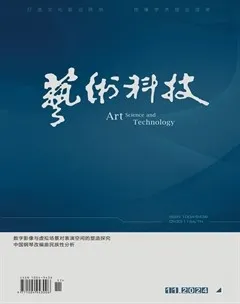明代戲曲文物的藝術美學研究

摘要:目的:城市中存在社會性宗教場所,作為城市保護神的城隍、后土等神祇具有祈福、保佑平安的社會屬性。這一類神廟往往建在城市中心,或者以城市為原點擴展,并按照延續千年的傳統習俗開展社會活動。針對此類普遍存在并仍在發揮社會影響的戲曲活動場所,應在調查研究的同時發掘其社會和藝術價值,以更好地傳承其文化內涵。方法:通過梳理城市保護神的歷史發展脈絡和地域社會特征,采用實地考察和調研的方式,選取代表性的山西省榆次、介休城市保護神廟中的戲曲活動和戲臺藝術,歸納建筑藝術特征,深入探究城市保護神廟的藝術美學內涵。結果:城市保護神廟類建筑凝聚著地方對民間信仰的尊重,因此建筑形制講究,裝飾精美。一般設有娛神的戲臺,承載社會聚集和娛樂功能。城市保護神廟作為祭神、廟會等社會活動的發生場所,是地方性文化場域的代表,充分認識并發揮好其功能,有助于實現貼近基層意識的文化傳承和社會功用。戲曲作為“俗文學”的代表,在傳統社會環境中不僅是娛神樂人的重要載體,還是發揮教化功能的最佳媒介。結論:文化遺產具有重要的文旅意義和地方社會文化價值,要對其充分利用并進行現代化改造,為基層戲曲主題文旅建設創造新契機。
關鍵詞:明代戲曲;城市保護神;美學
中圖分類號:TU251;I207.3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4)11-00-05
0 引言
城市保護神廟是指位于城市之中,供奉地方守護神的寺廟,這類寺廟一般建在城市中心,在地方發展過程中承擔著一定的文化與社會功能。明代的城市保護神信仰非常普遍,由于官方的推崇,城隍廟、后土廟香火旺盛。城隍神、后土娘娘都被視為城市的守護神,能夠保護城市免受災害和邪惡的侵襲。在明代,每個城市都設有城隍廟、后土廟,供奉著城隍、后土神像。這一類城市保護神廟通常是城市中最受歡迎的宗教場所之一,吸引了大量的信徒前來祈禱、獻香等,并會在神祇生日等重要時間節點舉辦規模較大的慶祝活動。探究城市保護神廟建筑和文化特色,有助于加深對傳統藝術形式的認識。
1 社會場域下的城市保護神信仰與戲曲活動
山西省內廣泛存在城市保護神廟,目前山西省內城市保護神廟主要分為兩類:供奉城隍神的城隍廟與祭祀后土娘娘的后土廟。“城隍”一詞最早可追溯到《周易·泰卦》:“城復于隍,勿用師”[1]5-6;《易經》曾言:“城復于隍,其命亂也”,這里“城”意為城墻、城郭,“隍”是指城外的壕溝,即護城河,“城隍”最初表達的是百姓對安居樂業、固本安邦的期待。“后土”崇拜最早源于人類對大地的崇拜,是一種土地信仰。上古原始母系社會,土地是人們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人們認為大地是人類的母親。《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提到“土正曰后土”[1]382-423,將掌管土地的神祇稱為“后土”。《楚辭章句補注》曾言:“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2]將地府冥界劃為后土神管轄的區域。《尚書·武成》描述周武王在伐商勝利后“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1]40-41,向上天神靈禱告伐商一戰的正義性,展現了古代統治者對皇天后土的尊重和敬畏之心。隨著社會的發展,“城隍”“后土”逐漸由物過渡為神,其自然屬性逐漸被社會屬性所取代,城隍信仰、后土信仰隨之產生并成為一種宗教文化。這類宗教文化可以追溯到中國古代的城市保護神信仰和祖先崇拜,其底蘊深厚、影響深遠,至今仍有不可小覷的影響。
在明代,地方守護神信仰的盛行也與當時的政治、經濟環境有關。“城隍神是明代以來官方和民間最有影響力的神祇之一。明初洪武改制,城隍神被封為王、公、侯、伯的爵位,并規定了都府州縣城隍神不同的品級,朝廷下令各級行政單位建立城隍廟,城隍神信仰達到了最鼎盛的階段。”[3]由于明朝時期許多城市都面臨自然災害、盜匪和戰爭等威脅,人們需要通過祭拜城隍、后土來獲得心理安慰。此外,城隍信仰還與商業活動密切相關,城隍被認為是能夠帶來商業繁榮和財富積累的神明,所以商人也會在城隍廟中祈福。后土信仰主要與人們對平安順遂、子孫繁盛的祈愿相關聯。城市保護神信仰在明代社會生活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僅是保護城市安全的信仰,還是經濟繁榮、社會和諧的象征。
山西的城隍廟分布范圍廣泛(見圖1),建于明代的城隍廟數量眾多,達22座。作為城市的活動中心以及地方的重要宗教場所,城隍廟通常位于城市的中心地帶。而明代修建的后土廟相較于城隍廟來說數量較少,僅有7座,后土廟的位置分布較為靈活,有位于城市中心的,也有散布在鄉村的。由于后土神掌管土地、生育、生靈等,所以其神廟多位于人口集中區域。城市保護神廟通常建造規模較大,由主殿、配殿和祭祀區組成。主殿供奉著城隍、后土神像,配殿則供奉著其他神靈或祖先。明清時期,古戲臺多依附于寺廟或祠堂而建,因此有城隍廟、后土廟的地方往往戲曲文物遺留較多、保存較好,戲曲活動也更加繁盛。
從地理位置來看,此類神廟主要沿傳統城市或較大的農村位置流布,主要分布在山西中部的平原地區,多數神廟沿用至今,保存完好。以城隍神、后土娘娘為代表的地方守護神在歷史上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文化和宗教方面,是當地城市精神文化的象征之一。在此類廟宇中,人們在祭祀或祈福的過程中不僅表達了對地方守護神的崇敬,還在潛移默化間傳承和弘揚了中國古代的宗教信仰和傳統文化。本研究以規模和影響較大的晉中榆次城隍廟、晉中介休后土廟為例,在分析其社會功能的基礎上對其中戲曲文物的美學藝術進行探究。
2 城市保護神廟作為場域社會中心的藝術特征
場域最早由法國的皮埃爾·布迪厄提出,他認為場域是經過客觀限定的網絡或者形構。布迪厄的場域概念并不是指被一定邊界包圍的領地,而是一種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社會空間,如美學場域、宗教場域、文化場域,等等[4]。城市保護神廟在古代社會既承擔著祈禱和供奉神靈的責任,又是開展民間信仰活動與傳承文化習俗的重要場所。作為祭祀城隍神的廟宇,城隍廟一般位于衙門附近,監督城市治安、維護社會秩序,同時還負責防范火災、水災等災害。后土廟的分布沒有嚴格的限制,既可以位于城市中心,又可以坐落在鄉村深處。因供奉的后土娘娘是掌管人口、生育、山川、生靈的神明,因此后土廟多建在人群聚集的區域,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和信仰寄托有著緊密的聯系。在民間,城市保護神廟在特定節日會舉行盛大的祭祀活動、廟會活動、祈福法會。這些活動促進了官方與民間的交流互動,同時帶動地方經濟發展,促進商品流通,因此這類神廟在古代可以視為社會場域的中心,具有典型的美學藝術特征。
城市保護神廟作為中國古代社會的場域中心,其建筑布局、用材以及藝術風格必須符合大眾審美。因為具有均衡對稱的結構布局、瑰麗多彩的琉璃工藝、繁復精美的裝飾圖案、結構復雜的古式戲臺,城市保護神廟多給人恢宏華麗之感。
2.1 均衡對稱的結構布局
“山西城隍廟建筑的形制和空間布局都帶有顯著的宗教禮制特征,符合儒家以尊卑等級為核心的思想。城隍廟建筑通常效仿宮殿建筑的格局,將主體建筑沿線性序列布置,形成一條中軸線,再由依中軸線對稱布置的附屬建筑結合主體建筑圍合,形成一進一進的院落空間,從而形成層層遞進、氣勢恢宏的建筑群。”[5]以榆次城隍廟為例,城隍廟建筑群以中國古建筑形制為觀照,布局呈現均衡對稱之美。榆次城隍廟作為我國最古老且保存最完整的城隍廟之一,結構緊湊和諧。山門、玄鑒樓、樂樓、獻殿、顯佑殿、寢殿從前至后,構成一條中軸線貫穿整個城隍廟,鼓樓、鐘樓分布在左右兩側相呼應,掖門、廊房、便門、配殿左右各一間,位置呈軸對稱分布的狀態。從整體上看,城隍廟布局勻整緊實、渾然一體,體現出穩重、和諧的特點,營造了一種靜穆莊重的氛圍。
2.2 瑰麗多彩的琉璃工藝
山西的琉璃工藝以光亮、色艷、防潮、耐久的特點聞名全國,自古以來山西的琉璃制品就被廣泛應用于皇宮、廟宇之中。介休后土廟建筑群以其堪稱海內外孤本的明代“萬勝朝元”彩塑和華麗的琉璃制品以及完整的古建筑而聞名,并且憑借精美且數量龐大的琉璃制品享有“三晉琉璃藝術博物館”的美譽[6]。在建筑用材上以琉璃為主,色彩明艷,其艷麗之色歷經多年而不褪,其華美程度令人嘆為觀止。琉璃裝飾大多采用黃、綠、藍三色,在視覺呈現上給人一種神秘感。具體來說,樓殿的脊剎、正吻顏色以黃、綠為主,其中綠色往往作為龍、獅、象等神獸的身體主色,黃色常作為脊剎“小閣樓”的配色。樓殿屋頂上常采用孔雀藍色琉璃構件覆蓋,與黃色琉璃構件相互映襯,色調搭配和諧,使城隍廟呈現出一種大氣恢宏之美。
2.3 繁復精美的裝飾圖案
城市保護神廟的裝飾圖案往往能夠反映當時的審美情趣和藝術風格。被譽為“三晉琉璃藝術博物館”的介休后土廟在脊飾圖案的選擇上具有典型性,多用龍、象、獅子、蓮花、牡丹等具有特殊內涵的圖案來裝飾正脊、正吻以及脊獸。后土廟建筑背部常常采用琉璃雕花進行裝飾,配色以褐、黃為主,花瓣層疊錯落,以盛放的姿態開在脊剎之上。正吻裝飾是指置于正脊兩端突出于屋脊的裝飾,山西城市保護神廟正吻都以龍為中心形象,不同的建筑樓殿上的龍形各有特色。以介休后土廟為例,屋脊兩端的大吻選擇“螭”作為主要裝飾圖案。螭是中國古代神話中龍的九子之一,造型為龍首魚尾,傳說它喜歡吞火,因此中國古建筑在屋脊設計時常選擇此種神獸,寓意為避除火災。后土廟的螭吻裝飾造型夸張生動,龍的眼、鼻、口逼真精美,龍嘴往往咬著屋脊,有一種“氣吞山河”的壯麗美感。
2.4 結構復雜的古式戲臺
山西作為公認的“中國戲曲搖籃”,其中歷朝歷代修建的古戲臺數量居全國之首。“有村必有廟,有廟必有臺”[7]道出了山西戲場建筑之多,山西戲場建筑在明代進入轉型期,建筑形制在傳承中不斷創新,同時觀演關系也發生了一定的變化。由于戲曲演唱的需要,元代戲臺不再適應場上“演”的需要,明代戲臺多變為三開間,有的甚至是五開間。從戲臺平面尺寸上看,明代戲臺更多為長方形,表演區面積明顯擴大,所容納的演員數量明顯增多。為適應平面的變化,明代戲臺梁架結構也從元代的亭榭式結構變為廳堂式抬梁結構,更加適應三開間的戲臺。在戲臺形制上,明代產生了“山門戲臺”,其是中國劇場史上的一座里程碑[8]。“山門戲臺”是將寺廟的山門作為戲臺臺基,戲臺與山門相互因借,外看是巍峨聳立的山門,內觀是氣勢恢宏的戲臺。山門戲臺的出現讓戲臺的占地面積大幅縮小,給觀眾留下了更多的空間。明代戲臺的形式多樣,戲臺與樓閣、山門、神殿合建,榆次城隍廟是將玄鑒樓、樂樓、戲臺三者融為一體,而介休后土廟則是將戲臺與三清閣有機結合。整體建筑群前后揚抑,錯落有致,左右呼應,和諧優美。
3 社會場域的城市神廟的文化內涵
城市保護神廟作為供奉地方守護神的場所,每年在特定節日都會舉辦各類活動,如祭祀儀式、祈福廟會、戲曲表演,等等。這些民間文化活動傳承與展示了中國傳統文化,承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活動中的儀式、音樂以及舞蹈都與民間習俗密切相關,展現出歷史悠久的民間信仰的深厚文化內涵。
3.1 廟會盛景:生產生活的祈愿
作為中國傳統民俗活動的廟會,往往于特定節日在寺廟周邊舉行。廟會既是民間信仰的表現形式,又是文化傳播與經濟交流的載體,具備豐富的文化意義和社會功能。以榆次城隍廟的廟會活動為例,其始于明末清初,歷史悠久。廟會期間,來自京、津、豫、陜以及蘇、杭等地的商人云集榆次城隍廟,出售各種商品,如綢緞、海味、珠寶等,因此榆次城隍廟廟會為人們搭建了一個重要的商業交流平臺。《榆次縣志》(民國版)曾記載廟會期間的繁盛景象,“萬商云集,經月不散”,廟會有助于各類地方產品在晉中地區流通,在發展地方經濟的同時促進文化交流。“廟會當中的文化娛樂活動因時、因地、因神之不同而約略有異,但無論城鄉,演戲是一個很普遍的節目……一個亭閣式的戲臺,這便從建筑景觀上體現出廟會乃至寺廟本身所具有的文娛特征。”[9]廟會活動借助寺廟的影響力擴大其輻射力,與當地百姓生產生活緊密聯系。一方面,廟會為百姓提供了一個集社交、娛樂等功能于一體的平臺,各類群體在節假日、慶典時期來到寺廟及其周邊開展社會活動。民間藝術表演如舞龍舞獅、雜耍表演等起到了傳播民俗文化的作用,展現了老百姓欣欣向榮的生活面貌,表達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期許。另一方面,廟會往往只在固定的時間節點舉辦,往往會帶動當地住宿、餐飲、旅游等業態的發展,同時會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增加當地居民的經濟來源,從而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
3.2 祭祀活動:禮儀文化的傳承
祭祀活動是一種祭祀祖先或者神明的禮儀活動,源于天地和諧共生的信仰理念,體現了人類對于自然神明的敬畏之心,“祭祀禮儀”是聯系人與神的精神紐帶。中國史書中有不少對祭祀活動的敘述,而明清禮典中對城隍祭祀的記載尤為詳細。陽城縣明弘治九年(1496)《重修城隍廟記》曰:“古先哲王以禮事神,于所當祀者,謂之宗祀,則載在祀典;所不當祀者,謂之淫祀,則毀而黜之。”[10]古代帝王以禮儀侍奉神明,城隍祭祀作為“正祀”更是帝王維護統治的重要手段。明清時期,新上任的地方官員常常需要在城隍廟行香祭拜,祭祀流程主要分為三部分:謁廟行香、齋宿、撰寫祭文。復雜煩瑣的祭祀流程體現了古人對禮儀的嚴謹態度,對城隍神的敬重與崇拜。祭祀城隍神的儀式歷經歲月洗禮,流傳至今,仍熠熠生輝。城隍廟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時至今日依然會舉行豐富的祭祀活動。每逢重要節日或特定紀念日,如城隍誕辰、春節、元宵節等,民間組織會在地方政府的指導下舉行祭祀儀式。儀式流程通常包括準備供品、擺放神像、誦讀經文等,意在向城隍神表達敬意、祈求福祉。從古至今,祭祀活動在百姓生活中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反映了民俗文化的包容性與多樣性,它與民間信仰、習俗文化緊密相連,對于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3.3 戲曲表演:時代風尚的映射
戲曲表演作為神廟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重要的神廟節日登臺亮相。“聲律和諧、為民所愛的戲曲則成為‘大樂’的替代。”[11]民眾喜聞樂見的戲曲發揮了更理想的禮樂教化作用。如在后土信仰中,后土娘娘的生日是重要節日,要通過演戲來酬神,相關活動會持續兩到三天。這樣的大型社會活動往往能吸引廣大民眾積極參與。戲臺上演的戲曲劇目不僅歷史悠久,與慶生等主題相契合,而且內容豐富多彩,兼具教育意味和娛樂性。例如,后土娘娘生日時演出的《滿床笏》有祝壽、子孫滿堂等美好寓意,對民眾的吸引力較強。
城市保護神廟在特定節日舉行的一系列戲曲表演活動,承擔著“娛神娛人”的職責,在發揮娛樂作用的同時兼具教化之能。戲曲表演通過人物動作、唱腔語言、劇目安排等,使觀眾在無形之中接受道德教化,同時往往圍繞映射時代風尚選擇劇目,借助音樂、舞蹈動作傳達主流文化理念。每年農歷的三月十八日是后土娘娘的誕辰,民間組織會在介休后土廟免費為當地百姓進行為期三天的戲曲表演,選擇的戲曲劇目包括《滿床笏》《渭水河》《打金枝》《姐妹易嫁》等。這一類戲曲劇目都根植于中國傳統歷史和文化,通過豐富的情節和鮮明的人物形象傳達忠孝節義、家庭和睦、善惡有報的中國傳統道德觀念,以藝術表演的形式展現時代精神。在后土神誕辰的前后幾天,民間組織、當地企業會出資聘請本地戲劇團演出,同時在廟前搭建現代舞臺,在廟內使用古式戲臺,以“兩臺同唱”的形式進行戲曲表演。現代戲臺高于地面,低于古戲臺,意在“娛人”而非“酬神”;而古戲臺遠高于現代戲臺,與后土圣母殿幾乎平行,留下的觀眾空間也更大,因此在古戲臺的場上表演兼有“酬神”和“娛人”的社會屬性。戲曲劇目中的人物唱詞多有“成雙成對”“天下太平”等表達對美好未來的憧憬之詞,創作者為祈求神明護佑國家安康,所以創作時往往會融入各類美好祝愿,以期獲得神明庇佑。戲曲表演作為民俗文化的典型代表,在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體現社會風貌和傳達文明友善的價值取向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具有深遠影響。
4 結語
承載城隍信仰、后土信仰的城市保護神廟,是普遍存在于山西城市和鄉村的社會場域,千百年來持續發揮著相應的影響力。但其具有顯著的局域性、地方性,在現代社會發展后勁不足。要想借助文化遺產打造文旅熱點,就要充分挖掘文化遺產的特色,克服鄉村文化記憶中斷、文化根脈植入不足等問題,以戲曲為主題串聯,打造集群效應,調動群眾參與積極性,規避模式化開發的弊端。深入挖掘其文化遺產和旅游品牌的內涵,根據其社會性和藝術特征,傳承中國傳統文化記憶,將城隍和后土文化發揚光大,打造文化遺產旅游地,以文化驅動鄉村文旅開拓創新。
參考文獻:
[1] 十三經[M].吳樹平,點校.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5-6,382-423,40-41.
[2] 王逸,洪興祖.楚辭章句補注[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201-221.
[3] 宋永志.城隍神信仰與城隍廟研究:1101—1644[D].廣州:暨南大學,2007:5-30.
[4] 高宣揚.布迪厄的社會理論[M].上海: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137-141.
[5] 續冠逸.城隍廟建筑的形制與空間布局分析:以山西省境內的城隍廟為例[D].太原:太原理工大學,2015:4-12.
[6] 高媛.山西介休后土廟建筑群琉璃裝飾藝術研究[D].太原:太原理工大學,2019:3-11.
[7] 郝曉凱.明清時期晉中地區神廟劇場研究[D].重慶:西南大學,2024:3-15.
[8] 馮俊杰.山西神廟劇場考[M].北京:中華書局,2006:219-245.
[9] 趙世瑜.明清時期華北廟會研究[J].歷史研究,1992(5):121-122.
[10] 朱樟,田嘉穀.澤州府志[M].太原:三晉出版社,2016:622-642.
[11] 蘇航.山西城隍廟劇場及其祭祀演劇研究[D].臨汾:山西師范大學,2020:135-150.
基金項目:本論文為2023年度山西省藝術科學規劃課題“山西明代戲曲文物的文化意蘊與美學研究”成果,項目編號:23BB024
作者簡介:武玥 (1990—),女,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明代戲曲、詩詞吟誦;郎儀瀅 (2001—),女,研究方向:元明清戲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