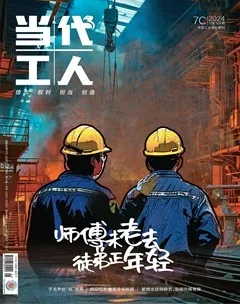能做出這檔綜藝,說明內娛有救

《歌手2024》沉寂4年重啟,以“直播、無修音、一遍過”的全新競技模式,向平靜已久的華語流行樂壇擲入了一枚“深水炸彈”。這在攪動資本市場重新打量流行音樂產業鏈的同時,也讓期待、質疑、驚艷等種種因歌手現場表現而誘發的大眾情緒,在輿論場中沸騰、發酵,最終演變為一場持續多日的全民“造梗”狂歡。
一檔“音綜”的新變
狂歡無處不在。
即使是不關注綜藝節目的網友,也能在各大社交平臺上窺見《歌手2024》迅速躥紅的痕跡。點開各熱搜排行榜會發現,歌手的現場表現、同行的紛紛請戰、網友的場外造梗等話題,正嚴絲合縫地滲入各個評論區。首期節目播出后,湖南衛視收視率0.44%,位列省級衛視收視榜第一;上線不到24小時,節目累計播放量破億;在某社交平臺上,還創下開播1分鐘即霸榜熱搜前列的紀錄。
從一檔闊別已久的音綜到無數網友茶余飯后的談資,《歌手2024》僅用了不到一周的時間。在音綜市場幾近飽和、優質綜藝后繼乏人的當下,這種成功來之不易,更難以復制。
出品方樂于見到這樣的場面。
綜藝市場向來是流量的擁躉,《歌手2024》出品方更是在這條賽道上一騎絕塵。流量由噱頭引發,噱頭意味著突破,突破意味著和常規敘事劃出一條涇渭分明的界限,這些出品方深諳其道。在國內音綜市場方興未艾之際,湖南衛視便致力于拓展音綜的內涵與外延。2013年,當《我是歌手》系列音樂競演綜藝橫空出世之際,便一改傳統音綜的面目。這里是一間由頂級音響、樂隊、燈光、舞美打造的密室,也是一場由實力唱將演繹的視聽盛宴。在這里,無論是知名歌星,還是無名唱將,都將憑實力重新排列座次。因此,音樂的魔力被最大限度地釋放。幾度引發全民狂歡后,這檔綜藝很快在內娛落地生根,至今不斷挖掘和輸送著優秀歌手。以其為代表的音樂競演類綜藝,也已成為音樂產業發展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切口。
遺憾的是,《我是歌手》系列綜藝即使一度驚艷了內娛,但依然不可避免地陷入“續集難叫好”的困境。出品方縱使幾度更新賽制,不遺余力地打造其他噱頭,也無力挽回逐漸審美疲勞的觀眾。7季綜藝的時間,內娛的儲備唱將被挖掘殆盡,節目組的“套路”“營銷”也逐漸被觀眾識破。繼《歌手·當打之年》潦草收場后,節目組后繼乏力,最終迎來了長達4年的停滯。
一邊是《我是歌手》系列綜藝的沉默,一邊是國內音綜市場的風起云涌,4年時間里,二者并行不悖。當以《天賜的聲音》為代表的后起之秀更新著觀眾對音綜的審美偏好時,當流媒體平臺成為傳播音樂的主要渠道時,當傳統綜藝市場陷入老調重彈、難出佳作的窘境時,改變自然迫在眉睫——迫切需要出品一檔爆款綜藝,以重新占據音綜領域的第一席位。
或許,《歌手2024》正是在這種語境中誕生的。在這檔綜藝里,處處可見標新立異之舉。直播無修音的全新競技模式,讓歌手的現場穩定性暴露無遺;國外歌手“降維打擊”,以至于網友紛紛“搖人”支援那英;“世界流行音樂演唱天花板”和草根歌手同臺競技,更讓觀眾驚嘆于節目的包容性……毫無疑問,《歌手2024》火了,而且沒有人料到,《歌手2024》會這么火。
久違的真實
然而狂歡背后,實則是出品方的有意布局。
“直播、無修音、一遍過”的口號,是噱頭,是營銷,更是“兵行險招”。節目全程實時播放,歌手的現場表演只能一遍過,沒有后期修音處理,也再無調整狀態重新登場的可能。和歷經層層彩排和“百萬修音”才得以呈現的其他綜藝節目相比,這些舉措過于大膽。
但它又不該是噱頭。按照正常的邏輯,直播是一場音樂表演最基本的要求,歌唱實力是一位歌手最核心的市場競爭力。當時間回溯至本世紀初,不修音或現場直播的音綜并不鮮見。在“超女”“快男”等音樂選秀類綜藝中,直播貫穿始終。在不摻一絲偽飾的鏡頭下,草根歌手只能憑借實打實的歌唱技術,為自己辟出一條成名之路。一位成名歌手卻“撐”不住直播現場,聽起來不太現實。但在近年來的內娛,這種現象遍地開花。當錄專輯可以在錄音室里無數次推翻重來時,當演唱會和音樂節大行“墊音”“假唱”之道時,當“全開麥”已成歌手勇氣和膽量的象征時,虛假隨處可見,觀眾厭其久矣。
虛假只是表象,背后是內娛流行音樂工業體系存在的種種問題。在現存的體系中,一位歌手的歌唱實力和所獲流量、商業激勵并不成正比。試想下,一位歌手打磨唱功,往往需要沉沒成本:天賦和努力,時間加精力。這些成本難以變現,更難以被迅猛發展的市場接納。很可能發生的是,在部分歌手苦練唱功之際,一批歷經批量化、標準化、工業化生產的“歌手”,加以矯飾和包裝,在粉絲和流量的助推下,足以登臺演唱。
這便解釋了為何《歌手2024》能在短時間內引發全網關注。出品方的商業籌碼,無意間撞到了人們心中最隱秘的期盼。觀眾厭倦了模式化的表演,厭倦了毫無營養的抖音神曲和口水歌,厭倦了屏幕背后的層層偽飾。虛假盛行時,真實便難能可貴。人們愿意為這種真實埋單,哪怕其上布滿瑕疵。
輿論場中的“戰爭”
意外的是,由《歌手2024》引發的全網狂歡,逐漸偏離了預設的輿論軌道。
真實是有代價的。節目開播以來,即使是作為華語樂壇常青樹的那英,也因受緊張情緒裹挾,難以發揮最佳水平。在第四期演唱周杰倫作品《擱淺》時,因過于緊張,那英的現場表現出諸多瑕疵。在不加矯飾的直播鏡頭前,這些瑕疵被一一放大。當晚,“那英這次真‘擱淺’了”成為熱梗。樂壇天后饒是如此,其他未必以唱功見長的創作型歌手和另類風格樂隊,所受抨擊更甚。“難聽”“早點兒回家”是網友對他們的判詞。
同樣受制于賽制壓力和洶涌輿情,外國歌手的驚艷表現,則是鏡像的另一面。加拿大歌手凡希亞的絲滑轉音足見其過人的歌唱技巧;美國歌手香緹·莫的強大機能使她穩居排名前列;而當世界流行樂演唱天花板亞當·蘭伯特作為襲榜歌手參賽時,簡單一句“hey”便足以讓網友驚嘆“原來節目音響這么好”。
同一檔節目,兩種光景同時存在。中外選手實力的相對參差炸出了洶涌輿論。如果說,客觀討論歌手唱功差距尚處于輿論理性階段,那么,當“英子碎了”等熱梗被無數網友傳播、效仿,甚至一度吸引場外歌手“請戰”時,事情開始變質。在輿論中,一場音樂競演,逐漸升級為涉及國家榮譽的榮辱之戰。
事實果真如此嗎?
“戰”字,本身就很微妙。將一場音樂競演升級為國別對抗,似乎印證了人們無處不在的愛國情緒。但從事實層面講,這又賦予了一檔音綜本不必包含的東西。正如節目組的回應:“在這里,音樂始終是交流的最大公約數。贏,只是歌手的一段路。迎,才是音樂的目的地。”在《歌手2024》里,不同國別、風格、類型的音樂相互交流、碰撞,才是這場“戰斗”的主旨。所以我們能看到,當國外歌手展現驚艷歌喉的同時,二手玫瑰以一首《耍猴》,展現一場極具先鋒實驗性質的表演;黃宣的爵士唱腔,足以展現他狂放不羈的舞臺魅力;杭蓋樂隊的表演,則始終致力于體現民族音樂和搖滾的混搭。也許,《歌手2024》的可貴之處,并非通過一種對立情緒來“扯下內娛的遮羞布”,而是在客觀提出內娛流行音樂工業體系存在問題的同時,也能展現它頗為獨特、值得交流互鑒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