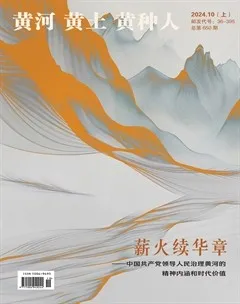初心如磐筑安瀾——黃河“根石”禮贊山東篇









1946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治黃事業從山東起步。
什么是人民治黃?
1947年11月,黃河歸故后的第一個汛期之后,黃委第一任主任王化云在冀魯豫區黃河安瀾大會上作了題為《一年來的黃河斗爭》的報告,他這樣回答“勝利是如何取得的”——有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人民空前團結,人民的力量戰勝一切。
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人民治黃的新紀元。在沒有汽車、沒有鐵路,經費和物料都不能保證的情況下,晉冀魯豫解放區共動員了23萬人民上工,堤外的群眾遠道馳援,出糧出力,支持治黃事業。解放區3000萬人民省下自家口糧作為復堤資費,拆掉自家院墻獻石15萬立方米,晝夜興工、孜孜不怠,在1年時間內共完成770多萬立方米的堤防修復工作。
萬丈高樓平地起。誠如中國共產黨諸多偉大事業一樣,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為主心骨,有人民群眾毫無保留的信任與支持,人民治黃事業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創造出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站在山東這片人民治黃事業的原點,回看70余年間山東人民治黃事業的探索歷史,字里行間都寫滿了——團結拼搏,務實奉獻,實事求是,開拓創新。
抗洪斗爭砥礪初心
有的使命,是天然刻在黃河人基因里的。
人民治黃的事業,就在迎戰黃河洪水中發端。
1946年,國民黨提出要堵復花園口口門,引黃河回歸故道,理由是要還豫、皖、蘇89萬黃泛區群眾以正常生活。
本著對全國人民負責的態度,中國共產黨以極大的誠意開啟了黃河歸故談判。1946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早期治黃機構——冀魯豫區黃河水利委員會和山東省黃河河務局相繼在菏澤和濱州成立,機構被賦予的最初使命就是恢復已經荒廢破敗了8年的堤防,遷移河床居民,讓歸故的黃河不再肆虐。
1947年3月,冀魯豫區黃河水利委員會在工作會議上提出第一個治黃方針:“確保臨黃,固守金堤,不準決口。”彼時,山東境內的黃河故道堤防尚且殘破不堪,這個方針并不基于客觀的防洪能力。面對這條歷史上“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的桀驁河流,“不準決口”的聲音振聾發聵,這是不留余地的必勝決心,更是敢于勝利的政治宣言。
大考接踵而至——
用生命譜寫的凱歌
1948年,位于黃河“豆腐腰”河段大溜直沖的高村險工首先出險。此時正值解放戰爭時期,高村作為軍事咽喉要道,一度在解放軍和國民黨軍隊爭奪拉鋸中被反復易主。高村搶險面對的是來自洪水和戰爭的雙重壓力。
同年6月中旬到8月中旬,由于河勢的劇烈變化,高村16個埽壩反復出現險情。更困難的是,國民黨軍隊阻撓工程搶險,其出動軍隊、飛機輪番進行轟炸、掃射,最緊張時,一夜出動飛機襲擾16次。搶險隊員們只得不停轉移,采取“敵來我撤,敵走我搶”策略。又值雨季,道路泥濘,沿黃群眾把這重重困難總結為“蔣、黃、雨”三兇鬧工。
“在敵人的襲擊下,在大雨滂沱的夜里,干部群眾毫不畏縮地堅持搶修工程,最緊張時,在雨中堅持七八個晝夜工作。人員有傷亡,干部病了大部分,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但最終的勝利,對我們是莫大的榮譽與光榮。”王化云回憶高村搶險時動情地說。
韓培城、李廣成,為了在敵人襲擾時掩護搶險人員撤離,直到敵人攻占大堤后才跳進黃河,被沖往下游5千米,幸被一條大船施救;郭國才在躲避敵人進攻時丟掉了被褥和衣物,僅靠一條麻袋在搶險現場過了1個多月……
高村搶險歷時2個月,有數萬名民工參加,婦孺老幼一起上陣,大筐抬土、被單兜草,有的甚至獻出家里的戶框門扇、棺槨壽板,大溜頂沖到哪里,搶險隊伍就搶到哪里。
高村搶險用秸料450多萬千克、青磚200多萬塊、石料500余立方米,先后反復搶修埽壩12道、護岸21段。200余人在此次搶險中犧牲、受傷。這是人民治黃以來與大洪水較量的第一首凱歌,是共產黨人樹立起的誓死保衛黃河、忠實捍衛人民利益的高大豐碑。
凌汛難防
1951年1月,黃河在利津王莊決口。
偉大的事業從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對黃河凌汛的認識過程中,山東黃河人付出了血與淚的代價。
黃河“幾”字彎末筆向上的一挑,造就了山東嚴峻的凌汛威脅。自黃河中下游分界點桃花峪至墾利入海口,緯度向北延伸了3.9度。由于緯度的差異,黃河山東段河道氣溫上段高下段低,往往上段已經解凍開河,冰水下泄,而靠近河口的河段尚在封河中。加之山東河道上寬下窄,極易在下游壅塞堆積、卡冰結壩,造成河道水位的急劇上升。
1951年的開端是一個寒冷的冬天。人們最不愿見到的“武開河”正在演進,4天內開河400千米,水助冰威,一路勢如破竹,卻最終在利津阻塞,并迅速形成冰壩。
同年2月2日,利津王莊險工背河堤腳發現3處碗口大小的洞口,300余民工奮力搶堵,臨河因為被冰凌覆蓋無法找到洞口。工程隊員張汝濱、于宗五等人來不及多想,冒著生命危險跳上冰層,用鎬破除臨河冰塊尋找洞口。
2月3日1時,大堤發出一聲悶響,轉瞬塌陷了10多米。隨著這聲巨響,正在臨河搶險的張汝濱、劉朝陽、趙永恩被卷入冰水中,不幸犧牲。
黃河決口了!
在大自然面前,人類的力量顯得如此渺小。決口發生前,山東黃河人已經竭盡全力。26名爆破隊員頂風冒雪,將50千克重的石夯一次次高高舉起,幾十次錘擊后打穿一個冰洞,然后掩埋炸藥爆破,4天時間內共炸開50米寬、350米長的河道,但并沒有遏制住延伸的冰壩。王莊凌汛決口后,山東省軍區先后出動了飛機、迫擊炮輪番上陣,但從炸翻的冰塊附著的泥土來看,冰塊已經深深扎入河底,河床里已經沒有水了!
王莊凌汛決口,造成利津、沾化兩縣300平方千米耕地、122個村莊受淹,倒塌房屋8641間,受災人口8.5萬,死亡6人。
“凌汛決口,河官無罪。”黃河人從不曾憑這句話開脫罪責。凌汛的發展預測期短,發展迅速,加之冬季天寒地凍,取土、運料和搶險都很困難,以當時的技術與人力條件,橫亙在河道的冰山難以被逾越。
行路難!山東黃河人吸取教訓,埋頭探尋更加系統、科學的凌汛解決方案。
人在堤在,誓與大堤共存亡
1958年7月,黃河出現了有實測水文資料以來的最大一場洪水,洪峰流量達22300立方米每秒。這是人民治黃以來未曾遇到過的巨大考驗,也讓王化云陷入了艱難抉擇。
根據防洪預案,當秦廠水文站發生20000立方米每秒以上洪水時,可以機動利用北金堤滯洪區分洪,這樣可以減輕黃河下游的防洪壓力。但代價同樣慘重,滯洪區內住著100萬人口,有1300多平方千米耕地,一次分洪大概要造成4億元的損失。對于剛剛結束抗美援朝、在百廢待興中起步的新中國,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負擔;具體到滯洪區的群眾個體,則是背離故土的流離失所。
分還是不分?經過幾夜的不眠不休,王化云在綜合分析雨情、水情后,認為此次洪水后勁乏力,憑借山東、河南黨政軍民堅決防守,依靠現有的堤防能夠戰勝洪水。
7月19日,洪峰正式進入山東境內,濁浪滾滾、迫岸盈堤。同年的《大眾日報》這樣記錄:“艾山水位達到四十三點一三公尺,流量為一萬二千八百秒公方,超過保證水位零點九三公尺,在警戒水位以上持續達一百四十八小時……東平湖水位高達四十四點八一公尺……水位比原來的湖堤還高。”
迎戰洪水,山東動員了110萬人上堤防守。“人在堤在,勢與大堤共存亡”的口號聲震寰宇、氣貫山河。在一兩個晝夜內,山東黃河沿線搶修了700千米的子埝,黨政軍民前赴后繼搶險情、筑子堤、堵管涌,詮釋了什么是“團結一心、眾志成城”,更詮釋了什么是“一切面向黃河”。
抗洪前線,全民皆兵。齊河縣許紡大堤出現漏洞,兩名小學生發現后立即上報情況。沿黃村莊迅速集結千余人搶修堵口,30名青壯年不懼危險跳進水中進行搶堵。在抗洪后方,機關、部隊、工廠的人員和廣大群眾喊出“前方要什么供應什么,什么時候要就什么時候供應”的口號,運送物料的車輛排成長龍。石料短缺,工廠就用推土機推掉院墻以供石料,老百姓一夜搬空城市道路的條石,再一車車送到堤防一線。
山東黃河人與黨政軍民一道,憑借著頑強的意志、辛勤的汗水,用血肉之軀在洪水面前筑成另一道堤防。
7月26日,洪峰安全入海。
回望1958年抗洪,這是一場人對洪水的險勝之役。周恩來總理曾不無憂慮地評價:“200萬人上堤,不能算解決問題。”如何讓黃河長治久安,這是擺在黃河人面前永恒的課題。
為人民加固堤防
治理洪水的首要措施,就是實施防洪工程建設。從某種意義上講,一部治黃史,也是一部防洪工程的建設史。
1946年到1949年,冀魯豫區黃河水利委員會的任務是“束水歸槽,防治河患”,人民群眾在解放區的組織下開展復堤整險工作,戰勝了人民治黃初期3個汛期來犯的洪水。
堤防筑得高又長,像銅墻不怕那黃水它發狂
萬里黃河,險在下游。當務之急,是要開始黃河下游的修堤工作,以防御比1949年更大的洪水為目標,加強堤防建設,確保大堤不潰決。
1950年,黃委確認了“寬河固堤”的治河思路,具體包括廢除民埝、加高培厚大堤、石化險工等一攬子措施,歷時8年的第一次黃河大復堤正式拉開序幕。
放眼山東黃河大堤,人山人海、旌旗招展。“只有修好了大堤,黃河才不會決口;只有守住了黃河,才能保衛國家。”復堤的民工秉持這樣質樸的情懷,誓要通過修復大堤守衛人民利益,守衛國家安全。
鄄城縣的吳崇華就是這次復堤中涌現出的全國勞動模范。歷史上鄄城飽受洪水災害,當地老百姓最能掂量修堤防洪的分量。他們從雞叫頭遍干到夜半三更,用杠子大筐抬土,甩開膀子拉車,喊著號子揮起沉重的石硪。吳崇華帶領本村170多名鄉親,車推肩扛,大干了46天。趕上月光明亮,他們干脆干個通宵。鄉親日均推土工效高達8.21立方米,吳崇華個人甚至創造了日推土25立方米的紀錄。作為全國勞動模范,吳崇華光榮地赴北京接受毛澤東主席的接見。當時,涌現出一大批推土英雄和修堤模范。
“腳踏實地干呀,趕在洪水前呀。”這是激情燃燒的歲月,這是值得揮灑熱血的事業。1950年至1957年,人民群眾完成土石方14090萬立方米,千瘡百孔的黃河堤防煥然一新。
20世紀50年代,正值黃河豐水期,1954年、1957年、1958年這3年,黃河汛期流量分別達到15000立方米每秒、13000立方米每秒、22300立方米每秒,第一次黃河大復堤,為戰勝歷次洪水奠定了堅實基礎。
黃河的問題很復雜,我們沒有經驗,還是看一看再說
對于黃河的認識,是一個不斷探索并逐漸深入的過程。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三門峽水利樞紐的建設,一度被認為是根治黃河水沙問題的終極方案。初衷在于通過這一“上攔”工程,攔蓄黃河泥沙,減少黃河下游泥沙淤積;通過調蓄來水,實現防洪調控。1958年,人們盲目樂觀地認為“根治黃河,指日可待”。黃河上中下游眾多工程相繼動工興建,在山東位山、濼口、王旺莊等水利樞紐工程倉促上馬,目的也是便于灌溉與航運。
然而問題接踵而至,三門峽水庫投入使用后,泥沙淤積速度超過想象。1962年,三門峽水庫不得已從“蓄水攔沙”運用改為“滯洪排沙”運用。沿河而建的梯級水利樞紐工程也很快顯出弊端——將河道攔腰切斷的位山樞紐造成回水河段泥沙大量淤積,降低河道排洪能力;蓄水造成工程地下水位上漲,耕地出現鹽堿化。濼口和王旺莊水利樞紐也因為后續經費及勞動力不足,相繼“下馬”。
專家研究后作出了破除位山水利樞紐攔河壩的決定。1963年12月6日,位山攔河壩在轟隆隆的爆炸聲中沉入歷史的長河。
此時正值國家經濟嚴重困難時期,山東黃河3座水利樞紐工程修建共投資1.5億元,工程興而復廢,給國家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損失,教訓極為深刻。
共產黨人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態度貫穿黃河治理始終。認識問題、承認問題、解決問題,任何一項黃河治理的重大決策,都是經過充分而激烈的辯論形成規劃意見。面對這條復雜的河流,黃河的治理要放在更長的時間跨度中去求索,不斷解決新問題,不斷糾偏,繼續上路。
黃河人吸取教訓,盡快恢復下游的排洪排沙能力,“上攔下排”的治河思路也逐步清晰。
1962年至1965年,以防御花園口水文站洪峰流量22000立方米每秒洪水為目標,黃河沿線開始實施了第二次大復堤。
一顆紅心兩只手,自力更生樣樣有
新的問題仍在不斷出現。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黃河處于枯水多沙年份,黃河下游河道出現嚴重泥沙淤積。1973年,花園口出現5890立方米每秒洪峰,洪水表現水位甚至比1958年22300立方米每秒洪峰水位還要高出0.2—0.4米。
泥沙,是黃河難治的癥結所在。歷史上,黃河始終無法跳出淤積—決口—改道的循環。1952年,毛澤東主席在第一次離京視察黃河時,就曾對黃河治理表達了深切憂慮:“黃河漲上天怎么辦?”
人民治黃以來,關于處理泥沙的探索從未停止。除了上攔工程的攔蓄泥沙,黃河中游的水土保持外,黃河下游也在積極尋找治沙的有效方案。
放淤固堤并不是一個全新的技術。1950年,山東利津縣綦家嘴率先打破黃河下游不能破堤建閘的禁區。這處引水能力只有1立方米每秒的涵閘,除了開啟了黃河下游引黃供水的序幕,也帶來了放淤固堤的附加功效。隨后,山東黃河沿線通過虹吸、閘門等,加快黃河放淤改土、淤填堤防等試驗。
1969年,齊河修防段職工大膽設想、科學實踐,開始嘗試在木船上加裝泥漿泵,開啟吸泥試驗,在收獲初步成果后,他們成立了造船組,決心造一艘黃河上的吸泥船。
這是一群經年與石頭、河水打交道的黃河人,雖然他們識水性、懂搶險、會工程,但造船對于他們來說完全是嶄新的領域。時任黃委工務處處長的田浮萍,與修防段的職工一道大膽鉆研,在南坦險工用破帳篷拉起的廠房里,靠著一個個土辦法,克服了一個個難題。憑借著一臺電焊機、兩個氧氣瓶和幾把大錘,他們平地挖爐,冒著高溫將圓鋼一錘錘砸成型,又一錘錘將鋼板碾平;他們自學電焊技術,自研模具工具,憑借著敢為人先的探索精神與自強不息的創造思維,造就了黃河上第一艘自航式吸泥船,并于1970年7月成功下水。
山東黃河人將造船精神總結為“一顆紅心兩只手,自力更生樣樣有”,并將這艘吸泥船命名為“紅心一號”。造船的職工扶老攜幼,光榮地站上“紅心一號”的甲板,參加它的首航。他們當時不曾想到,這艘黃河上不起眼的小船,卻在此后的黃河治理實踐中成長為巍峨巨輪。
利用吸泥船將黃河中的泥沙通過管道輸送到大堤背面,排走清水,淤填堤防,既培厚了堤防,也有效緩解了河道的淤積。黃委迅速推廣了這項技術,明確將制造吸泥船淤背固堤作為黃河下游治理的重要措施之一,并列入國家計劃。
1974年,第三次大復堤提上日程,堤防設防水位以防御花園口流量22000立方米每秒,山東艾山以下窄河道按照11000立方米設防,機淤固堤被廣泛應用于大堤的加高培厚。此外,還同步推進了涵閘改建、滯洪區改建等工程,共歷時12年。
放眼全河,3次大復堤共計培修堤防1300多千米,完成土方22.7億立方米,兩岸堤防平均增高2.15米。這是幾十萬群眾手拉肩扛書寫的工程史詩!
寧可汗水漂起船
21世紀之初,黃河下游堤防建設又添重器——標準化堤防。受1998年特大洪水的警醒,黨中央、國務院決心對黃河堤防再度提升,作出了“建設高標準堤防”的重大部署。
2002年7月,國務院批復了《黃河近期重點治理開發規劃》,要求用10年左右的時間初步建成黃河防洪減淤體系,選定放淤固堤作為黃河下游堤防加固的主要措施。所謂“標準化”,就是堤頂寬度10—12米,堤高程為設計洪水位加超高,建設30—50米防浪林和100米寬的防滲加固淤背體。這是黃河治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超級堤防”。
根據規劃,標準化堤防工程將分步實施,一期示范段設計山東東明段62千米,濟南市區66千米,將為后續標準化堤防建設打造樣板。其工程項目之集中、任務之艱巨、時間之緊迫、施工強度之大,均創山東黃河工程建設之最。
以菏澤、東明標準化堤防建設項目為例,1年多時間內,要在61千米范圍內,完成4000萬立方米土方、18.6萬立方米石方。僅土方工程量,按照第一次大復堤時工效計算,需要近11萬群眾在堤防上用木輪車推一整年。如果將輸沙管道連接起來,可以把黃河水從東明送到北京。變化的是工程技術,不變的是黃河人矢志不渝的奮斗意志。
2005年臘月二十九下午,山東東明黃河標準化堤防建設工地,3號船的鋼纜被流冰拉斷。船長楊興泉來不及多想,撲過去搶修河里的管道。其不慎被卷進黃河的冰水里,一路漂浮,最后,幸運地被1.5千米外的吸泥船的浮筒掛住。被救上岸時,他已休克失去知覺。在此之前,工地下了入冬后的第一場雪,河道溫度達零下13攝氏度,輸沙管道凍住了。黃河人用火烤、用棍子敲,穿上皮衩褲,一個個跳進齊腰深的冰水里,一節節把幾千米長的管道里的冰摳出來……
酷暑8月,黃河灘地的一片沼澤地里,一群光著膀子的黃河漢子吼著號子,蹚過齊腰深的黑泥臭水,用肩膀扛起8根碗口粗的大杠,抬起3噸重的沙泵向前走。灘地沒有路,車上車陷、人上人陷。有的地方人一腳踩下去,可以陷到大腿根。每次吸泥船轉場,黃河人就是赤身光腳,僅穿一件貼身內褲,拖著管道一步步向前挪,這是一群新時代的黃河纖夫,他們用鋼鐵一般的意志,扛起標準化堤防建設的重任。他們說“寧可汗水漂起船,不讓工期拖一天”。
在標準化堤防的冰與火中,淬煉出的是“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特別能奉獻”的黃河鐵軍。
3年時間內,山東黃河河務局集全局之力,5000多名職工全力以赴、不計得失,克服了難以想象的困難,涌現出不計其數的感人故事。2008年,濟南標準化堤防工程榮獲中國工程質量最高獎——魯班獎,這是迄今為止中國大江大河中唯一獲此殊榮的堤防類工程,也是對過往戰天斗地的筑堤歲月的最好褒獎。
長堤無言,血淚筑歌。凝望著這水上的巍巍長堤,母親河被攬入胸懷,鐫刻著探索與艱辛,守護著亙古不變的安瀾夢想。
重點攻堅護安瀾
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于將黃河山東段的工作重心比作一個啞鈴,啞鈴中間是黃河干流河道,啞鈴的兩端,則是東平湖與河口。
原因顯而易見,東平湖是黃河下游最重要的蓄滯洪區,事關大河安瀾大局;黃河三角洲則是重要的生態保護區域,穩定的入海流路關乎東營市城市經濟、社會穩定發展。
在針對東平湖、河口地區的建設與治理過程中,山東黃河人走過了艱苦的探索之路。
防汛王牌的底色
在世界大江大河治理過程中,蓄滯洪區與水庫、堤防、河道等共同構成了防洪工程體系。蓄滯洪區也是保護大河安瀾的最終“底牌”,從誕生之初,就烙印下“犧牲自我、保全大局”的奉獻品格。
1951年,國務院決定開辟北金堤滯洪區,它地跨河南、山東兩省。北金堤滯洪區的運用條件較為苛刻,需黃河花園口水文站發生22000立方米每秒以上洪水,且在運用三門峽、小浪底、東平湖蓄滯洪區調控仍不能解決問題時方能啟用。
東平湖的使用排序靠前。在黃河花園口水文站出現10000立方米每秒以上洪水時,東平湖蓄洪區調控就會相繼開啟,目的在于通過滯洪削峰,來保證黃河艾山水文站以下洪水流量不超10000立方米每秒。
黃河山東段河道特征是上寬下窄,從入魯首站的東明20千米寬的河道,行至聊城艾山卡口,河道一度縮窄到不足300米寬,行洪能力驟然下降,成為過洪“瓶頸”。東平湖恰恰位于黃河下游窄河道的上端,是洪水最后的回旋空間。
1949年,山東黃河兒女頑強地與洪水拼搏,孱弱的堤防防洪標準很低,有的堤段僅僅超出水位2—3厘米,此時,是東平湖敞開了胸懷,納入黃河洪水。
但是,犧牲同樣慘痛,洪水席卷庫區,吞沒民房,沖走牲畜。東平、汶上、梁山等縣2000平方千米的土地盡是澤國。由于東平湖的自然滯洪,下游堤防得以保全。
1950年7月,東平湖被正式確定為黃河自然滯洪區。
1954年,東平湖遇到了黃河、汶河同時來水的不利局面。花園口最大洪峰流量達到15000立方米每秒,大汶河經戴村壩注入東平湖,流量最高達到4120立方米每秒,兩相疊加,東平湖全線告急,二道坡堤段水位一度高出堤頂9厘米,1萬多群眾連夜上堤加高子埝。洪水浩蕩,湖堤岌岌可危,黃河人與縣區干部一道,挨家挨戶動員群眾撤離。最終,135個村莊近3萬群眾一夜撤出滯洪區。第二滯洪區開啟滯洪。
1958年,黃河花園口發生洪峰流量223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東平湖自然滯洪8億立方米,削減了黃河艾山以下河道洪峰流量近2900立方米每秒,給下游抗洪勝利提供了可能。
1958年大洪水過后,關于修建東平湖水庫工程的計劃獲得批復。結合西北部群山的天然堤防,規劃修建70余千米的環湖圍壩,并在圍壩臨湖面修筑石護坡以抵御風浪襲擊,共同構筑東平湖水庫湖區。
為了籌備石料,東平湖施工指揮部從鄰近3縣調集5000名開山工人。凜冽寒風中,地動山搖,鐵錘震裂工人的虎口,鮮血沿著錘把滴落,2米長的鋼釬被磨到只剩下幾寸長,工人用雙手劈開了高山峻嶺,用滿腔熱血點燃了1958年的冬天。
1963年至1965年,修筑二級湖堤,將東平湖水庫分為老湖、新湖兩區,實現分級運用。配套修建了分洪、泄洪水閘。1959年至1960年,修建了十里堡、徐莊、耿山口進湖閘和陳山口出湖閘。1982年,東平湖唯一一次實施人工分洪,分滯洪水4億立方米。
1988年,東平湖又相繼建成了林辛、石洼進湖閘和清河門、司垓泄水閘,不斷改善了東平湖蓄滯洪區控制運用條件,提高了分洪、泄洪能力。“十一五”到“十三五”期間,東平湖不斷改善薄弱環節,重塑鋼筋鐵骨。經過不斷完善與改建,東平湖蓄滯洪區逐漸成長為保障黃河下游防洪安全的一張王牌。
此外,在歷經1951年、1955年黃河利津段兩次凌汛決口,以及1968年至1969年“三封三開”的嚴峻凌情后,1971年,山東省在齊河—濟南和東營—利津兩處窄河段,分別建設齊河展寬(北展)工程和墾利展寬(南展)工程,用作分凌滯洪區。
回望蓄滯洪區建設,不能忽視的是犧牲底色。
1949年,東平湖自然滯洪,梁山、東平兩縣外遷黑龍江、河南和山東省其他市縣6925戶26897人。1954年,黃河、汶河相遇,梁山、東平兩縣遷往黑龍江6958戶32220人。1958年,改建東平湖水庫,并設計常年蓄水運用,工程占用區群眾外遷,遷出527個村莊57405戶278332人。蓄滯洪區的群眾,被迫離開了祖祖輩輩生活的家鄉。
1982年東平湖分洪,造成直接經濟損失達到2.7億元。分洪過后,泥沙俱下,老湖區5平方千米良田被黃沙掩埋,群眾失去生產條件。加之泥沙造成的荒漠化,風卷塵沙起,生態環境也遭遇嚴重破壞。
南北防凌展寬區作為分凌滯洪區,不能修建阻水建筑物,展寬區經濟發展受到制約,群眾生活水平低于當地平均水平。
國家利益高于一切,國家責任重于一切。蓄滯洪區的群眾所作出的犧牲,會被歷史永遠銘記。
為妥善安置蓄滯洪區的移民問題,加快東平湖庫區的建設生產,黨和國家分多次安排專項資金。黨的十八大以來,山東省啟動黃河灘區居民遷建、易地扶貧搬遷、移民避險解困等重大工程,加快推進東平湖的民生建設。
隨著黃河小浪底工程的建成,2008年7月,國務院正式批復,取消南北展寬工程的分凌分洪運用任務,允許開發建設。至此,南北展寬區退出歷史舞臺。
手牽黃河跟我走
翻看山東治黃歷史,黃河河口的兒女總是敢于“第一個吃螃蟹”。在入海口,誕生了“以淤代石”的防汛搶險技術,建設了黃河下游第一座引黃涵閘——利津綦家嘴引黃閘,組建了第一支機械化土方施工隊。諸多個“第一次”,也是山東黃河人開拓進取的最好例證。
在黃河三角洲這片扇形土地上,自1855年黃河在銅瓦廂決口形成現行河道以來,在近170年間,黃河共改道10次,留下了9條入海流路。
黃河善淤、善決、善徙的特點在河口尤為突出。河水挾帶的泥沙,自窄河段進入河口地區,六成沉積在河口河道,四成進入渤海。泥沙讓東營市不斷向海生長,而發展到一定程度,淤積的泥沙讓河口河床愈來愈高,最終黃河水便會另覓低洼處入海,自然發生改道。
人民治黃以來,山東黃河兒女胸懷“人定勝天”的氣魄,擁有“敢教日月換新天”的膽識。他們執著地探索,讓黃河尾閭隨著人的意志來轉移。
1953年,黃河行走甜水溝。此時尾閭小水三河并行,山東黃河人第一次實施人工改道,黃河改走神仙溝入渤海。10年一個輪回,至1963年冬天,黃河入海口處小沙汊河卡冰阻水,洪水圍困孤島地區。為解燃眉之急,第二次人工改道被迫倉促實施,黃河北走刁口河入海。
1961年,在東營土地上打出了第一口油井,勝利油田開啟建設。黃河三角洲蘊藏著豐饒的“黑色黃金”,是新中國迫切依賴的重要能源與經濟命脈。然而,黃河入海流路的不斷變遷卻阻滯了東營市的發展腳步。1964年7月,勝利油田遭遇8650立方米每秒洪水,油井在一片汪洋中停工。1975年,利津洪峰達6500立方米每秒,堤防險情頻出,勝利油井再次停產。此時,行河僅11年的刁口河流路已盡顯疲態,5河并行,漫流入海,改道似乎已迫在眉睫。
早在1967年10月,一支由黃委、濟南軍區、山東黃河河務局等組成的河口查勘隊伍就已出發,他們背負沉重的勘測設備,在沒有路的河口荒原上跋涉,一路披荊斬棘,頂著咸濕的海風和暴烈的陽光,擠睡在漁民與采油隊的窩棚內。1個月后,包括電筒溝子、土匪溝子、甜水溝子在內的18條潛在備用流路被逐一摸清,詳細繪制在黃河入海流路形勢圖上。
經過激烈的討論、反復權衡,離海較近、影響范圍較小的清水溝進入了決策者的視野。
1968年,51000名民工開展了河口治理的第一次大會戰。開挖引河、培厚南大堤、修筑防洪堤。1976年,首次有計劃、有設計、有準備、有科學理論依據的人工控制改道正式實施。同年5月27日,黃河口羅家屋子人工截流成功,黃河正式改道清水溝。河灘上,近百名工人席地而坐,參加黃河改道截流祝捷大會。現場旌旗獵獵,旗幟上書寫著“手牽黃河跟我走”的豪言。
1987年,又一個10年過去。清水溝流路再次出現主道不暢、六汊并行。仿佛希臘神話人物西西弗斯的詛咒,一次次推著石頭上山,又一次次無功而返。黃河尾閭,10年一個輪回,又到了行將擺動改道的前夕。
1983年,東營市正式成立。這個被石油和黃河托舉起的新興城市,經濟產業剛剛起步,黃河流路的穩定是一切發展的基石。穩定清水溝流路勢在必行,黃河人審慎提出了《穩定黃河口清水溝流路30年以上的意見》,立志要將黃河尾閭牢牢固定,開啟一番前無古人的事業。
為了延長清水溝流路的行水年限,黃河口綜合治理循序推進,先后開展河口疏浚試驗,打通河海交匯處的“攔門沙”;實施“截支強干,束水攻沙”,6年時間截堵支汊80余條,延長加高北大堤,修做導流堤;實施一期工程,加固堤防新建險工,開展一系列河道整治;開展“清8出汊”,調整入海口門位置,將向南的行河方向改變為向東北方向入海,采用泥沙填海造陸的方式,為油田營造陸路開采的條件;結合挖河固堤和調水調沙,降低黃河河床……
黃河治理是一項系統工程,經過多年的水土保持工作,黃河中游的來沙量持續減少,加之小浪底等骨干水庫上馬,水沙調控的手段措施越發豐富。2002年,舉世矚目的調水調沙試驗開始運行,大水出好河,黃河下游通暢安流。多管齊下,清水溝至今穩定行河48年,已經遠遠超出了最初設想。黃河收斂了暴戾,不再隨意擺尾。
尊重自然,敬畏自然。黃河治理早已從除害轉向興利。黃河人將河流作為一個生命體對待,黃河三角洲生態保護的重要性凸顯。
1999年,黃委根據國務院授權對黃河水資源進行統一調度,徹底扭轉了黃河用水無序、斷水頻發的局面。黃河河口地區的基本生態用水得到滿足。
2008年,黃委再次提出要轉向功能性不斷流的更高目標。這一次,黃河河口提出結合調水調沙,有計劃地對黃河三角洲進行生態補水。
2010年,干涸34年的刁口河故道重新迎來了生命之水。涓涓黃河水流經龜裂的地面,瀕臨崩潰的生態系統開始逐步恢復,赤地千里的故道重現旖旎風光。
繼往開來志彌堅
幾度春秋,幾多風雨。山東黃河人歷經抗洪洗禮、千重磨難,見證堤防生長,守護初心如磐。
洪水風險依然是黃河流域最大威脅,生態環境脆弱,水資源保障形勢嚴峻,發展質量有待提高,黃河治理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依然需要一項一項去改進、去解決。
那些刻在黃河人骨子里的責任感,仍在代代相傳。
2021年,黃河發生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秋汛。山東黃河河務局5000名職工各司其職,風雨中逆行,堤壩上奮戰,晝夜堅守。
金堤河,上有12市(縣)澇水下泄壓境,下有黃河水出流頂托。上壓下頂,洪澇重疊,聲聲告急。聊城黃河河務局職工家屬叮囑職工陳守一:“腳下是洶涌的洪水,身后就是百姓的家園,決不能退半步!洪水未退,莫要歸家!”
東平湖超警戒水位0.75米,黃河、汶河、金堤河“三水相遇”,峰峰疊加,東平湖調度至關重要。泰山壓頂不彎腰,東平湖管理局副局長孫百啟說:“要在夾縫中求突破,下足‘繡花功夫’,利用極為狹小的洪水調度空間,按照‘一個流量、一方庫容、一厘米水位’的精度進行調度。”
東明黃河河務局防汛辦公室主任劉柱法含淚將重病的母親托付給家人,從伏汛到秋汛,不曾離開崗位半步。他說:“大汛當前必須堅守崗位,職責所在必須沖鋒在前。河安事關民安國安,為國盡忠就是在為母盡孝。”
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重大國家戰略實施5年來,山東黃河人夙興夜寐,不敢有須臾松懈。工程在變,經過幾期標準化堤防建設,2024年,山東黃河800余千米堤防已經實現全線標準化,黃河下游、東平湖、河口的綜合治理提升正在加速推進;生態在變,2023年起,黃河三角洲補水方式由汛前大流量補水,轉為全年按需補水,備用流路刁口河的補水效率屢創新高;手段在變,率先構建“三個全覆蓋”信息感知網絡,以數字孿生山東黃河建設加速實現“四預”功能,數字化、科技化正在賦能治黃工作效能迭代升級。
什么是人民治黃?
人民治黃是面對洪水的團結拼搏;是數十萬人上堤防守,一切為了黃河,一切面向黃河;是抗洪搶險不怕犧牲,以身堵口守護家園;是建設防洪工程的務實奉獻,是嚴寒酷暑中埋頭堅持,星夜兼程拉磚獻石,三過家門而不入;是犧牲局部保全大局,是慎重權衡之后的全局考量。
人民治黃是治河實踐中的實事求是與開拓創新;是大河工匠的大膽革新與小心求索,打破禁區破堤建閘,一窮二白憑心造船,敢立潮頭唱大風;是艱難摸索黃河秉性,踐行求真求實的科學真諦,在與水沙較量中吸取經驗,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反復循環。
人民治黃從山東起步,身背泥土、手掬河水,篳路藍縷、砥礪求索。九曲黃河在山東入海,面朝大海、心向安瀾,昂首未來、闊步向前。
這里有治河先輩的故事,也將留下我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