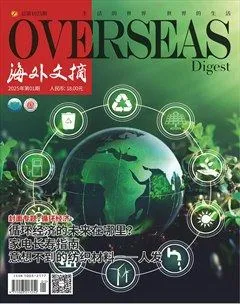新一代非洲國際公民
每年,數百名肯尼亞人前往英美名牌大學學習。畢業時,許多人陷入一個尷尬的境地:無法融入國外社會,但又感覺自己不再屬于家鄉。
| 特殊階層 |
2023年12月30日,女孩們都來到基利菲。桌上擺著酒瓶,揚聲器里放著音樂,離這座度假別墅不到200米就是海灘和印度洋。其中有些女孩曾一起在紐約、邁阿密和西班牙伊維薩島開過派對。現在,她們又相聚在了肯尼亞海岸。
和成千上萬名同屬于一個特殊社會階層的非洲年輕人一樣,這些女孩曾就讀于英美名牌大學。畢業后,有些人回國從事金融或咨詢等高薪工作,有些人則留在國外,生活在倫敦、紐約、巴黎或世界其他金融中心。每年12月,她們都會回國探親。
幾周前,我打電話給表姐瑪麗亞,告訴她我要寫一篇關于這群國際精英階層的文章。瑪麗亞在內羅畢長大,后來去了賓夕法尼亞大學攻讀工程學,眼下在紐約一家藍籌投資公司工作。“你認識符合這些特征的人嗎?”我問道。
她笑了。她說,新年期間,她要去參加一個音樂節——“猴面包樹下”,地點就在基利菲美麗的沙灘邊。這正是我所尋找的特殊社會階層的聚會地點。就這樣,我和她們一起來到了這座度假別墅。
晚上6點,我們在露臺上。人們來來往往,絡繹不絕。瑪麗亞走進屋子,帶著一個女生走了過來。她裹著浴巾,頭發濕漉漉的。“這又是一個聰明姑娘。”瑪麗亞說。隨后,她們回到了屋里。屋內的低音炮在沸騰,每個人似乎都為即將降臨的夜晚感到興奮。
一個高個子女孩來到露臺。她頭發上插著一朵花,墨6a75f3e0dac241e5a71c5ed03ea9882e55883bd06b9102719b46fa4932e8e4c2鏡推到了頭上。她問我能不能給她起個化名。“給我起個性感的名字,就麗莎吧。”她停頓了一下,“不,叫奈昂吉吧,我就叫奈昂吉。”奈昂吉問我:“你會把我寫成一個聰明的孩子嗎?我拿到了一所偏僻大學的全額獎學金。”
之前那個裹著浴巾的女孩走了出來,換上了白色短裙。通常她在12月回到肯尼亞時,會在內羅畢與家人共度跨年夜,然后回到華盛頓特區,她在那里的一家科技公司工作。這一年,她的空閑時間更多,所以來到了基利菲,遠離嚴厲的父母,在海邊參加派對。
奈昂吉告訴她,可以自己起個化名。她說:“哦,那我就起個非洲名字吧。維多利亞湖之前叫什么來著?我就叫那個,‘沒有殖民色彩的維多利亞’。”
像瑪麗亞、奈昂吉和“沒有殖民色彩的維多利亞”這樣的年輕人數以萬計。從19世紀起,殖民國家就開始向一些非洲學生提供西方精英教育,希望這些聰明的年輕人回國后代表西方統治這些國家。但其中不少學生在留學后變得激進,回國后領導了獨立運動。
20世紀50年代末,冷戰時期,東西方大國為爭取非洲影響力,開始向非洲學生提供獎學金。作家阿米娜塔·福爾納將這一時期前往西方的學生稱為“文藝復興一代”,其中包括她的父親——塞拉利昂政治家穆罕默德·福爾納,加納政治家喬·阿皮亞(著名哲學家奎邁·安東尼·阿皮亞的父親),以及《哈佛法律評論》第一位黑人主編的父親老貝拉克·奧巴馬。在一些非洲國家,村民們對自己孩子獲得學位并回國管理國家的前景滿懷期望,于是籌款支持孩子出國留學。尼日利亞作家欽努阿·阿契貝的小說《再也不得安寧》就講述了這樣一個孩子的故事:在村里人的資助下,奧比·奧貢喀沃去了英國上大學。
| 海歸與歸海 |
此后幾十年,出國留學越來越普遍。如今,不出所料,常春藤盟校、牛津劍橋和少數其他大學的學位是最受歡迎的。過去十年,布朗大學來自非洲的新生人數幾乎翻了一番。康奈爾大學也是如此,2013年該校有104名非洲新生,2023年則有195名。賓夕法尼亞大學新入學的非洲學生從2004年的88人增加到了2023年的232人。(以上數據均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
在這些非洲學生中,肯尼亞人是最多的。當他們畢業后回到這個貧困率徘徊在40%左右的國家,幾乎立馬就會發現自己屬于該國收入最高的人群。在內羅畢,你很容易辨認出這個社會階層,尤其是那些二三十歲的年輕人。他們住在中心街區:拉文頓、基利馬尼、基勒萊什瓦和春谷。他們在索尼婭之家餐廳吃飯,去戈科咖啡廳聽現場音樂,在高檔舞廳跳舞,在內羅畢街頭餐廳喝啤酒、吃龍蝦卷。他們參加杜松子酒品鑒晚會,有時還會出席校友聚會(肯尼亞哈佛俱樂部、肯尼亞耶魯俱樂部、肯尼亞牛津與劍橋俱樂部)。他們會去“毯子與酒”,這是內羅畢每隔幾個月舉辦一次的流行音樂節。他們對書籍的品味不俗,但也不太文藝,《蝲蛄吟唱的地方》就很好。
他們在麥肯錫、達爾貝格等管理咨詢公司工作,或在科技公司任職,或在一些以“拯救非洲”為名義的歐美非政府組織工作。每逢周末,他們乘飛機去印度洋沿岸的度假勝地:馬林迪、拉穆、達累斯薩拉姆和基利菲。如果假期較長,他們會去歐洲旅游,或者去聽碧昂斯的演唱會。他們的口音有點像美國人,元音拉得很長。他們周六打板網球,去卡魯拉森林散步,去奈瓦沙遠足,或者去那些你從未聽說過,但《時尚》《孤獨星球》或《名利場》等雜志卻介紹過的“隱秘景點”。
這樣的生活很愜意,但歸國者也會遇到困難。許多人開始覺得,自己無法融入國外社會,也無法適應家鄉。無論生活在哪里,他們都是局外人。29歲的生物學家比拉在耶魯大學和劍橋大學完成學業后,回到了內羅畢。她告訴我,她曾夢想成為一名“可愛的小科學家”,但這在內羅畢似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你出國留學的目的是發財,那還好說;可如果你像她一樣,懷著改變國家的遠大理想去求學,情況就不同了。
對有些留學生的父母來說,孩子的大學學位足以說明一切,可以拿來向親戚朋友炫耀,而且孩子回國后在內羅畢找到了輕松又高薪的工作。另一些留學生回國后的日子卻沒那么美好。他們不斷被問到同一個問題:為什么回來?美國或英國的生活不是更好嗎?理想主義者是最慘的。他們出國是為了幫助家鄉人民,但回國后卻不知道該怎么做。阿契貝筆下的奧比·奧貢喀沃就是如此:烏姆奧菲亞的村民期望他能幫助他們,就像他們當初幫助他一樣,但他沒能做到,這讓他們感到失望。
瑪麗亞、維多利亞和奈昂吉都沒有回到肯尼亞,而是留在了美國工作。瑪麗亞告訴我,她正在爭取美國綠卡;奈昂吉則準備前往費城的德雷塞爾大學攻讀流行病學碩士學位。奈昂吉和瑪麗亞的住處僅相隔五分鐘車程,她們在費城的大多數朋友也來自肯尼亞。
我問奈昂吉是否會考慮搬回肯尼亞。她說:“除非能掙到很多錢。”奈昂吉對肯尼亞的某些社會現象頗有微詞,因此不愿回國。但她也表示,自己更討厭美國的槍支問題和殘酷的資本主義。我不知道這句話有幾分是真的。我覺得她是兩邊的好處都想要。
這些在美國接受教育的女孩們父母都工作不錯,是飛行員、醫生、教師或保險從業者。這些圈子里流傳著一個笑話:美國名校里有兩種非洲學生,一種是像瑪麗亞、奈昂吉和維多利亞這樣的中產階級孩子,他們用中學成績贏得的獎學金再加上助學貸款和兼職打工來維持開銷;還有一種孩子乘飛機回家過圣誕節和復活節,從不缺錢,經常飛到邁阿密或墨西哥坎昆度周末——而正是這些孩子的父母讓他們的國家缺錢。
| 無以為家 |
我們到達了音樂節停車場。天上星光閃爍,遠處傳來音樂。音樂節的創意總監馬特·斯沃洛告訴我,“猴面包樹下”音樂節是由一些具有環保意識、希望在人與人之間建立聯結的人發起的。基利菲或許是肯尼亞唯一可以舉辦這種音樂節的地方,因為這里有純凈的白色沙灘、珊瑚礁和全年普照的陽光。你可以在帆船上徹夜狂歡,或打高爾夫球,或橫渡基利菲溪。
在音樂節現場,女孩們很快融入主舞臺旁邊的人群。音樂節看起來和肯尼亞其他地方不太一樣:人群中約50%是白人——盡管白人在肯尼亞人口中所占比例不到1%。就我所見,約80%的男人赤裸著上身,目之所及全是胸肌、肱二頭肌和腹肌。人們聚集在酒吧和餐臺,歡度美好時光。
在主舞臺邊的一捆干草上,我遇到了28歲的奧黛麗。她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后回到了肯尼亞。她穿著黑色短褲和薄紗上衣,嘴里叼著一根棒棒糖。我問她是否快樂。她說:“永遠都不夠。人們對你的期待不一樣,對成功的定義也不一樣。”
她搬回內羅畢,是因為她想待在一個她覺得自己了解一切事務運作方式的地方。在普林斯頓,她一直問自己是否足夠優秀,但現在這個問題不存在了。她留在美國的朋友都在投資公司工作。“我要是做金融或者在麥肯錫那樣的地方工作,肯定不會快樂。”她說。
我問她是否會和像她一樣的海歸在一起玩。“會。我們對自己的經歷有共同的理解。”她說,“我能以大多數肯尼亞人無法企及的方式接觸世界,很多時候,我會為此感到內疚。”
當晚離開音樂節時,我想起了我的朋友們。他們和奧黛麗一樣,沒有留在美國或英國,而是回到了家鄉。他們很多人都曾夢想對社會產生影響或成為藝術家。他們為大學校刊撰稿、策劃畫廊展覽、參與戲劇演出——但回到肯尼亞后,他們發現自己無法實現這份理想。與此同時,他們感受到學位帶來的壓力,正如奧黛麗所說,他們必須找到一份與高學歷相匹配的高端工作。有時,這仍然不夠。看著那些在紐約從事金融或管理咨詢工作的昔日同學,他們會覺得自己被甩在后面,永遠也追不上。
| 誰是外來者?|
女孩們在音樂節一直待到次日清晨7點。我晚些時候去別墅時,她們都躺在床上,宿醉未醒。別墅里來了一個新人:克勞迪婭。她在基利菲長大,先后就讀于維思大學、牛津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現在,她穿著橙色泳衣,躺在露臺的躺椅上,旁邊是她的兩個妹妹。
克勞迪婭一開口,大家都駐足傾聽。她談到基利菲的階級和種族,以及像“猴面包樹下”這樣的活動如何創造了一個將與會者與當地居民隔開的小圈子。她在20多歲時曾是基利菲的活動人士,但現在,她承認,“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還有資格替這里的人發聲,因為我不住在這里。”
克勞迪婭感覺自己就像一個外來者。她與住在附近的家人見面時,提到自己遭遇的一次種族歧視事件并表示憤怒。她的一位阿姨嘲笑著告訴她,是她的“美國態度”讓她如此苦惱。克勞迪婭感慨道:“好像是我把我的種族觀念帶到了這里一樣。”
女孩們表示,回到肯尼亞,卻在基利菲發現自己是為數不多的黑人,這種感覺很奇怪。瑪麗亞說:“比如昨天,我們在泳池里,有個白人問我們是和誰一起來的。我們不知道什么情況,就說‘我們自己來的’。然后他就把他的黑人妻子叫出來和我們說話。”
話題又回到了種族。肯尼亞白人至今仍被稱為“定居者”。殖民時期,從英國來到肯尼亞的白人家庭得到了大片土地。如今,這些土地仍然是財富和憤怒的來源。在基利菲,殖民掠奪的歷史隨處可見。“定居者和游客是有區別的,”克勞迪婭說,“定居者不和黑人打交道。”
她提到,別墅旁邊有一家人氣很高的酒吧,曾被指責優先為白人顧客提供服務。“我去這些地方是為了支持在那里工作的當地人。我會直接給他們很多小費,幫助他們養家糊口。”
瑪麗亞嘆了口氣。她在內羅畢和紐約都沒有家的感覺。“在這里,我不了解我同胞的生活。在紐約,我也不了解我公寓樓里的住戶。”瑪麗亞說,“我在尋找克勞迪婭對基利菲的那種感情。我就沒有那樣的地方,因為我小時候經常搬家,上的還是寄宿學校。”
阿契貝寫道,奧比·奧貢喀沃在英國時,“他對回家的渴望引發了劇烈的身體疼痛”。那是在上世紀50年代,他只能坐船回家,而旅途的艱辛意味著他在畢業前從沒回過家。因此,他最終回到一個煥然一新的故鄉時,內心很是迷茫。瑪麗亞、奈昂吉和維多利亞則不同。現在是21世紀,從紐約到內羅畢有直飛航班。如果愿意,她們一年可以回幾次家,但這并不能消除她們的背井離鄉之痛。她們的失落感與奧比不同,但同樣深切。
對她們來說,一起回到肯尼亞、一起慶祝新年很重要。三個人因為思鄉之情而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大學畢業后,她們都留在了美國,遠大志向又把她們團結在一起。也許,奧比的悲劇在于沒有人可以分享他的經歷,沒有人理解他接受的教育給他帶來的內疚、野心、孤獨和責任。而瑪麗亞、奈昂吉和維多利亞擁有彼此。此刻,她們正聚在基利菲溪畔,迎接新年的到來。
編輯: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