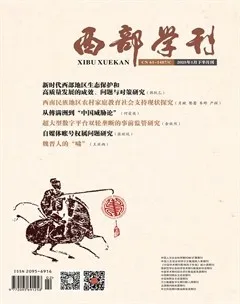莊子哲學中的道器論
摘要:道器論演變長期影響中國哲學思維,是眾多哲學家關切和討論的重點之一。綜觀先秦至近代時期,道器關系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而不斷更新,“器”對“道”發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戰。尤其是自近代以來,“器”的地位得到了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成為時代發展變化中的一個重要縮影,但不難發現主流觀念中視“道”高于“器”的認知結構并沒有被顛覆,這一觀點也一直在對國人價值觀產生著主導影響,而莊子哲學中的道器關系極具個人特色,本質是強調人和物可以達到某種和諧的關系,更加認同各物內在的自足與存在的本身意義,對于當代社會價值觀有極大啟示。
關鍵詞:道器論;莊子;工具;價值
中圖分類號:B223.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5)02-0160-04
On “Dao” and “Qi” in Zhuangzi’s Philosophy
Wei Xing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Dao” and “Qi” theory has long influenced Chines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nd is one of the key concerns and discussions of many philosophers. From the pre-Qin period to the modern perio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o” and “Qi” has been constantly upd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he times, with “Qi” launching one challenge after another on “Dao”. Especially since the modern times, the status of “Qi” has increasingly captured people’s attention, serving as a significant refl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he times. Yet, it is evident that the mainstream perception, which places “Dao” above “Qi”, remains unchallenged. This viewpoint continues to play a dominant role in shaping the values of the populace. In the philosophy of Zhuangz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o” and “Qi” is distinctively personal, fundamentally emphasizing the potential for a harmonious connection between humans and objects. It advocates for a recognition of the inherent sufficiency and the intrinsic value of existence within all things, offering profound insights for contemporary societal values.
Keywords: “Dao” and “Qi” theory; Zhuangzi; technique; value
哲學自誕生之日起就不僅是解釋宇宙,更是一門改造宇宙的實踐學問。其中,道器論演變長期影響中國哲學思維,是眾多哲學家關切和討論的重點之一,一直對國人的價值觀有著主導影響。莊子作為道家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哲學思想豐富精深,不僅具有很強的文學色彩,也頗具哲學智慧,本文主要從《莊子》一書中所闡釋的“道”“器”思想展示莊子獨特的人生觀與價值觀,突出莊子學說在當今思想環境下的警醒與啟發意義。
一、道器論的基礎含義演變
道與器在哲學范疇中具有多方面的含義,“道”首先有道路的意思,如《孟子·告子上》“行道之人弗受”中的“行道之人”是指四處游歷的人;“道”又是途徑、方法的意思,如《論語·里仁》中“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則是此意;“道”又為道德倫理的最高原則,《論語·里仁》中“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就是在闡釋孔子仁的核心;“道”也指治理國家的原則,“道千乘之國”[1]9就強調了治理;“道”還可指學術思想,“吾道一以貫之”[1]44中的“道”就精準表達了此意。“器”意為器皿,指代有形象、可名狀的具體事物[2]。
“器”作為與“道”相對概念的出現是先秦理論思維發展的重大躍進和重要標志,如在《周易》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3]關于道與器的關系,中國古代哲學家一般表述為“道寓于器”“道在器中”“器體道用”或“據器而道存,離器而道毀”。道作為事物的規律、法則是不能脫離客觀事物的,也就是“道者,器之道”。
莊子也將“道”引入了自己的哲學范疇,引出萬事萬物的矛盾旨在暴露出判斷標準的相對性和不確定性。《秋水》一篇中的“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之中的“道”即超出一切相對事物之上的水平,強調在“道”的審視下,萬事萬物所謂的被評價與被比較都是沒有意義的,評價的結果也是極其主觀不確定并且變化的,萬物都可以化去而看作是齊一的,合達于“道”。
對于政治與社會觀念方面,“道器之辨”在中國古代哲學中的主流思想一直是重“道”勝過“器”的。而且由于統治階級的需要,為使我國人口固定于土地之上展開的一系列家族觀念以及土地政策,形成了非常穩固的所謂“士農工商”身份等級觀念。這就導致“器”一直處于并不主流的被冷落方,鉆研“器”之更新與獲利的行為都不被士人所推崇,雖然也有一些“治器”方能“顯道”,“道器合一”等肯定“器”之地位的觀念提出,但都無法改變其根本地位。直到晚清之后,由于西方的沖擊與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傳統文化的進程在各個方面被從外部打破,發生極大改變。
這時的“道器”更多與“體用”“本末”等放在一起闡釋,并且會自然的代表中西物質及意識觀念的不同,與“文明”或“落后”進行聯系。魏源是近代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即倡導學習西方的先進文化技術——也就是用“器”來推動國家的發展,使國家壯大,擺脫現階段被人魚肉的命運。這個觀點的提出可謂是開“學習西方技術”之先河,對后世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也是中國哲學中“道器論”有不同重點的轉折之處。
隨著西方侵略程度的加深以及西方商品文化的影響,人們開始主動或被動地斟酌“道器”話題。清同治五六年間(1866—1867年),朝廷準備令科甲正途學習西方天文算學,但引起了許多爭論沖突,除了是否應“以夷為師”的中西沖突之外,更重要的其實是士人是否應該學習器物制造的道器沖突[4]。在這次沖突中,原本是儒家六藝之一的算學也淪為“機數”而遭抵制,這正是由于中國傳統上一直維持道高于器的理念,但特殊時期又要讓士人擅長所謂的技藝而造成的矛盾。
西方商品經濟的強大使國人感受到了“器”的重要性與作用,只有各方面的技能強于他國并不斷發展更新,才能使國家擁有自保的能力,使民眾生活舒適,保持對“器”的鉆研與推崇。如果一味將“西器”視為末藝,將“士農工商”的價值體系筑牢,這種錯位不僅會使民眾晉升與發展渠道單一,也會造成國家畸形發展,最后招致滅亡。對于“道器”應保持謹慎,明白其觀念對于國家與百姓的引導,盡力保持發揚器與道的益處,防止過度。
哲學在中國自誕生起就承載著所謂政治形態和意識路線的問題,道器觀念作為長期影響中國哲學思維的范疇,不僅是眾多哲學家關切和討論的重點內容之一,也一直在對國人價值觀起著巨大的引導作用。反之,在對一種哲學思想進行評價定論時,我們也無法逃脫對于所產生國家國力是否強盛以及經濟、科技是否先進的考察。道器是長期影響中國哲學思維的范疇,道器之論中不能略去人的參與性,離開人之橋梁作用,道與器就無法達到和諧統一。莊子哲學中的道器關系極具個人特色和代表性,具有很強的探討價值。
二、莊子哲學中的獨特道器論
現階段,面對著科技理性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人類必定會開始重新找尋人生價值的意義,重新考慮科學與道德、理性與情感的意義,尋找到更加具有共性的美德。中國哲學在人生問題上是有先天優勢的,莊子所追求的人生逍遙,從來不是切斷人和物的關系達到一種不與任何外物處的“獨”,而是一種強調人和物的和諧、人和人的和諧所徜徉的自我自在發展狀態。莊子重視人的自主性與自由度,強調自然,想要保全實現各物的自然本性,這些極具中華特色智慧價值的觀念對現階段有極大啟示。
《莊子·人間世》中“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5]156這句話是將樹擬人化,把“我”以樹的身份進行申訴:你與我同為天地之物,為何要把我視為你的工具,在你的標準下探討“我”是否有用,“我”是否有價值。同時,又在警示木匠一味追求有用的同時不僅會迫害樹,反過來也會傷害木匠自身。樹的價值在于作為工具對人有用,那么同樣的,人的價值也會是作為工具對人有用。我們在將物視作人的工具時,人也自然而然地變成了對他人有用的工具,也變成了物,這實際上是將人工具化。這種價值觀的盛行會使任何個體生命首先要面臨價值評級,價值的尺度猶如戒尺將人在頭腦中輕松衡量,猶如刀斧一般雕刻“有用”之功能,削去“無用”之棱角,有用無用的價值尺度,最終施加在了人身上。
從生存角度出發,人的一面必然在社會中有世俗的物質要求與價值尺度,人必須借萬物來維持自身的生存和發展。所以世俗化的價值評級普遍存在,莊子在借樹表達我們人類自身與面對自然事物應當協調的價值評價與自我評價尺度,試圖調和物的本性和人的本性包容和諧。處理價值和自我兩種尺度之間的沖突是錯綜復雜又無法解決的真實問題,那么就需要超越于兩種價值之上更高的智慧來應對,也就是“道”,當發生兩種既合理的但又對立的情景時,在此之上必有一條更高的“道”來維持和諧。
莊子提出的第一層叫“處乎才與不才之間”[6],超越價值與自我兩種單獨的價值尺度,又在此之上提出最終的答案是“乘道德而浮游”,本質是領會萬物與我和諧共處,人自身本性包含與自然萬物相協調,主觀削弱非生存基礎外的主觀欲望與人為附加的欲望,最終達到“物物而不物與物”的狀態。這樣既保持了人的主體性定位,又尊重了物的主體性,達到取用萬物而不為萬物所累的恰當。這種主體性并非人處于支配的地位,而是一種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相關狀態,和如今我們所強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觀有很大的關聯性。從《尚書》開始,中國文化往往將自然界的萬物視為天物,“天物”一詞,既肯定了萬物本身即是自我存在的依據,萬物各有自己的天性,要順其自然保存自己的天性,規定了個物的主體性。另外,人類為了生存與發展,取之于天地,用之于萬物,也應做于天地有益的事情。
莊子的認識論表面結論是從人的特定角度與需要出發,抽取客觀事物的某一方面與片段而形成的極其主觀的、片面的認識;而人又把這種主觀認識用來認識客觀的世界。所以我們的知識都帶有一種“成心”,也就是主觀的偏見,這種偏見使得事物的性質和人的認識都是相對的。我們每個人的心都類似于一個“管洞”,是非都來自成心,我們都在“管洞”之中,只能得到片面的信息。莊子又說:“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5]487從道的觀點來看問題,物是沒有任何貴賤分別的;只有從物的觀點來看才會有高低貴賤之分,所以一切客觀的標準都是不存在的,標準是隨主觀而轉移的、相對的。莊子認為,人沒有任何客觀標準可以遵循,萬事萬物都是同等的。這種認識論的最大突破其實是對一種高與低等級價值觀的打破,是將上層禁錮在評判人成功途徑與自身價值的唯一設置推翻,并且試圖將這種評價權利交到每個人的手中,以期使每個人獲得自我世界里的自在與尊重。
無論哪種評價體系,只要是他者帶來的,未經個人對照自我審判強加的,都帶有強制性與錯誤。評價中重要的不是體系,是主動權與評價權永遠保持在每位個人手上。對于世界的思考與萬物的和諧歸根在于尊重,尊重自己存在的自性,也平等地尊重他人以及他物的主體與自性,我與萬物平等,不低于也不高于的一致。
三、由道器論到獨立人格
一切人的人格都是平等的,但在中國傳統倫理觀念中,從最根源的“天為陽,地為陰”[7],即天在上,地在下的等級觀念出發。這種不平等的觀念就造成了中國社會不平等人格起源。在此基礎上,“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等觀念加深了這種不平等人格,其中“夫為妻綱”流毒最廣,時長最久,造成的壓迫也最深。在古代對女子纏足、殺害女嬰、各種男女不平等的惡習導致從人之生命權開始就無法平等,更難提一切生存權。在這種社會習俗下難以樹立獨立人格,國人更像是社會關系中的符號,而并非實體之人。社會關系中的人存在意義在個體人意義之前,一系列社會關系與人際關系致使人容易養成壓抑自我以求得符合社會高評價的附屬性人格。只有極少數有堅定自我與內在價值的人才能堅守獨立人格的維護,不過,也往往會付出相應的代價[8]。
真正的平等是建立在獨立人格與獨立人格之間的人際關系。如果人尚未獲得主體性,這種雙方相互性關系的形成就無從談起,也就不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平等。在封建帝制所謂的綱常倫理下,依托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制為國家機器提供了強有力的道德統一,在這種宗法制下人與人都作為蛛網上的點存在,而并非活生生的個體的人。與此同時,個體的感覺被有意或無意地縮小,直至取消個人存在的本身價值。中國雖然沒有本土宗教,但是西周初期,統治者通過總結商朝滅亡的教訓,認識到人心比天命重要,進行了一場類似西方的宗教改革,用道德取代了宗教,我們的文化里其實無時無刻有比宗教緊密得多的統一塑造人的制度。在封建時代,“宗法行而天下如一家。故必先齊其家,然后能治國平天下。”[9]這種等級價值觀的統一可以高效地統一出社會想要培養的國民類型。莊子“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的齊物認識論;佛學中的“一多相容”,一和多沒有什么區別,我與眾生沒有什么區別;也包括老子的“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其實都有在認識層面對俗世等級制度的破解。
莊子在齊物論認識上所追求的逍遙游認識,是一種不同于相對自由的絕對精神自由,是指在各種不同場所,與不同的人交往中所達到的和諧關系。這種和諧關系并不排斥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建立深厚的關系,也并非完全的出世,本質是強調物和人可以達到某種和諧的關系,更加認同各物內在的自足與存在的本身意義。物的意義也并非要滿足人的某種需求,肯定“無用之物”是有用的,有其自身存在的價值與根據。但是,莊子也明白這種和諧的狀態在世俗社會中是很難達到的,他對現實困境有清晰的心理預期與了解。這與西方的人類中心主義實際上是完全不同的,人類中心主義是指僅把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作為最高目標,以人為中心評價其他物種,以人的利益需要去對待和處理其他物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觀更強調所有物的主體性,將人類也看作是生物鏈中緊密聯系的一環,認為人類不能簡單地單向度索取,并以人類中心為尺度來審判和我們共同存在的物種,這種無節制的取用破壞必然會反噬傷害到人類[10]。
四、結束語
莊子的認識論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的人生觀。莊子認為,外界物質和自身肉體都是一種對自我的束縛,也就是莊子所言的“有待”和“有己”。而真正的自由是一切條件都不需要依靠,一切限制都沒有,在無窮的天地之間自由地行動,這叫作“無待”;同時,各種主觀自身的條件也要擺脫,以達到“無己”的逍遙狀態。道器論思想之所以在不同的時代都能產生影響,就在于它不僅僅是特定時期社會生存所境遇的焦慮與反省,更根自于對人處在社會與他者之中必然存在的困境與掙脫。個體的人進入社會即意味著必須接受社會中關系的約束并改變自己,會修飾自身并根據某種判斷被評價與劃分等級,追尋自我與價值評價之間的必然矛盾,是我們與生俱來無法解決的矛盾與困境。
參考文獻:
[1]論語·大學·中庸[M].陳曉芬,徐儒宗,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5.
[2]張立文.中國哲學范疇發展史:天道篇[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392.
[3]周易[M].楊天才,張善文,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600.
[4]陳子恒.“器”對“道”的不斷挑戰:近代中國道器觀的嬗變[J].西部學刊,2022(22):164-168.
[5]莊子今注今譯:上冊(最新修訂版)[M].陳鼓應,注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
[6]謝徐林.《莊子》“不材之木”寓言的生態倫理意蘊[J].船山學刊,2023(6):114-125.
[7]黃寶先.試論《易傳》的基本哲學范疇[J].周易研究,1998(2):8-14.
[8]汪鳳炎.獨立自我和互依自我:從文化歷史演化看中式自我的誕生、轉型與定格[J].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4):61-77.
[9]蔡尚思,方行.譚嗣同全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1:368.
[10]化貫軍.從《莊子》天下觀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建構[J].太原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3):8-12.
作者簡介:未新格(1998—),女,漢族,河南安陽人,單位為黑龍江大學,研究方向為中國哲學。
(責任編輯:楊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