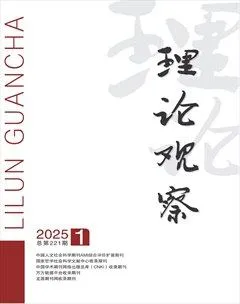數字資本權力的邏輯展開
摘要:數字技術的發展在改變人類生活的同時也重構了資本權力運行機制,塞德里克·杜朗與雅尼斯·瓦魯法基斯等學者提出數字技術發展讓資本主義蛻化為一種新封建主義,控制壟斷平臺的科技寡頭行使著封建領主式的權力。科技寡頭在數字空間中掠奪指令價值以擴張數字平臺,瓜分數字公共空間形成“云封地”,將使用者變為“云農奴”;同時與金融行業聯合進行金融化,提升自身價值占據市場主導地位,改變資本的價值體系與整體運作結構;并介入現實生產,讓產業資本附庸于數字資本,無產階級變得朝不保夕,將數字空間的奴役延續至現實空間。面對數字資本所帶來產業大蕭條,無產階級需要認清情勢,扭轉技術封建主義的趨勢,讓數字技術為促進數字社會主義的建設而服務。
關鍵詞:數字資本;技術封建主義;數字平臺;資本權力
中圖分類號:F091;A8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2234(2025)01—0038—07
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在改變人類生活、引發產業革命的同時,卻因為被少數科技巨頭所壟斷而產生了新的不平等。為分析數字技術所引發的不平等現象,國內外學者提出了諸多如“監控資本主義”“左翼加速主義”“數據殖民主義”等理論與概念試圖說明數字資本如何施展權力造成剝削與壓迫。其中,以經濟學家塞德里克·杜朗(CédricDurand)與雅尼斯·瓦魯法基斯(YannisVarroufakis)為代表的學者提出了名為“技術封建主義(techno-feudalism)”的理論以說明在數字技術的影響下資本主義所發生的改變。他們認為在新技術的幫助下資本主義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遷,傳統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盈利模式已經被封建主義的地租模式取代,在數字資本蒸蒸日上的時候為資本主義宣判了死刑。這一理論一經提出就因其獨特的觀點與深刻的分析吸引了諸如約迪·迪恩(JodiDean)、齊澤克(Slavoj?譕i?觩ek)、祖博夫(Zuboff)等學者廣泛討論,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面對數字資本紛繁復雜的表現形式,本文以“技術封建主義”理論作為透鏡,基于國內外對于數字資本權力已有的研究,為研究數字資本提供新的視角,
一、數字資本權力的創制:價值虛構與圈地擴張
資本在發揮權力作用時,本質上是一種對他人社會勞動具有支配力的經濟權力而出現的,這一點在資本權力數字化之后也仍是如此。[1]數字資本也正是通過吸納數字勞動中各個要素的方式,改造數字勞動的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從而達成其自身的擴張與權力的形成。但無論是資本抑或數字資本,其指揮勞動的能力并非與生俱來,所以研究資本權力的創制問題,必須從數字資本對于勞動的控制能力入手,也就是說從數字資本所依賴的平臺與數字勞動的特殊產物數據入手。
在數字空間中,正是平臺作為私有化的“云領地”承擔了資本運動的中介作用,將數字空間中的各種要素置于自身的系統之內,為資本的運轉服務。技術哲學家本杰明·布拉頓就指出,“平臺擁有一種制度邏輯,這種邏輯不能簡化為我們通常認為的國家、市場或機器的邏輯。它們是一種不同的,但可能同樣強大和重要的形式。”[2]41布拉頓認為,平臺的運行依賴于整合不同的用戶與商家,他們雖然擁有各自的標準,但平臺的作用就在于以自身的標準,也即接入的協議,重塑整個交易,讓用戶與商家都整合于平臺的系統之內,就像組裝工業產品的不同零件一樣,形成了系統內的標準化(intrasystemicstandardization)。當平臺介入了數字空間中的交易與流通的時候,原本的“買方—賣方”的流通過程被置換為了“買方—平臺”與“平臺—賣方”的組合,而平臺以數據的流通協調用戶與商家的平衡并且獲利。布拉頓指出,“平臺對用戶輸入信息的調節可能會導致該信息對用戶的價值增加。平臺網絡效應吸收并訓練這些信息,使其對個人來說更可見、更結構化、更可擴展用戶或與其他用戶的關系,進一步使用它,從而增加其社會價值。與此同時,從這些流通中獲得最大凈利潤的可能是平臺本身。每次用戶與平臺的控制算法交互時,它也會訓練這些決策。”[2]48價值的增值依賴于平臺的調控作用,當用戶使用平臺獲取信息時,平臺能夠通過對于數據的整理與調節為用戶匹配最合適的信息,經過平臺的調節原有的數據才能被稱之為信息,此時數據進入了流通之中獲得了價值形式,其價值得到了提升,而平臺在此之中獲得了更多數據的積累,平臺本身以及其所使用的算法也得到了訓練,從而提升了自身的總價值。所以在數字空間中,“數據采集為算法提供信息,算法反過來又指導行為,兩者在反饋循環中相互促進”[3]109,也就是說以算法為中介,行為的產物數據在平臺算法的處理中成為行為的“前提”,使得平臺算法不斷優化以及數據本身再生產。基于此,平臺與數據形成了“正反饋循環”,不斷增強著對于數字空間中行為的調控。
在此,平臺的調控能力能讓記錄日常活動的數據獲得了“指令價值(commandvalue)”的價值形式,而這一價值來自經過算法訓練后引導我們購買的商品的剩余價值與生產指令價值的社會勞動時間。[4]也就是說,平臺可以無償從指令價值的兩個來源——平臺內的商家與用戶處分得或者無償占有其剩余價值,從商家處分得的剩余價值作為“云地租”而被繳納,而用戶一般并不能通過自身行為的數據獲得收益,所以用戶的價值則是被無償占有。我們可以發現數字資本榨取剩余價值的方式混合了封建主義的直接掠奪與資本主義的通過雇傭勞動的剝削,并且保留了資本逐利的本性。平臺通過算法產生并分析數據,指揮著數字勞動中各個要素的流通,源源不斷地獲取數字空間中的經濟權力,而當經濟領域中權力得到固化,即平臺獲得了壟斷地位時,經濟權力就擴張為政治、社會等多方面的權力。因此法國經濟學家迪朗提出了“技術封建主義”這一假說以描述基于數字技術發展所引發的經濟、政治以及社會等多方面新變革,并提出,“平臺正在成為領地……平臺組織的數字領地被分割成相對獨立的、相互競爭的基礎設施。誰控制了這些基礎設施,誰就集中了對參與其中的人的政治和經濟的支配權。”[3]116在迪朗的筆下,平臺通過其有效的資本與勞動的調控作用,形成了新的基于經濟的依附關系,并以此為基礎收取“地租”,而當依賴關系進一步發展至壟斷之時,原初的互聯網公地也就被科技寡頭所分隔,數字空間所承載的公共服務也被私人占有,形成了類似于封建主義的社會結構。所以瓦魯法基斯將數字空間的私有化稱之為“新圈地運動(NewEnclosure)”,并提出“這是我們在二十一世紀獲得自己身份的途徑”。[5]72
正如“圈地運動”不僅僅是單純的經濟事件一樣,互聯網的“新圈地運動”產生的影響不僅限于經濟領域內,同樣重要的是形成了超越原有民族國家界限的數字秩序。[6]與直接受到物理限制的現實空間不同,數字空間可以隨著軟件、算法等因素的發展不斷拓寬自身的界限,這使得“云領地”的主權不像國家被物理的界限所劃分,而是會隨著技術的發展不斷更新并且拓寬自身的邊界。“云領地”的范圍實際上與能夠接入平臺的使用者的數量與所提供的服務范圍成正比,這也就意味著擁有越多用戶提供越多服務的平臺具有更大的權力范圍,而對于使用者而言則意味著需要與平臺進行交互,將自身的信息通過平臺數字化才能成為數字空間的主體,也即平臺的“用戶”。但大多數獲得了“用戶”的身份的使用者也同時成為平臺的“云農奴”,在不斷地受平臺引導無償貢獻數據、點擊率以及大量內容為平臺提升吸引力,讓平臺源源不斷地獲取指令價值的同時,卻無法得到報酬。所以,擁有類似封建領主權力的科技寡頭為獲得價值增值必須不斷吸引更多使用者進入平臺以擴張自身的范圍,而足夠大的平臺又因其提供服務的優勢與壟斷的特征能夠吸引更多使用者,形成新的“正反饋循環”。而這也就意味著,用戶更加難以離開平臺,并且平臺的控制能力將會在迭代中不斷增強,所以數字資本所推動的“新圈地運動”所形成的數字秩序在對于主體的規訓以及權力的擴張這兩方面的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擴張與增強。
我們可以發現,數字資本權力的創制建立在平臺的價值虛構之上,算法賦予的指令價值的積累是數字資本能夠獲得超額利潤的來源,而平臺的權力構成與范圍擴張也基于相同的邏輯,數字資本權力并非內在于數字空間之中,而是通過炮制出不同的規則與規范引導使用者參與的述行性(Performativity)結果,這也正是馬克思在分析商品拜物教中所提到的,“生產這些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為起調節作用的自然規律強制地為自己開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頭上時重力定律強制地為自己開辟道路一樣。”[7]如同必要勞動時間作為起調節作用的自然規律依賴于市場中的所有參與者按照這一規律行動,數字資本權力的邏輯也需要所有平臺內的參與者按照其所指定的規律行動,而這正是依賴于社會尺度的價值形式的建立,讓所有使用者相信擁有流量擁有用戶的平臺是高價值的唯一選擇,即使價值的形式甚至價值的估值由平臺賦予,并最終使得數字資本權力在數字空間內形成了閉環并且不斷增值。
二、數字資本權力的聯姻:數據化與金融化的并駕齊驅
數字資本在數字空間中獲取權力的過程并非孤立無援,已類似于產業資本在流通中需要商業資本與生息資本的協助。同樣,數字資本的運作同樣也需要金融資本將平臺金融化以完成自身的資本積累。數字資本所獲得的平臺壟斷地位可以為其在數字空間內獲取超額剩余價值,但資本逐利的本性讓其野心不止于此,正如馬克思所言,“(資本)力求摧毀交往即交換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個地球作為它的市場”[8],科技寡頭們需要通過金融化的方式進一步提升自身的價值,超出數字空間與科技行業的限制,在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剩余價值的分配中占據主導地位,以攫取超出數字空間內的權力,而這需要通過與金融行業的聯合。
科技寡頭所引導的數據化與金融行業施行的金融化過程有著相似的述行性邏輯,在實際運行過程中二者也是相輔相成。金融行業所屬虛擬資本與傳統的產業資本存在質的不同,虛擬資本并不需要真實地參與流通,也并不與產業直接掛鉤,其價值的增值依賴于對于未來價值所產生的預期,即使現實市場的行情下跌,金融行業仍可以通過套利、對沖以及投機等無風險或者低風險交易策略讓虛擬資本所虛構的價值增加。這些策略實際上是通過將不確定性的波動率用公式與模型的方式作為參考因素確定化,反身性地讓所有參與者以被數據化的風險作為參考進行交易,也就是說將交易的本身的過程作為交易的前提,從而讓“對于未來的預期”成為“實際發生的未來”[9]112,以符合公式與模型的測算。在此,我們可以發現金融化與數據化直接的緊密關系,金融化依賴于數據化,而數據又可以通過金融化被賦予更高的價值,這為科技寡頭與金融行業的聯合提供了基礎。
金融化在重新分配價值的同時也重塑了商品市場,潘塞斯基將金融化的作用總結為,“述行性和客觀化的統一導致了(市場)整體性的重新概念化,即從自成體系的形式轉變為永久性再客觀化的形式”,并且這種“(市場)整體性只不過是一個真實的社會虛構”。[9]153正是能夠標示不確定的金融模型與參與者的按照金融模型的投資行為產生了參與其中的金融市場本身,而金融市場又是其所依賴的金融模型的準確性的來源,正是這種循環結構通過數據化進程讓金融市場成為“真實的社會虛構”,從而能夠不斷利用對于波動率的控制提升價值,收割財富,改變傳統市場中價值分配的格局。數字資本在其云領地內的自我賦權完成了虛構資本的職能,以地租的形式瓜分了數字空間內獲得的剩余價值,而金融行業的介入則幫助平臺進一步擴展了數字資本的虛構,在市場中提高了數字資本所控制的無形資產的價值,使其在數字空間之外仍能參與剩余價值的分配。
虛擬資本相對于生息資本因其自身價格的特殊性,不受限于具體的生產流通仍能參與剩余價值的分配,那么數字資本的金融化就是在不失去對于數字勞動的剝削的權力的前提下,越過數字勞動生產流通過程的限制,提升自身的價值。我們知道,數字平臺的增值直接依賴于基于算法的數據的產生與流通,也就是說數字資本雖然能夠通過算法賦予數據價值,但是其數據本身的增值過程仍然直接與用戶的使用掛鉤,訪問量與下載量仍是數字平臺體現其內在價值的重要指標。但是當平臺接受金融行業的資本注入之后,平臺的獲利方式將不僅僅限于出售所提供的服務或者從中抽成,而是通過其自身所占據的壟斷地位與所預估的發展潛力來吸引投資者進行投資。也就是說,平臺雖然能夠通過對于勞動的掌控,在數字空間中獲得超額剩余價值,但是價值的獲得仍然依賴于商品的流通過程,例如通過外賣平臺的抽成或者直接的數據販賣,但是當金融資本能夠給平臺帶來巨額的融資時,平臺發展所考慮的就不是如何保證收支平衡,而是如何擴張自身完成更高的市值預估,這也是為何大量互聯網平臺企業的巨額虧損都不影響企業存續的原因。[10]
正是在金融資本的幫助下,數字平臺的增值才真正跳出了具體商品生產流通過程的限制,當然這并不是說平臺的價值與生產無關,而是說平臺的價格以及其獲取剩余價值的能力并不再受到具體的商品生產流通過程的限制,因為“這些科技平臺的金融估值,主要不是建立在它們吸引廣告收入的盈利能力上,而是與它們吸引未來投資的感知能力有關。”[11]正如前文所言,平臺自身的發展邏輯與金融行業的增值邏輯并行不悖,都需要依賴于對于未來的預期而獲得增值,并且相對于其他產業,數字平臺自身并不參與生產卻指導生產,其估值也更加依賴于預期,容易產生規模效應形成壟斷。因此,大量金融資本的注入可以讓平臺以“空間換時間”,通過低價競爭、收購、合并等方式快速增加自身用戶量,獲取更強的壟斷地位,以形成對于未來發展得更好的預期,從而讓新的資本愿意投資,原有金融投資方所擁有的投資回報也會獲得增值,平臺本身則可以發展壯大。所以,相對于舊有的產業資本與商業資本,金融資本更愿意與數字資本結盟,將資金注入數字平臺,這不僅僅是因為數字技術的發展本身就可以讓金融投機活動擁有更多方式與更低風險,更是因為兩者的發展都具有相同的“客觀化”與“述行性”邏輯,所以數字資本與金融資本的聯合能夠形成相互促進的增值機制。
數字資本與金融資本聯合不僅實現自身的增值,還深刻地改變了資本整體運作的結構,在金融資本的調控下,產業資本的利潤空間被擠壓,而數字資本所獲取的“云地租”成為金融資本追逐的新目標。約迪·迪安指出,“越來越多的資本不再投資于生產,而是作為租金而儲存或再分配。價值的自行增殖因而被削弱。”[12]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各國央行通過大量印發貨幣來拯救市場,但是巨量的資本并未用來復蘇產業,促進市場的流通,而是被逐利的投資者用于購買選擇對于增長預期更為敏感的股票、債券以及金融衍生品,因為央行的救市政策給予市場增長的信心。而能夠從金融市場快速獲利的則是與金融行業有著相同邏輯的數字平臺,擁有充足資金的壟斷平臺能夠以其壟斷地位獲得更高的估值,獲得更多的融資,最終促進市場繁榮的政策成為阻礙市場發展、產生壟斷的原因。所以,正如齊澤克所指出的,“它們(金融措施)的目的不是幫助實體經濟,而是將大量資金投入金融領域(以防止像2008年那樣的金融崩潰),同時確保這些資金的大部分不會流入實體經濟(這可能會導致惡性通貨膨脹)”。[13]金融行業與科技寡頭的聯合并未促進實體經濟的復蘇,而是讓經濟脫實向虛的程度進一步加深,讓投資活動從促進經濟運行的“潤滑劑”變為了從產業資本處吸血的“寄生蟲”,傳統產業資本所賴以生存的自由市場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依賴自由市場的生產活動也被數字資本所擠壓。
三、數字資本權力的入侵:實在依附虛構、虛擬奴役現實
數字資本的擴張并不滿足于控制其所創造的數字空間,當數字資本借助金融資本完成金融化的改造之后,數字資本所統治的數字空間將不再作為一個平行于現實世界的虛擬世界起作用,而是被真實地“嵌入”了現實生活當中,作為“抽象的實現”參與進市場運行之中。此時,現實中產業資本與商業資本運行邏輯將讓位于數字資本運行的邏輯,作為派生的數字空間中的價值分配反而能夠決定現實中利益劃分,數字資本權力以此入侵現實,讓現實成為虛擬的“附庸”。數字資本與傳統產業或者商業資本雖然同屬資本,卻擁有不同的剝削邏輯,這使得在技術封建社會中的地位產生了巨大差別,數字資本家加冕為“云領主”,而傳統產業資本家則淪為前者的附庸。數字資本的云主義者不僅能夠在屬于自己的云封地,也即數字平臺中獲得封建領主式的權力,同時也能在現實世界中獲得同類的權力。
數字平臺能通過自身提供的大數據服務調節現實生產,讓加入平臺的企業在競爭中能夠獲得優勢,使得企業不得不向平臺繳納基于平臺的無形資產的租金。而數字平臺卻并不需要遵循市場競爭的邏輯,也即通過降低產品售價或者提升產品質量以相互競爭市場份額的市場邏輯。“沃爾瑪沒有壓低亞馬遜的價格,也沒有提高其商品的質量,而是利用自己的數據庫吸引更多的用戶進入其新建立的云封地。”[5]131平臺之間的競爭是通過制造差異,創造而非吸引更多的用戶需求的競爭,通過為自己的云領地重新劃界,將更多用戶吸納入自身的領地之中。因其區別于傳統資本主義而類似于封建主義的運行方式,科技寡頭不僅僅在其創造的云領地中是“云領主”,在現實生產生活中,也作為擁有類似封建權力的“云領主”而存在。同時,由于云領主們擁有信息系統所固有的不對稱性以及和企業間的不平等的議價能力,能夠在數據流通中獲得相對于單個企業更多的數據,并且還能利用這些信息進一步提升自身的創新能力,從而能夠鞏固自身的信息壟斷地位,整合整個價值鏈,成為生產活動中不可或缺并且占據領導地位的一環。
而與之相對應的,瓦魯法基斯將從事傳統商品生產的資本家稱之為“附庸資本家”,并指出,“云資本最大的成就是在其人工智能-算法-數字網絡中不僅引入了為云主義者的利益而改變工人和消費者行為的過程,而且還引入了市場本身——將整個資本家階級變成了它的附庸。”[5]296的確,傳統的商品生產越來越依賴于按照所提供的大數據的分析結果進行生產,這使得產業資本家失去自身的獨立性,成為數字資本的附庸;但更重要的是,從整體的資本循環結構而言,從資本主義價值的生產與分配而言,傳統產業資本家所剝削的剩余價值在不斷地向數字資本與金融資本的聯合體中輸送,金融資本獲得利息與金融地租,而數字資本獲得平臺地租,產業資本被迫限制了自身的投資發展,而正如前文所言,即使國家出手救市,能夠在超發貨幣政策中獲利的仍是數字資本。并且當金融行業與數字資本的聯合體占據主導位置時,傳統產業為了獲得更多投資,必須砍掉低收益的有風險的部門,并且不再利用利潤擴大再生產,而選擇在金融資本的幫助下運用金融手段獲得收益。[14]這使得商品市場進一步萎縮,傳統產業的運行模式越來越像金融行業與數字資本的聯合體,傳統資本家最終只能淪為附庸。
數字平臺的迅速崛起與傳統產業的逐漸沒落成為被杜朗稱之為“加州意識形態”的互聯網能夠通過技術來實現無剝削的烏托邦觀念最好注腳,其核心正是“信息技術與創業資本主義密不可分的神話”[3]144。以谷歌、蘋果、亞馬遜為代表的坐落于加州的科技公司的繁榮發展看似是科技的進步淘汰了落后的產能,但是其繁榮同時也帶來了產業的衰落、就業的不足以及生態的惡化。在先進生產力戰勝落后生產力敘事的偽裝之下,實際上是生產關系的根本性變革,數字資本并不與產業資本并列,在剩余價值的分配中,數字資本能夠占有產業資本的剩余價值,所有宣傳的個人奮斗與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都只適用于附庸們之間的斗爭,而云領主自身則是置身事外。數字資本所追求的地租模式戰勝了產業資本所追求的利潤模式,數字資本展現的權力模式讓傳統資本家淪為附庸,而民眾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成為朝不保夕的云無產階級。
隨著傳統產業的衰落,企業為減少成本進行資產重組改革,使得處于非核心部門的員工從正式員工淪為合同工或者外包,而為增加利潤所引入的彈性工作制更加便于算法的管理,讓工作的數量、工作的內容以及工資都能被算法調控,人為地增加產業后備軍的數量。同時,傳統工作場所與工作模式也隨之發生改變,加州意識形態所許諾的自主性與創造性并未為大多數勞工帶來自由,數字資本能夠更加精細化的算法意味著對于勞動更嚴格的控制,工作在變得更復雜的同時也變得更加壓抑。在數字資本的影響下,云無產階級們承受著經濟與精神的雙重壓力,經濟上無產階級面臨著失業的困境,雇傭安全越來越得不到保證,越來越多的勞工被迫成為朝不保夕的流眾,而不得不從事多項兼職工作以養家糊口,但為從事兼職所花費培訓技能的無償時間與前期投資卻將其拖入了無止境的深淵,讓其成為越忙越窮的窮忙族;在精神上,短期與多線程的工作模式讓勞動者在工作時往往需要面對大量信息,快速做出行為決策,而忽視了反思與集中注意力的能力,更難從事專精的工作,更難跳出兼職與外包工作的泥潭,看到通過職業發展上升的路。斯坦丁指出,朝不保夕者經歷著四個A的精神階段分別是:“憤怒、失范、抑郁與異化”[15]。而造成其現象的原因正是數字資本所促進的經濟體制的改革提升了工作的彈性與不安全感,這就使得勞動者無法在工作中獲得自尊與社會價值,無法形成社會認同。這也是為何瓦魯法基斯會認為云無產者過于弱小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自身遭到了產業資本與數字資本的雙重剝削,更是因為算法與屏幕的阻隔使得云無產者無法自發地形成有力的團體,又由于工作的不穩定性更難以求助工會等團體為自身發聲。
綜上所述,數字資本的高歌猛進帶來的卻是產業資本的附庸化以及無產階級朝不保夕的狀態,所以杜朗將數字資本所帶來的創新稱之為“沒有增長的創新”[3]55。科技寡頭在近二十年間通過掠奪云農奴無償的數字勞動、收取附庸企業的云地租以及擠壓云無產階級的工資獲得了巨量的財富,但是巨量財富的累積卻并沒有用于市場的循環,而用于進一步擴張自身的云封地的范圍,增加自身無形資產的比重,以獲得更多的云地租。這也是數字資本與一般產業資本的區別所在,產業資本的擴大再生產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市場的流通,在增加不變資本投資的同時也會相對應地增加可變資本的投資,但是數字資本積累帶來的卻帶來了市場的停滯,因為相對于可變資本的投入,數字資本的獲利模式就決定了數字資本相對于傳統產業資本必然更加不成比例地投資于不變資本,也即投資于數字平臺的擴張,傳統企業同樣在這一模式的主導下選擇重資產輕人力的模式以提升自身的估價,并且可變資本的部分卻能在數字技術發展的過程中減少,這將會提高資本有機構成并導致利潤率的下降最終引發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所以瓦魯法基斯將以“誰殺死了資本主義”作為其書的副標題,數字資本殺死了傳統產業資本所依賴的市場,重塑了資本網絡中的權力關系,讓“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二元結構,變為了“云領主、附庸資本家、云無產階級與云農奴”的四元結構。這也就意味著,不能混淆云領主與附庸資本家之間、云無產階級與云農奴之間的區別,云領主不需要像傳統資本家一樣,直接通過對于勞動力的剝削獲得剩余價值,直接剝削剩余價值的工作由附庸資本家完成,而是以云地租的形式虹吸資本循環過程中其他環節的剩余價值,使自身藏身于幕后,降低勞資沖突所帶來的風險,并能夠控制整個勞動過程,并將其影響輻射至市場之外,形成了經濟、政治與意識形態領域的全方面控制。
四、結語
以“技術封建主義”理論作為透鏡,可以明晰數字資本權力的施展方式,解開經濟生活、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態交織的扭結。數字資本雖然能虛構出指令價值等新形式,但剩余價值的來源仍然是工人的剩余勞動,所以并不真正參與現實生產的數字資本的增殖實際上形成于數字平臺與現實世界之間的雙向運動。數字平臺賴以生存的數據來自對于現實活動的記錄,但數據經過算法處理之后能夠為平臺所使用服務于數字資本,并且數字平臺在金融行業作為催化劑的作用下重塑商品市場中的生產關系,讓平臺能夠控制現實勞動,使得數字資本在現實世界肆意增殖。也就是說,數字資本的邏輯來自對現實生活的抽象,而數字資本的抽象邏輯最終無差別地將自身實現,現實的抽象與抽象的實現這兩條道路讓所有人都卷入了橫跨虛擬與現實的“技術封建帝國”之中。瓦魯法基斯等人深刻地發現了當代資本主義的癥結,卻忽視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程其實處處存在著矛盾,做出了“資本已死”或者“資本主義正在消亡”的錯誤判斷,最終只是照貓畫虎般地提出了云無產、云農奴與云附庸聯合的口號。
實際上正如瓦魯法基斯自己分析的,技術封建主義是經濟形式、地緣政治、科學技術與意識形態等多方面因素的產物,科技寡頭實際上正是承接了晚期資本主義的復雜情勢才獲得了封建領主般的權力,正如馬克思對于波拿巴復辟的分析一樣,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的調整所引發的動蕩會被上層建筑中的反動力量所利用,產生上層建筑在形式上的倒退。但馬克思同樣還指出,波拿巴“既被他的處境的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磨”又“不得不以不斷翻新的意外花樣吸引觀眾把視線集中在他這個拿破侖的頂替者身上”。[16]也就是說,試圖利用階級對立從中為自身謀利的波拿巴,最終會因為其自相矛盾的政策而無法平衡多方利益,最終走向失敗。科技寡頭與波拿巴處在相似的位置之上,只不過波拿巴在全球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的經濟對立中選擇了民族國家,而科技寡頭則屬于能夠收割全球剩余價值的數字資本一邊,而兩股勢力的對抗又共同形成了“歷史的反復”。所以柄谷行人指出,“新的‘階段’并非超出了《資本論》所提示的認識,即,資本主義經濟的‘界限’。資本的積累—擴大如果沒有這種大蕭條帶來的暴力性重組,是難以實現的。”[17]
當下正處于數字資本所帶來產業大蕭條正在對舊有資本主義內部權力關系進行重組的情勢當中,科技寡頭向附庸資本家承諾算法的發展能夠提升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而向云無產階級承諾個人雇傭與彈性工作制能為個人帶來工作的自由,向云農奴許諾了數據的采集能夠提供更好的服務,但科技寡頭的承諾無一兌現,只有自身與伙伴金融行業獲得了收益。所以,與波拿巴逐漸不能再調和階級關系、成為代言人一樣,數字平臺對于現實行為數據的收集分析能力也將越來越差,當然這并不是簡單的因為“失去民心”,而是因為無論是算法提供的行為預測還是商品定價都依賴于市場的繁榮,只有在普遍的社會交換的市場環境中對于價格等信息的處理與預測才有意義,所以無論是科技寡頭還是金融資本都是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鼓吹者。但是當科技寡頭與金融行業對于剩余價值的虹吸將導致其賴以生存的自由市場遭到毀滅性的打擊的時候,市場運行以及預測算法的述行性邏輯將會被改寫,數字平臺與金融資本的擴張將會暫緩,甚至萎縮。因為無論是勞工還是普通產業資本家,都無法掌握市場的全貌并且需要在市場中進行經濟活動,所以不得不依賴于價格等信息體系做出商業上的判斷,但是當市場失去了有效配置資源的能力時,就需要律法、政治手段等其他反饋調節機制發揮作用,那么對于市場的預測將需要考慮更多超出市場的變量而變得更加困難,同時因為市場作用的減弱,對于市場的預測也將變得更加沒有意義。也就是說,如果知識、信息與數據不能占據主導地位而只是作為要素而參與生產,那么就沒有成為資本的能力。[18]而數字平臺對于市場的擠壓正好會毀滅市場所擁有的普遍性的調節能力,讓知識、信息與數據失去成為資本的地位。實際上技術封建主義仍然是長在資本主義樹上的果實,依賴資本主義的市場作為養料而生長,其擠壓市場的行為對自身也無異于釜底抽薪。瓦魯法基斯的技術封建主義的判斷應該繼續補充,技術封建主義發展不僅僅會殺死資本主義同樣也會殺死自身。所以,為了避免最壞的結果的發生,無產階級所需要正是運用當下的情勢,扭轉技術封建主義的趨勢,讓數字技術為促進數字社會主義的建設而服務!
〔參考文獻〕
[1]胡樂明.規模、空間與權力:資本擴張的三重邏輯[J].經濟學動態,2022(3):3-11.
[2]BenjaminH.Bratton,TheStack:OnSoftwareandSovereignty,Massachusetts,Cambridge,MA:MITPress,2015.
[3]塞德里克·迪朗.技術封建主義[M].陳榮鋼,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4.
[4]MOROZOVE.Yanisvaroufakisoncrypto,theleftandtechno-feudalism[EB/OL].[2024-07-30].https://the-crypto-syllabus.com/yanis-varoufakis-on-techno-feudalism/.
[5]VAROUFAKISY.Technofeudalism:Whatkilledcapitalism[M].London:Penguin,2023.
[6]陳堯.數字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基于壟斷資本積累、空間權力擴張雙重視角[J].理論月刊,2023(9):84-93.DOI:10.14180/j.cnki.1004-0544.
2023.09.009.
[7]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
[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9.
[9]阿希姆·潘塞斯基.21世紀金融資本論:投機資本的新理論[M].王彩萍,黃志宏,許金花,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23:153.
[10]劉震,蔡之驥.政治經濟學視角下互聯網平臺經濟的金融化[J].政治經濟學評論,2020(4):180-192.
[11]亞當·阿維森,埃拉諾·科萊奧尼,楊佳鋒.信息資本主義視域中互聯網上的價值創造與價值分配[J].國外社會科學前沿,2022(9):25-42.
[12]約迪·迪安,靳呈偉.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新特征[J].國外理論動態,2022(4):117-127.
[13]趙丁琪.倦怠社會、技術封建主義與西方資本主義的危機——訪著名哲學家斯拉沃熱·齊澤克[J].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4,9(6):68-79.
[14]CEDRICDURAND.FictitiousCapitalHowFinanceIsAppropriatingOurFuture[M].London:Verso,2017:138
[15]蓋伊·斯坦丁.朝不保夕的人[M].徐偲骕,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36.
[1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7.
[17]柄谷行人.歷史與反復[M].王成,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31.
[18]藍江.一般數據、虛體與數字資本:歷史唯物主義視域下的數字資本主義批判[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2:208.
〔責任編輯:侯慶海,周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