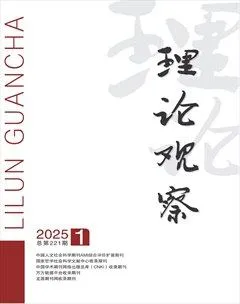馬克思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視閾下“文化工業(yè)”的概念辨析
摘要:將《啟蒙辯證法》中的“文化工業(yè)”視為“大眾文化”“通俗文化”,或將其定性為對某種特定文化現(xiàn)象的批判是對“文化工業(yè)”理論的誤解。實際上,阿多諾早就在《文化工業(yè)再思考》中對“文化工業(yè)”詞源上的模糊及爭議性作出闡述。霍克海默也曾在《論真理的問題》中提出馬克思主義與形而上學觀念論之所以不同的根本基礎——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本文認為,要回歸“文化工業(yè)”的真正內涵,必須結合馬克思的《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與《資本論》的意識形態(tài)批判和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理論。“文化工業(yè)”作為歷史范疇,是一種非文化且“另有所圖”的事物,不僅是以文化形式出現(xiàn)的“特殊商品”,更產生著“文化拜物教”一般的負面影響。
關鍵詞:文化工業(yè);馬克思;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啟蒙辯證法;阿多諾
中圖分類號:B0-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2234(2025)01—0055—06
通常認為,對大眾文化的批判是貫穿于法蘭克福學派發(fā)展歷程始終的重要議題之一。由此,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阿多諾在其與霍克海默合著的《啟蒙辯證法》中的“文化工業(yè)”批判理論也自然被視為是對“大眾文化”的批判。許多學者將“文化工業(yè)”等同于對大眾文化現(xiàn)象和價值的討論,而與其他思想家進行比較研究,比如同屬于法蘭克福學派的本雅明,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葛蘭西,甚至是早期文化研究思潮中的伯明翰學派的一些代表人物,例如威廉斯、湯普森、霍爾等。實際上,這種比較無益于我們理解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文化理論,這使得“文化工業(yè)”失去了其哲學理論基礎和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的基礎。究其根源,這源自我們對“文化工業(yè)”概念的誤解。一方面,“文化工業(yè)”的真正內涵不在于對大眾文化的現(xiàn)象批判;另一方面,“文化工業(yè)”的探討域與大眾文化批判和一般文化研究是截然不同的。若將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文化工業(yè)”作為大眾文化批判的一般性理論進行解讀,就會產生偏離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的問題,從而將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流俗為對一般文化現(xiàn)象的批判和文化方面的敵意與傲慢,甚至造成其理論合法性的問題(例如英國馬克思主義在文化研究中所產生的“基礎-上層建筑”矛盾問題)。
要理解阿多諾與霍克海默的“文化工業(yè)”,必須摒棄“文化工業(yè)”等同于“大眾文化批判”的傳統(tǒng)認知,并重新審視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政治經(jīng)濟學基礎。這一觀點得到了國內眾多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學者(例如,南京大學的張一兵、李乾坤;復旦大學的王鳳才等)所支持。對于西方馬克思主義,很多人一貫具有“從經(jīng)濟學和政治學轉回哲學”、放棄所謂“成熟馬克思所關切的問題”的誤解。在這種解讀下,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往往失去結合馬克思這一理論淵源的合法性,從而造成“兩個馬克思”的認識斷裂。事實上,馬克思的《資本論》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理論淵源之一。同時也有學者指出,對于漢語學術界來講,法蘭克福學派與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之間的關系直到現(xiàn)在依然是一片尚待深入的研究領域。于是,目前對“文化工業(yè)”的大多研究仍忽視著法蘭克福學派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這一重要基礎,將“文化工業(yè)”理論簡單處理為對大眾文化的“現(xiàn)象批判”。為糾察這一誤解的根源,首先應當回到阿多諾和霍克海默本人的所公開發(fā)表的文本,結合《文化工業(yè)再思考》和《論真理問題》這兩篇文章,再思考“文化工業(yè)”的真正內蘊。
一、“文化工業(yè)”概念的深層內涵辨析
(一)詞源模糊性及學界的誤用
首先,阿多諾的文章《文化工業(yè)再思考》(1967)曾明確辨析“文化工業(yè)”和“大眾文化”的區(qū)別,這有助于我們重新認識“文化工業(yè)”理論。阿多諾曾經(jīng)在《文化工業(yè)再思考》中作出以下說明:“文化工業(yè)(cultureindustry)這個術語可能是在《啟蒙辯證法》這本書中首先使用的。霍克海默和我于1947年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出版了該書。在我們的草稿中,使用的是大眾文化(massculture)。大眾文化的倡導者認為,它是這樣一種文化,仿佛同時從大眾本身產生出來似的,是流行藝術(popularart)的當代形式。我們?yōu)榱藦囊婚_始就避免與此一致的解釋,就采用文化工業(yè)代替了它。我們必須最大限度地把它與文化工業(yè)區(qū)別開來。”[1]翻閱這篇文章的原文可以得到,阿多諾在此處嚴格地區(qū)分了“文化工業(yè)”“大眾文化”與“流行藝術”的區(qū)別。在該文章的原文中,這幾個概念所對應的德文單詞也有所不同,分別是Kulturindustrie、Massenkutur和Volkskunst.
由此可知,對于他和霍克海默而言,“文化工業(yè)”(cultureindustry)并不等于“大眾文化”(massculture),也不等同于流行藝術(popularart)的當代形式。他們正因擔心出現(xiàn)這種誤解,才在《文化工業(yè):作為群眾欺騙的啟蒙》中使用了“文化工業(yè)”(cultureindustry)這個概念,而非草稿中原定的“大眾文化”(massculture)。這便表明了“文化工業(yè)”這個概念在詞源上的模糊性和爭議性。這篇文章的問世比《啟蒙辯證法》遲了二十余年,因此并沒有引起學界的廣泛重視。在這篇文章出版后的很長時間內,大眾對“文化工業(yè)”理論的解讀仍僅基于《啟蒙辯證法》的參考,而較為廣泛地對“文化工業(yè)”產生著詞源上的誤解。人們通常語境下的“大眾文化”是從人民群眾中誕生的,是由廣大人民群眾天然的文化需求和文化從業(yè)者的創(chuàng)造性共同作用下能動地被創(chuàng)作出來的,是“流行藝術”的當代形式——“文化工業(yè)”則不然。處于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大眾文化”實質上是一種披著文化形式的工業(yè)產品,是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的商品,亦即“文化工業(yè)”。阿多諾在《文化工業(yè)再思考》中明確闡釋了他對這種誤解的擔憂,并且因此解釋了之所以在《啟蒙辯證法》的草稿中使用“大眾文化”,而在最終出版的《啟蒙辯證法》中使用“文化工業(yè)”的原因。阿多諾指出,“文化工業(yè)”的全部實踐就在于把赤裸的贏利動機投放到各種文化形式上。這里,明顯可以得到,“文化工業(yè)”的實踐的全部目的在于贏取利潤,這一點與馬克思的商品交換理論不謀而合。阿多諾指認,“文化工業(yè)”所投射的客體——各種各樣的“文化形式”——實則也并非是文化的產物。這種“文化形式”只是承載著“文化工業(yè)”盈利目的的一種無靈魂的軀殼,是一種特殊的商品,而非真正的文化產品。
(二)“文化工業(yè)”的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理論基礎
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曾多次提到其關于文化領域的認識具備著堅實的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的理論基礎。這也提示著我們,應當回到馬克思的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這一理論淵源處,對“文化工業(yè)”的闡釋路徑再作尋覓。
霍克海默1935年在發(fā)表于《社會研究雜志》第4卷第1期的《論真理問題》中通過對比康德、黑格爾等人的哲學體系,指出其理論的缺陷與進步,最終對辯證法及馬克思哲學體系作出評價。霍克海默認為,黑格爾的辯證法是克服西方近代哲學之對立的最宏偉的嘗試,但黑格爾式的辯證法卻是不為唯物主義者所認同的,因為當黑格爾把一種整體性賦予某個歷史階段,即他自己的哲學,并把它視為絕對真理時,便又陷入了新的教條主義。這也體現(xiàn)出傳統(tǒng)形而上學“天真的”特點。形而上學總是基于各種觀念產生其“幻想的基礎”,然而現(xiàn)實社會中的“內在機制”產生的不確定性和持續(xù)的壓力卻從未被揭示出來。由此,霍克海默通過《論真理問題》將理論的目光從觀念世界轉移至現(xiàn)實社會。從而以大段篇幅論證并認定了馬克思的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于現(xiàn)實社會的重要性,即“社會中的某些現(xiàn)實趨勢被理論化后的“相互關系”體現(xiàn)為——大資本的積累與整個社會階層的比例失調、失業(yè)率的上升、社會勞動在各種商品中的分配與大眾需求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等等。霍克海默指出,以上的這些過程早就被馬克思所論證且重視了,并且這些政治經(jīng)濟學現(xiàn)象在理論探索中是十分必要的。但在資本主義歷史發(fā)展的進程中,似乎只有少數(shù)幾個先進國家正在對此進行研究,而且還處于萌芽狀態(tài),(在當時)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所崇尚的前景似乎還很美好。然而,霍克海默指出,歷史現(xiàn)實在發(fā)展中不僅首先預言且認定了這些批判性的社會經(jīng)濟關系,而且還證明了它們的必要性。霍克海默同時指出,商品作為資本主義社會中最一般的初始存在,馬克思從其中發(fā)展出了價值概念,從而產生了與這一切密切聯(lián)系的貨幣、資本等范疇。而上述的一切經(jīng)濟“相互關系”則都由價值這一概念所設定,并以現(xiàn)實邏輯可以層層遞進、推導出來。霍克海默認為,這種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理論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的。一方面,它具有現(xiàn)實的實踐性。因為現(xiàn)實的人們在馬克思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這一理論指導下所做的努力,可以防止社會重新陷入“野蠻狀態(tài)”。馬克思的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理論是經(jīng)過歷史進程所證實的理論,這意味著它不僅是一種純粹的、形而上學永恒式的理論,而代表著一種具有解放意義的實踐時刻。正如霍克海默所說一般,這是與受到威脅的人民的全部急迫感聯(lián)系在一起的現(xiàn)實的理論。另一方面,它具有理論的基礎性。因為對所有經(jīng)濟、政治和文化領域的理論認識都可以通過商品的一般概念這一原初的認識而被中介得到。[2]
在這里,應當注意到:霍克海默認為,我們關于“文化領域”的認識,是通過“價值”這一原初的認識,而被中介得到的。眾所周知,馬克思從“商品”這一普遍性概念推導出“價值”。霍克海默認為,馬克思政治經(jīng)濟學理論框架之后的大多經(jīng)濟范疇都由“價值”這一概念所設定,正如列寧所說一般,商品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細胞”,包含著一切尚未展開的主要矛盾[3]。商品作為“第一個最一般的概念”,在馬克思而后在《資本論》的論述中逐漸豐富其內蘊,從抽象上升為具體,正如霍克海默所指認——“其抽象性隨著理論的發(fā)展而被克服”。商品這一概念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霍克海默認為,對經(jīng)濟、政治、文化領域的所有認識都是由商品交換這一“原初的認識”而被中介后所得到的。由此可以察覺,霍克海默對作為一個整體領域的“文化”的認識,是與馬克思的政治經(jīng)濟學的基本原理相結合的。“文化工業(yè)”作為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論述文化領域過程中所提出的重要理論,我們通過霍克海默參照馬克思的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理論所勾勒出的批判理論范式的研究方法可以得到,若要真正理解“文化工業(yè)”的深層內涵,便應將“文化工業(yè)”批判理論與馬克思的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理論相結合。絕不能將“文化工業(yè)”的批判對象簡單歸為由大眾文化流行而產生的社會文化現(xiàn)象。阿多諾和霍克海默提出“文化工業(yè)”批判理論,旨在通過“文化工業(yè)”對社會作出整體性的批判反思,而非對某種表層的文化現(xiàn)象作淺顯否定。實際上,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是借用“文化工業(yè)”這一概念批判偽裝成文化,實則并非文化,且另有“所圖”的事物。
二、“文化工業(yè)”實質:非文化且“另有所圖”的事物
在傳統(tǒng)大眾文化批判視域中,通常將“文化工業(yè)”視為一種流行文化于大眾而言的負面形式,或是指認文化作品成為“工業(yè)生產”中的一環(huán)而產生的種種后果,卻很少有將“文化工業(yè)”理論和馬克思的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相結合而進行的探討。“文化工業(yè)”實質是非文化且“另有所圖”的事物。首先,“文化工業(yè)”實際上是以文化形式出現(xiàn)的、以逐利為主要目的的商品。它在誕生之初便與其他的文化產品有所不同,因為文化產品通常包含著審美的意蘊,是為滿足人民的文化需要的產物。而“文化產業(yè)”自誕生之初便帶有逐利這一目的,其全部的實踐意義也在于此。其次,在“文化工業(yè)”誕生后,便會演變?yōu)橐环N“文化拜物教”,也就是在逐利這一經(jīng)濟功能的基礎上,又帶有了“意識形態(tài)”熏陶這一政治功能。
(一)作為“非文化事物”的“文化工業(yè)”
“文化工業(yè)”實則是將“贏利動機投放到各種文化形式上”的非文化事物。這是對馬克思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中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之分別的承接。
阿多諾曾在《文化工業(yè)再思考》中強調文化變?yōu)樯唐泛蟮闹鹄浴T谖幕I(yè)的各個分支中,“特意為大眾的消費而制作并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消費的性質的那些產品,或多或少是有計劃地炮制的。”也就是說,文化工業(yè)之所指不再像是從前古典藝術家們所投入激情與創(chuàng)造的文化產物,而是為了在大眾群體中獲取利潤而有計劃地“炮制”出來的。亦即,當“文化”和“藝術”成為資本的附庸,成為逐利的產品,在這種意義上,“文化”和“藝術”便變?yōu)榱朔俏幕⒎撬囆g的東西,即“文化工業(yè)”。因此,“文化工業(yè)”并不能稱作是大眾文化,而只能是一種“工業(yè)商品”。
針對勞動的不同性質,即生產性和非生產的區(qū)別,《資本論》中明確指出:“同一種勞動可以是生產勞動,也可以是非生產勞動。”[4]生產勞動所生產的是用于資本增殖的商品,而非生產勞動創(chuàng)造的則是使用價值。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是一個受社會關系所限的歷史范疇,二者的界限是相對的。馬克思指出:對于消費者而言,飯店中的侍者和廚師的勞動行為屬于非生產勞動,而對于飯店老板來說則是生產勞動,“因為他們的勞動轉化為飯店老板的資本。”但如若老板將這些人視為家仆,那么他們便是非生產勞動者,因為家仆的服務并未創(chuàng)造資本,雇主此刻也僅是將自己的收入花費在這些服務上。[5]生產勞動者為他們的雇主(即他們勞動能力的買者)生產商品的過程實質上就是參與資本增殖的過程。但非生產勞動者為他們勞動能力的買者生產的卻只是使用價值。在這里,馬克思著重強調,這種使用價值是“想象的或現(xiàn)實的使用價值,而絕不是商品”。[6]而當這種使用價值進入文化領域之時,便體現(xiàn)為阿多諾所強調的出于激情所能動創(chuàng)造出的文化產物,比如貝多芬的音樂作品。但“文化工業(yè)”卻是在經(jīng)濟上參與資本增殖過程并純粹屬于商業(yè)范疇的“工業(yè)商品”。由此,馬克思明確地總結:服務有一定的使用價值(想象的或現(xiàn)實的)和一定的交換價值。當文化領域的產品不再服務于想象的使用價值,而是服從于交換價值時,便普遍地變?yōu)榱税⒍嘀Z與霍克海默所言的“文化工業(yè)”。
同時,《剩余價值理論》第四章關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理論以英國作家約翰·彌爾頓(JohnMilton)創(chuàng)作《失樂園》和萊比錫的“一位無產階級作家”為例生動說明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區(qū)別。
文本明確提出,約翰·彌爾頓創(chuàng)作《失樂園》后得到5鎊,他是非生產勞動者。即“密爾頓出于同春蠶吐絲一樣的必要而創(chuàng)作《失樂園》。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動表現(xiàn)。后來,他把作品賣了5鎊。”[7]彌爾頓作為十七世紀聲名鼎赫的文化從業(yè)者,未曾經(jīng)歷工業(yè)革命,也未曾置身于階級社會,他的作品屬于英國的前資本主義社會。因此,《失樂園》是純粹出于審美和文化需要而誕生的。《失樂園》不是為了滿足大眾的消費和文化需要而被“炮制”出來的,便不屬于“文化工業(yè)”,而是他天性的“能動表現(xiàn)”。在這里,《資本論》中所提到的“春蠶吐絲一樣的必要、天性的能動表現(xiàn)”和阿多諾所強調的古典音樂創(chuàng)作家的“激情、創(chuàng)作”實則是一回事,都是一種在文化領域的“非生產勞動”。阿多諾認為,只有這種“非生產勞動”才能被稱之為真正的文化、藝術,而“文化工業(yè)”則不然。
與之相反,為書商提供工廠式勞動的作家,則是生產勞動者。“在書商指示下編寫書籍的萊比錫的一位無產者作家卻是生產勞動者,因為他的產品從一開始就從屬于資本,只是為了增加資本的價值才完成的。”[7]處于十九至二十世紀撰寫剩余價值理論批判的作家屬于無產階級,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當階級范疇出現(xiàn)的一刻起,就意味著它生存并服從于資本主義社會整體。隨著階級差距的分化,即便一位作為無產者的作家所生產的文化產品旨在批判資本,也只能歸屬于“勞動產品”。因為這種文化產品經(jīng)過發(fā)行商與書商的出版和銷售,便會使作家成為提供工廠式勞動的“文化商品”生產者。
關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分別,《資本論》中舉出了許多生動的例證,上述關于作家的論述是在文化生產領域最直白的一個例證。由《資本論》上述對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區(qū)別的例證和阿多諾的《文化工業(yè)再思考》可以理解,“文化工業(yè)”實則是處于文化領域的勞動變?yōu)榱艘环N“生產勞動”,而非“非生產勞動”。文化領域的創(chuàng)作普遍地變?yōu)橐灾鹄麨槟康牡纳a,“文化工業(yè)”便誕生了。
(二)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文化工業(yè)”
當“文化工業(yè)”被造就后,則不再滿足于逐利性,而是變?yōu)橐环N意識形態(tài)、公共關系,這是馬克思從《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對顛倒了的意識(即意識形態(tài)),到《資本論》中拜物教思想的接續(xù)。在霍克海默與阿多諾所處的年代,“文化工業(yè)”實則產生著“文化拜物教”一般的負面影響。“文化工業(yè)”不僅擁有商品的逐利性,同時也具備著服務、鞏固極權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作用。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所處的歷史時期,在致富欲的推動與極權主義的操縱下,人們越發(fā)地創(chuàng)造出“文化工業(yè)”、沉迷于“文化工業(yè)”,就越成為“文化工業(yè)”的手段,最終使主體意識屈尊于意識形態(tài)的強權之下。
《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下文簡稱《形態(tài)》)在批判傳統(tǒng)的觀念論時曾指出意識形態(tài)的顛倒。現(xiàn)實的人的生存與實踐困境導致了顛倒的意識形態(tài)的產生。這種意識形態(tài)不僅是社會局限性的產物,更是資本主義整體下無產階級生存境遇的真實反映。馬克思在《形態(tài)》的手稿中說明,人有關于自然界、他人、自身的觀念都是由現(xiàn)實生活得來的,“如果這些個人的現(xiàn)實關系的有意識的表現(xiàn)是虛幻的,如果他們在自己的觀念中把自己的現(xiàn)實顛倒過來,那么這又是由他們狹隘的物質活動方式以及由此而來的他們狹隘的社會關系造成的。”[8]也就是說,意識形態(tài)的“顛倒”根源于現(xiàn)實的“顛倒”。但在《形態(tài)》這一階段,馬克思還未能完全結合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理論深入到資本增殖過程的內核。馬克思也如此作出說明,如果要徹底澄明曾在德國占統(tǒng)治地位的歷史方法,以及說明它為什么主要在德國占統(tǒng)治地位,“就必須從它與一切意識形態(tài)家的幻想,例如,與法學家、政治家(包括實際的國務活動家)的幻想的聯(lián)系出發(fā)……而從他們的實際生活狀況、他們的職業(yè)和分工出發(fā)。”[9]直至《資本論》,馬克思通過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具體生產關系,達到了對古典政治經(jīng)濟學準確而全面的批判認知,才在真正意義上從他們的“實際生活狀況、職業(yè)和分工”出發(fā),從而完成了這一“說明”。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提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拜物教”概念。“拜物教”批判理論是馬克思在《形態(tài)》中“顛倒了的意識形態(tài)”理論的接續(xù)。拜物教原指在原始社會,人們限制于自身的實踐水平,缺乏科學知識,無法理解自然現(xiàn)象,從而將自然物神化,把它們當作神來崇拜的現(xiàn)象。馬克思認為,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中,同樣存在類似的“拜物教”觀念,包括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資本拜物教等。一方面,拜物教體現(xiàn)為主客體的顛倒,主體本來作為產品的創(chuàng)造者應當主宰并使用自己的創(chuàng)造物,但在以逐利作為目的的行為驅使下,將能主宰其命運的客體神化,而產生崇拜般的迷信。在資本主義社會主要體現(xiàn)為對消費的無限沉迷、對物欲的無限追求及不擇手段的逐利行為。另一方面,在拜物教根深蒂固的影響下,在拜物教的主客體關系中,客體不再局限于“物”本身,而演變?yōu)槲锘说纳鐣P系。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商品形式的奧秘就在于把“生產者同總勞動的社會關系反映成存在于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10]
“文化工業(yè)”實則產生著“文化拜物教”一般的負面影響。首先,在“文化工業(yè)”面前,正如阿多諾所論述的一般,大眾絕不是首要的,而是次要的。亦即,大眾是被算計的對象,是機器的附屬物。顧客并非上帝,不是文化產品的主體,而是客體。這就導致了主客體的顛倒,人作為文化產品的創(chuàng)造者和享有者本應是審美的主體,如今在“文化工業(yè)”的逐利性面前卻變?yōu)榱吮凰阌嫷目腕w。這種主客顛倒的狀況使得顧客僅僅是“文化工業(yè)”的消費者,而非“文化產品”創(chuàng)造者和享有者。顧客在“文化工業(yè)”的生產和銷售過程中作為被資本剝削的一分子,心甘情愿為“文化工業(yè)”商品買單,從而參與到資本社會的商品交換過程當中。其次,人民群眾在“文化工業(yè)”中麻痹自我,以獲得由于階級矛盾而導致的悲慘現(xiàn)實中的短暫寬慰。形形色色的文化產品在表面上擁有不同的形式與風格,“文化工業(yè)”則戳破了這些風格背后的秘密——即對社會等級秩序的遵從。[11]在資本主義社會,“文化工業(yè)”縱橫,在這種狀況下,人們越是探討所謂的“文化”,就越是被已經(jīng)代入公共關系領域的“文化工業(yè)”所索引和分類。因為現(xiàn)實的沖突導致人的不平等狀況,文化工業(yè)作為資本的產物實則加強了階級的固化,使原本平等的個體被不斷地分類、標簽化。霍克海默和阿多諾以電影為例說明了這一點,電影生產商為觀眾炮制出各種文化垃圾,這種文化工業(yè)使人們感到欣慰,“使所有人都認為自己依然可能會有堅韌的和真實的命運”。與此同時,這種命運一定是一種“拒不妥協(xié)的命運”[12]而在資本現(xiàn)實中,無產階級的命運很多時候卻不為自身所掌控,而表現(xiàn)為資本的支配力量。也就是說,在文化產品中所描述的在敵人和苦難面前,人們所表現(xiàn)出的“勇敢、自由的情感”,其根本在于現(xiàn)實的個人與資本社會根本對立的這一社會實體。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所處的二戰(zhàn)時期,以法西斯主義為代表的權威力量吞噬了人們的反抗能力,這正是通過文化工業(yè)“從孤立無援的人們身上獲得整合的奇跡”而被表現(xiàn)的。社會根本矛盾被文化工業(yè)所表現(xiàn)出的被迫害者的所謂的勇敢、自由等情感悄然無息地掩蓋、包裹住了,這使極權主義的殘酷行徑變得“溫文爾雅”。[13]于是,“文化工業(yè)”也變?yōu)榱艘环N更為廣泛的意識形態(tài)根深蒂固于社會結構中,如同馬克思從《形態(tài)》到《資本論》所論述的“顛倒了的意識形態(tài)”和“被物化了的社會關系”一般,具有較強的穩(wěn)定性。
文化工業(yè)誕生之初以逐利的姿態(tài),成為“徹頭徹尾的商品”。隨著商品逐利性質的不斷發(fā)展,便不再僅僅滿足于致富欲,而逐漸演變?yōu)橐环N公共關系、意識形態(tài)。正如阿多諾所說,文化工業(yè)曾經(jīng)是從直接追求利潤發(fā)展起來的。而如今,“利潤帶來的這些利益已經(jīng)在它的意識形態(tài)里對象化了,甚至已經(jīng)使它們自身獨立于售賣文化商品的沖動之外。”也就是說,“文化工業(yè)”此刻便轉化成為維持資本運轉的意識形態(tài),對社會產生著“文化拜物教”一般的負面影響,而不涉及特定的商社或可銷售的貨物。
三、反思與啟示:“文化工業(yè)”與“當代文化”
在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發(fā)展歷程中,霍克海默與阿多諾提出的“文化工業(yè)”理論引領了一時的學術熱潮。這一理論,根植于二戰(zhàn)烽火連天歷史背景下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土壤,不僅是馬克思主義文化批判理論的重要觀點,更是一個深刻反映時代特征的歷史性范疇。
文化工業(yè)理論深刻揭示了受資本增殖驅動的文化所遭受的根本性負面影響,同時,它也潛藏著對極權主義政權和當時美國大眾流行文化的深刻批判。文化工業(yè)在資本的操控下,逐漸喪失了其獨立性和多樣性,成為了一種標準化、同質化的商品生產模式。這種文化產品的批量生產,不僅削弱了文化的批判性和創(chuàng)新性,還進一步強化了極權主義政權對民眾思想的控制。同時,美國流行文化作為文化工業(yè)的典型代表,其表面的多元與自由背后,實則隱藏著資本邏輯的深刻影響,成為了一種新的文化霸權。對“文化工業(yè)”進行再辨析,不僅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當代資本主義文化發(fā)展的新形態(tài),更提醒我們要時刻保持對文化霸權和資本邏輯的清醒認識,以批判性的眼光審視我們所處的文化環(huán)境,推動文化的多樣性和獨立性的發(fā)展。
簡單地將“文化工業(yè)”與某些負面文化現(xiàn)象(如低俗文化、落后文化等)畫等號這一誤解遮蔽了“文化工業(yè)”理論的政治經(jīng)濟學內涵。事實上,“文化工業(yè)”與大眾文化之間存在著本質的區(qū)別,它并非大眾文化的同義詞,而是對特定歷史時期文化生產模式的一種深刻剖析與批判。作為學術范疇的“文化工業(yè)”,不僅是對資本主義文化生產機制的一種深刻揭示,更是對文化發(fā)展與社會變遷之間復雜關系的深入探索。但同時,無可否認的是,阿多諾與霍克海默對“文化工業(yè)”的批判也暗含著其對文化審美精英主義式的傲慢和否定性批判的態(tài)度。因此,在理解“文化工業(yè)”時,我們應超越表面的標簽與誤解,深入挖掘其背后的理論邏輯與歷史脈絡,以更加全面、準確地把握其在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對當代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啟示意義。
在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引領,推動“兩個結合”深入發(fā)展的新時代,從理論層面剖析,深入挖掘文化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相契合的深刻哲學內涵,并提升文化哲學在學術體系中的重視程度,具有極為顯著的現(xiàn)實意義與理論價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在保持文化傳統(tǒng)的基礎上創(chuàng)造出適應現(xiàn)代化建設的新文化,而且我國文化是一個開放的系統(tǒng),只有具備開放性才能在此基礎之上交流、融合,經(jīng)過涵化進行文化創(chuàng)新。我國文化也是創(chuàng)新的文化,只有不斷進行理論創(chuàng)新才能適應現(xiàn)代化建設的需要,社會進步才能具有持續(xù)的力量。[14]在現(xiàn)實實踐中,面對廣大民眾廣泛接受并喜愛的豐富文化現(xiàn)象,我們應秉持繼承與發(fā)展的積極態(tài)度,而非簡單地采取否定性的批判視角。結合馬克思主義對“文化工業(yè)”理論進行再思考能夠給予我們堅持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啟示,具體而言,這要求我們明確區(qū)分“文化工業(yè)”與“當代文化”之間的本質區(qū)別與界限,并針對兩者采取不同的理論立場與實踐策略,以確保文化發(fā)展的正確方向與可持續(xù)性。
〔參考文獻〕
[1]TheodorW.Adorno.CultureIndustryRecons-idered[M].DukeUniversityPress,1975:12.
[2]MaxHorkheimer.ZumProblemderWahrheit[M].ZeitschriftfürSozialforschung,JahrgangIV.Heft3,1935.
[3]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0.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06.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0.
[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1.
[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06.
[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2009:524.
[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4.
[1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9.
[11]霍克海默,阿道爾諾.啟蒙辯證法[M].渠敬東、曹衛(wèi)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18.
[12]霍克海默、阿道爾諾,啟蒙辯證法[M].渠敬東,曹衛(wèi)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37.
[13]霍克海默、阿道爾諾,啟蒙辯證法[M].渠敬東,曹衛(wèi)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39.
[14]丁立群,陸鵬飛.全球化視域下我國文化自信的生成邏輯和當代價值[J].馬克思主義哲學,2021(4):81.
〔責任編輯:侯慶海,周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