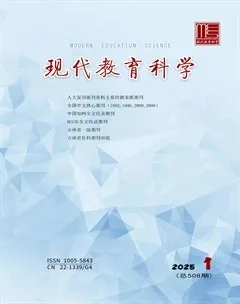我國“在地國際化”研究的興起、本土特征及審思



[摘" 要]我國的“在地國際化”研究興起于“國際化”與“本土化”之爭中,研究歷程可分為自發(fā)探索期、概念自覺與緩慢起步期、迅猛增長與深化拓展期3個階段。具體研究內(nèi)容呈現(xiàn)出鮮明的本土特征,包括術(shù)語與概念內(nèi)涵的本土化、價值認(rèn)知的本土關(guān)懷、實踐路徑探索的本土特色等。其內(nèi)涵界定的“目標(biāo)取向”拓展了概念的認(rèn)知維度,有望為價值和實踐路徑的本土探索貢獻(xiàn)跨文化案例。但總體而言,我國的“在地國際化”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本土實踐機(jī)制探索尚待深入,實證研究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理論的驗證、拓展及深化。在“在地國際化”實踐成為大勢所趨的背景下,有必要啟動實證研究,檢驗既有理論并生成本土實踐工具;直面現(xiàn)實困境,加強(qiáng)基于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的“在地國際化”路徑創(chuàng)新研究;將研究對象放在與跨境流動的關(guān)系中深入探索,加強(qiáng)二者協(xié)同作用機(jī)制研究。
[關(guān)鍵詞]高等教育國際化;在地國際化;本土國際化;跨境流動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843(2025)01-0001-07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5.01.001
[收稿日期]2024-10-08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2021年度教育學(xué)一般項目“后疫情時代以‘在地國際化’加速我國國際化人才培養(yǎng)研究”(項目編號:BIA210182)。
[作者簡介]房欲飛(1977-),女,山東聊城人,博士,上海市教育科學(xué)研究院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國際化。錢夢婷(1996-),女,浙江紹興人,華東師范大學(xué)教育學(xué)部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比較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國際化是與現(xiàn)代大學(xué)相伴而生的現(xiàn)象,并日益被各國視為推進(jìn)教育現(xiàn)代化的重要舉措[1]。既往的高等教育國際化通常被視為人員的跨境流動,但隨著全球化對畢業(yè)生國際化素養(yǎng)要求的日益提高,傳統(tǒng)的“境外國際化”范式逐漸暴露出受益面過小的局限性特征。因此,主張為所有在校生提供國際化教育的“在地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由于我國同時存在“本土國際化”這一表述,下文根據(jù)需要有時用“IaH”統(tǒng)稱二者)理念應(yīng)運(yùn)而生。
“在地國際化”在空間維度上是與“境外國際化”相對的概念,是指發(fā)生在本土校園的國際化活動,通俗而言即高校充分利用校內(nèi)外可及的國際化資源來提升教育教學(xué)國際化水平的過程。自1999年尼爾森(Nilsson)正式提出這一概念以來,“在地國際化”正式成為高等教育國際化研究的新領(lǐng)域,方興未艾。最初以尼爾森、瓦赫克(Wchter)、貝倫(Beelen)、提肯斯(Teekens)、奧騰(Otten)等歐洲研究者對其價值、概念內(nèi)涵、歷史演進(jìn)、歐洲語境、實踐要素等方面的探討為主,后期隨著實踐區(qū)域的不斷拓展和世界各地學(xué)者的逐步加入,對實踐的具體探討開始帶上不同文化語境的痕跡[2]。我國學(xué)者引入“在地國際化”的時間相對較晚,但與國外學(xué)者研究對區(qū)域文化背景的關(guān)注相適應(yīng),在研究推進(jìn)的過程中,無論是術(shù)語的使用還是具體的研究內(nèi)容,都帶有鮮明的本土色彩。因此,對我國研究的背景與現(xiàn)狀進(jìn)行系統(tǒng)梳理,有助于豐富“在地國際化”研究的跨文化案例,并貢獻(xiàn)關(guān)于這一議題的中國智慧。將我國的研究放在更廣闊的國際視野下進(jìn)行審視,也有助于在更宏大的場域下審視既有研究的得失,展望未來的研究路向。
一、歷史背景:“國際化”與“本土化”之爭
我國學(xué)界在使用“在地國際化”的概念以前,曾有關(guān)于“本土國際化”的探討,國外的“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也曾一度被我國學(xué)者譯為“本土國際化”,至今仍存在兩個術(shù)語同時使用的局面。這種情況與新世紀(jì)以來我國學(xué)界高等教育“國際化”與“本土化”之爭有一定關(guān)系。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進(jìn)程展開以來,由于作為發(fā)展中國家的相對弱勢地位以及國際學(xué)生“從南半球向北半球、從東半球向西半球”的流動趨勢,曾一度遭遇“西化”“美國化”的意識形態(tài)風(fēng)險和人才流失的困境。與此同時,隨著全球化進(jìn)程中尊重多元文化意識的覺醒,“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全球化的成功就在于它植根于本土化”逐漸成為學(xué)界的共識[3]。在這種背景下,“本土化”漸漸成為耳熟能詳?shù)脑捳Z,如何在全球化和國際化大潮中扎實本土根基成為高等教育不得不面對的課題。正如我國學(xué)者操太圣所說,“在國際化的呼聲甚囂塵上之時,關(guān)于高等教育本土化的議論也不斷冒升,有堅決捍衛(wèi)個體和民族認(rèn)同者,有強(qiáng)調(diào)吸納國外高等教育的有用元素為我所用者,但大家所共同信奉的則是盡量謀求兩者的平衡”[4]。但由于我國在國際知識生產(chǎn)體系中的邊緣地位以及高等教育體系的相對弱勢地位,實現(xiàn)這種平衡面臨著較大的挑戰(zhàn)。針對這種現(xiàn)狀,操太圣于2005年提出了“本土國際化”的概念,主張通過中外合作辦學(xué),讓更多學(xué)生在中國本土完成留學(xué)生涯,從而實現(xiàn)國際化人才培養(yǎng)的本土化。從此“本土國際化”開始成為高等教育國際化領(lǐng)域中不可忽視的議題。2008年將“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引介到中國的丁笑炯也將其譯為“本土國際化”[5]。比之“本土國際化”,“在地國際化”的提法在我國出現(xiàn)得相對較晚,最早可見于2011年一篇關(guān)于中國人民大學(xué)“在地國際化”的報道。文中提到,“在地國際化”旨在“讓本校學(xué)生不用跨出國門,就可以接觸國際一流教師,聆聽國際一流課程,與不同國家和文化的學(xué)生自由交流,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收益”[6]。由此可見,“本土國際化”與“在地國際化”兩個術(shù)語在我國出現(xiàn)之初,有著不同的動因和意蘊(yùn):前者是為了應(yīng)對中國在高等教育國際化中的不利地位,后者是為了基于本土校園營造人才培養(yǎng)的國際化氛圍。前者沿襲了“國際化”與“本土化”之爭的民族利益表達(dá),關(guān)注的層面比較宏觀,有著更多的政治意蘊(yùn);后者則更關(guān)注校園層面的國際化教育機(jī)會,關(guān)注的層面比較微觀,旨在以較低的成本擴(kuò)大國際化教育的受益面,可以說有著更多的經(jīng)濟(jì)、倫理意蘊(yùn)。不過,雖然二者提出的初衷有別,關(guān)注的側(cè)重點(diǎn)也有所不同,但從后續(xù)研究者對兩個術(shù)語的定義來看,目前二者的內(nèi)涵已無實質(zhì)性的差異[7]。從學(xué)界對兩個術(shù)語的使用頻率來看,最初“本土國際化”是相對主流的表達(dá),但2016年蔣冰清首次將“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譯為“在地國際化”后,“在地國際化”的使用頻率增加趨勢明顯,已成為當(dāng)前主流的表達(dá)方式。對兩個術(shù)語使用情況的統(tǒng)計(為了呈現(xiàn)完整的年度發(fā)文趨勢,統(tǒng)計截至2023年底)詳見圖1,這也是本文用“在地國際化”統(tǒng)稱我國IaH研究成果的原因。
圖1" 我國學(xué)界對“本土國際化”與“在地國際化”兩個術(shù)語的使用情況及年度發(fā)文量一覽
然而,不管學(xué)者們對“本土國際化”與“在地國際化”的使用如何取舍、有何側(cè)重,有一個趨勢卻是不容回避的,那就是如何統(tǒng)合本土性與國際性之間的關(guān)系、如何有效擴(kuò)大國際化教育的受益面,使其成為當(dāng)前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重點(diǎn),或許這也是近年來我國的相關(guān)研究迅速增加的動因之一。
二、我國“在地國際化”研究的發(fā)展脈絡(luò)
回顧我國“在地國際化”的研究歷史,根據(jù)其研究內(nèi)容特點(diǎn)和文獻(xiàn)增長情況可以將其劃分為自發(fā)探索期、概念自覺與緩慢發(fā)展期、迅猛增長與深化拓展期這3個階段,不同的發(fā)展階段具有不同的特征。
(一)自發(fā)探索期(20世紀(jì)50年代—2004年)
“在地國際化”雖然是一個新概念,卻并非全新的事物。根據(jù)國外學(xué)者的研究,“在地國際化”的實踐要素主要包括課程國際化、師資國際化、政策與制度的國際化、相關(guān)機(jī)構(gòu)設(shè)置和基礎(chǔ)設(shè)施、外語學(xué)習(xí)、信息通信技術(shù)(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 的運(yùn)用等[8]。以此觀之,我國學(xué)界對其部分要素的探索由來已久,尤其是對外語學(xué)習(xí)、師資國際化、課程國際化的研究,更是分別在1957[9]、1995[10]、1996[11]年就出現(xiàn)了相關(guān)文獻(xiàn)。只是在“在地國際化”的概念出現(xiàn)之前,這類探索都是自發(fā)進(jìn)行的。事實上,即使是“在地國際化”概念出現(xiàn)以后,由于其作為“初生之物”尚未廣為人知,相關(guān)議題的研究也未形成這方面的理論自覺,很多研究探索依然是在非“在地國際化”的專題框架里進(jìn)行,主要散見于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諸多文獻(xiàn)中。
(二)概念自覺與緩慢發(fā)展期(2005—2019年)
2005年“本土國際化”概念的提出,標(biāo)志著我國學(xué)界對“在地國際化”的研究進(jìn)入了自覺階段。2008年丁笑炯正式將IaH概念引入中國,更是標(biāo)志著我國對這一概念的關(guān)注開始與國際接軌。但此后這一領(lǐng)域的研究進(jìn)展一度非常緩慢,2017年之前只出現(xiàn)了10篇文獻(xiàn),年均不到1篇。2016年蔣冰清首次將IaH譯為“在地國際化”[12]。2017年,張偉與劉寶存發(fā)表了國內(nèi)本領(lǐng)域最高被引文獻(xiàn)《在地國際化:中國高等教育發(fā)展的新走向》[13]。在此之后,發(fā)文量出現(xiàn)了一個小高潮,但2018年又有所回落。此時期出現(xiàn)的27篇文獻(xiàn)中,來自國內(nèi)外的案例和經(jīng)驗研究占了主流,研究主題主要涉及國際化人才培養(yǎng)模式(41%)和課程教學(xué)(30%)。此外就是對“在地國際化”必要性的呼吁。值得一提的是,此時期還出現(xiàn)了一篇實證研究文獻(xiàn),即《基于本土國際化模式培養(yǎng)學(xué)生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實證研究》[14]。從研究內(nèi)容來看,這一階段我國“在地國際化”研究開始關(guān)注國際化人才培養(yǎng)。這一時期張偉和劉寶存對“在地國際化”的定義成為迄今為止我國被引用最多的定義,而他們對“在地國際化”的內(nèi)涵界定,就是以“國際化人才”培養(yǎng)為目標(biāo)導(dǎo)向的(詳見下文對我國“在地國際化”研究本土特征的分析)。
(三)迅猛增長與深化拓展期(2020年至今)
2020年開始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阻斷了人員的跨境流動,對傳統(tǒng)跨境國際化模式替代方案的尋求使得“在地國際化”日益走進(jìn)研究者的視野。與現(xiàn)實需求相適應(yīng),我國的“在地國際化”研究也經(jīng)歷了迅猛的發(fā)展,年度發(fā)文量接近倍速增加,2020—2023年,篇名文獻(xiàn)的發(fā)文量分別為6、13、24、44篇。雖然新冠疫情在2022年就開始逐步消退,但我國學(xué)者對這一議題的關(guān)注并未隨之淡化。究其原因,研究的逐步深入帶來的認(rèn)知深化功不可沒。如果說疫情暴發(fā)之初“在地國際化”更多地被視為傳統(tǒng)國際化模式停擺的替代方案,那么隨著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學(xué)者意識到“在地國際化”并非應(yīng)對疫情的權(quán)宜之計,而是對高等教育國際化本質(zhì)的強(qiáng)調(diào)[15],是對高等教育國際化發(fā)展學(xué)術(shù)與育人屬性的回歸[16],是結(jié)合國際優(yōu)質(zhì)教育資源以提升本國高等教育質(zhì)量的過程[17],是對高等教育國際化內(nèi)涵建設(shè)的承諾[18]。如此,“在地國際化”研究就有了其相對獨(dú)立的價值,進(jìn)而獲得了可持續(xù)研究的意義。同時,后疫情時代大國關(guān)系的博弈以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的技術(shù)封鎖,也使得我國國際化人才的自主培養(yǎng)受到更多關(guān)注,而我國學(xué)界對以國際化人才培養(yǎng)為統(tǒng)領(lǐng)的“在地國際化”價值取向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了其研究的必要性。隨著研究文獻(xiàn)的不斷增加,本領(lǐng)域的研究視角進(jìn)一步分化,比較研究的國別進(jìn)一步豐富,研究前沿也呈現(xiàn)與國際接軌的態(tài)勢。其中,研究視角出現(xiàn)了共生理論視角[19]、基于制度創(chuàng)業(yè)理論的分析[20]、生態(tài)文明背景[21]等,比較研究從上一階段的美國、德國拓展至印度、馬來西亞、歐洲、日本、卡塔爾等。與國外相關(guān)研究近年來對信息與通信技術(shù)(ICT)賦能“在地國際化”發(fā)展的重視相適應(yīng),當(dāng)前我國學(xué)者也開始關(guān)注基于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的“在地國際化”路徑創(chuàng)新[22-24]。可以預(yù)見,隨著“在地國際化”的獨(dú)特價值被更廣泛地推廣,以及后疫情時代對國際化人才自主培養(yǎng)需求的增加,相關(guān)研究還將進(jìn)一步豐富。
三、我國“在地國際化”理論研究的本土特征
綜觀現(xiàn)有文獻(xiàn),可以發(fā)現(xiàn)我國學(xué)界的“在地國際化”研究涵蓋了其內(nèi)涵、價值指向、實踐要素及路徑探索、挑戰(zhàn)與建議等諸多方面,具體論題與國外的研究并無明顯的不同,其研究內(nèi)容卻有著鮮明的本土特點(diǎn)。
(一)概念的“本土化”及新取向
目前國外學(xué)者對于“在地國際化”的概念認(rèn)知尚存分歧,但基本有兩個認(rèn)知取向:一個是活動取向,以尼爾森經(jīng)典定義為代表,即“教育領(lǐng)域除海外流動之外所有與國際化相關(guān)的活動”[25];另一個是課程取向,以貝倫和瓊斯(Jones amp; Elspeth)的定義為代表,即“把國際性與跨文化維度融入面向所有在校生的課程與非正式課程的過程”[26]。我國在引進(jìn)IaH概念后,學(xué)者們對其內(nèi)涵的界定出現(xiàn)了一個不約而同的共性,那就是對“國際化人才培養(yǎng)”的強(qiáng)調(diào)。由表1可見,幾個代表性定義都與國際化人才培養(yǎng)密切相關(guān),主張把現(xiàn)有國際化資源整合進(jìn)人才培養(yǎng)過程。顯然,這是不同于既有兩個認(rèn)知取向的新取向,即“目標(biāo)取向”明確將“在地國際化”指向國際化人才培養(yǎng)這一目標(biāo)。
我國學(xué)界對“在地國際化”的界定之所以會出現(xiàn)“目標(biāo)取向”,與新世紀(jì)以來我國學(xué)界日益重視國際化人才培養(yǎng)的趨勢或許存在一定關(guān)聯(lián)。從文獻(xiàn)來看,自2002年深圳大學(xué)提出培養(yǎng)國際化人才以來[30],相關(guān)研究就出現(xiàn)了逐年增多的趨勢,尤其是《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年)》(以下簡稱《綱要》)提出“培養(yǎng)大批具有國際視野、通曉國際規(guī)則、能夠參與國際事務(wù)和國際競爭的國際化人才”的要求后[31],相關(guān)文獻(xiàn)更是增加明顯(詳見圖2),截至2023年底已經(jīng)出現(xiàn)1 365篇文獻(xiàn)。在這種背景下,將“在地國際化”指向國際化人才培養(yǎng)的目標(biāo)也是很自然的選擇。
“目標(biāo)取向”的“在地國際化”定義與課程取向的主張有所不同,但也有一個共性,那就是都強(qiáng)調(diào)面向?qū)W生的教育教學(xué),二者與活動取向的定義相比,對“在地國際化”的功能定位更加聚焦,將重點(diǎn)放在了人才培養(yǎng)方面,對科研與社會服務(wù)則未做規(guī)定。筆者認(rèn)為這種定位更符合“在地國際化”的初衷,即讓那些沒有機(jī)會出國的在校生也有機(jī)會享受國際化教育。
(二)結(jié)合本土需求闡釋“在地國際化”的價值
“在地國際化”的提出,預(yù)設(shè)了其相較于“境外國際化”的特殊價值,國外學(xué)界對于其價值的關(guān)注,也通常在這個比較意義上展開,我國學(xué)者也不例外。但我國學(xué)者對其價值的具體論述特別關(guān)注了我國的本土需求,更偏重解決中國高等教育問題,尤其關(guān)注“在地國際化”在新冠疫情暴發(fā)后的存在價值。我國學(xué)者最初對“在地國際化”價值的關(guān)注,除了試圖用新的視角回答“如何推進(jìn)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這一命題外,部分源于對我國跨境流動為特征的國際化范式帶來的“西化”危險的關(guān)注[32]。同時,本土高等教育發(fā)展面臨的特殊需求也成為我國學(xué)者關(guān)注“在地國際化”的特色背景。如在我國地方院校與部屬院校二分的管理體制背景下,有學(xué)者從我國地方院校的立場出發(fā),認(rèn)為比之重點(diǎn)建設(shè)院校及部屬院校,地方院校師生出國留學(xué)的機(jī)會和渠道比較受限,走“在地國際化”之路才是更現(xiàn)實的選擇[33]。《綱要》提出大規(guī)模培養(yǎng)國際化人才的要求后,越來越多的學(xué)者開始意識到傳統(tǒng)的境外流動與中外合作辦學(xué)模式都難以勝任這一使命,主張通過“在地國際化”擴(kuò)大國際化教育的受益面[34],以加速國際化人才的培養(yǎng)進(jìn)程。隨著研究者對“在地國際化”認(rèn)識的深化,其在創(chuàng)新和帶動國際合作教育的體制機(jī)制改革、促進(jìn)國際合作教育內(nèi)涵發(fā)展、通過吸收融合國際先進(jìn)教育理念提升中國高校全球競爭力等方面的價值得到較多的強(qiáng)調(diào)[35]。新冠疫情暴發(fā)后,人員流動受阻、國際關(guān)系格局的變化等使得“在地國際化”之于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內(nèi)涵發(fā)展的價值受到進(jìn)一步關(guān)注。有學(xué)者重點(diǎn)論述了后疫情時代“在地國際化”對我國地方高校發(fā)展的意義,包括克服由于經(jīng)費(fèi)局限難以大規(guī)模跨境流動的弊端、對國際化課程體系建設(shè)的推動作用、挖掘國際合作交流中的特色優(yōu)勢等[36]。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會議后,隨著人才的自主培養(yǎng)受到更多關(guān)注,有學(xué)者開始從國際化人才自主培養(yǎng)的角度關(guān)注“在地國際化”的價值。房欲飛從當(dāng)前我國國際化人才培養(yǎng)面臨著的四大矛盾出發(fā),認(rèn)為傳統(tǒng)的跨境流動模式已經(jīng)難以獨(dú)自承擔(dān)滿足國際化人才需求和保障民族利益的使命,亟須通過“在地國際化”補(bǔ)償其受益面小、對外依存度高、意識形態(tài)風(fēng)險大、后疫情時代不確定性強(qiáng)等方面的弊端[37]。李均、鄭錦秀基于利益相關(guān)者的視角,認(rèn)為傳統(tǒng)國際化模式及西方的科技與人才封鎖制約了我國企業(yè)的海外擴(kuò)張,通過“在地國際化”掌握國際化人才培養(yǎng)的自主權(quán),有助于滿足我國企業(yè)提升國際影響力的需求[38]。
(三)“在地國際化”實踐探索的本土特色
我國“在地國際化”實踐探索的本土特色主要表現(xiàn)在3個方面。一是與我國政策話語的緊密結(jié)合。如“雙一流”[39]“雙循環(huán)”[40]“新發(fā)展格局”[41]“課程思政”[42]等政策話語被視為“在地國際化”實踐探索的背景,或者被作為細(xì)分的議題。二是對于跨文化要素的本土探索。如對于課程國際化這一普遍存在的“在地國際化”核心要素,我國學(xué)者的探索就密切結(jié)合了本土實踐背景。有學(xué)者指出了我國課程國際化中“全英文課程等同于國際化課程”“聯(lián)合培養(yǎng)學(xué)位項目下教授的課程就是國際化課程”兩個傳統(tǒng)認(rèn)知誤區(qū)[43]。針對我國課程國際化中簡單引進(jìn)西方教材的現(xiàn)象,有學(xué)者指出了文化侵襲的風(fēng)險,主張對引進(jìn)的課程進(jìn)行本土化改造,培養(yǎng)有根的世界公民[44]。有學(xué)者進(jìn)一步主張建立綜合國內(nèi)外教育精華又具有中國特色的自主課程體系[45]。再如,在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受到廣泛關(guān)注的本土學(xué)生與國際學(xué)生的互動也受到我國學(xué)者的關(guān)注,但我國學(xué)者關(guān)注這一實踐路徑的動因與西方有所不同,西方國家是因為國際學(xué)生較多希望借此優(yōu)化校園文化生態(tài),我國學(xué)者關(guān)注這一議題則是由于我國整體上文化同質(zhì)性較強(qiáng),異質(zhì)文化匱乏,故將推進(jìn)中外學(xué)生互動視為“在地”培養(yǎng)跨文化能力的現(xiàn)實路徑[46]。張駿提出了中外學(xué)生的“四同式”趨同管理模式[47],李小紅等進(jìn)一步主張中外師生互動中的文化雙向傳播,增強(qiáng)文化互信[48]。三是提出國外學(xué)者未曾關(guān)注的“在地國際化”議題。我國學(xué)者王英杰提出應(yīng)重視大學(xué)治理制度的“在地國際化”,研究如何把大學(xué)自治、學(xué)術(shù)自由、學(xué)術(shù)共同體的民主管理等大學(xué)本質(zhì)屬性與中國特色制度和傳統(tǒng)文化結(jié)合起來[49]。這一議題在國外相關(guān)文獻(xiàn)中未受到關(guān)注,之所以我國的權(quán)威學(xué)者關(guān)注到這一點(diǎn),可能與我國近年來比較重視現(xiàn)代大學(xué)治理制度的建設(shè)有關(guān),在這個過程中,西方大學(xué)的學(xué)術(shù)自由與自治通常成為備受關(guān)注的議題。
四、結(jié)論、審思及建議
本研究基于現(xiàn)有文獻(xiàn)資料,首次對我國“在地國際化”研究的興起及本土化特征進(jìn)行了評析,研究發(fā)現(xiàn)我國學(xué)界正日益重視“在地國際化”的研究價值,本土探索的自覺意識正在生成,且不乏理論貢獻(xiàn):所提出的“目標(biāo)取向”本土定義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學(xué)界對這一概念的認(rèn)知;對其價值和實踐要素的探索,既關(guān)注了我國高等教育發(fā)展的特殊背景,又提出了國外“在地國際化”研究者不曾關(guān)注到的教育治理議題。學(xué)者們提出的觀點(diǎn)中,也不乏一些創(chuàng)新性的提法,如張應(yīng)強(qiáng)等在論述人員流動與“在地國際化”關(guān)系時,對“表層現(xiàn)象”與“育人本質(zhì)”的論斷,徐一淥等對通過微證書重建“在地國際化”與流動關(guān)系的建議,等等。但總體而言,我國學(xué)者對IaH的探索尚處在起步階段,“始生之物,其形必丑”。與歐洲已經(jīng)形成本土化的實踐工具[50]、美國已形成廣受認(rèn)同的“全面國際化”模型①相比,當(dāng)前我國的研究還處在概念引介、價值啟蒙、政策呼吁階段,對本土實踐機(jī)制的探索還有待深入。從研究方法上看,當(dāng)前的文獻(xiàn)基本還是思辨性為主,基于現(xiàn)狀調(diào)查的專題實證研究尚鳳毛麟角,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既有理論的驗證、拓展及深化。現(xiàn)狀的缺憾不能抹殺“在地國際化”的研究價值,可以預(yù)見,隨著全球化進(jìn)程對國際化人才需求的增加,通過“在地國際化”擴(kuò)大國際化教育的受益面將是必然趨勢,國際資源日益頻繁的全球流動也有望提供更現(xiàn)實的可行性,適合本土文化背景的“在地國際化”探索也將更有其必要性。建議后續(xù)研究推進(jìn)過程中,針對目前尚存的問題適當(dāng)完善研究方法,調(diào)整研究方向,拓展研究內(nèi)容。
一是啟動實證研究,驗證現(xiàn)有理論并生成本土實踐工具。當(dāng)前國內(nèi)外的理論研究已經(jīng)涉及廣泛的論域,對于實踐操作也有一些理論化的探討,但對于國外的理論是否適合我國國情,以及我國學(xué)者提出的理論是否有實際操作性,都需要基于實證研究進(jìn)行檢驗,并在此基礎(chǔ)上調(diào)整或拓展現(xiàn)有理論。二是直面現(xiàn)實困境,加強(qiáng)基于ICT的實踐路徑創(chuàng)新研究。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社會文化背景相對單一,“在地國際化”可資利用的本土跨文化資源相對較少,加之后疫情時代大國關(guān)系之間的不確定性、西方對我國的技術(shù)封鎖等,致使我國可以獲取的本土國際資源受到一定限制,如何借助信息通信技術(shù)突破時空限制推進(jìn)課程國際化、拓展本土學(xué)生與國際學(xué)生的在線跨文化接觸機(jī)會,將成為一個值得考慮的議題。目前我國對基于ICT的“在地國際化”路徑創(chuàng)新研究剛剛起步,可以進(jìn)一步加大力度。三是著眼國際化的完整格局,加強(qiáng)與跨境流動的協(xié)同機(jī)制研究。雖然“在地國際化”研究需要對跨境流動做排他性的界定,但實踐中“在地國際化”并不拒斥跨境流動,二者只存在發(fā)生場域與受益群體覆蓋面的區(qū)別,是相互補(bǔ)充而非互斥的。只有二者協(xié)同發(fā)揮作用,才能形成完整的高等教育國際化格局。但目前我國除了徐一淥等對“在地國際化”與流動的關(guān)系略有涉及外,其他研究對二者的協(xié)同作用機(jī)制都尚未予以關(guān)注。國外學(xué)者布寧(Joris Boonen)等曾結(jié)合荷蘭的案例對其進(jìn)行初步探索[51],也未見其他相關(guān)研究。如果繼續(xù)忽視這一議題,很容易造成對其實踐機(jī)理探索的偏頗,即過于注重其內(nèi)部工作機(jī)制而忽視其在整個高等教育國際化系統(tǒng)中的定位、與其他同類活動資源的競合關(guān)系等。故有必要扭轉(zhuǎn)當(dāng)前研究中“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局面,將研究對象放在與跨境流動的關(guān)系中深入探討,積極推動適應(yīng)新發(fā)展格局的“在地國際化”實踐與探索。
注釋:
①由于文化語境的不同,美國的“在地國際化”更多被納入了“全面國際化”和“校園國際化”的概念框架。美國教育委員會國際化與全球事務(wù)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Global Engagement,CIGE) 提出了他們稱之為“CIGE 模式”的全面國際化模型。
參考文獻(xiàn):
[1]郜正榮.全面推進(jìn)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幾點(diǎn)思考[J].中國高等教育,2016(05):18-20.
[2][7][8]房欲飛.“在地國際化”研究的國際視野及最新進(jìn)展[J].比較教育研究,2022(08):28-36;86.
[3]蔡克勇.教育國際化、本土化與學(xué)校個性化[J].湖南師范大學(xué)教育科學(xué)學(xué)報,2002(03):5-10.
[4]操太圣.人才培養(yǎng)的本土國際化——尋找“中外合作辦學(xué)”政策的理論基礎(chǔ)[J].公共管理高層論壇,2005(02):189-200.
[5]丁笑炯.本土國際化:國外院校培養(yǎng)國際化人才的新理念[J].世界教育信息,2008(09):67-69.
[6]洪大勇.人大國際小學(xué)期:立足本校,實現(xiàn)“在地”和“雙向”國際化[N].新京報,2011-07-18(02).
[9]朱光潛.關(guān)于外語教學(xué)的一些雜感[J].西方語文,1957(01):6-12,122.
[10]舒志定.文化傳播與高校師資培訓(xùn)國際化[J].上海高教研究,1995(03):47-50.
[11]謝作栩.美國高等教育課程國際化的歷史演進(jìn)[J].教育研究,1996(06):65-68.
[12][17][27]蔣冰清.論新建地方本科高校的在地國際化[J].湖南人文科技學(xué)院學(xué)報,2016(02):99-102.
[13][28][32]張偉,劉寶存.在地國際化:中國高等教育發(fā)展的新走向[J].大學(xué)教育科學(xué),2017(03):10-17;120.
[14]唐君.基于本土國際化模式培養(yǎng)學(xué)生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實證研究[J].吉林化工學(xué)院學(xué)報,2017(06):79-85.
[15]房欲飛.“在地國際化”之“舊”與“新”:學(xué)理思考及啟示[J].江蘇高教,2021(08):41-45.
[16]張應(yīng)強(qiáng),姜遠(yuǎn)謀.后疫情時代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向何處去[J].高等教育研究,2020(12):1-9.
[17][29]蘭思亮,馬佳妮.在地國際化:嬗變、實踐與反思[J].比較教育研究,2021(12):98-107.
[18]房欲飛.主要發(fā)達(dá)國家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發(fā)展動向與趨勢[J].世界教育信息,2024(01):12-21.
[19]王中興,劉越.共生理論視角下的高等職業(yè)教育在地國際化策略研究[J].煙臺職業(yè)學(xué)院學(xué)報,2021(03):32-36.
[20]易學(xué)瑾.歐洲國際教育協(xié)會在地國際化的制度化探索——基于制度創(chuàng)業(yè)理論的分析[J].比較教育研究,2023(03):103-112.
[21]陳昳舟,陳丁江,朱小螢.生態(tài)文明背景下在地國際化人才培養(yǎng)的思考與實踐[J].黑龍江教育(高教研究與評估),2022(01):74-75.
[22]任令濤.數(shù)字技術(shù)賦能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的現(xiàn)實價值與邏輯向度[J].現(xiàn)代教育管理,2024(02):105-114.
[23]楊啟光,王帥杰.高等教育虛擬國際化的動因、特征與未來趨勢[J].黑龍江高教研究,2024(03):91-96.
[24]段世飛,錢跳跳.虛擬國際化:概念、動因與機(jī)制[J].比較教育研究,2024(02):103-112.
[25]Wchter B.Internationalisation at home–the context[R].Internationalisation at home:A position paper,2000:5.
[26]Beelen J,Jones E.Redefin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R].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Between critical reflections and future policies,2015:59-72.
[30]春華.深圳大學(xué)加速培養(yǎng)國際化人才[J].深圳大學(xué)學(xué)報,2002(02):91.
[31]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工作小組辦公室.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年)[EB/OL].http://www.moe.gov.cn/srcsite/A01/s7048/201007/t20100729_171904.html,2024-04.
[33]徐同文,房保俊.探索本土國際化機(jī)制,培養(yǎng)地方應(yīng)用型人才[J].中國高等教育,2014(01):44-47.
[34]李妍.高校本科生本土國際化的途徑探索與實踐——以中國政法大學(xué)小語種語言興趣班為例[J].中國法學(xué)教育研究,2016(02):114-125.
[35]屈利娟,何蓮珍.適應(yīng)新發(fā)展格局的“在地國際化”實踐與探索[J].中國高等教育,2022(10):28-30.
[36]毛錫龍,楊凱.后疫情時代我國地方高校在地國際化的探索——基于浙江師范大學(xué)的實踐[J].浙江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22(03):111-120.
[37][46][50]房欲飛.新時期我國推進(jìn)“在地國際化”的戰(zhàn)略意義、挑戰(zhàn)及對策探析[J].復(fù)旦教育論壇,2022(02):82-88.
[38]李均,鄭錦秀.我國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的動因、問題及對策——利益相關(guān)者的視角[J].西北工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23(03):34-43.
[39]鄭淳,閆月勤.“雙一流”高校推進(jìn)在地國際化的價值機(jī)理與邏輯理路[J].高等理科教育,2023(04):16-27.
[40]蔣冰清,楊柳.“雙循環(huán)”背景下普通高校的在地國際化研究[J].科技風(fēng),2023(34):161-163.
[41]閻利,王吉超,吳琴.在地國際化:新發(fā)展格局下地方本科院校的戰(zhàn)略選擇[J].神州學(xué)人,2023(06):20-24.
[42]呂晨.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下的課程思政:挑戰(zhàn)與破解路徑[J].高教學(xué)刊,2022(S1):22-25.
[43]鄭淳,閆月勤,王海超.在地國際化的概念演進(jìn)、價值指向及要素條件——基于歐洲地區(qū)高等教育一體化進(jìn)程的思考[J].江蘇高教,2022(03):34-42.
[44]王璐.高等教育課程國際化的本土追求與設(shè)計[J].當(dāng)代教育科學(xué),2015(07):14-18.
[45]蔡永蓮.在地國際化:后疫情時代一個亟待深化的研究領(lǐng)域[J].教育發(fā)展研究,2021(03):29-35.
[47]張駿.高校國際化人才本土培養(yǎng):“一境四同”實踐路徑研究[J].國家教育行政學(xué)院學(xué)報,2014(10):8-11.
[48]李小紅.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意涵闡釋、全球案例與中國借鑒[J].西北師大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24(02):65-74.
[49]王英杰.后疫情時代教育國際化三題[J].比較教育研究,2020(09):8-13.
[51]Boonen J,Hoefnagels A,Pluymaekers M,et al.Promoting international learning outcomes during a study abroad: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ternationalisation at hom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2021(07):1431-1444.
(責(zé)任編輯:孫冰玉)
The Rise,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flection of the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 in China
FANG Yufei1, QIAN Mengting2
(1 Shanghai Academy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Shanghai 200032, China;
2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 in China has risen from the discourse betwee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fā)ocalization,” and the research histor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period of spontaneous exploration, the period of conceptual self-awareness and slow start, and the period of rapid growth and deepening expansion. The research histor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spontaneous exploration, conceptual self-awareness and slow start, and rapid growth and deepening expansion. The specific research content presents distinctive local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the localization of terms and conceptual connotations, the local care of value cognition, and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practical path exploration. The “goal orientation” of its connotation has expanded the cognitive dimension of the concept, and it is expected to contribute cross-cultural cases to the local exploration of values and practice paths. However, in general, the exploration of “l(fā)ocal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China is still in the initial stage, and the exploration of local practice mechanism is still in-depth, and the lack of empirical research affects the verification, expansion and deepening of the theory to a certain extent. As the practice of “l(fā)ocal internationalization” has become a major trend, it is necessary to launch empirical research to test the existing theories and generate tools for local practice; to face up to the real dilemmas and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of the path of “l(fā)ocal internationalization” based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o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with cross-border mobility in the research object. It is necessary to face the real dilemma and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of the path of “l(fā)ocal internationalization” based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 put the research object in the relationship with cross-border mobility for in-depth exploration, and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synergy mechanism between them.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 local internationalization; cross-border internation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