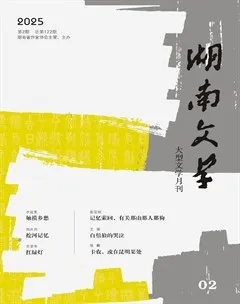小說短巧,像一聲嘆息
幾年前我回湖南過年,在家住了整月。傍晚陪父母出門散步,他們帶我散步,路過曾經念過的小學,此刻已變成鎮中心的商業超市,門口的喇叭和電動搖搖車震天響。隨著城鎮發展,商業中心、健民廣場、現代小區逐一出現。它們對我來說,很陌生。童年時的熟悉的家全然變了模樣。
有趣的是,有年我偶然在香港小住,意外選了本地人聚集的村子。難以想象在繁華的都市里,這村子靜靜落在山腳,由上百幢三層小樓匯聚而成。房子要么獨院,要么聯排,樣式略有區別,但也像湖南的白瓷磚藍玻璃的房屋。我住進去的傍晚下小雨,走在村子里,一樓廚房傳出聲響,我探頭聽——有人招呼吃飯;院子里支出植物來,我抬頭看是不是桂花樹。那一瞬間讓我不可思議,兒時的“家”復現,可此時離家千里,難道在做夢?
親臨舊夢,驚喜又失落,我很想記住錯位的家鄉感,于是有了寫一篇小說的想法。
那種錯位里不只是建筑和環境的熟悉與親切,還是對生活巨變的驚詫和迷茫。作為作家,我時常描寫當代生活;作為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我熟悉城市的冷漠、邊界和無鄰里,用這種方式生活了很久。不止于城市和鄉土、過去和現在,觀念的變遷亦然。婚戀也是其中一項,在《紅綠燈》中,有自由戀愛,也有父母撮合的相親對象。前者在幾十年前被推崇,代表了自由、開放、熱烈;后者近年越來越多出現在人們的視野里,大家紛紛談論起門當戶對。這些都讓我迷惑,或許也是很多人的困惑,哪種觀念是對的?又或者哪種觀念才會讓人幸福?
小說當然無法給人生活的答案,只是將生活提煉成故事與思考。在寫小說的時候我回想,在過去幾十年的自由里,我們得到自由的好處,又付出了自由的代價。在香港村落中的那個傍晚后,我慢慢意識到對家的眷念。自五四以來,作家寫家,多為反抗和逃離——兒子反抗父親,女人出走。在那個時刻后,我開始想,或許不止于此,還有東西可以挖掘。于是我寫了這篇小說,明秋的期期艾艾,含混不明,想自由卻不能,想傳統也不能,在猶豫和拉扯里時間過去,這就是我理解的現在——矛盾、迷茫,就像沒有紅綠燈的十字路口。
小說短巧,像一聲嘆息。
責任編輯:易清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