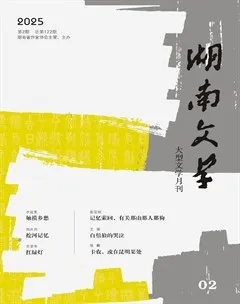延時的鳥鳴
越界
為了攔截幾只搬運糧食
不慎越界的螞蟻
天空出動了閃電、雷霆和一場暴雨
梳子
出于對頭發的尊重
我準備了很多梳子
出于對頭發的憐惜
我剃成了光頭。梳子閑置
有些沮喪,但它
仍然仔細地梳著空氣
它要從空氣中梳出
類似白發一樣的東西
來安慰自己的斷齒
安慰
夜色在冒充誰的呼吸
逆光而行,有一種呼喚
似曾相識,像小時候
母親在黃昏的河邊喊魂
我不敢應答,月光披身
像一塊塊傷疤。這么多年
我東奔西跑,身體被贗品
反復替換,面目全非
我怕母親認不出我,會哭
我怕母親認出我之后
會號啕大哭,而我的手
在她佝僂的后背上
已拍不出兒子那樣的安慰
延時的鳥鳴
我聽見的鳥鳴
穿過了很多事物
有些延時,即使是在喊我
我滯后的回答
也會被其他聲音
淹沒。整個早晨
我一直保持沉默
但臉上始終含著微笑
我想讓遠方的鳥知道
它的呼喚,我聽見了
即使不是在喊我
穿過我微笑的鳥鳴
也會讓后面的事物
聽起來覺得
更加婉轉,更加暖心
內斂的漩
憂心的事情不多也不少
這足以讓窗外大葉榕的枝條
保持克制。油鋸閑置
但它的聲音經常溜出來
恫嚇遠處那只僭越的蟬
這是多么奇妙的時刻
不用望天,云朵是天空
丟棄的手帕,你用它擦掉
一叢野菊嘴角的夢囈
和后背的冷汗,可再次丟棄
也可用來包裹受傷的心
雖有些臟,但它一旦包裹了心
就會變成大海,有些顛簸
但不必擔心它會把你
拋出來,像一個內斂的漩
河邊
夏日河邊,一個人
坐在兩棵麻柳樹中間
沒有垂釣,沒有吸煙
沒有用樹枝撩弄螞蟻
也沒有吹奏近旁的草葉
他像兩棵麻柳樹中間
鼓出的一個小土包
在風的吹拂下,一動不動
河水兀自流過,麻柳樹
獨自蒼綠,我遠遠望著
如果他轉身就會看見我
但他沒有。如果我繞到對面
就會看見他的臉
和表情,我也沒有
有毒的繩子
伸出手,所有事物都在逃離
在它們看來,你就是一根有毒的繩子
只能捆住一些虛幻的東西
比如把一首詩,勒出血來
還在持續用力,想逼出隱藏其間的星辰
恍惚
星空遼遠,仿若假象
我迷戀這遼遠的假象
如同迷戀近旁那棵青草
佝僂著,在黑暗中慢慢泛綠
這綠太淺,我們看不見
甚至會誤認為它是黑
在一個瞬間出現的恍惚
死結
不能像大海一樣
把萬千支流孩子一樣領養
恰恰相反,我想讓萬千支流
把我領走。雖然所剩無幾
但我仍像大廚一般
切著自己,如切一根蘿卜
盡可能讓每一絲
都均勻,透明,可口
讓那些支流不會因為
分我不均心生憤懣
進而糾纏在一起
為大海,打一個個死結
陽光下
陽光把日子照得很亮
南瓜葉子蔫垂,露出的南瓜
渾圓、橙黃。藤上的七星瓢蟲
得到了陽光的激勵
和我的注視,在預設的方向
比昨日多爬了九步
另一種春天
春天不是一朵花
也不是一萬朵花。不是花的形狀
色彩和香味,也不是它內心
燒著的火焰。不是圍過來的蜜蜂
不是蜂蜜,不是甜
春天是苦時,對甜的一種執念
疾病一樣跟隨你的一生
當它發作的時候,花就會開
奇異的形狀、鮮艷的色彩、芬芳的香味
就會翻江倒海而來,蜜蜂
是花朵涌起的波浪
它釀的蜜,虛幻且恒久
好像是苦,等待幾生幾世的愛人
白鶴
那一年
我被一場病擄走
在遠離人間的地方
鑿洞而居,飲露為藥
在夢中,與一只白鶴偶遇
惺惺相惜,義結金蘭
病愈,以失憶之痛
換取重回人間
沉淪為一個專畫白鶴之人
我畫的白鶴
別人都說
不像他們看見的白鶴
想起蓑草
在紙上寫詩的時候
我總想起老家的蓑草
披散在記憶的山坡
如山的胡須。經過染灰
蒸料、煮料、溫坑、碾漿
等一系列工序后
變白,成為一張張白紙
在白紙上寫詩,每一個字
都像釘子一樣,釘在
蓑草的骨頭和血液里
不僅牢實,還會生長
不像在電腦和手機上寫詩
總感覺那些句子是飄的
好像無根一樣,站不穩
風一吹,就可能消失
距離
我靈魂的輜重
堆放在一只蝸牛的殼里
這么多年
我一直走走停停、停停走走
只是為了與遠山
和蝸牛保持恰當的距離
讓它們每時每刻
都在我的視野之中
前可瞻,后可望
迷離中
還可重疊在一起
責任編輯:青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