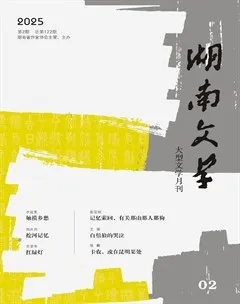我們從湘北走來

1983年,我在湖南湘陰縣官驛橋中學讀初二,那時候,我很喜歡寫作文,我是受了我那愛著寫小說的舅舅殷平陽的影響的。這時他給我介紹了彭見明與他二舅舅李自由的小說。那時我就知道了彭老師的寫作故事,他十幾歲就招到平江縣劇團,做演員和舞臺美術工作,僅有初中學歷,不知怎么就成了一個作家,頗有些傳奇色彩,其時對我們這些愛好文學的學生,影響很大。
每到下雨天,不需要下地勞動,我舅舅就躲過外婆到我家來,關緊房門寫小說。我是在舅舅這里讀到發表彭見明的小說《那山那人那狗》這一期《萌芽》雜志的。看來我舅舅已經讀過幾遍這篇小說了,他給我談了不少讀后感,我記得他對我說過一句很重的話:“如果你腦子里沒有人物,就寫不出小說來。”
我對《那山那人那狗》里的鄉郵員太熟悉了,每個星期,他們都會來送信和報刊,他們騎著綠色的專屬自行車、挎著綠色的郵包,我家訂閱的報紙與文學期刊,以及我對外的投稿退稿,都要經過他們之手。開始郵件送到公社,后來送到大隊,再后來送到我們村的孤寡老人陽爹那里,他再轉送到鄉鄰手中。我家也有一條彭老師小說中的狗,不過我家的狗有名字,是我媽媽取的,叫“麻烈”。
彭老師的《那山那人那狗》與何立偉的《白色鳥》,成為我文學啟蒙中比較重要的兩篇小說,但這兩篇小說的語言風格完全不同,前者質樸醇厚,獲得1983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后者流暢清郁,獲得1984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二者的共同之處在于,都充盈著飽滿的詩意,那時于我,充滿著很大的誘惑,以至于我后來癡迷于詩歌創作。
彭見明的小說創作脈絡啟發我去細心關注身邊的生活,后來我也寫起了長篇小說。何立偉的小說引導我的中學作文注重文學的表達。而那時的語文老師,卻給了我“費解”的批語。
1986年夏天,我到縣文化館找文學專干成明進,我知道他與彭老師熟,我希望他介紹我與彭老師見見面。為慎重起見,先是通信聯系,后再見面,沒想到他是平易近人的,見面就成了文友。他那時是岳陽市作協主席,推薦我加入了岳陽市作協,后來又推薦我加入湖南省作協。
翻看我的文學創作活動年表,里面有這樣的記載:1986年冬天,岳陽市作協主席、小說家彭見明老師來信鼓勵,信中夾了現金100元。
那時的農村文學青年,生活清苦,彭老師是深有體會的。好像是快過年的時候,鄉郵員給我送來了彭老師的信。拆開信,發現里面夾了100元錢,我還記得他漂亮的字跡。那100元錢支持我跑到長沙袁家嶺新華書店買回了一大堆詩集,這一批充滿人情味的珍貴讀物,現在還存放在我北京的書房里。那時我協助成明進為《岳陽民間文學三套集成》撰稿與畫插圖,還創辦了《造山神》文學報。彭老師對農村文學青年的關心,讓我終生難忘。
后來我在成明進的影響下,轉向了詩歌創作,很快我就在安徽《詩歌報》與河北《詩神》發表了與湖南鄉土詩歌并不一樣的詩歌作品。1988年,我離開了湖南到武漢讀書,并在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了處女詩集《繆斯的情人》。但與彭老師的聯系并沒有中斷過。有一次我在北京與作家邱華棟一起參加活動,他對我說:“你老家的作家彭見明講段子是高手,很好玩的。”

我至今記得彭老師對我說過的一句話:“你這創作的黃金時期,要抓緊多寫東西。”我在武漢十年只寫了一部長篇小說《曖昧大街》與少量的短篇,到了北京后才寫出《中關村的烏鴉》《原汁原味》《蘋果》等6部長篇小說,但我一直羞于與彭老師談及我的小說寫作。在我寫不動的時候,彭老師的話就會在耳邊響起,看來他這句話會跟隨我一生了。
2021年,我從北京到了深圳,我與發小周藝文發起了一個項目——“到福田聽名家講座”,我倆共同的心愿是請彭老師來深圳講一次課。這時他已經退休,很多時候在湘北的大山里忙活,他的愛好多,最初是寫字畫畫,后來寫文章,都不愿放棄,所以有干不完的活。我們在深圳高鐵站接上他后,我說彭老師您辛苦了,他對我說:“有高鐵坐,好舒服啊,有什么辛苦,又不要我走路來。”此話讓我聽來感慨萬千,對于湘北的農家子弟,“走路”是我們兒時的必須,多遠都要用腳量,鄉郵員要走路,祖祖輩輩都是這么走過來的。彭老師沒有忘卻以過往的辛苦來比照此時的享受,可見他雖已被人稱作名家,但堪稱“知足”的故鄉情懷依舊存活在他的血肉中,這話能夠讓我感動,因為我們都是在泥巴路上“走”出來的人。做好一個作家,不但要有美好文字,更要有美好良知。
那次講座前,我向讀者播放了《那山那人那狗》的電影片段,亮麗的畫面,純樸的敘述,溫馨的情感,把深圳讀者拉回到一個理想主義的年代,與他的講座內在統一。他一貫的純凈、低調、堅毅和不懈的創造活力,讓深圳讀者看好。
彭老師談到文學要“講人話,講人聽得懂的話,講有趣的話”“寫自己熟悉的生活”,只有順著自己熟悉的生存體驗途徑,才有可能挖到屬于你的藝術礦藏。他從自己最初的寫作與生活談起,告訴大家真誠厚實的體驗同感悟,才是文學藝術之本。
我在作講座總結時講了一段話:“彭見明老師是我的文學啟蒙老師,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在老家開始文學創作時,就得到了他的幫助,他那時已經是全國一線作家,卻對我們這些初學者非常關心,為我們走上文學道路給予了無私的幫助。今天在深圳再次聆聽他的講座,我看到了一個作家的靈魂始終如一地真實與強大。他似乎每隔十年就會對我說:‘這是你創作的黃金時期,抓緊寫吧!’這次見到他,我深感彭老師的淡泊與堅定。在文壇他是淡泊的,在藝術上他是堅定的。他再一次深深地激勵了我。”
近年來,彭老師重新回到書畫藝術創作中,我認真看過他的書畫,他的書畫藝術既有傳統底蘊,又有人文風骨,更有他自己的獨立思考。在我看來,彭老師是一個不斷尋找突破與創新的作家、藝術家。
那次深圳講座,我們在一起待了一天,我又當面問了他一遍《那山那人那狗》的創作故事,其實我是知道的,但還是想聽他親口講一次。講座完后,他要求當天回長沙,他說他不想麻煩人,早來晚歸,任務完成了,沒有住一晚的必要了,大家的時間都要緊。那次除了“有高鐵坐,又不要我走路來”,還有他所說的“寫文章”,這也是故鄉老人的話,聽起來古老而親切。他從八十年代的湘北走出來,我們跟著他,他就像那個老鄉郵員,我們跟著他跑郵,給他人送讀物。
哦,那次見面,我忘記問了:“你那一抹英氣勃勃野性十足的絡腮胡子,什么時候給刮掉了?多么可惜。”
我與很多湘北寫手,都有與他年輕時候的合影,他的烏黑靚須,令我等文友們懷念。
責任編輯:易清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