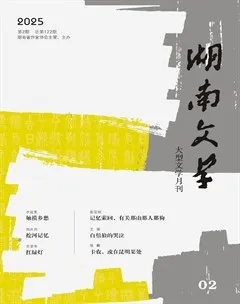那小說 那電影

一
我和大哥彭見明走上文學(xué)創(chuàng)作這條路,很大程度上是受我家二舅李自由的影響。
二舅早年就讀于湖南農(nóng)大,后因生病退學(xué),在那些生病的日子里,他為了打發(fā)時(shí)光,便在家里寫字畫畫,后來在鄉(xiāng)里畫出了名,被招到了平江縣文化館去畫宣傳畫。后來“文革”爆發(fā),二舅寫的毛體字,畫的“毛主席去安源”的巨幅油畫像,一下子遍及平江城鄉(xiāng)以及瀏陽、萍鄉(xiāng)、安源一帶……這一陣風(fēng)刮過之后,二舅又轉(zhuǎn)入了文學(xué)創(chuàng)作。我最早讀到他的作品,是一本叫《護(hù)身符的秘密》的連環(huán)畫。那時(shí),我的老家長田公社的供銷社,在布匹柜臺的轉(zhuǎn)角處,擺著大約二三十本書,其中有《金光大道》《艷陽天》等,突然有一天我看見其中擺著一本二舅寫的連環(huán)畫,便找母親要幾角錢,去買這本書,母親原本不給,但聽我說這書是二舅寫的,她一咬牙也就給了。我如愿買回了《護(hù)身符的秘密》,一遍又一遍地讀,二舅成了我心目中崇拜的人。
大哥比我大八歲,在我還沒有上學(xué)時(shí),他已到鎮(zhèn)上寄宿讀初中去了,一到寒暑假,母親要大哥回家砍柴,二舅卻對母親說:“不要將孩子老關(guān)在家里干農(nóng)活,要讓他到外面去開眼界。”
二舅的話母親是愿意聽的,因此一到寒暑假,大哥便能逃避砍柴之苦,到縣城里跟著二舅去“開眼界”。在開眼界之余,他也跟著二舅學(xué)畫畫、寫毛筆字。在大哥高中畢業(yè)還差兩個(gè)月的時(shí)候,他在二舅的推薦之下,招到了縣文藝宣傳隊(duì)去當(dāng)演員,后來又學(xué)習(xí)畫舞臺布景。
我十六歲時(shí),在大哥的推薦下,被招到平江縣文藝宣傳隊(duì)去當(dāng)小演員。那時(shí)“文革”剛結(jié)束,“傷痕文學(xué)”在一夜之間鋪天蓋地興起來。于是,大哥在畫舞臺布景之余,偷偷地搞文學(xué)創(chuàng)作。看到大哥在寫,我也偷偷地寫,因?yàn)槲覍?shí)在是演不好戲,每次分給我的角色都是跑龍?zhí)住F鋵?shí),我去搞文學(xué)創(chuàng)作更是不自量力,我在村里小學(xué)畢業(yè)之后,本來可以像大哥一樣到鎮(zhèn)上去上初中,但卻沒有去成,因?yàn)榇謇镞@時(shí)辦了農(nóng)中,所謂農(nóng)中,就是一邊讀書,一邊搞農(nóng)業(yè)勞動,一半的時(shí)間用來挖地、挑糞、開墾菜園。曾經(jīng)一度,我父親不想讓我去上學(xué)了,他說:“到學(xué)校去挑糞,何不在家里挑糞。”
就是在這樣的農(nóng)中,我也還沒等到讀完,便被招收到縣文工團(tuán)當(dāng)小演員去了,因此,我的肚子里確實(shí)沒有幾滴墨水,我估計(jì)我那時(shí)所認(rèn)得的字還不到千個(gè)。我每次寫了小說,便送去給大哥看,他用紅筆給我修改錯(cuò)別字,有時(shí)改得不耐煩了,故意將一個(gè)個(gè)圈打得很大、很醒目。
1988年我考入武漢大學(xué)的作家班讀書,臨行前到大哥家去告別,他對我說:“我看你到了武漢大學(xué),主要的任務(wù)是多認(rèn)識幾個(gè)字。”由此可見,他對于老給我改錯(cuò)別字這個(gè)差事已是深惡痛絕。
其實(shí),在我上武大作家班之前,大哥也去考過,卻沒能考上。在我們?nèi)雽W(xué)時(shí),武大中文系的副主任曾慶元老師跟我們班同學(xué)見面時(shí),講過這樣一段話:“彭見明曾經(jīng)來參加過作家班的考試,因一門不及格而沒有錄取他,現(xiàn)在看來,他沒有來入學(xué),這對于武大中文系來講,不得不說是一件遺憾的事情。”
后來我問了問我大哥,是不是這么回事。他說沒這么簡單。說是武大作家班第二屆招生時(shí),武大派了一位負(fù)責(zé)招生的科長,長途跋涉,來縣里見我大哥,他是受學(xué)校招生部門委派,動員我大哥去作家班就讀,當(dāng)時(shí)縣委宣傳部還派了一位工作人員陪同,并做思想工作。我大哥說如果是要考試,就不去了,他“文革”時(shí)期的高中都沒讀完,在劇團(tuán)工作已是十多年了,都做父親了,考試是做不到的。這位科長說,武大是希望你能去就讀的,至于考試,那也不過是走過場,作家班吧,是培養(yǎng)作家的。我大哥當(dāng)時(shí)還是沒有答應(yīng),這時(shí)已有十多家出版社和刊物向他約稿,已經(jīng)沒有閑空時(shí)間去干別的。后來那位科長又來信動員我大哥說:你來看看武大也不錯(cuò)啊。我大哥沒有去過武漢,也沒見識過大學(xué)是什么樣子,便答應(yīng)可以去看看,就當(dāng)是時(shí)下流行的“旅游”吧。我大哥到武漢后,受到那位科長的熱情接待,他領(lǐng)我大哥在校園里轉(zhuǎn)了一圈后,把我大哥領(lǐng)到一個(gè)簡樸的辦公室里,這時(shí)有人遞上了一摞試卷,交給我大哥,然后帶上門,讓我大哥慢慢考,說是不受時(shí)間限制。
于是,我大哥有幸成為一所名牌大學(xué)舉行的不受高考日期和考試時(shí)間限制,享受獨(dú)立專場的個(gè)人考試。我大哥大概只待了半個(gè)小時(shí)就草草交稿離開了考場。出來后,連考了些什么內(nèi)容都記不住。
二
大哥在縣劇團(tuán)做舞臺美術(shù)工作時(shí),也常去幫助縣文化館主辦的內(nèi)部刊物《平江文藝》畫插圖,設(shè)計(jì)封面,也嘗試著寫點(diǎn)小文章,自1978年起,也發(fā)表過幾篇千字文。這時(shí)我也在這個(gè)小小的陣地上發(fā)表作品,打基礎(chǔ),進(jìn)行自我訓(xùn)練。
1981年,大哥正式向官方文學(xué)刊物進(jìn)軍,處女作短篇小說《四妯娌》在《萌芽》發(fā)表,被《小說月報(bào)》轉(zhuǎn)載,當(dāng)年獲得了《萌芽》文學(xué)獎和湖南省文學(xué)創(chuàng)作獎。1982年,我寫了一篇題為《月亮溪》的短篇小說,經(jīng)大哥推薦在《萌芽》1982年第10期發(fā)表,我遲大哥一年,在全國發(fā)行的大刊物上發(fā)表了小說處女作。
再后來,我就沒有大哥幸運(yùn)了,1983年,他的短篇小說《那山那人那狗》在《萌芽》雜志發(fā)表后,一下子便在全國引起轟動。
1982年底,平江縣要召開一個(gè)年底的表彰大會,縣委宣傳部將大哥從文化館臨時(shí)抽調(diào)到了宣傳部去寫材料,分給他寫的是長壽區(qū)郵電分局一個(gè)老鄉(xiāng)郵員的材料,分局長對我大哥說:“這個(gè)材料,要請你替我們好點(diǎn)寫著,我們這個(gè)鄉(xiāng)郵員太辛苦,挑著郵包在南橋的大山里一圈走出來要三天,每天要走幾十里山路。”大哥寫過這個(gè)材料之后,再加之他此前和鄉(xiāng)郵員也有過一些接觸,那年冬天他便開始寫《那山那人那狗》,在塑造這位鄉(xiāng)郵員時(shí),很大程度上融入了我祖父的形象。
我家老祖父是做過大生意的,平江縣山地多產(chǎn)油、麻、茶、紙,老祖父便將這些油、麻、茶、紙一船一船販到漢口,又從漢口一船一船將洋布洋紗洋油販到平江。祖父年輕時(shí),便在老祖父的茶行里學(xué)習(xí)看茶,一把紅茶抓在手上看看、聞聞,再泡上一杯喝上一口,便能定出三等九級的價(jià)錢。解放以后,老祖父沒有生意做了,祖父憑著自己練就的這一門看茶的絕活,一到收茶季節(jié),便被山里的供銷社請去做看茶的臨時(shí)工。我曾到祖父的收購站上去玩過,那是大山里一座明代遺留下來的寺院,名叫“九方寺”,后來改成了供銷社,里邊有南雜柜、百貨柜、布匹柜、屠凳坊和祖父的收購站。天亮后,山民們便挑著一擔(dān)擔(dān)茶葉到祖父這里來了,祖父和顏悅色抓一把茶看看,聞聞,泡上一杯喝喝,便將三等九級的價(jià)錢定下來了。祖父定來的價(jià)格,山民們從來不懷疑有差錯(cuò),因?yàn)樗麄兌忌钪易娓傅蔫b別水平。
祖父一邊忙著收購茶葉,還一邊要包做這個(gè)供銷社上五六個(gè)人的飯菜,吃完飯人家一抹嘴巴走了,他還要洗碗收拾。太陽落山后,賣茶的山民都走了,祖父再到菜地里去忙乎——這五六個(gè)人吃的菜全靠他種植。天黑盡后,偶爾還有山民來請他去接骨頭、治蛇傷。我祖父自幼習(xí)武,摞皮接骨、尋草藥、治蛇傷,練就了一身本事,他給人接骨治傷,卻又從來不收分文報(bào)酬……我的祖父拿著那一份微薄的臨時(shí)工的工資,就像一只勤勞的蜜蜂一樣在那片山地上忙碌著。每次回家,都是半夜里打著一個(gè)手電筒回來,雞叫三遍之后,又打著那個(gè)手電筒離去,祖父就這樣奔走到七十五歲時(shí),我父親他們幾兄弟才霸蠻將他的鋪蓋從山里的收購站搬回家了,從此不允許他再起五更睡半夜到外邊去奔走。祖父活到七十九歲悄然走了,祖父去世時(shí)山里來了幾百號人為他守夜,人們一邊敘說著我祖父的千般好處,一邊流淚……試想,大哥以祖父這一人物形象為原型來塑造的老郵遞員,能不感人至深么!
《萌芽》雜志1983年第5期發(fā)表了《那山那人那狗》。那時(shí)我在鄉(xiāng)鎮(zhèn)擔(dān)任團(tuán)委書記,星期天回縣城,便到大哥家去了,大嫂拿出《萌芽》雜志對我說:“你哥又在《萌芽》發(fā)了一篇小說。”
我拿著這本雜志一口氣便將《那山那人那狗》讀完了,我對大嫂說:“大哥這篇小說肯定會轉(zhuǎn)載。”
大嫂說:“不可能,這個(gè)編輯老師只怕也是看在他去年獲了《萌芽》獎的面子上,照顧發(fā)在最后一條。”
我說:“你放心,肯定會轉(zhuǎn)載的。”
1983年《小說選刊》第7期果然轉(zhuǎn)載了《那山那人那狗》。于是,大嫂逢人便說:“二弟的眼睛有蠻毒,他說《那山那人那狗》能轉(zhuǎn)載,真的就轉(zhuǎn)載了。”
我當(dāng)時(shí)所能想到的是能轉(zhuǎn)載,卻是做夢也不會想到能獲全國獎。現(xiàn)在回顧起來,一篇發(fā)在最后一條的小說,居然能被《小說選刊》轉(zhuǎn)載,一個(gè)山州草縣的無名之輩,一舉能獲得全國大獎,那是一個(gè)多么公正純潔的文學(xué)年代啊!
三
《那山那人那狗》盡管獲了獎,但大哥的書在中國卻從來就沒有暢銷過,20年之后,大哥做夢也沒有想到,他的書將在一個(gè)島國暢銷開來。
1997年,北京電影制片廠和瀟湘電影制片廠將《那山那人那狗》搬上了銀幕,后來,這個(gè)電影獲獎無數(shù)。但是,獲獎歸獲獎,國內(nèi)真正看到這部電影的人并不多。
在某一屆電影展會上,這部電影卻被一個(gè)名叫深澤一夫的日本老先生看中了,他以近乎買“白菜”的價(jià)錢(6萬美金)買下了在日本國的放映權(quán)。影片買回去后,他拿到東京的電影俱樂部去放映,深澤一夫是位資深的電影經(jīng)紀(jì)人,他分層次請了一批又一批的人來觀看。例如:他請企業(yè)界的老板們來觀看時(shí),他的廣告語是“要教育你們的員工如何敬業(yè)么?你們就組織員工們來看看這位老郵遞員是怎么敬業(yè)的”。組織寵物協(xié)會的人來看,他的廣告語是“如何增進(jìn)人與寵物的感情,你們就來看看老郵遞員和他的狗吧!”組織親子協(xié)會的人來看,他的廣告語是“如何增強(qiáng)父子之間的感情,你們就來看看老郵遞員和他的兒子吧!”組織婦女聯(lián)合會的人來看,他的廣告語是“如何增進(jìn)夫妻之間的感情,請來看看老郵遞員和他的妻子吧!”

經(jīng)深澤一夫這一精心操持,很快將日本國各個(gè)層面的觀眾都動員起來了,這部電影在日本的院線上久放不衰,深澤一夫賺得盆滿缽滿。
電影在日本火爆之后,靈敏的日本書商隨即與大哥簽約,翻譯出版小說集,不過,書名不再叫《那山那人那狗》,而是叫《山里的郵遞員》,據(jù)說是因?yàn)檫@有點(diǎn)詩化的語言不好翻譯。照我想,直接翻成《那座山那個(gè)人那條狗》不就得了?有什么不好翻譯的呢?但我一個(gè)懂日語又了解一些日本文化的朋友說,這可能是因?yàn)槿毡救藢?shí)打?qū)崳幌矚g花里胡哨的緣故。但不管怎樣,這個(gè)題目是翻得有點(diǎn)可惜。當(dāng)然,書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本書在日本一版再版,還翻譯成了學(xué)生口袋版、盲文讀物版、中日文對照閱讀版。大哥靠寫文章在中國從沒發(fā)過財(cái),而在日本卻發(fā)了一筆小財(cái)。
《那山那人那狗》發(fā)表至今已有41年,發(fā)生的相關(guān)故事太多。1984年底,岳陽市文藝界開年會,晚上搞聯(lián)歡,有人出了一副對聯(lián),上聯(lián)是:“那山那人那狗”,要求下聯(lián)對岳陽的三位作家,于是有人立馬對出:“彭東彭見彭舅”。平江稱呼他人,習(xí)慣叫前面兩個(gè)字,下聯(lián)一對上,哄堂大笑,無疑是搞笑我二舅,讓狗對上他,于是,就有人跳起來說:“歡迎對上了那狗的作家講幾句話。”
二舅便站了出來,他說:“我十分高興大家將我對狗,我作為岳陽市文聯(lián)主席,愿意為作家、藝術(shù)家效犬馬之勞。”
于是,滿堂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這便是我家二舅的牛皮,人們本來想搞點(diǎn)惡作劇,拿他開玩笑,誰知他卻擺出了一副人民公仆的樣子。
2003年我回平江老家掛職擔(dān)任縣委副書記,分管宣傳和旅游方面的工作,我引進(jìn)了一位外地老板,在連云山的峽谷里開啟了第一個(gè)漂流項(xiàng)目,名曰:連云山峽谷漂流。
老板聰明,借助我大哥的作品名,做成廣告“那山那水那尖叫”,一時(shí)間此句廣為傳播,家喻戶曉,于是,這個(gè)溪谷的漂流,很快火爆起來,一到夏季,那山里,那水中,總是充滿了快樂的尖叫。
2015年,我回到老家的村莊上,將一棟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間的祖屋,加固維修,命名為“坪上書院”,又招商引資在這老屋的后院建起了民宿,接待了不少到平江旅游和漂流的游客。
我們將《那山那人那狗》這部電影,定格為坪上村的文化地標(biāo),于是,請了縣上電影放映隊(duì)到這里來放映。放映前,我們會向觀眾推介這部獲過中國電影最高獎“第十九屆金雞獎最佳故事片獎”的高層次影片,同時(shí)介紹這部電影是根據(jù)我們村里出生的彭見明寫的小說改編的。這個(gè)電影里的老鄉(xiāng)郵員,就是根據(jù)我祖父的美徳來塑造的。
開始的播放,很受一些村民歡迎,老一輩的鄉(xiāng)親評價(jià)說:“電影里的那個(gè)好人,還真像你們的祖父。”
但是,如此的文藝片,很難滿足來自基層的鄉(xiāng)親和游客的欣賞需求,很少有堅(jiān)持看到底的。這部能夠在日本國創(chuàng)下十億日元票房的影片,要被當(dāng)下國人的審美情趣接受,還有待時(shí)光。
責(zé)任編輯:易清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