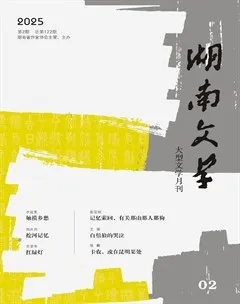蜜 獾
蔡根把剝皮刀緊貼著胸口,用右手吃力壓住時,就聽喉嚨里“嗖”一聲,有團氣流離開身體,鉆過護欄,拉長,變成響尾蛇貼著水泥路上的白虛線,游走,瞬間,又一躍而起咬住公交車的眼睛。下午的陽光像半截粗大的肥腸翻滾過街道。
為什么不早點開口問下朱爺呢?順山集離縣城不遠,三朵云的距離,騎上電瓶車,也就是一支煙的工夫。關于兒子的下落,沒有一個人知道。村上人只關注熊孩子殺人。他越來越討厭聽他們講的故事——傳說中的剝皮刀順著自己的骨頭剔著肉。
從縣醫院檢查身體后,回家的路上,他看到天上云彩像倒立的棉花田,飛揚的柳樹枝把奔跑的火車捆扎起來。道路像子宮在收縮。一群羊馱著小村的天空,使得它們不會穿過云彩掉到鐵軌上。
剝皮刀有了羊膻味的體溫,舔著彎彎上翹的刀尖,蔡根決定和朱爺好好談一次,身體不能再等了,回到順山集就去。
順山集人說,蔡根把錢全花在女人身上了。
在順山集,蔡根的父親是兩腳踩不出悶屁的老實人。蔡根膽子更小,連一條蚯蚓都能把他嚇暈,村上有個姓朱的三歲小孩都敢爬到他頭上屙屎。他見人就賠笑,仿佛有人在他臉上裝上一個隱形識別開關,一碰面,遙控就會自動打開。父親到死也沒有能力將蔡根臉上的開關扯掉。
摘去蔡根臉上開關的人是熊孩子,自從砍人事件發生后,蔡根見到姓朱的就很少賠著笑臉了。
順山集人說那些女人像各種燒烤:有的切成片,有的串成串;有的涂上甜汁,有的抹上麻油;有的松軟,有的香脆。口味各異。找蔡根的女人,都是帶拖油瓶的。她們主動找來,說什么天上的云遲早會被風吹散,她們想請蔡根用手里的羊繩拴牢孩子的腳。女人都夸蔡根會疼人,舍得將賣羊錢花得連一根羊毛都不剩,可不懂事的孩子都說蔡根身上的羊膻味像屁眼塞進開塞露,聞到后就想蹲下來屙屎。更讓她們莫名不安的是蔡根把羊群趕進院子,就鬼魂附體。他捏著刀尖刷牙,用羊毛洗臉,拿襪子擦碗,甚至把一個粉紅的內褲套在頭上。怎么說呢,凡是進過蔡根院子的女人,不管高矮胖瘦,都說他是怪人,連住哪間房子都有忌諱。
他家三間主房,東西各兩間偏房,前屋是門樓——順山集人管那種院子前面墻頭建個屋頂蓋、后背沒有磚墻的房子叫門樓。
一個瘦似張雞(兩腿纖細的水鳥)的女人說,睡覺可以去東屋,也可以在西屋,甚至躺在門樓下,但就是不讓她進堂屋。半夜,堂屋里還傳來瘆人的低吼和火車軋鐵軌的震顫聲。
一個身段胖如石碾(又更像水缸)的女人說,傍晚,羊群一進院子,蔡根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開堂屋門上那把足足有三斤重的鐵鎖,像個鬼,閃進房間里。她曾偷偷透過門縫,隱約看到蔡根貼著冰柜在吻一個人。
一個身高差十厘米(可能是十五厘米)就到兩米的女人傳得更邪,說蔡根會把他恨的人的靈魂收回來,關到堂屋里,接受他的懲罰。
一個矮如一頭母羊(差不多羊抬起頭的高度)的女人也證實,她親眼見到蔡根把滴著紅酒的內褲套在一個男人的頭上,然后用一把尖刀在剝那個人的皮……
對于女人們口里的各種傳說,順山集人聽后只是搖頭一笑,知道她們是在為離開蔡根找一個讓人同情的借口。
看著駛來的火車張開嘴將女人和孩子一口吞掉,蔡根每次都會轉過身摸著臊羊堅硬的彎角說:“又走了。”
當有女人帶著孩子找來,他還是會晃著猩猩般的長手臂,屁顛屁顛地把女人帶到羊群里。
村里也有人勸蔡根:多攢點錢,將來等兒子回來,好給他建三間新房,安個家。
蔡根答非所問地說:“通火車真好!”說這話時他把眼睛移向村南,看到東西延伸的鐵路像一條死蛇躺在莊子門前,天邊裂開一道縫,似手術刀在皮膚上割出來的長長刀口。
年紀大的人都說順山集是塊“椅子地”。村莊東西長,南邊低,門前一個大洼地,北邊高,背靠兩座黃土山。中間方方正正,遠遠望去就是一把太師椅,四平八穩擺在火車道北側。
白天,火車只來一趟,總會停在順山集人說的“椅子背”上。小站名叫梅鎮車站。在順山集人眼里,那奔跑的火車是通往順山集的。他們知道東邊是海城,西邊是山城,火車頭天下午兩點從西向東開過去,當天夜里又會準時由東向西開過來。
在蔡根眼中,梅鎮車站似嬌艷的小媳婦,順山集就像一個黃土埋到脖子的老太婆。也許真的是因為居住在椅子地,順山集走出了很多大學生。看著奔跑的火車,蔡根喜歡拍著雙手唱:青龍、青龍,搖搖頭,先蓋瓦屋,后蓋樓;青龍、青龍,擺擺尾,家家走出狀元郎……唱著唱著,淚就像兩條被刀斬斷的蚯蚓,在臉腮上滾動。
一群羊,猶如一把大白兔奶糖撒落在椅子角。
羊群是蔡根家的。
以前,蔡根也干農活。村里人說,他老婆的魂被銀匠砸出的亮光吸引去了。而女人說,順山集的天空套著個圓玻璃,罩得她喘不過氣來,再不離開,她會像朱家孩子酒瓶里裝的蝴蝶一樣,窒息死掉。蔡根用手掌斬斷一束刺槐花,他把白花兒織成圍巾拴在兒子細細的脖子上。后來,熊孩子用刀將天砍出了個窟窿,他就懶得去過問農田了。
地里的草像一群瘋子,在摟抱、廝纏著。
蔡根說,兒子喜歡趴在深深的青草里。村上人不敢接話,他們擔心蔡根想孩子,會瘋掉。順山集人沒有在草叢里發現人,卻看到瘋長的青草中露出兩只羊角。
兩個春天過去,沒有人影的椅子地跑出來一群羊。蔡根放著羊,把云朵一朵朵摘下來,鋪到地上。云彩里不時會冒出紅的胳膊、綠的腦袋、黃的大腿,黑的屁股……村上人說,妖精在挑選白羊吃哩。
蔡根把走進羊群的孩子摟在懷里親個夠。看著騎在臊羊背上的小孩賴著不下來,順山集人就夸,蔡根真會討女人歡心。女人們說,蔡根是真心喜歡孩子。
擠在羊群里的內褲,沒有人親眼見過什么顏色。正因為說不清楚,羊群中的女人在順山集人的嘴里變得五彩繽紛起來。朱爺說有個女人真瘋了,在羊群里脫光衣服洗澡,像倒立的一只母羊。蔡根嚇得把自己反鎖在院子里,一個下午不敢出來。
男人們不相信朱爺的話——那只公羊會用舌頭給女人擦洗身子。女人們說,羊毛遲早會被那些野孩子拔光的。
收麥,別人在田里干農活,蔡根就坐在村口的刺槐樹底下,學織毛衣。有人問他,大熱天打毛衣干嗎?他頭也不抬地回答,春天很短的,一脫單衣服就是夏天了,過完夏天,一眨眼就到秋天,秋天眼一閉冬天來了,冬天不下雪,也冷的,你冷,他冷,俺也冷,剝皮后的羊更冷……他的話像一團長毛線,大家急著趕去收麥子,沒有人愿意聽他把話說完。
有細心的人發現,蔡根把紅毛衣編織完,就拿著剝皮刀,一刀一刀割旁邊那個僵硬坐著的草人,碎麥秸散落在毛衣上,像火燒云,更似點點鮮紅的血。蔡根說,他在剝一個人的皮,一個讓兒子詛咒的人。他剝累了,就抬起頭來看天,云朵一會兒飄浮成一只憨態可掬的羊兒,一時又舒展成一個袒胸露乳的女人。在羊群和女人的注視中,一條空蕩蕩的紅胳膊,變魔術般冒出一只手來。
一個草人割完,樹上的葉子就開始飄落了。人們發現蔡根手里的剝皮刀在陽光下冒著寒冷的血光,他又開始用麥秸不停地編東西。他編得很慢,兩天才豎起一只耳朵,三天才伸出半個腳丫。
有人好奇地問:“是人嗎?”
蔡根停下手中的剝皮刀,半天才慢吞吞地吐出兩個字:“像嗎?”然后又專心細致地挑選麥秸了。
看到麥草編成的眼睛瞪著鐵路,大家又會想起讓人害怕的傳說來。
蔡根望著奔跑的火車,把刀插在一個形似寸頭的毛線球上。一節、兩節、三節、四節、五節、六節、七節、八節……
一個秋天,蔡根都在用麥秸編著一個長長的怪物,高昂的頭比呼嘯而過的火車威武多了。順山集人從沒有見過如此怪異的家伙,形如蜜獾的腦袋,卻長出人的手腳。
一看到火車開過來,蔡根就會放下手中的麥秸,伸開四肢仰面躺在麥草上,不,是躺在一節車廂的車頂上。金黃色的火車,迎著天上的羊群飛去。那是河還是湖呢?肯定是一片水,水里全是蛋糕,奶油上爬滿了小白羊。兒子把火車停下來,拎著一個藍桶向他招手。他從火車頂滾落在水面上,水是乳白色的,像乳房般柔軟。他站在上面,并不下沉,如同走在一塊剛烙好的甜餅上。兒子拉起他的手,在水面上彈跳。他一跳,一只母羊就“咩咩咩”地輕聲叫喚著,跑到他們身邊。兒子把藍桶放在母羊的乳房下面,不停用手擠著粉紅的乳頭,乳汁射進桶中,傳來悅耳的聲響。等一桶羊奶擠滿,兒子雙手捧著藍桶遞到他嘴邊,一股奶香撲鼻而來,他的眼睛也進了奶水,順著桶邊滴成一串珍珠。他啟動兩片厚厚的嘴唇,吮吸起來,好香的奶呀。他用嘴咬住桶邊,不松開。幸福時光太短,兒子不見了,眼前突然蹦出一只怪物,怪物叼起藍桶縱身躍過羊群,在羊叫聲中,他看到熊孩子披著銀披風,飛遠了。有羊奶灑向羊群,他閉上眼睛抓住母羊下垂的乳頭,緩緩降落在鐵道旁。
咩,咩咩,聲音溫柔得像棉花糖,他不用睜開眼睛看,也知道是母羊飽滿的乳房,他伸開手腳,以懷抱大樹的姿勢,躺著。
他面向云朵,閉著眼睛,一直躺著。
在他眼里,呼嘯駛過的列車不是熊孩子坐的火車,兒子的火車可以飛。奔跑的列車是朱爺家的(鋪設順山集段鐵路時,忙壞了朱爺,他指揮挖土機把椅子地挖出好多個坑,土全用來墊路基了。順山集人暗地里說,那些坑在別人看來是土,可在朱爺眼里就是錢匣子,鬼知道里面裝了多少錢)。
朱爺說飛馳的火車是順山集年輕人的。他最煩朱爺說這句話。火車是屬于孩子們的?不如說,火車是專為紅酒開通的。村里人都說,一鋪鐵路,紅酒就逃離順山集,去香格里拉了。朱爺卻說兒子坐的是飛機。這就如同朱爺喜歡喝白酒,卻叫兒子“紅酒”一樣,讓蔡根想笑。
當年,自己給兒子剪平頭是有原因的。村里人說他們祖輩不該選擇在順山集落戶的。順山集姓朱的人多。豬吃菜。別說住一戶姓蔡的,就是再來幾戶,也不夠一窩豬吃的。他心里不信邪,可豬將菜吃了,連根都不留下。豬喜歡吃菜,什么動物能吃豬呢?能殺死豬的動物,在平原上基本滅絕了。他很心痛,別人家孩子都坐上火車離開了順山集,而熊孩子連看一眼都不行。跑過順山集的火車,他一遍遍數過,共十七節。這個定格在自家院子里的數字,他永遠不會忘記。他用麥草編數著:一節、兩節、三節、四節、五節、六節、七節、八節、九節、十節……它是兒子的。除了他,誰都不可以觸摸,連朱爺也不能。
朱爺在順山集干的事,全鎮人看在眼里,沒有人敢說。大家心里清楚,說不定哪天攤上事情,還要求著朱爺哩。
細想,也不對,他連死都不怕了,怎么會懼朱爺的臉色喲。再說,現在的朱爺坐在輪椅上,一眼看去,就像他編的一個草人。
摸著貼在胸口的剝皮刀,他頓時覺得渾身的血管像加了半碗開水,上翹彎曲的刀尖,有了溫度。
他又看到傳說中的那座城。
坐上輪椅后,朱爺開始想紅酒了。紅酒不止一次夸香格里拉天空的云朵:真白,軟得如曬干的棉花。可蔡根說,再白的云朵也沒有羊群好看。這話,朱爺信。他喜歡看蔡根放羊,不過不太樂意瞧那怪怪的草人,總感覺它像一個人。當蔡根把尖刀握在怪物巨大的手掌里時,他會悄悄地轉過輪椅,看著不遠處的羊群。他知道自己離不開它們了,看著羊,他的耳邊會再次響起紅酒說的白云,香格里拉的白云,雪花般白。
蔡根用手輕輕一揮手里的尖刀,羊群就像移動的云朵,聚集在朱爺身旁。蔡根舉起長長的左手臂,遠方的火車,像是他一把拉出來似的,飛跑過來。朱爺的眼前又閃過那把閃亮的刀尖,他臉上異常平靜地問:“去哪里?”
“香格里拉。”蔡根張開厚厚的嘴唇,四個字就像飛吐出來的四塊葡萄皮。
“香格里拉?”朱爺忍不住好奇地重復。
“你不是天天想紅酒嗎?”蔡根的眼里瞬間亮了起來,左眼上那顆黃豆大的黑痣,隨時像要滾下來。
“太遠。俺老了。”朱爺輕嘆了一口氣。
“火車跑得快。”蔡根又似吐出五塊葡萄皮,黑茄子般的臉上瞬間裂開六七道皺紋。
朱爺沒有回答。他抬頭望了眼村東,這是一個早晨,樹梢上的太陽如油鍋中的雞蛋黃,散發出誘人的香味。他將目光移向南方,火車已跑得無影了。鐵道像條黑蛇東西方向臥著,他確定,太陽是從東方升起的。他腿好時,曾不止一次走在順山集炫耀:紅酒去香格里拉開了一家酒吧。
沒想到,蔡根真還惦記著紅酒。
朱爺不由罵了一句:“日他奶奶的。”他罵的是自己的腿。他得了腦梗,雖然搶回一條命,卻不能站著行走了。他坐在輪椅上,看著火車從東向西或是由西朝東奔馳,一顆心,像是氣球被針扎了一個細細的小孔,慢慢漏著氣。他乘過多次火車,可眼前奔跑在家門口的火車卻沒有坐過。
“以前熊孩子就喜歡在香格里拉喝著紅酒。”蔡根說這話時,左眼上那顆黑痣又向上滾動一下,眼睛里有了亮光。朱爺還是不敢迎接那目光,他不明白早晨的太陽怎么會掛在西邊的樹梢上呢?蔡根請他坐火車去山城,說是去香格里拉看紅酒。他知道,自從發生了那件事情,蔡根也愛談紅酒了。村里人說,蔡根沒有離開過順山集,卻知道香格里拉,還說香格里拉是離天堂最近的地方。在他們眼里,他像了解自己的羊群那般熟悉香格里拉。談到香格里拉,說那是熊孩子的家。他知道蔡根嘴里的香格里拉不是紅酒說的香格里拉。
朱爺心想,吹散的云朵,遲早還會聚攏來的。不能走,他再也站不起來了,他活得很累。黑暗中,仿佛會有野獸隨時沖出來,把他撕成碎片。特別是當紅酒去香格里拉后,他更害怕寂靜的夜晚。他一閉上眼,就能看到那染著一頭白發的怪物從火車里跳出來,爬上火車頂,沖著順山集咆哮。他舉起菜刀,怪物突然長出翅膀,飛了。他的眼珠猛地彈了出來,跟著它,穿過沙漠森林,飛越雪山,嗅著紅酒的氣息,找到了香格里拉。怪物一定是想吃紅酒的。盡管他不止一次告訴自己,一切都是傳說,可自己的嘴里散發出來的還是葡萄酒的味道。
答應陪蔡根坐火車去香格里拉后,朱爺整個人像一朵云,輕得可以飄起來。他不知道為什么會做出這么一個莫名其妙的決定,難道就因為蔡根說的香格里拉?可有人說,香格里拉已不是當年的香格里拉了,那家舞廳早關門了。
看著坐在輪椅上的朱爺,蔡根抬起右手按著胸口,剝皮刀還在,只是軟得像根肋條。
蔡根賣了羊群,連公臊羊也不要了。
去坐火車的頭一天,蔡根特意到鎮上舒服地泡了澡,擦身、敲背、打鹽、抹奶,來了個遍,就連那把剝皮刀,他也一樣洗干凈,彎翹的刀尖上,蹲著兩只睜圓的眼睛。刀口舔著他的胸毛,他的手不再顫抖。他更不恐懼,連體內的惡瘤都不懼,還會害怕什么呢?
當他出現在朱爺面前時,撲鼻的奶香,外套灰夾克,內穿白襯衫,黑皮鞋上挺立的兩條褲筒,像倒掛著的兩桿黑鋼筆。
朱爺發現,洗去羊膻味,蔡根花白的頭發有了光亮。他又想到熊孩子了。
“怪不得女人喜歡上門找你呢。”朱爺的目光低得只能看見自己的黑布鞋尖。
“你相信他們說的嗎?”蔡根問這話時,茄子臉上的皺紋在深秋的陽光下又裂開來。
“他們就喜歡你編的故事。”朱爺答非所問。
“傳說?多著哩。”蔡根說。
“你真的說過那些話?”朱爺口氣明顯弱了許多。
蔡根第一次推著輪椅坐火車。他不敢相信,當年威風八面的朱爺,坐在輪椅上比武大郎還要矮。想到自己像帶著孩子一樣推著朱爺去香格里拉,蔡根擦了把黝黑的臉頰,心像是被麥草輕輕劃了一下。蔡根啟動厚厚的嘴唇說:“他們也愛談你過去哩。”
火車上旅客很少。看著坐在不遠處的一個婦女,蔡根想到那些高矮胖瘦的女人,她們如一朵朵泛起的水花,很快沉到水底了。他只記得在她們身上賣掉一百二十五只羊。賣羊時他會難過的。是它們,女人和孩子才愿意陪他的,能帶著朱爺來坐火車,也應該感謝羊群,讓他牽拉過那么多可愛孩子的小手。
偷偷望著朱爺僵硬的左腿,蔡根心想,難道夢是真的?自從賣掉羊后,他常會出現幻覺:一列長長的綠色火車,帶著他飛向潔白的云朵時,車廂里忽然甩出一把明亮的剝皮刀,瘋狂刺向羊群。瞬間,白羊身上綻出血紅的桃花,羊群在車廂里沖跑。他嗅到了血腥的味道。剝皮刀飛得比羊群快多了。他眼睜睜看著鋒利的刀口劃破羊兒溫暖柔軟的肚皮,它們像一個個炸飛的氣球,在一節節火車廂里“砰砰砰……”接二連三地消失了。剝皮刀瞪著血紅的大眼,刀尖吐著血紅的濃濃膻味,順著狹長的火車廂,突然改變飛行的方向……他絕望地一把抓住朱爺的胳膊,發現自己正坐在去山城的火車上。
摸著冰涼的輪椅,蔡根想到了趴在水坑里的女人,還有香格里拉。他一點也不害怕體內的腫瘤,是它給了他找朱爺的勇氣。當他看到朱爺像截木頭插在輪椅上,剝皮刀慢慢就被紅毛線纏在村口的刺槐樹上了。他莫名地喜歡站在朱爺面前的感覺。他突然希望朱爺就那么杵在輪椅里,任由黑夜慢慢將朱爺的頭還有那截僵硬的身子一點一點吃掉。
面對夕陽,兩人似乎很疲倦,這節車廂如同一壟敗園的西瓜地,稀稀拉拉的幾個腦袋像熟透了的西瓜賴著吊在瓜藤上。看著窗外,黃昏像條饑餓的狼兇殘地啃食著鐵道兩旁的村莊和田地。蔡根把眼睛轉向朱爺:“想聽熊孩子的故事嗎?”
“太遠了。”朱爺眼睛并沒有睜開。
“熊孩子沒有看到家門前的火車。”蔡根吐出這句話時,臉上表情顯得異常平靜,就像嵌在車窗上的一塊玻璃。
朱爺的朝排餅(用炭火烤的長方形火爐燒餅)臉上蕩起了波紋:“噢!”
“出事那年他就死了。”這句話,像是從蔡根的嘴里隨意漏出來的。
在朱爺眼中,順山集人從內心里害怕熊孩子。熊孩子不怕死,剃個寸頭,染成白發,整天披著一塊銀披風,走在村里特別扎人眼。孩子們私下里都喊熊孩子“平頭哥”。說他殺人,順山集人不會懷疑的。
蔡根記得那天是清明節。他去給父親燒紙,不小心踩到朱爺家幾棵麥子。朱爺女人開口就罵,老婆跟別人跑了,活該獨蛋子(獨蛋子是順山集人對男子惡毒的詛咒),一直從墳地罵回順山集。
蔡根裝孬,不理她,這反而刺激了朱爺女人。她擋在路口。他推她一下,朱爺女人一屁股坐在地上罵。碰巧朱爺回村,看到大哭的女人,沖上來就是一拳。頓時,蔡根鼻子里的血就像擰滑絲的水龍頭里的水,淌不停。
順山集人知道朱爺是倚仗兄弟多,欺負蔡根。盡管蔡根還有兒子,可畢竟還是一個乳臭未干的娃。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讓他們再也不敢小瞧熊孩子了。
熊孩子系著銀披風,拎把明亮的砍刀,守在村頭。朱爺沒當回事。他剛到村口,一團白,狂奔而來。朱爺嚇傻了。陽光下,雪亮的長砍刀閃著寒光,他猛然反應過來,轉身就跑,幸好逃得快,但刀尖還是劃破了黑毛衣,背上有血流了出來。
順山集人以為朱爺會教訓熊孩子,沒想到朱爺卻上門給蔡根道歉。
熊孩子砍了朱爺之后,還選個周日,跑去山城第一中學,叫來紅酒。熊孩子故意讓風吹起銀披風,抽出長砍刀,紅酒嚇得尿褲子了。
看著兒子脖頸上粗紅的刀痕,再一想到熊孩子瘋砍過來那一刀,朱爺害怕。
接二連三的事情還沒結束,朱爺家不是豬被人家藥死了,就是門前草垛讓人點火燒光了,女人還在院里看到裝滿鞭炮火藥的啤酒瓶。那團白,就像一個幽靈,讓朱爺懸著的心不能放下。朱爺女人上門討好蔡根,求他讓兒子不要鬧下去了。
蔡根嘴上說早忘了,內心卻罵:賤女人。
有一天,熊孩子離開順山集,說是去山城,還說香格里拉才是他的家,他不想再回順山集了。再后來,就聽說他在那家叫香格里拉的歌舞廳和幾個小混混用亂刀砍死了一個老痞子。別人都被公安抓了,送進了牢房。唯有熊孩子扒火車跑了。
當年,熊孩子揮向朱爺那一刀,順山集人談起來還心有余悸。他們說,熊孩子不在外面砍死人,在家也會惹出人命來的。
朱爺不喜歡聽到這句話,可一想到那把刀,就心虛得發慌。
一路上,蔡根都在說著兒子。他告訴朱爺,不管熊孩子揮刀砍人,還是別人用刀捅死兒子,他都不會怪熊孩子。
那年冬至傍晚,熊孩子從山城回村,在院子里被人一刀戮了。蔡根放羊回家,推門走到院中,發現熊孩子趴在葡萄樹下,銀披風上的血窟窿猶如一個咧開嘴的熟石榴。熊孩子過完春節才十七歲呀。
蔡根說:“村里人都笑話俺,連一只雞也不敢宰,更不敢拿刀去殺人。”
“他們……有點……過分了。”朱爺結巴得厲害。
“以為熊孩子在香格里拉結下仇,小痞子跟蹤到家殺死他的,”蔡根看了眼朱爺像死尸般僵硬的左手說,“懷疑有人教唆兒子去砍人。”
“證據呢?”坐在輪椅上的朱爺腦袋一晃,像是被人用針扎了下。
“沒有,只是一種感覺。”
“你為什么……到處說他……在香格里拉殺人……”
“香格里拉有紅酒,熊孩子喜歡那里,他說從沒有喝過那種甜味的酒。”蔡根的聲音有點哽咽,眼睛在燈光下忽然明亮起來,像映在玻璃上的兩粒炭火。
“順山集一通火車,紅酒就去香格里拉了。”
“原來小孩子殺人可以不償命的。”
“長年沒有紅酒,身子又僵硬……不如死哩。”
“放心吧,俺身上沒帶刀。”
“紅酒眼里只有香格里拉。”
兩個人對話,更像是自言自語。
“俺喜歡熊孩子冰冷的額頭,做夢都和他坐火車去香格里拉。醫生說,晚了,再鋒利的手術刀也割不盡胃里多長出來的硬疙瘩。不要笑話,俺以前挺怕死的。”蔡根說這話時,嘴角流露一絲不易察覺的苦笑,“不過,孩子們是真心喜歡香格里拉的。”
看著玻璃里閃著余火的眼睛,朱爺說:“她走了,村子也快拆了……你還恨她吧?”
蔡根當然知道朱爺女人是怎么死的。她從娘家走回來,一頭栽倒在椅子地的一個小洼塘里,那是修鐵路時朱爺挖的坑。過了大暑,朱爺去接女人,才知道她早回家了。朱爺見到女人時,就是一堆腐爛的臭肉,紫色連衣裙被鼓脹的肚子撐破了,那雙平底黑皮鞋鉆滿了黃泥,右鞋窩里還爬出來一條小青蛇。女人趴在地上的姿勢,就像是一只撅著腚低頭喝水的母羊。
女人的死,朱爺心里有愧,她血壓高,一個人去的娘家。沒想到回來時,她會抄近路走椅子地。天熱,羊會去那個水坑喝水的,怎么就沒發現人呢?
當蔡根找來時,他又想到去年夏天。女人臨終的慘樣仿佛烙印在他腦海里,抹不去。他從辦案警察嘴里知道,天熱,蔡根確實待在村頭刺槐樹樹下用麥秸編織著一個人。連羊群都沒有離開過。可夢里,他看到有一只公羊叼著剝皮刀,站在水坑旁盯著倒立在水中的母羊笑呢。是自己想得太多了。許多人傳言,刺槐樹上的尖刀,晃得人眼疼。可事實呢?也許蔡根就是想去熊孩子曾經喜歡的香格里拉喝一杯紅酒。
“聽說香格里拉的白云比棉花還白,熊孩子喜歡那里,俺正好過去陪他放羊。還有,去告訴紅酒,別再害怕村里人的傳說了,也該回家看看你了。生病后,俺忽然就想明白了,火車經過村子時,除了風,什么也沒有留下。俺連剝皮刀也丟了。”蔡根說完這句話,整個人一下子變得輕松起來。
朱爺終于相信那個胖如石碾的女人說的話是真的了。蔡根親吻的真是一個人。每天晚上放羊回家,把羊群趕進圈里,蔡根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開家中的三把鎖——主屋門上的鐵鎖,里屋門內的暗鎖,纏繞在冰柜上的銅鎖……
他愧疚地想啟動輪椅上的開關,手卻麻木得有點不聽使喚了。
火車緩慢停下。山城到了。
冷風撲面。
蔡根迎風打個噴嚏,用力提起輪椅:“香格里拉應該還在的。”
“熊孩子一直陪著你?”朱爺肥碩的頭顱僵硬地晃動了一下。
盡管蔡根早將藏在身上的剝皮刀插在村頭那棵刺槐樹的脖子上,可他還是習慣地抬起右手按了下胸口。
迎面有火車駛來。
輪椅像是中了魔法,斜著沖了過去,燈光里,朱爺坦然地閉上雙眼,嘴角還掛著一絲微笑……
責任編輯: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