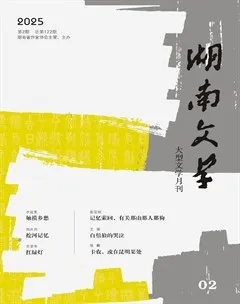觀念之于小說
〇〇后小說家曾子恒的兩篇小說《蟲魚鳥獸》《再見黃泉》被沈念兄推到我面前。我渴望了解青年寫作者,渴望知道他們在想什么,會怎么寫,便不推辭讀了起來。老實說,曾子恒的兩篇小說辨析度頗高,不是那種溫吞水、面目模糊的類型。小說讓我想到很多,感觸最深的便是觀念性之于小說這一話題,往深里說其實是小說中觀念性與技藝性的辯證。
常見很多青年作家,小說寫得中規中矩,甚至可說細膩綿密,若要論起來卻頗覺為難,缺少點屬于思和觀念的東西。技藝走在觀念前面,如果能走得特別遠,技藝本身也足以成為觀念。問題是,往往看似密密匝匝的技藝,也多在前人的腳印里。另一種情況則是,小說有新鮮的想法,有觀念和闡釋空間,憾于敘事的針腳和邏輯過于粗疏,也不能讓人信服。好的小說,當然是技藝和觀念的結合,青年寫作者,當有此自覺。不過,對于青年寫作者,我常常更看重其觀念。是否能異想天開,是否有奇思妙想,決定了小說的可能性。依我之見,對于青年作家,可能性高于完成度。可能性代表著思想的活力和小說新維度的開啟,完成度則可能只是依葫蘆畫瓢。
某種意義上說,曾子恒的《蟲魚鳥獸》《再見黃泉》便是觀念走在技藝前面,但又因其拓展出的可能令人期待。《蟲魚鳥獸》中的巫老師和栗教授,同是將理性視為律令的科學狂人。他們奉進化律為圭臬,誓在創造出完全符合“理性”的完美的人。當然,現實比他們的想象更復雜,栗教授的造物“思壯”一出生便一身肌肉、一副利齒,見人就咬,甚至強暴了栗教授的妻女。巫老師是繼栗教授之后的又一“瘋子”,他帶著學生大海去尋找傳說中的薩姑姑,希望她能幫他們造出理想的新人——心慧。心慧當真被孵化出來,卻與巫老師的初衷不同,對人類的情感和理性擁有自身的理解,并最終與巫老師決裂。《蟲魚鳥獸》的觀念性很明顯,它反對并批判了科學狂想對人類過于理性、刻板的想象。這種批判具有相當的現實性,科技作為一種現代社會以來最重要的塑造力量,正野心勃勃地改造著世界,并把人類帶向不知所終的境地。譬如正來勢洶洶的AI,很多人為其歡呼,有人則將其視為人類面臨的最大挑戰。相比之下,《再見黃泉》則由一個更具現實性的情感議題升華出懺悔的主題。小說情節的玄幻并不足為奇,有趣的倒是這個設定:一個將死者若不得其“冤家”的懺悔,則不得重返世間。這個設定有別于傳統佛學的善惡輪回,卻特別強化了懺悔的必要性。整篇《再見黃泉》一言以蔽之,即懺悔之必要!“我”一再為自己的行為開脫,懺悔則撕下了這層矯飾的面紗,讓人直面內心的“罪”。一個青年寫作者有此意識,是令人驚奇的!
不過,我也要說,小說的觀念性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這種觀念如何獲得讀者的認可。小說與其說是一種“真實”的藝術,不如說是一種讓人信以為真的藝術。在很長時間里,受機械反映論的影響,很多人誤以為小說可以像鏡子一樣反映現實,可是現實并不是一個乖孩子,老實地待在那里,等著小說去認領。很多作家都表達過類似的意思——“小說家的任務是創造一個世界,而不是復制現實”。帕慕克則表達得更有意思:“當我們做夢的時候,我們相信夢是真的,這就是小說的定義。”是的,小說是夢,但小說必須讓讀者像經歷夢境那樣的逼真。這種逼真性,很大程度上來自于細節。有情節而無細節,或者有想象無細節,都會使小說像一幀分辨率低下的模糊圖像。細節是小說構建真實感的關鍵,人們常說,上帝就藏在細節中。事實上,對于小說而言,世界也藏在細節中。好而豐富的細節,使小說如汁液飽滿、新鮮芬芳的果實。沒有或是缺少精彩的細節,小說便從鮮花退化為圖像花再退化為概念花。
藝術是一種偉大而逼真的幻覺,雖幻猶真。尼采說:“藝術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來的形而上活動。”但無論如何,藝術傳遞偉大信念的首要前提在于讀者因真(逼真)向善,如何以細節和分辨率讓小說的觀念展現出強大的說服力,這可能是寫作者伴隨一生的問題。
責任編輯: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