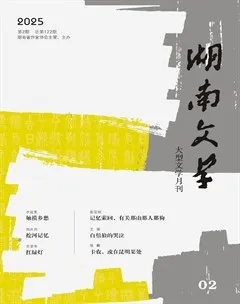不順的人生該如何嚴肅地表達
編者按:本輯評論脫胎于湖南省社科院“德雅文學工作坊”對一泓長篇小說《孑孓》的研討。《孑孓》是一部具有清晰的文體創(chuàng)新意識、內(nèi)傾書寫意識和隱喻建構意識的小說,具備多維解讀的條件。小輯也擬從文體、社會、人物等多個方面折射《孑孓》光彩,助力讀者理解與思考。羅山深度剖析了小說的文本創(chuàng)新與精神表達,以“討厭嚴肅”關聯(lián)時代精神狀況,精準解讀了小說在情緒驅動下的利弊,視角獨特新穎。鄧謙林從文學的城鄉(xiāng)傳統(tǒng)出發(fā),將小說置于城鄉(xiāng)寫作經(jīng)典脈絡中加以考察,深挖小說在呈現(xiàn)城鄉(xiāng)差異、后現(xiàn)代敘事、人物異化等方面的特點,凸顯了文化意義。陳雅琪沿著小鎮(zhèn)青年的城居蛻變軌跡,梳理了主人公“我”與鏡像決裂、尋找原鄉(xiāng)、學會生活、于現(xiàn)實困境中進行內(nèi)在性建構的幾個階段,進而順勢導出小說的內(nèi)在性之要義。
“我討厭人為的嚴肅,所以我時時刻刻渴望盡早回到紅花坡。紅花坡不需要嚴肅。”小說《孑孓——鎮(zhèn)上人城里生存文本》再一次展現(xiàn)了王朔那種“玩世不恭的深情”和語言狂歡的風格,但作者一泓創(chuàng)新了小說的書寫方式,用格言、日記、書信、論文、說明書、清單、菜譜、病例、檢討書、檔案、引言、詞條、宣言等文本穿插、拼貼在小說敘述里,甚至有的就直接成為小說敘述,使得這部長篇成為多文體復合的小說體。這些文本所具有的理性、冷峻意味或者說嚴肅性嵌合了小說主角“我”的個人奮斗的失敗和精神世界的虛無。
“討厭嚴肅”展現(xiàn)了千禧年后知識青年的心靈變化以及整個社會的精神狀態(tài),使得小說具有了心靈史的特質。作為閱讀量頗為龐雜的知識青年,敘述人“我”具有一定的思想素養(yǎng),如果有機會表達或者有合適的工作展現(xiàn)出來,“我”可能走向不同的人生。可現(xiàn)實是,“我”只能委身成為一名廣告業(yè)務員,后來辭職寫作。作家這種身份卻遭到連小學都沒有畢業(yè)的鄰居刀哥的鄙視。“我”擁有這種身份也只是為了有利于拉廣告。“我”無法展現(xiàn)自己的才思,只能隨波逐流,經(jīng)歷了失業(yè)、離婚等諸多不順。這種“生不逢時”的失落感,讓“我”很難將對世界的認識和感悟外化成為公共的文字,從而向內(nèi)變成一種獨自的絮語,呈現(xiàn)出精神內(nèi)耗后的語言狂歡。結合本世紀初“娛樂至上”的時代氛圍,恰巧“我”也在當時推崇娛樂風格的電視臺工作,小說的反嚴肅的語言風格倒是和其主人公“我”的失敗人生故事形成奇妙的對應,小說的形式和內(nèi)容高度統(tǒng)一,使得小說具有反映那段“娛樂時代”的典型性,“討厭嚴肅”的表達恰恰成就了小說成為一部嚴肅作品的可能。
在作者這一代人的青少年時代,有過類似經(jīng)歷的人或許也遺忘了,少男少女們喜歡在筆記本上抄寫名人名言、歌詞,囫圇吞棗地完成一部分知識和思想積累。這樣的閱讀和消遣方式,姑且稱之為“前段子”文化。因為,現(xiàn)在流行的正是一種“段子”文化。我們在手機上閱讀的更多的是短篇的段子文本,風行的脫口秀也可視為段子的語言表達——用短小精悍的段子在較短的時間內(nèi)傳達出作者想要表達的信息或觀點。“前段子”時期的那種段子在小說中比比皆是。首先是每一章的引言和最后的注釋引用了大量的文本片段,包括佛教典籍、社會學著作、文學理論、哲學典故、中外小說、民間舊俗,還有一些曲藝戲劇的文本歌詞、報紙新聞和詩歌等等。其次,作者大量閑言碎語的表述呈現(xiàn)出段子文本的形態(tài)。從小說最后標注的寫作過程可以看出,小說的寫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著多年段子文本的積累,有些神思妙想可能很早就寫出,只是后面才加入小說之中。故事的情節(jié)反而隱藏了起來,與段子式的文本之間呈現(xiàn)出一種割裂性。這種割裂也有些娛樂節(jié)目的氛圍,一種情緒表達欲望打斷了節(jié)目程序性,同樣地,也打斷了小說核心故事情節(jié)在閱讀上的流暢性。夾雜在文本中的段子或許可以更精練,更融合進敘事之中,不會讓讀者讀完整本小說記住的多是作者那種沉積多年的不吐不快的情緒。
正因為這樣,小說并不是用情節(jié)來推動的,而是情緒來推動的。作為帶有回憶色彩的小說,作者從一開始就帶有很強的情緒,類似于屈原的孤傲和獨醒,批判著社會上形形色色的虛偽和不公。情緒化的寫作似乎是私人化寫作的標配,類似于日本的私小說,取材于作者自身經(jīng)驗,毫無保留地暴露自我的內(nèi)心。從小說文本的非線性敘事安排來看,個人的經(jīng)歷讓作者在書寫過往的時候,不是想好好地通過經(jīng)歷來打動大家,而是在傾瀉這些經(jīng)歷帶給作者的愛恨情仇。故事情節(jié)也有意安排在相關的情緒表述之中,而且故事情節(jié)比較短小,也呈現(xiàn)出段子特點。文本的互文,恰恰反了過來,各種文本的引用是情緒的注釋,各種個人或他人的故事也成了情緒的注釋。強烈的情緒表達,讓小說具有強大的內(nèi)驅力,但是,作者情緒的單一和不節(jié)制,又讓小說缺少了應有的嚴肅性,讓作者諸多的思想和感悟成為一種炫技,流入“玩世不恭”的虛無之中,讀者難以體會到一泓對真我、真誠、真情的追求,正如同“我”在生活中難以被理解、被接納、被珍視,這是不是一種遺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