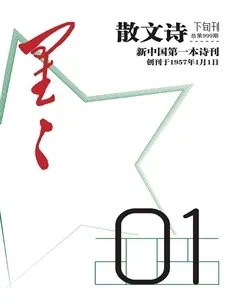洮州城(組章)
西大街
晨光下,高原小城逐漸醒來,環(huán)衛(wèi)工和學(xué)生的身影牽出一天的斑斕。
穿城而過的西大街是一條河流,打開小城古老與現(xiàn)代融會的畫卷。
江淮遺風(fēng)的古建筑和高樓大廈錯(cuò)落有致,西門十字路口,擺滿帶著露珠的蔬菜,香氣四溢;汽車的喇叭聲、小販的叫賣聲和廣場舞的音樂,此起彼伏,在生活的舞臺上,演繹著小城的生機(jī)與活力。
無數(shù)的小巷溪水般,攜著明亮的浪花,匯入河流。小巷的青石和水泥路,磨光歲月的棱角,千百年的滄桑與光芒靜臥于白墻黛瓦和磚雕門柱的光影里。花格木窗上的柔情與斑駁,像一股溫?zé)岬臍庀ⅲ咳雰?nèi)心。
在西大街,或仰望或趕路或駐足的人,都有不易察覺的念想。他們,是你,也是我,浪花般涌現(xiàn)于各個(gè)角落,泛著無數(shù)微光,驅(qū)散生活的迷茫。
直到夕陽灑落,夜幕低垂,車燈、路燈、霓虹燈……替他們繁星般閃耀映入河流,照亮一座城。
靜謐的夜色里,停止流動的街道上突然有風(fēng)穿過,像誰躡手躡腳地替我們拽了拽生活的被子。
高原之春
我所住的城郊,窗外是一片片田地,像時(shí)間留下的補(bǔ)丁,剛好遮住目光的空洞和心靈的空白。更遠(yuǎn)處是矮矮的雪山,起伏于永無止息的風(fēng)中,在城與郊的縫隙,野草占有一席之地。
我們是一簇簇異鄉(xiāng)的野草,在生活里游離。白天進(jìn)城,夜晚歸郊,循環(huán)往復(fù)。
當(dāng)山上的積雪消融,城郊向陽處,陽光溫?zé)帷L筋^的草是我們身體的一部分,它們,最先感知高原上的乍暖還寒,像一把生銹的鑰匙,需要一滴油的潤滑,打開被困于泥土的萬物生靈和被封于冰塊之下的清澈。
而春風(fēng),是一把行色匆匆的剪刀,無須時(shí)光的磨刀石,也能剪出滿坡的桃花、杏花、櫻花、梨花……剩下為數(shù)不多的冰塊,在陡峭的河岸像一個(gè)個(gè)濕潤的詞語,滴落水面,率先組成一行行春歸的身影。而清脆的波浪,在春風(fēng)中鳥鳴般一遍遍擦拭著倒映在水中的天空。
轉(zhuǎn)瞬之間,已是遍地青草,遍地花兒,遍地鳥鳴。
窗外的油菜金燦燦地盛開,而青稞和燕麥業(yè)已長大,等待出穗。我們像一個(gè)個(gè)用舊、遺棄的詞,繞過發(fā)白的時(shí)光,在高原城郊,重新被春雨洗刷一新。
洮州衛(wèi)城
高原如海,群山如浪,而洮州衛(wèi)城是海浪上的一艘帆船。
六百年的風(fēng)雨侵蝕,像一個(gè)古老的傳說,在洮州大地上生生不息;六百年的榮辱滄桑,像一條洶涌的洮河,在西部大地熠熠生輝。
宏偉的城墻,承載著歷史的厚重和歲月的痕跡;高大的城門內(nèi)外,呈現(xiàn)著古樸與繁華。
穿越迎薰門,巨大的褐色條形石塊上,斑駁的紋路和痕跡,似乎流動著戍邊將士的溫?zé)釟庀ⅰP凶哂诔菈χ希莾?nèi)櫛比鱗次的洮州民居,依然保留著完整的江淮遺風(fēng),裊裊炊煙縈繞著白墻黛瓦和雕花的木門木窗。而城外的山坡上,烽火墩像守望者,在風(fēng)中呵護(hù)著梯田和牛羊。城前是南門河不息的奔跑,城后是海眼碧波蕩漾的幽靜。
它們,構(gòu)成時(shí)間的流逝之憾,空間的交錯(cuò)之感,生命的堅(jiān)韌之力。
1936年8月,紅四方面軍在洮州衛(wèi)城休整,并建立了甘南歷史上第一個(gè)蘇維埃政權(quán),開啟了洮州人民的嶄新史篇。
每一次穿越衛(wèi)城,都是與歷史的邂逅。依山蜿蜒的城墻,需要你我用一生的時(shí)間去凝視,去攀登。而每一個(gè)眼神,滿含堅(jiān)毅,星火般點(diǎn)燃生活——
與山相依,與水相伴,與萬物相融。
山 歌
山的近處,是山;山的遠(yuǎn)處和更遠(yuǎn)處,還是山。
那么多的山,像我至愛的父老鄉(xiāng)親,互相攙扶著,冷了,就彼此依在一起;累了,就彼此靠在一起。
他們,在洮州大地血脈相連,像一條條溪水匯入洮河,匯入黃河,哺育萬物生靈。
每年六月,蓮花山就是歌的海洋,你方唱罷我登場,人們不分晝夜,男女老少,以山歌的方式抒懷,表達(dá)對時(shí)代、生活和人生的態(tài)度。
山的上面是山,山的下面還是山,再往下就是平川——
“上不起山巒就下不來平川,經(jīng)不了苦難就分不清香甜。”
時(shí)代的春風(fēng),吹遍高原。堅(jiān)定的目光中,一座座山說綠就綠了。
山坡牧羊,溪邊飲馬。清冽的溪水,蕩盡心靈的灰塵,一片草原上的花兒說開就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