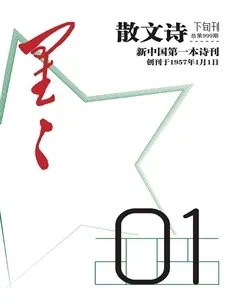圓明園(外一章)
2025-02-18 00:00:00雨歌
星星·散文詩 2025年1期
用上鐵器和烈火,傷害一個不說話的石頭,身體被肢解,四散各處,留下碎玉和瓦片的片刻世界。頂著烈火的燒灼,土地正在發燒,搬起這燒紅的石頭,砸在列強的頭顱,搏斗,廝殺,用盡所有的力氣和園林一起掙扎著。
站在雨果的雕像前,那張可以開口說話的嘴,替良知說出的話都刻在石頭上,那些不曾留下的話,躺不平的石頭都在替我們講出來,等待來來往往的人,還原真相。
在圓明園地鐵站,一雙棕色的翅膀緩緩停留在我身旁,棕色的臉龐,黑色的發辮,黑色的短衫,似那塊燒焦的圓木。
一路上,我都是被這如同灰燼的顏色籠罩著。
在白塔木雕園
車床上小如盤扣的木器,在木匠手心玩轉。
在木雕園,我們都是讓自然之木成為中規中矩且為物所用的人,讓心里的藍圖與拇指的指紋相吻合,井口枋、挑檐、斗拱緊緊相扣。床榻上的木枕,上房里的木桌、木椅,閨房里雕花的梳妝臺,連同四書五經,唐詩宋詞藏身的書柜都已經被精心地打磨好。
用木頭在三圍空間繡花,一刀一刨在毫厘之間精準打磨,任祥云在廊檐舞動,金魚越過了龍門,萬字符和如意環環相扣。
用上好的松木去修補歲月的裂痕,為敦煌莫高窟大佛閣補上挑檐,奔赴月牙泉來一場木器與黃沙,精雕的自然與荒漠的對峙,仿古建筑群在沙漠應運而生。
一棵樹與另一棵樹的默契,讓大與小的穿插勾連,收納了一塊空曠之間的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