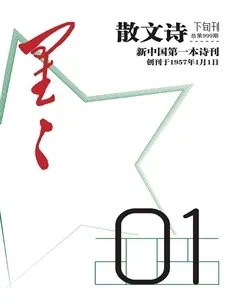理性氣勢及冷冽的戰栗(簡評)
張靜的《燈下走筆》(組章),我認為更傾向于詩的一面,詩人纖細的內心肌理和明潔的氣質躍然紙上,具有純詩的美感、銳利和跳躍。她詩歌題材多源于自然和對自然的輕輕打探和叩問,有強烈的自然主義特色。如《寧靜》的第一句便是:“我打破了寧靜。”隨之我們讀到的便是一個已被打破了的寧靜。誠然,這一切都是在詩人內心完成的,通過這首詩,詩人表達了一種“打破”與“黏合”的重塑的命名:“我守著一件叫寧靜的瓷器,卻失手打碎了它。我以為只要使用思想強有力的黏合劑,假以圓熟的技藝,它就能完好如初。”
相反,《六月》則是將“高燒”的六月,從躁動下安靜下來:“如果六月是一部言辭激烈的躁動之書,我就是動中求靜的那粒詞語,正以四兩撥千斤的力量,為命運泄火,敗毒,療瘡。”意味著什么呢?詩人面對自然,有一種“叛逆”情緒,但又是對準了自己,而不是自然。她對唯美世界的情愫,包含了批判與思考、焦慮與無奈,在自然與自我間深刻互視而產生復雜的詩性發現。
在《聲音》這首詩中,詩人所寫的“隔壁在拉琴”已然是一種對自己的無情穿刺,“在精神層面徹底擊垮我,摧毀我”,實際上,聲音所能產生的破壞力,主要生成于自身,外界的干擾通過內心的放大,讓自己產生困境,我想,這正是生活中很多人的內心寫照。而《塵埃》這首詩,通過幾個“如果我知道”更是把內心焦慮的火焰燒到了極致:“一陣最小的風,就能推翻我的過往,愛恨和悲歡。”再來看看《傷疤》這首詩,一塊早已痊愈但留下的疤痕,“是與我血肉相連的另一個我”,她內心的一部分仍然活在這道傷疤里。在此,“傷疤”只是個喻示,但確實又是生命里不可磨滅的東西:“我要用一生來修復這道傷口。”
《和解》讓生活有了喘息和寧靜,但這一和解,又是在自己與時光搏斗后無奈的選擇,甚至可以理解為一種“接受”,然而這又有什么呢?我們絕大多數人都是這樣的“失敗者”“落魄者”,如詩中寫道:“我已淪為光陰的囚徒。我把我交給了虛無。/除了疾病,我一無所有。除了疼痛,我兩手空空。”但這就是注定的人生之恨。這首詩既有對生命的浩嘆,也有最后的澄明即對真正自我的尋找:“我要失聯多年的我,在百感交集的語境中叩響門扉。”即對自我的接納與認識。與世界的和解,還不如說是自己與“另一個我”的和解。《白玉蘭》是“傷口一樣從身體里掏出絕望和芬芳”,以及《燈下走筆》中:“一張紙落空了。一顆心宣告破滅。夜晚只剩下疆域遼闊的失望,剩下這間墳墓一樣的孤島,剩下身體里一口枯井。”表明詩人內心始終有濃郁的壓迫、無望、蒼茫感,也可以理解為她對這個世界一再的憂郁冷凝,給讀者以理性氣勢,及凜冽的戰栗感。
張靜在表現手法上,借鑒現代象征主義,既有意象的有序鋪陳,又有自我心靈訴說,兩者的結合,似乎于完美。組章中的八章散文詩,相互獨立,又有氣場和情韻上的貫穿與相通;有具體生活細節的陳述,又有對生活和生命的焦慮、妥協與思索。她的詩,推進沉著但不乏內在的波瀾與燃燒,呈現了精巧、雅致、痛徹、古典又浪漫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