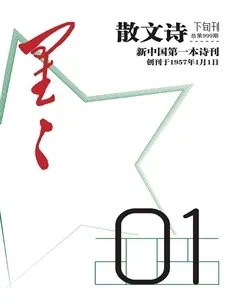甘 南(組章)
夏河機場
太陽升起,天地漸漸具體起來,草原呈現出了進步的意義。
飛機在草原之間的場地轉了一個彎,帶著陽光和人的信念一躍而起,像騰空的鷹,形象不斷延伸。
風被重重摔到窗戶后面,這些風曾把天空的雷電有意逆轉。云的精神取向超出了生活的折射,它的變換有質感,考究的形狀讓高處的人們心領神會。
大片的光芒在前方,鐵的翅膀驚動了風,尾巴在空中留下一條線,給天空出示感嘆的符號。飛翔帶著鳴叫,聲音沖擊著生活的漣漪。
好比鷹在時間里穿過,把草原的情感交織到雪域之外的地方。
無數祖先一生的腳印仍留在故鄉,他們沒有走完的路確定了今天要去抵達的方向。
羚城廣場
時光在緬懷,時光里陽光和大理石承載著一個環境。
矗立在羚城廣場的牦牛和羚羊,在滾動的日子中,被風帶走了曾經的語言和溫度,它們共同經歷過電閃雷鳴,經歷過野草野花的起死回生,如今在沉默中眺望,失去柔軟的目光不能鋪展足跡,曾經的雷聲依然在盤旋,但它們無法在人間穿行。
它們不同于羚城逐漸多起來的鋼筋水泥,它們有來自生命的悸動,只是這種悸動被固定起來,內心也一樣只留在過去的光芒里。
這種光芒值得懷念,站在城市中央,給來往的人群證明曾經的歷史中存在過的所有生命和熱愛。
積蓄春暖花開的時刻
山野里的草像一個集體一同奮斗,它們要是集合起來,就能開展一場革命。
我喜歡生長的事物。
野草剛鉆出大地,像人類那種意氣風發的樣子,它的內心從不輸給人類。把冬天拋在腦后,嘴里說:“能讓太陽悸動起來。”
一堆干柴在小河旁燃燒,發出青銅的聲音,我有足夠的耐心看風搖曳篝火,看眉清目秀的青草鉆出泥土的樣子。
一頭牦牛從山岡走過,它帶著粗俗的表情,眼睛濕潤。
綠草叢里保留著一些冬天的羊糞,大部分早已干裂。
前方有森林,森林的積雪在光線里很白,在樹木的根部,枯葉堆里鉆出一棵棵綠色的嫩芽。
成群的鳥飛來,掠過我頭頂,飛到羚城的上空,一座城市被漫山遍野集合起來的春風鼓動,與剛出頭的蠢蠢欲動的草葉一樣,積蓄春暖花開的時刻。
羊群站在尕紹麻山上
身體的背面,上升著一朵粗狂的云。
一只手里是炮嘎*,另一只手里握著生活的輪廓,在散不去的習性里,潛伏著一代又一代延續的生命。一條通往山頂的小路,與他有千絲萬縷的關系,每天只要走過這條路他就感念生活,從幾千年不退的本色里,他求證過現實帶不走的輪回。
嘰嘰喳喳的麻雀飛過頭頂奔向山谷,才讓東智目送它們遠去,他想象遇見自己的前世,想象一只麻雀用誘惑的方式,接近天空然后種下藍色的種子。
他時常會在巖石上磨刀,更多的時候被生活打磨,就像起伏的山巒,熟悉風雨雷電的屬性。
羊群到達尕紹麻山頂,領頭的羊站立,然后抬頭發出低沉的聲音,羊群里有了高高低低的回應。
“那些語言是合理的,像最初善良的人類。”才讓東智知道羊所能代表的一切,羊的目光里有他了解的一個個符號。過于復雜的需求,讓羊早早地接近現實。一條黑色的狗有感應時會有成熟的尖叫,它很快走出一個影子,蹲在才讓東智身邊。
山光水色在尕紹麻村**的上空迂回,延伸的霧把山下的羚城逼向更遠的地方。
*炮嘎,草原牧民放牧時使用的一種遠距離驅趕牲畜的工具。
**尕紹麻村,甘肅省甘南州合作市那吾鄉一牧村。
青 稞
一茬青稞猶如光景,猶如五百年前的時光那樣形成。它在曠野里有秩序地站立,從鉆出土地就在抒情,就鋪展開糧食的聲音。
九月,陽光有意走進,幾只鷹從大片的青稞地里起飛,鷹沖到天空的對面,藍天一再深刻,這種深刻讓鷹以及其他事物,形成了一個與另一個細節。
那些低頭吃草的牛羊,它們不會講現實的邏輯,只是留意山谷里正在發生的事。天依然在藍,草原像一片沒有象征的云,簡單地過著一個個樸素的日子。
青稞尊重青藏的風,尊重頭頂稀薄的氧氣,它單薄的身體里有高原的脾氣。
在甘南,青稞一直是有意義的糧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