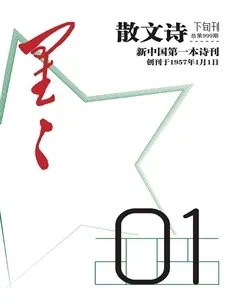最美丘陵在南充排排坐(組章)
落下閎:星辰與煙火
落下閎站在蟠龍山惆悵,擺了擺長(zhǎng)衫,順帶抖落了一些露珠。
看了一整夜的星空,他并不打算帶走一枚星辰。盡管心里養(yǎng)了一片蒼穹,卻仍然要回到雨滴敲打青石板的人間生火。
炊煙還是那炊煙,只是少了一些喜悅。
落下閎伸手掐指算了算,迎著太陽想了想,決定好好為地球畫一道線,并在一年的時(shí)光里圈二十四個(gè)節(jié)點(diǎn)。他知道,光在巴郡閬中建立觀星臺(tái)仍不夠,光在嘉陵江的懷抱里歡喜也不夠,得北上,從丘陵此起彼伏的蜀地東北,到黃土厚積的大中原。
他走得很慢,步步生輝,也步步生蓮。從太初歷到渾天學(xué)說再到通其率,他始終沒有走出閬中,他只是從嘉陵江看了看長(zhǎng)江,和黃河見了見面,在廟堂之上思考了一些時(shí)間。隨后,跳入民間成露,過了一些平常人家的生活。
但在最后他變成了一顆行星,盡管肉眼無法看見,我卻可以枕著管星街入眠。有時(shí)候酣睡,漲潮的嘉陵江推不醒我,走下戲臺(tái)的皮影也喊不動(dòng)我。
司馬相如:仗劍、撫琴以及辭賦
騎著馬、提著劍,嘉陵江就這樣蕩漾了。
他其實(shí)是隱居在蓬州的一枚星星,唯有仗劍才能生輝。他其實(shí)是一位落魄書生,流落臨邛,眼里有琴臺(tái),手中用妙筆。他其實(shí)最歡喜的是風(fēng)輕輕吹動(dòng)了珠簾,酒香動(dòng)搖了黃昏。
利劍出鞘,他在大西南深處目光如炬,寫出了柳暗花明的好辭賦。嘉陵江越來越清澈了,嫩綠的桑葉上長(zhǎng)出了幼蠶。幼蠶吐出《諭巴蜀檄》《難蜀父老》等絲兒,把歲月串了起來。琴聲悠揚(yáng),他在臨邛當(dāng)壚賣酒,洗滌杯盤瓦器,心里泛著舟,《封禪文》猶如玉米,粒粒飽滿金黃。
文章寫不盡天下憂愁,琴弦奏不動(dòng)生活窘狀,利劍斬不斷江水滔滔。臨邛、蓬州、淮陽都是城,城里最多的是人民。《子虛賦》也罷,《上林賦》也罷,都不過是一道厚重的門,他知曉玄機(jī),有機(jī)會(huì)推,就必須全力推,身后還有太多等著的山群。
有些故事只能藏進(jìn)歷史,有些故事卻需要一點(diǎn)點(diǎn)打開。比如他的劍,并沒有丟失在異地他鄉(xiāng),依然在舊地迎著太陽發(fā)光。那些泛黃的辭賦,都蒼翠欲滴,有時(shí)候落在頭頂,有時(shí)候落在心里。嘉陵江還是那樣恬淡,但蓬州卻寫就了蓬安志。
譙周:推開江水夜讀
沏一杯香濃茶,讓泡沫浮在上面,綠蔭沉潛杯底,戰(zhàn)事已經(jīng)逼近,《仇國(guó)論》已經(jīng)幾易其稿。殿堂之上,煮一鍋大雜燴,色香味俱全,但粗鄙的陶罐卻在山河之外,唯有心中懷揣明月清風(fēng)之大才,方能夠讓草木原路返回。
安樂不再思蜀,這是一個(gè)人的良策,同安于天下黎民百姓方才是鴻儒的胸襟。
借著月色歸家的陽城亭侯,走在《巴蜀異物志》的經(jīng)緯里,唯有少數(shù)人能夠讀懂他的踉蹌。其實(shí),他望的不僅僅是故鄉(xiāng),而是越來越殘缺的彎月。他也思考過嘉陵江為什么避開充國(guó)掉頭而去的原因,他知道未來還有很多更美的故事會(huì)有人填寫。
一千多年的時(shí)光,濃縮于一杯茶,有多少水滴在變冷,但暖心的形狀,卻不曾改變,經(jīng)過灼燒的泥土,它依然本色依舊,從不更改屬于它的屬性與芬芳。
是時(shí)候講述了,他的故鄉(xiāng)已經(jīng)茁壯成長(zhǎng),不再是一枚粗糧。是時(shí)候表達(dá)了,他的故鄉(xiāng)沃野千頃,已成為大雪抵達(dá)不了的有機(jī)之鄉(xiāng)。
陳壽:臨江讀史
他知道,嘉陵江也是走著走著才通達(dá)的。他還知道,嘉陵江不慢走,不遠(yuǎn)走,不會(huì)那么美。他愿意活在嘉陵江的曲流里,只為了蓋好一棟萬卷樓。
很多次,我驅(qū)車從他蓋的樓下經(jīng)過,不僅看見了舊歷的顏色,也聽見了嶄新的江水之聲。那些古人走過的臺(tái)階,我一直沒有勇氣去攀登,但我想找一塊石板坐下,聽一聽樹葉落下的聲音。沙沙,沙沙,就像蠶在閱讀桑葉,就像曲流在閱讀嘉陵。我也想比鄰一座青居小鎮(zhèn),我還想遠(yuǎn)觀一座凌云之川。
《三國(guó)志》就不讀了,我知道三國(guó)源,還知道劉備、關(guān)羽、張飛。我只想請(qǐng)陳壽先生喝一杯酒,金鳳酒、闕家酒,太平白酒,或者鳳和黃酒。喝醉了再一起讀史,講一講安漢縣是怎么變成南充城的。不說絲綢、不說桑梓,但說渡口、但說曲流。
說到動(dòng)情處,寫傳記的寫傳記,寫詩(shī)的寫詩(shī),就讓嘉陵江一直奔跑去,就在萬卷樓慢慢等黃昏,等月亮升起來,再看一看彎月就可以各自歸去睡覺了。
夢(mèng)也許很淺,但故事必然變得更加開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