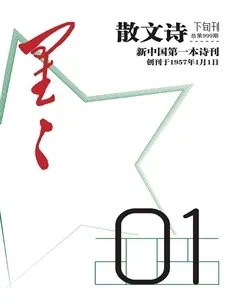古城脈韻(組章)
閬中古城
臨水而居,難免被水灌醉。
韁繞合護(hù),形勝之地。始終處于微醺狀態(tài)。
城門,一直開著。門內(nèi)有繡花鞋,有良家女子?
江邊舟楫,被時光鏤空,又被川北道署的鼓聲驚醒。
雙柵子街的青石板上,遠(yuǎn)去的腳印堆積如山:車夫、商販、貨郎、匠人拖著艱辛的赤腳印;貢院里,考生們散發(fā)書香的布鞋印;王皮影掌心里形形色色的小腳印;紅四方面軍疾馳而過的草鞋印……
一路走來,沿途的風(fēng)水和春天,次第綻放。靜聽流水回聲。江光可抱城廓,山勢卻難鎖煙霞。春風(fēng)不倦。漢桓侯祠里的香火,愈燃愈旺。翼德的臉,由黑變白,由白變紅。被落下閎星命名的天空,夜晚也是白晝。
長公在上,上善若水。一位老人捧出春節(jié),敬獻(xiàn)蒼生。與水結(jié)緣,閬苑自成仙境。
等我兩千三百年,佳人癡心不改;我只輕輕一瞥,便白發(fā)蒼蒼。
相如故城
在花蕊里,返老還童。用朝拜的目光,輕叩門扉。此刻,我淚眼蒙眬。
堂前檐下,風(fēng)在隨意翻動春天。高興處,還笑出了聲。玉環(huán)書院依舊正襟危坐,仿佛仍在默誦上林、長門或美人中的名言金句。背陰處幾株花草灌木,口中念念有詞。一闋漢賦的密碼,誰能輕易破譯?
江水和文君可以作證。那枚奇異的卵石,曾被兩千多年前那個乳名犬子的頑童,打過水漂,做過定情物。剔透的玉指,在料峭春風(fēng)中撫琴而嘆。衙鼓的訴說、衙役的吆喝,早被浪花淘盡。嘶啞的蟬鳴,卻經(jīng)久不息,從長卿祠旁那棵千年古樹傳來。每一聲,恰似賦圣深情的吟哦。
陽光,在古城墻上涂抹溫暖與寂靜。有必要對每一塊飽經(jīng)風(fēng)霜的漢磚,保持仰望的姿勢。
它們字字珠璣。用人間最美的漢字,細(xì)數(shù)前朝月光,或者,用虔誠廝守子虛、烏有的宮殿;臨摹辭宗絕世的孤獨,和光芒。
淳祐故城
一杯濁酒,獨飲寂寥。
緘默七百多年的石頭城,終于開口說話。
恰似雄辯的思想家,一字一句,入石三分。
山嵐,不甘寂寞。總想從古城墻堅硬的表情里,摳出馬蹄聲,摳出光陰里的每一粒疼痛,摳出早已風(fēng)干的血跡。
江水,也不想再隱瞞真相。總想從曲流環(huán)抱的牛肚壩,古渡的前津后津、上下碼頭,復(fù)原長鳴的汽笛,復(fù)原金戈鐵馬的廝殺、刀槍不入的傳說,和三千抗蒙將士舍身跳江的吶喊。
“山峙兩巖南北峭,地盤一水古今流。”唐朝的姚昂不知道,一江春水流到今,依然如泣如訴。
黎明,遲早被春天占領(lǐng)。
刀槍劍戟迸發(fā)的火星,也早已風(fēng)化成無言的結(jié)局。
在這里,我不想驚擾青居煙霞,更不愿讓青居山人①《游靈跡廢寺》的完整與精彩,擱淺歲月的沙灘。
我只望一場遠(yuǎn)去的風(fēng)暴,能留下時光的胎記。
最好,讓石頭開花,或者在陽光下沸騰,升華為歷史輝煌的斷章。
① 青居山人,明朝中期名臣、四川順慶府人陳以勤的別號。
周子古鎮(zhèn)
一部發(fā)黃的線裝書。扉頁上寫著:嘉陵江上最后的碼頭古鎮(zhèn)。
一枚光陰的戒指,佩戴在吳道子三百里錦繡畫布上。
古碼頭的背影、古民居的燈火,在畫布上點亮;古商鋪的吆喝、古客棧的鐘聲,從畫布上傳來。一群復(fù)活的精靈,從歷史襁褓里跳出來——
下河街的腳印川流不息,反復(fù)丈量著深藏不露的時光;畫江樓上,顏魯公毫筆扯出的纖繩,在歲月的礁石上晃悠;火星四濺的鐵匠鋪里,許多生硬的詞語,已熔化成水;愛蓮池中,每一片荷葉上,搖曳著依稀可聞的蛙聲……
萬壽宮內(nèi),誰在一抹夕陽里修補殘缺的歌謠?
臨江閣里,那些似醉非醉的眼神,早已看慣帆影,閱盡蒼生。
苦難與蹉跎,從老戲臺前躲到幕后。我不知道,在你內(nèi)心深處,還有多少柔軟與溫存,正在塑造龍角山的瑰麗與風(fēng)骨。用星光繁衍漁火。用浪花沖刷苦悶。
一枚桑梓,早被一條江吟詠成雋永的絕響。
馬鞍古鎮(zhèn)
身著樸素,像朱德的草鞋。但穿斗式木結(jié)構(gòu)肌理,足以使你身板硬朗,精神矍鑠。
客家風(fēng)情,本是骨子里的天性。但好長一段時間,你既沒客家,也無風(fēng)情,甚至連一套合身的石榴裙都沒有。好在,盤纏花光,還有更多孳息。
走出夜色那天,你印堂發(fā)亮,面色也越來越紅潤。是琳瑯山下那個娃子最初的啼哭和戰(zhàn)馬的嘶鳴,喊紅;是紅軍街上飽蘸激情和鮮血的石刻,映紅;是無數(shù)火鳳凰浴火騰飛的丹心碧血,染紅……
那些紅,是井岡山上蔓延開來的滿江紅,華夏子孫血脈里洶涌的中國紅。那么多紅映入眼簾,不難想象你當(dāng)年的盛況——
天空明朗。手搭涼棚,就能望見北斗。
就像那些入鄉(xiāng)隨俗卻不懂風(fēng)情的紅五星,熟諳客家檐下炊煙緣何裊裊不絕,子彈和刺刀怎樣勢如破竹。他們簇?fù)碇牭陡^,用槍桿子詮釋一句著名的箴言。盡管,好多鮮血淌在黎明前的黑暗里。
但他們卻以豐碑的方式,走進(jìn)德鄉(xiāng)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