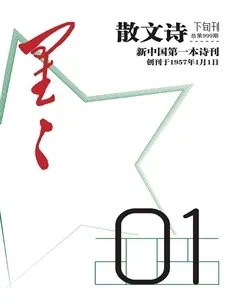嘉陵江與一座城飛奔(組章)
一片桑葉,飛成了女神
一棵樹,從河床爬起來。
在六合絲綢博物館,用炭化的身體,告訴一條江,兩岸五千多年的養(yǎng)蠶史。
春禮祈求農桑豐收,秋禮酬謝蠶神賜福。嫘祖,把始蠶的傳說,從一個地區(qū)講到遠古。
“天上取樣人間織,滿城皆聞機杼聲”。綢都,在白居易的《繚綾》里,搖著紡車。
一匹絲綢,兩次飛上巴拿馬萬國博覽會的獎杯。是要懷念那個叫張瀾的賢士,為它創(chuàng)建了一所學校和一個工廠?
母親,從貧瘠的桑葉上,摔下來。她看到臂上的白色綁帶,長成了蠶兒吐的一根根銀絲。
而我的夏夢,隨著煤油燈一跳一跳。父親的目光,還是讓我,把蠶寶寶養(yǎng)成小弟小妹。
祖父用稻草和篾條,把老蠶請上蔟;業(yè)主小饒,替妻子,用愛的芯片,為蠶兒自動切桑、喂桑、除沙。
銅鼓萬畝桑園,染綠返租倒包戶的夢。共育室和養(yǎng)蠶大棚,正齊心協(xié)力,給鄉(xiāng)村織件絲綿衣。
桑葉,正在嘉陵錦衣還鄉(xiāng):桑茶、桑食品、桑飲料、桑保健品……
奧特斯的有機桑園,一邊減排,一邊跟國際碳匯談交易。
巴蜀大地上的一根蠶絲,飛上服裝,飛上絲巾,飛上畫軸,飛上扇子,飛成蜀繪。與蜀繡、蜀錦,三絕合璧。
一枚蠶絲的愛絲絲入扣:軟,就織成降落傘線;柔,就溶進你臉上的面膜;深,就牽起手術線甚至架起心臟支架,抑或鉆進骨折手術可降解蠶絲螺釘;高,就升上宇宙飛船的那面國旗!
一襲綢衣,正在南充的中心,帶著一尊女神,把一座城市,舞得風情萬種。
一條江,與城市飛奔
一條1345公里的江,把300公里的最柔最美的身段,獻給南充。
沙溪、金銀臺、紅巖子、新政……臥在江上的水電站,是9顆明珠。
一邊尊貴著嘉陵江,一邊用31億度的熱情,點亮江邊的萬家燈火。
嘉陵江用溫柔的手臂,把一個“閬”字圍了三面。
于是,一座兩千三百多年的古城,氤氳著張飛的臉譜、杜子美的詩篇和滕王閣。
火峰山一言不發(fā),只想用自己的名字,記住一支隊伍的鏖戰(zhàn)和火種。
滿福壩的水杉波光粼粼,把島上大禹的足跡,從嫩綠講到金黃,從金黃講到深紅。
秀水長灘的九只石牛,盡職地看著江水。
向上的頭角,是一個為水而生、靠水而建的城市的倔強和勤懇。
古埠碼頭不言,千年的離堆不言。
風輕輕領頭,蘆花還是紛紛傳頌三軍總司令身經百戰(zhàn)卻毫發(fā)無損的神奇,和普通一兵的奮不顧身。
馬回電站抬升了水位。對岸的綠色,還是讓兩百多頭水牛,發(fā)起百米沖刺。
對,太陽島和月亮島就是春天。
一條江,走著走著,又拐了個彎。在以她命名的城市,化蝶成一尊楚楚動人的雕像。然后,一起飛奔……
一句話,讓縣城聲情并茂
“客而家焉”,一聲客家人,溫暖如春;一部客家史,力透紙背。
一句話,從戰(zhàn)亂、瘟疫和自然災害里遷移。
一句話,從中原出發(fā),帶母攜子,背井離鄉(xiāng),把孝感走成天涯。
一句話,落戶儀隴,把天涯的水,走成倔強的人。
一句話,說成朱、鄭、丁、饒、陳等二十多本家譜,在儀隴的山山水水里生長……
火紅的送親儀式,客家人演繹了四百年。
最響亮的那句客家話是朱老總說的:我家是佃農,廣東韶州,客籍人。
最生動的客家話是丁字橋小學的那本自編教材《我們的根》,瑯瑯上口的是“寧賣祖宗田、不賣祖宗言”的母音。
最宏大的客家話是丁氏莊園,大大小小108間房屋,以及院墻、護宅河,靜靜地述說客家人的勤勉和孤獨。
最地道的客家話是九大碗,葷素搭配,清淡爽口。“九九歸一”是最大的熱情和最美的祝愿。
一句話,讓一個縣城,聲情并茂。
一輛車,領跑西南風
一臺內燃機,點燃一座城。
但延安路孤獨的公交站臺,留不住三千職工的子弟校的朗讀聲。
遺落站臺的,是一縷東風的記憶。
新時期的風,是新能源的風。
嘉陵,用一個特色小鎮(zhèn)擁抱汽車。
一臺汽車,就是一個魔方。產業(yè)的魔方,城市的魔方,景觀的魔方。
四個縣的合力,讓一臺汽車的零配件精益求精。
是風,就成為旋風。
每年六萬輛的能量,正聚集成強勁的西南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