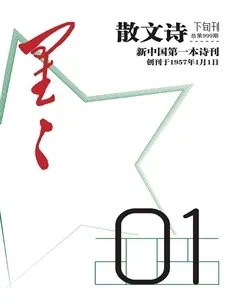醉花陰(組章)
梅 花
立春前后,總有一枚穿嫩黃衣裳的鸝鳥,在陽光的枝丫,唧唧啾啾。
叫聲清婉而幽麗。似乎在尋找什么,又似乎在否定與肯定之間猶疑、躊躇。但短時間內,并沒有離開的想法。
后來,我撐一把傘,一個人往雪的墨痕深處去,雪的硯臺深處去,雪的白茫茫的梵音深處去。在水邊的一個亭子,亭子倒影的中央,停泊。
似乎在尋找什么,又似乎在否定與肯定之間猶疑、躊躇。
然而,梅花已經開好了,你還沒有出現。
然而,梅花已經開累了,梅花已經開落了,梅花已經變成與春風舉案齊眉的葉子,我仍舊空空站著。等自己下雪,等自己把心里的花,再開一遍。
成為一朵橫笛紛紛的小花冢。
杏 花
一船薄霧,由橋洞的胸口側身穿過。熹微的鱗光,漾出你粉白的劉海兒。
云朵葉芽般吐蕊,天空被風箏吹向更遠的天空。我無法撐起記憶的小船,游到落英繽紛的墻根下,拾一朵杏花雨,別在頭上。
就讓鷓鴣的口琴,端坐于蒂上,采桑子,阮郎歸吧。就讓一根巷子挑著扁擔,從依次洞開的世界盡頭,返回另一個世界盡頭吧。
兩枚雀鳥在瓦壟間,播種去年的草籽。
繡坊,繡娘,繡鴛鴦。流水的,紅鴛鴦,白鴛鴦。
牡 丹
五月的廊橋,把蝴蝶的蝴蝶,留在云鬢娥娥的亭間。
柳樹夢見梅花。娘子抖落一聲繞指柔。吧嗒,吧嗒,櫻桃落,枇杷黃,被燕子濡濕的銅環,映綠良辰,染紅朱戶。
誰的媚眼兒眸子一驚,裊過綠肥紅瘦的漏窗?
誰的瓔珞叮叮醉紅,飛做翠帷,飛做霞裳。
那一年,車馬稀,花影薄。
那一年,牡丹,牡丹,任你怎樣喊,亭子都不回頭。任憑你怎么找,一幀執扇端坐的仕女,留白的后頸,低胸的香肩。愁煞個人。
梔子花
一朵露珠的小月亮,棲在我經過的籬邊。
猶如宛在,葫蘆瓢里的潔白信,將無字的書頁,一滴一滴朗讀。
聲音皎潔而盈潤。
楚楚的芬芳,從一枚鐘形的雅器,粲然溢出。但并不妨礙我的離去。
梔子花,一瓣白,瓣瓣白。
梔子花。你回過頭來。你聽我說。
荷 花
背對著你。心情是水做的。
紅的,粉的,白的。香氣的盤花紐扣。風,一朵兩朵三五朵。流過你的裙邊,又退回來。
倘若你剛剛出水,而我恰巧轉身。葉子的手掌是青蛙的,我沒有理由,想要蹲在那兒。
然而,黃昏還是忍不住,提前落了,竟這樣,把我的紅蜻蜓打碎。是你。
幸好還有一孔竹笛,用來傷懷。幸好,我又重新回到橋上。
桂 花
下臺階,轉彎,忽聞,一粒粒微微翕動的芬芳,細細簌簌跟上來。
我恍惚了一下。轉身瞅瞅,卻未見異常。繼續往前。就在這時,一粒粒緊密翕動的芬芳,又細細簌簌跟上來。已然絆住我的腳跟,已然拽緊我的衣裳,已然蒙上我的雙眼。憑著激切,沖動,霸道,任性的作態,我可以肯定,這是丹桂。
誠懇的脅迫,使我松軟下來。
啊!唇齒相依的表達,萬籟俱寂的守候。就在剛剛下過雨的那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