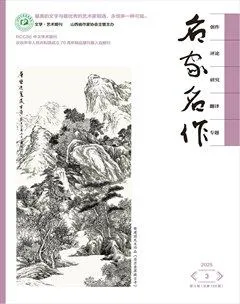“鼓盆而歌”與“向死存在”
[摘 要] 生死問題作為指向主體存在最深刻且無法逃避的根本性追問,是哲學(xué)視域下不可忽視的終極性問題。死亡作為在世的終結(jié),卻不能簡單地被視為完結(jié)與消失,反而在與“生”的照面中具有敞開性的意義。在審視本己之死與他者之死的具體情境時,莊子和海德格爾分別在“道”與“存在”中實現(xiàn)主體價值的找尋。在莊子面對妻死時的“鼓盆而歌”和海德格爾所言的“向死存在”中,可見莊子和海德格爾對死亡問題的關(guān)注與深思。兩位哲學(xué)家有關(guān)生死的哲學(xué)思想在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中產(chǎn)生碰撞,為當(dāng)下從未停止過哲學(xué)之思的人類提供主體存在與找尋希望的智慧引領(lǐng)。
[關(guān)" 鍵" 詞] 莊子;海德格爾;生死;主體存在;“鼓盆而歌”
引言
人類自誕生以來便無法擺脫對生死這一終極性問題的思考與追問,在哲學(xué)家視野里,生與死同樣是占據(jù)中心位置的研討話題之一。蘇格拉底曾指出:“真正的哲學(xué)家一直在練習(xí)死。”[1]叔本華也道明:“如果沒有死亡的問題,恐怕哲學(xué)也就不成其為哲學(xué)了。”[2]由此可見,生與死在哲學(xué)思想史上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在與主體之存在密切相關(guān)的過程中指引主體修身養(yǎng)命,找尋存在與希望。莊子和海德格爾對生死觀念的闡發(fā)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他們分別以“鼓盆而歌”與“向死存在”引導(dǎo)主體在直面死亡時實現(xiàn)對生之有限性的超越,啟發(fā)主體上升到對“道”和“存在”的追問,為時常處于異化與沉淪狀態(tài)下的今人帶來冥想和反思,從而通達對生命本身的觀照。
一、本己之死與他者之死
莊子文本中對生死的基本看法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釋德清將命注解為自然而不可免者,林希逸釋:“人力所不得而預(yù),此則天地萬物之實理也。曰‘命’‘天’,即此實理也。”[3]185-186可見,在莊子那里,所謂人之生、死是不可避免的,如同黑夜與白天的交替,遵循著自然常有的規(guī)律。
由于死亡的不可傳達性,對他者之死的關(guān)注成為人們理解死亡的方式,而他者之死對于本己而言,實則是一種外在的、可旁觀的死的經(jīng)驗。莊子借孔子之口,道出了主體性“吾”的重要性:“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耗精。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非吾乎?”[3]207作為主體的“吾”能夠?qū)ψ约旱纳兄苯印氐椎母兄c領(lǐng)悟,而楊立華學(xué)者指出,在莊子那里,“屬于本己的‘吾’的死是無法被對象化的,也不是任何意義上的經(jīng)驗,處于完全的不知之域”[4]。在面對他人的死亡時,孟孫才居喪哭泣而不戚不哀,是因為他領(lǐng)悟到死亡只是人有形體上的變化而沒有心神的損傷,只有軀體的轉(zhuǎn)化而沒有精神上的消亡。在死亡的不可傳達性方面,主體對于死的認(rèn)識是完全意義上的不知,往往這種無知使得人們以日常生活中經(jīng)驗到的他人之死代替本已之死出場,“存在者表現(xiàn)出對于死的懼,死被當(dāng)作一個事件來打量。死亡意味著一個聲色貨利、權(quán)錢名譽的世界的消解,存在者執(zhí)著于生的往而不返,面對死亡往往表現(xiàn)出懼的情緒”[5],懼怕之后哀情過當(dāng),將生視為得,死視為失,由得到失怎不悲乎。莊子告誡人們不應(yīng)將他人死亡的經(jīng)驗過度投射到自己身上,因為他人之死僅構(gòu)成一種外在的經(jīng)歷。最終,個體應(yīng)該在實現(xiàn)對自我的復(fù)歸中體悟生死,在內(nèi)在體悟中真正理解和接納生死。
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指出:“死所意指的結(jié)束意味著的不是此在的存在到頭,而是這一存在者的一種向終結(jié)存在。死是一種此在剛一存在就承擔(dān)起來的去存在的方式。‘剛一降生,人就立刻老得足以去死。’”[6]282海德格爾所說的死雖然意味著生命的結(jié)束,卻仍然構(gòu)成生命存在的一種形式,而這種存在的可能是從人一出生便趨向的,每個人的死都必須是一種切身經(jīng)驗①,他人無法代替任何人去經(jīng)歷死亡。
海德格爾和莊子一樣,都指出了他人死亡是旁觀者獲得的一種外在經(jīng)驗。海德格爾進一步指出了這種經(jīng)驗的可傳達性,每一個此在本身不可能完全經(jīng)驗到自身的死亡,但在面對他人的死亡時感受到觸目驚心,“此在的某種了結(jié)‘在客觀上’是可以通達的,此在能夠獲得某種死亡經(jīng)驗,尤其是因為它本質(zhì)上就共他人存在”[6]274。由此,海德格爾指出了死者和共在者之間的關(guān)系。首先,死者作為一種可能的存在并不再在“此”,而是使得在這個世界上遺留下來的人與之共他同在,“共在”意指在同一世界上共處。其次,共在者雖與死者共在,卻無論如何都不會代替死者經(jīng)歷他所經(jīng)歷的喪失。最后,海德格爾強調(diào)去追問臨終者的死亡過程之存在論意義,在生存論意義上理解死,便是進一步確定了死不具有代理的任何可能性,誰也無法從他人那里取走他的死,這也正是海德格爾所說的“每一此在向來都必須自己接受自己的死……死確乎意味著一種獨特的存在之可能性:在死亡中,關(guān)鍵完完全全就是向來是自己的此在的存在”[6]276。莊子和海德格爾都看到了死亡是無法替代的,他者之死無論如何也代替不了本己之死,正是這種向死的必然性使得人們不應(yīng)渾渾噩噩過完一生,在與“生”的照面中如何實現(xiàn)主體存在的意義成為將要解決的問題。
二、“鼓盆而歌”與“向死存在”——對“生”之有限性的超越
“鼓盆而歌”是莊子在《至樂》篇談到的命題,回到具體語境中,進一步理解莊子本人對生死的態(tài)度。莊子妻逝后擊缶未悲,惠子疑惑其悖倫理。莊子解釋,雖初感悲傷,但悟生命由氣聚散,生死如四時更替、順應(yīng)自然。妻歸天地自然,他認(rèn)為哭泣是未通生命之理,故泰然處之。莊子曰:“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3]462-463在這里,能夠看到莊子對“氣”這一概念的引入,萬物由氣構(gòu)成,生死循環(huán)無窮,在生死一體的基礎(chǔ)上,莊子否定世俗的悅生惡死觀。面對亡妻鼓盆而歌,看似在大聲宣揚生苦死樂,事實上,“莊子并不是真的寄希望于死后的世界……莊子的本意是否定任何可以期待的人生最終目的。他說死可能比生強,實際上是以一種嘲諷的語氣否定對肉體長存的希冀”[7]。莊子認(rèn)為,生死并非人能抉擇,應(yīng)破除生執(zhí),超然生死,達至自然之境,超越生命有限。此超越指在有限生命中創(chuàng)造無限可能,而非執(zhí)著于名利是非等肉體生存追求。
海德格爾在此在的意義上提出了“向死存在”,此在的生存便是“向死存在”,“死亡不是尚未現(xiàn)成的東西,不是減縮到極小值的最后虧欠或懸欠,它毋寧說是一種懸臨”[6]287。正是在與整個世界照面的過程中領(lǐng)會懸臨于前的死亡,而此在的生存、實際性與沉淪也在這一面對死亡的過程中顯露。海德格爾指出,死亡是確知而又不確定的,“日常的向死存在”在人終有一天會死但暫時尚未的說法中步入沉淪,在死亡的懸臨面前有所閃避。一方面,沒有人會懷疑人終有一死,死亡從始至終便具有其可能性;另一方面,死又被推遲到往后的一天,人們可以暫時忘記死亡的羈絆,投身于日常活動的操勞中。正是如此,日常狀態(tài)中的人們在這兩種認(rèn)知的基礎(chǔ)上實現(xiàn)對死的遮蔽,并削弱和減輕死亡來臨之際的畏懼,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沉淪。
海德格爾將“向死存在”分為兩種,即本真的向死存在和日常的向死存在。與上述日常的向死存在相比,“本真的向死存在不能閃避最本己的無所關(guān)聯(lián)的可能性,不能在這一逃遁中遮蔽這種可能性和為遷就常人的知性而歪曲地解釋這種可能性”[6]299。在海德格爾這里,本真的向死存在與主體的自由是統(tǒng)一的,在明確了“向死存在”的本質(zhì)后,為達到對日常的向死存在的超越,就是直面死亡的,將此在的死亡視為不可能的可能性,實現(xiàn)此在的完整性。超越日常的向死存在便是跳出日常的沉淪帶來的人們對于懸臨的死亡的麻木性,從而能夠不逃避和遮蔽死亡,在對死亡的感知里體悟生的意義。
莊子和海德格爾都觀照到了死亡之于生的意義,勸誡世人不要將死亡視為在世的消失而哀痛。他們主張超越生命的有限性,把握死亡的價值。莊子以“鼓盆而歌”表達順應(yīng)自然生死的超然態(tài)度;海德格爾則強調(diào)不要在日常的沉淪中暫時忘卻了死亡的懸臨,而要從日常沉淪中覺醒,回歸本真存在,實現(xiàn)向死而生的自由。二者關(guān)注死亡的自然與本真,轉(zhuǎn)變常人畏懼死亡、逃避死亡的心態(tài),教人如何更好地生存于人世間。
三、對“道”與“存在”本身的復(fù)歸
莊子在道之本體的依據(jù)下講求生死一體,倡導(dǎo)不為生死所動、自在無待的逍遙境界,海德格爾追求在此在的本真狀態(tài)中追尋存在本身的意義,生死之間展開此在的無限可能性。在對生之有限性加以超越的過程中,莊子和海德格爾都遵循自身理論的形而上學(xué)依據(jù),分別是“道”與“存在”。
莊子哲學(xué)體系在構(gòu)建的過程中始終離不開其背后的那個“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上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3]189的道之本體。陳啟天說:“道彌宇內(nèi),無所不在。道貫古今,無時不在。”[3]190—191道作為萬物生化之本根,高于人之生死存亡,道為無形之氣,使人成其形,造就人之生,也可使人安息死亡,道主宰著萬物由生至死的歷程,既是生命開始的源頭,又是生命終結(jié)的尾端。
海德格爾強調(diào)存在問題在存在論上的優(yōu)先地位,把存在(是)界定為哲學(xué)中對存在意義的追尋,存在總是指向某種存在者的存在,存在是作為本真性的向死存在的形而上學(xué)依據(jù)而存在的。在他看來,存在作為最普遍的概念,體現(xiàn)了存在者時時刻刻都在把握著對存在的某種領(lǐng)會。存在具有不可定義性,“存在這個表述即使在今日也仍然不是一個口令,而是一個中心問題的稱號”。[8]在海德格爾那里,不可定義卻不意味著取消存在的意義。他用“此在”這個概念,指明普遍性的存在在有限性時間范圍內(nèi)的存在,存在者從日常的向死存在向本真性的向死存在的超越過程中,找尋存在的意義,所謂去存在便是從逃避死亡的操勞活動中抽離出來,本真性地直面死亡。“海德格爾充分地意識到人的生死的互依和轉(zhuǎn)化,強調(diào)人‘出生’即‘入死’,因而敢于‘生’的人就要敢于‘死’。他把能夠‘向死而生’的人稱為‘此在’,認(rèn)為唯‘此在’可以體現(xiàn)、通達存在,所以‘此在’的‘生存’就是對存在的承諾。”[9]此在是存在者在有限存在的世界中的主體,經(jīng)歷著實際的生與死,因而在海德格爾那里,對此在的觀照更有益于存在意義的敞開。
莊子和海德格爾所遵循的形而上學(xué)依據(jù)“道”和“存在”都是不能被看得見、摸得到、聽得見的,不可過多定義和言說,但道和存在在指向主體自身的存在方面具有無法取消的意義。在莊子那里,道常無言,孕育萬物,造化萬物,在天地之間沒有一物是能夠脫離道而自生自滅的。在人的生死之間,人能夠以最直觀的體悟去感受在道的作用下,生與死是自己無法操控的,最好的解決方法便是順應(yīng)天道。道雖在形式上“無”,卻生有著萬事萬物。主體正是能夠在道的關(guān)愛下,力所能及地實現(xiàn)自己無限的可能性,拋卻形、名、是非、貴賤等一切對“生”產(chǎn)生束縛的外在之累,達到自然無待的境界。海德格爾在時間視域下對存在意義進行闡發(fā),“此在”作為存在者,歷經(jīng)生到死這一有限性的過程,若在日常生活中沉淪,生活中充斥的操勞與繁忙便一步步淹沒了對最本真的存在方式的觀照。因此,海德格爾強調(diào)此在主體以本真的向死存在始終直面死亡,在有限的生命里讓存在的意義展露在日常生活中,即使到了生死交接的一瞬,主體也不至于驚慌失措,存有的還是對于死亡的本真性的坦然面對。
結(jié)束語
莊子和海德格爾在生死問題上的共鳴之處展現(xiàn)了哲學(xué)家對人之生存當(dāng)下的思考與關(guān)照,他們直面死亡之到來,在道和存在的形而上學(xué)依據(jù)之上看待生與死,尤其在對本己之死與他者之死的比較中,道明死亡必須是本人親臨的死亡,任何人無法代替。“對有死的人來說,他所能做的,就是學(xué)習(xí)如何使自己沒入黑暗之中以便在白天能看到星星。其實,無論白天還是黑夜,星星都在那里,只是由于白天的光明遮蔽了黑暗。”[10]我們都在黑暗中找尋生的希望和光明,正因為有了人這一主體性存在,光明得以顯現(xiàn)。但以主體為中心的光明的周圍依然是毫無邊際的黑暗,只有發(fā)揮主體性,將自身淹沒于黑暗中,直面黑暗——直面我們的死亡,超越黑白的邊界——生死的邊界,實現(xiàn)當(dāng)下對存在的追尋。
參考文獻:
[1]柏拉圖.斐多:柏拉圖對話錄之一[M].楊絳,譯,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12-13.
[2]叔本華.愛與生活的苦惱:生命哲學(xué)的啟蒙者[M].陳曉南,譯,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86:149.
[3]陳鼓應(yīng).莊子今注今譯[M].北京:中華書局,2009.
[4]楊立華.莊子哲學(xué)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20:239.
[5]廖永林.“以道觀死”與“向死而在”:莊子與海德格爾的死亡觀比較分析[J].中州大學(xué)學(xué)報,2008,25(5):69-72.
[6]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M].陳嘉映,王慶節(jié),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6.
[7]顏世安.游世與自然生活:莊子評傳[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2:132.
[8]倪梁康.胡塞爾與海德格爾的存在問題[J].哲學(xué)研究,1999(6):45-53.
[9]張曙光.生死問題與存在視域[J].哲學(xué)研究,2001(1):40-47.
[10]張志偉.“白天看星星”:海德格爾對老莊的讀解[J].中國人民大學(xué)學(xué)報,2002(4):40-46.
作者單位:安徽大學(xué)哲學(xué)學(xué)院
注釋:
①切身狀態(tài):即切身性,指的就是人在現(xiàn)實遭際中的處身狀態(tài),是人被觸動的直接的當(dāng)下狀態(tài)。在莊子和海德格爾那里,存在者在日常世界中有著切身和不切身兩種狀態(tài)。
作者簡介:曹煒(2001—),女,漢族,安徽六安人,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莊子哲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