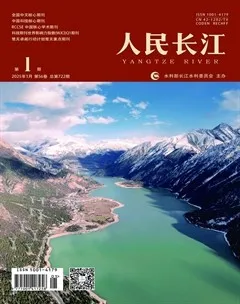基于DPSIR模型的山西省生態健康評價








摘要:
為了探究山西省2011~2021年生態健康指數變化及限制因素,基于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響應(DPSIR)模型構建24個指標組成的評價體系,評價山西省生態健康狀況,分析11個地級市生態健康時空演變特征,并利用障礙度模型診斷影響其發展的主要障礙因子。結果表明:① 山西省生態健康綜合評價指數逐年上升,由亞病態向臨界轉變;壓力子系統上升最明顯,由0.34上升到0.63,生態壓力大幅降低。② 時間上,2011~2021年各市生態健康指數呈上升趨勢;空間上,整體呈現東南部城市生態健康水平較高、北部與西南部水平較低的格局,2021年太原市、晉中市率先進入亞健康狀態。③ 人類活動強度、產水模數、有效灌溉面積、人均水資源量和生活用水占比是主要障礙因子;影響子系統障礙度不斷增加,驅動力、狀態和響應子系統保持不變,壓力子系統障礙度不斷減少。
關" 鍵" 詞:
生態健康評價; 障礙因子; DPSIR模型; 山西省
中圖法分類號: X826
文獻標志碼: A
DOI:10.16232/j.cnki.1001-4179.2025.01.010
收稿日期:2024-06-15;接受日期:2024-09-11
基金項目: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52079051);河南省高校科技創新團隊支持計劃資助項目(24IRTSTHN012);河南省高等學校重點科研項目(22A570004,23A570006)
作者簡介:
李英杰,男,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水資源管理。E-mail:380949564@qq.com
通信作者:
汪順生,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為節水灌溉、農業水土、水環境水生態保護。E-mail:wangshunsheng609@163.com
Editorial Office of Yangtze River.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under the CC BY-NC-ND 4.0 license.
文章編號:1001-4179(2025) 01-0074-07
引用本文:
李英杰,梁帥濤,汪順生.
基于DPSIR模型的山西省生態健康評價
[J].人民長江,2025,56(1):74-80.
0" 引 言
區域生態健康是人類生活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和首要條件[1]。長期以來,山西省興于煤、困于煤,礦產資源開采和煤炭產業給省內生態環境帶來破壞,加之地處黃土高原,自然條件較為脆弱,常年存在水土流失問題,2010年黨中央決定將山西省作為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在這一背景下,客觀評價山西省生態健康狀況,不僅可以有效判斷轉型改革的成效,而且可為山西省生態系統健康管理與決策提供思路,對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生態系統健康是生態結構和功能的綜合性概念,用來反映區域的生態活力、韌性和質量[2]。Rapport等[3]認為生態系統健康(ecosystem health)是指一個生態系統具有穩定性和可持續性,在時間維度上可以維持組織結構、進行自我調節,并且擁有對外部脅迫的恢復能力。宋蘭蘭等[4]認為健康的生態系統具備滿足人類社會合理要求的能力和生態環境自我維持與更新的能力。生態系統健康評價的方法以指示物種法和結構功能指標法為主[5]。指示物種法經驗性較強,且指示物種選擇不恰當會引起評價偏差[6]。結構功能指標法具有更強的綜合性,在生態系統健康評價時能夠將生物學、社會經濟、人類健康、社會公共政策等方面的指標納入評價體系[7-8]。在生態系統健康指標評價研究中,PSR(壓力-狀態-響應)模型[9]、VOR(活力-組織力-恢復力)模型[10]、投影尋蹤模型[11]和BP神經網絡預測模型[12]等,能夠綜合考慮生態系統內在關系,被學者們廣泛應用。如:趙建鵬等[13]基于驅動力-壓力-狀態-響應(DPSR)模型對2010~2020年黃河流域甘肅段57個區(縣)生態系統健康進行評價,發現生態系統問題并提出合理的管理恢復策略;周啟剛等[14]從生態系統活力、組織力和恢復力3方面構建VOR模型,綜合診斷全面蓄水后三峽庫區消落帶的生態系統健康狀況。
綜上所述,當前關于生態健康的評價研究已經形成了較全面的體系,主要研究以某一流域或特殊地區為主,以省為單位進行生態系統健康評級的研究較少。山西省位于黃河流域中游,是實現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一環。因此,本文利用DPSIR模型構建山西省生態健康指標體系,運用綜合評價指數模型從時間和空間上探究山西省及各市2011~2021年生態健康演變特征,并利用障礙度模型對指標體系進行障礙因子分析,最終結果可為山西省高質量發展提供理論依據。
1" 研究區域及數據來源
1.1" 研究區域
山西省(110°14′E~114°33′E,34°34′N~40°44′N)地跨黃河、海河兩大流域,河流屬于自產外流型水系(圖1)。山西省共轄11個地級市,常住人口為3 466萬人。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用水量持續增加,而水資源卻在不斷減少,導致有限的地下水資源被大規模開采,太原、運城等盆地出現較大范圍的地下水超采區,多地不同程度出現了地下水位嚴重下降的問題。此外,山西省位于黃土高原生態脆弱帶,長期以煤炭為主的經濟發展加劇生態環境惡化,大氣污染、水污染問題頻發。山西省也是黃河泥沙主產區之一,2021年山西省8條主要河流控制站懸移質輸沙量,控制面積為83 645 km2,年輸沙量為345.2萬t,年平均輸沙模數為41.3 t/km2,這也造成了嚴重的水土流失問題。
1.2" 數據來源
生態健康評價與障礙因素研究所用到的數據來源于2012~2022年《中國統計年鑒》《山西省統計年鑒》,2011~2022年《山西省水資源公報》等。
2" 研究方法
2.1" DPSIR模型指標構建
DPSIR模型是一種用于探求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關系的概念模型,通過驅動力(D)、壓力(P)、狀態(S)、影響(I)、響應(R)反映指標間的因果關系,映射出生態健康在不同系統層面對社會發展的具體表現形式。
依據DPSIR模型原理[15],結合山西省2011~2021年發展狀況及指標間的反饋關系,構建山西省生態健康指標評價體系,見表1。
2.2" DPSIR指標權重計算
本次研究采用熵權法和CRITIC相結合的組合賦權法計算指標權重,彌補了單一方法計算權重的缺陷,提高了綜合評價的科學性[16]。
(1) 熵權法是常用的客觀賦權方法,基于信息熵的思想,通過計算各個評價指標的權重來量化他們對決策結果的貢獻程度。熵權法計算步驟如下:
數據標準化處理。
正向指標:
x′+ij=xij-minxjmaxxj-minxj
(1)
負向指標:
x′-ij=maxxj-xijmaxxj-minxj
(2)
式中:x′ij為指標標準化后的值;maxxj、minxj分別為指標j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計算第j個指標的熵值Ej。
Ej=-1lnmmi=1fijlnfij
(3)
式中:fij=x′ij/mi=1x′ij;當fij為0時,令fijlnfij=0。
計算第j個指標的變異指數dj。
dj=1-Ej
(4)
計算第j個指標的權重wj。
wj=djnj=1dj
(5)
(2) 變異系數法(CRITIC)又稱標準離差法,是基于指標對比強度與指標間的沖突性來綜合衡量指標權重的客觀賦權方法[17]。計算步驟如下:
計算信息量。
cj=σjnk=1(1-rkj)
(6)
σj=mi=1(xij-x—j)2n-1
(7)
式中:cj為指標j的信息量;rkj為第k個指標與第j個指標間的相關系數;σj為第j個指標的標準差;x—j為第j個指標的平均值。
確定各評價指標權重。
wj=cjnj=1cj
(8)
式中:wj為各指標的客觀權重。
(3) 組合權重計算。將熵權法得到的權重記為w1,變異系數法得到的權重記為w2,將w1和w2線性組合,得到各指標最終的權重值,記為wi。
wi=aw1+bw2
(9)
式中:a和b分別表示主客權重的重要程度,0≤a≤1,0≤b≤1,且a+b=1。本研究認為兩者同等重要,因此a和b均取0.5,權重計算結果見表1。
2.3" 生態健康評價
結合組合權重計算方法,計算DPSIR模型指標的評價指數,計算公式為
DPSIRi=kj=1wjx′ij
(10)
式中:DPSIRi為山西省生態健康準則層的綜合評價指數;k為準則層內指標個數;wj為各子系統指標j的組合權重值;x′ij為第i年指標j標準化后的數據。
根據準則層綜合評價指數計算結果,運用線性加權法計算山西省生態健康綜合指數,計算公式為
DPSIR=mt=1wtDPSIRi
(11)
式中:DPSIR為生態健康綜合指數;wt為準則層的權重,分別為0.180,0.179,0.213,0.218,0.210。
本文借鑒已有研究成果[18],對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響應綜合指數計算結果分別設置了不同等級的判別標準,如表2所列。
2.4" 障礙度模型
生態健康狀況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引入障礙度模型對指標體系進行分析,得到山西省生態健康的主要障礙因素,可為未來發展提供政策導向。計算公式如下:
Dij=(1-x′ij)wj
(12)
Hij=Dij/nj=1Dij
(13)
式中:x′ij是標準化后的值;wj是各指標權重;(1-x′ij)是各指標偏離度;Hij是障礙度。
3" 結果分析
3.1" 山西省生態健康綜合指數
山西省生態健康綜合評價指數如圖2所示。2011~2015年上升趨勢較緩慢,2015年以后生態健康指數增長迅速,實現從2011年亞病態到2021年臨界狀態的轉變,整體增幅偏小。主要原因是2010年國家批復山西省為“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以來,山西省在綠色發展轉型的同時,對于大氣污染、水污染和生態治理的投入逐漸增加,改革效果日漸顯著。
2011~2021年山西省驅動力子系統由0.21增長到0.39,城鎮化率和人均生產總值穩步增長,社會經濟發展為生態健康的改善提供了保障,但研究時段內山西省人口數減少了80萬,總人口持續下降,對城市未來發展構成威脅;壓力子系統呈現顯著增長趨勢,這是由于“十三五”時期山西省大力培育和發展創新型經濟,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行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隨著山西省產業的綠色升級,二氧化硫有害氣體排放量減少了10萬t,大氣環境明顯改善,極大緩解了生態健康壓力;狀態子系統2011~2021年一直處于較差狀態,尤其是2019年,受降雨量和水資源量影響,評價指數最低,這主要是由于降雨分布不均勻,城市間人均水資源量存在較大差異性;影響子系統評價指數呈現波動增長趨勢,省內溫室氣體排放、人類活動強度和人均消費增加對生態健康造成不利影響;響應子系統評價指數從0.39增加到0.58,健康等級從較差效果提高到一般,這一時期山西省實現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2.5倍,污水處理率由81%提高到97%,建成區綠化率提高了7%,水資源利用率降低25%。這些變化表明政府制定合理的政策措施有效地改善了生態健康狀況,社會各方面發展取得長足進步。
3.2" 各市生態健康時空變化
通過山西省各市生態健康指數時間演變分析(圖3),2011~2021年各市均處于上升趨勢。2011~2015年運城市生態健康指數下降最明顯,由0.38降到0.34,主要原因是持續大氣污染與過度水資源開發引起嚴重生態破壞。這一時段運城市二氧化硫年均排放量12.5萬t,2012年水資源利用率達152%。2016~2021年長治市生態治理成效顯著,生態健康指數增長0.22,主要是由于長治市堅定不移地開展治污行動、構筑生態屏障、推動能源革命,把生態建設與產業發展相結合,創造生態經濟型林業發展新模式,為生態健康與經濟發展起到促進作用。2021年底太原市與晉中市率先進入亞健康階段。一是因為兩市在2011年起就領先于其他城市,分別為0.47和0.39,太原市已經處于臨界狀態;二是這一時期太原市和晉中市在污染治理方面取得優異成果,太原市和晉中市可吸入顆粒物濃度分別降低36%和39%;另外,太原市開展了“九河”綜合治理工程,提升了汾河水質,改善城市生態環境。整體來看,近十年來山西省在高質量發展上不斷取得新突破,在轉型發展上蹚出了一條新路,先進綠色產能數量不斷增加,做到生態治理與產業發展互促共融。
由2011、2016、2021年山西省生態健康時空分布圖(圖4)可以看出,2011年除太原市外,其余各市生態健康等級處于亞病態水平,城市間差異不大,省內生態環境問題面臨嚴峻的挑戰。到2016年,其余各市分別進入臨界狀態,生態健康水平顯著提升。到2021年,山西省各市生態健康指數由高到低為:太原市gt;晉中市gt;晉城市gt;長治市gt;陽泉市gt;運城市gt;臨汾市gt;呂梁市gt;忻州市gt;大同市gt;朔州市,11座城市生態健康指數均達到臨界水平,生態健康整體格局為東南部水平較高,北部與西南部水平較低。
通過對山西省各市2021年DPSIR模型準則層分析可知(表3),太原市驅動力和壓力指數最高,表明太原市生態健康對經濟發展的驅動力較強且生態壓力較小,相比之下忻州市驅動力較弱,運城市生態壓力最大,因此兩市需要重點關注生態環境建設。狀態子系統中太原市由于人均水資源量與人均糧食產量遠低于其他城市,導致其狀態子系統指數較低,這說明太原市是缺水城市,應當落實節水優先方針并建設調水工程促進自身發展。影響子系統中晉城市最低,其人均消費與人類活動強度高于其他城市,制約生態健康良性發展。響應子系統指數均處于一般及較好水平,主要是因為污水處理率、建成區綠化率和優質空氣天數等指標顯著提高,改善了山西省生態健康狀況,城市公共服務與居民生活環境也得到相應加強。
3.3" 障礙因子診斷
根據公式(12)和(13),計算出2011~2021年各指標障礙度,障礙度均值結果如表1所列。人類活動強度(X15)、產水模數(X3)、有效灌溉面積(X18)、人均水資源量(X10)和生活用水占比(X5)是排名前五的障礙因子,總占比達到47.6%。
對DPSIR模型指標歷年障礙度變化特征進行分析(圖5)可知,驅動力、狀態和響應子系統障礙度基本保持不變,說明研究時段內山西省生態健康驅動力水平沒有明顯提升,因此要重點關注城市人口變化,通過提高城市競爭力,提供良好的宜居環境,避免人口外流造成的勞動力和人才短缺。此外,研究時段內山西省人均水資源量均值為354 m3/a,屬于嚴重缺水省份,嚴重阻礙了山西省的發展。影響子系統障礙度呈現增長趨勢,研究時段內溫室氣體排放量障礙度漲幅達82.2%,主要是因為經濟發展與煤炭消費仍未脫鉤和可再生能源尚未滿足新增用能需求。壓力子系統障礙度不斷減少,由0.17下降至0.11,與2011年相比,可吸入顆粒物濃度下降34%,萬元GDP用水量下降51.7%,目前生態環境經過治理,水生態環境、大氣環境得到了極大的改善。
4" 結論與建議
4.1" 結 論
本文以山西省為研究對象,通過對山西省及各市生態系統健康進行綜合評價和障礙因子探究,得到以下結論:
(1) 山西省生態系統健康綜合評價指數呈上升趨勢,2021年生態健康等級進入臨界水平。不同系統間存在較大差距,驅動力、壓力和影響子系統指數較高,狀態和響應子系統較低。
(2) 時間上,山西省各市生態健康指數呈現增長趨勢。空間上,山西省地市之間發展狀況差異顯著,太原市、晉中市指數較高,率先進入亞健康階段,大同市、朔州市指數較低,東南部城市領先于北部與西南部城市。
(3) 山西省生態健康評價指標體系中,人類活動強度、產水模數、有效灌溉面積、人均水資源量和生活用水占比是主要障礙因子;影響子系統障礙度不斷增加,壓力子系統障礙度不斷減少。
4.2" 建 議
(1) 針對山西省內各市生態健康指數的差異性,各市應結合自身實際制定合理措施助力山西省高質量發展。太原市作為省會城市,要持續優化產業結構,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深化能源轉型改革,實現生態健康發展,形成集約高效、宜居適度、山清水秀、開敞舒朗的城市發展格局。朔州市、長治市、晉城市和大同市煤礦產量較大,要推動煤炭清潔高效開發利用,加快煤礦綠色智能開采,提高城市空氣質量。同時,煤炭消耗量升高造成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各市要合理調整能源消費結構,持續實施節能減排政策。這些措施,既能促進山西省生態系統健康高水平發展,也可為實現省內“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做出貢獻。
(2) 針對省內人類活動強度、水資源量等主要障礙指標,山西省歷年來煤炭開采量大,對歷史遺留問題進行整治,完成礦坑、礦山等的治理工作,致力恢復礦區生態環境,可以有效降低省內人類活動對生態健康帶來的影響。同時,需要加快構建全省水網體系,打造“三縱九橫、八河連通”的水網布局,增強山西省跨流域調水供水能力,有效解決省內水資源短缺的現狀。此外,大力宣傳節水優先方針,提高全省人民節水意識,通過降低生活用水量、萬元GDP用水量等來緩解用水壓力,綜合促進生態系統高質量可持續發展。
(3) 針對山西省黃土高原生態環境脆弱及水土流失問題,要加大植樹造林力度,提高森林覆蓋率,尤其是忻州市、呂梁市、臨汾市和運城市,通過修建淤地壩、種植水土保持林,減少泥沙流失、加強水源涵養能力,在山西省黃河流域沿線構建生態安全屏障。同時,出臺生態治理修復政策與措施,推動黃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此外,完善水土保持法律法規、加大監管力度,將監管保護貫穿于水土保持全過程,加強人為水土流失防治,進一步鞏固治理成果。
參考文獻:
[1]" 婁保鋒.水生態評價方法探索:以漢江中下游為例[J].人民長江,2023,54(1):24-36.
[2]" 羅鵬,談存峰,齊婷婷.基于PSR模型的黃河流域甘肅段生態系統健康評價及預測[J].水土保持通報,2024,44(3):180-189.
[3]" RAPPORT D J,WHITFORD W G.How ecosystems respond to stress[J].BioScience,1999,49(3):193-203.
[4]" 宋蘭蘭,陸桂華,劉凌.淺析生態系統健康評價研究現狀[J].河海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4(5):539-541.
[5]" 孔紅梅,趙景柱,馬克明,等.生態系統健康評價方法初探[J].應用生態學報,2002,13(4):486-490.
[6]" 王敏,譚娟,沙晨燕,等.生態系統健康評價及指示物種評價法研究進展[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2,22(增1):69-72.
[7]" 吳剛,韓青海,藍盛芳.生態系統健康學與生態系統健康評價[J].土壤與環境,1999(1):78-80.
[8]" 張宏鋒,李衛紅,陳亞鵬.生態系統健康評價研究方法與進展[J].干旱區研究,2003,20(4):330-335.
[9]" 楊訸晴,胡慧琴,張勤旭,等.基于PSR模型的遼河流域盤錦河段生態系統健康評價及其驅動因素分析[J].人民珠江,2023,44(7):80-89.
[10]竇世卿,張楠,靖娟利,等.基于耦合模型的廣東省生態系統健康時空動態變化[J].科學技術與工程,2022,22(27):12223-12232.
[11]周有榮,崔東文.云南省水資源-經濟-社會-水生態協調度評價[J].人民長江,2019,50(3):136-144.
[12]張迪,王彤彤,支金虎.基于IPSO-BP神經網絡模型的山東省碳排放預測及生態經濟分析[J].生態科學,2022,41(1):149-158.
[13]趙建鵬,武江民,賈臘春,等.基于驅動力-壓力-狀態-響應模型的黃河流域甘肅段生態系統健康評價[J].生態與農村環境學報,2024,40(5):602-611.
[14]周啟剛,彭春花,劉栩位,等.基于VOR模型的三峽庫區消落帶2010~2020年生態系統健康評價[J].水土保持研究,2022,29(5):310-318.
[15]俞永梅,張懷春.上海市水資源生態風險評價及驅動因素分析[J].人民長江,2013,44(15):86-89.
[16]陳義平,李敘勇,江燕.武漢城市群生態環境質量評價[J].水利水電快報,2023,44(5):87-95.
[17]李林子,鄧陳寧,詹麗雯,等.長江流域城市綠色發展評價與障礙影響[J].生態學報,2024,44(15):6554-6566.
[18]邱夢,左其亭,馬軍霞,等.黃河流域生態系統分區及PSR綜合評價[J].人民黃河,2023,45(2):20-27.
(編輯:黃文晉)
Evaluation on ecological health in Shanxi Province based on DPSIR Model
LI Yingjie1,2,LIANG Shuaitao1,WANG Shunsheng1
(1.School of Water Conservancy,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Zhengzhou 450046,China;
2.Bank of Zhengzhou Co.,Ltd.,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in the ecological health index and limiting factors in Shanxi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21,an evaluation system including 24 indicators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Driver-Pressure-State-Impact-Response (DPSIR) model to evaluate the ecological health status of Shanxi Province,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of the ecological health of the 11 cities and diagnose the main obstacle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development using the obstacle degree model.The results showed that:①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of ecological health in Shanxi Province has been increasing year by year,shifting from sub-pathological state to critical state;the pressure subsystem has increased most significantly,from 0.34 to 0.63,and the ecological pressure has been reduced significantly.② Temporally,the ecological health index of each city in Shanxi Province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from 2011 to 2021.Spatially,the overall pattern showed that the ecological health levels were higher in the southeastern cities and lower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western cities,Taiyuan City and Jinzhong City first manifested the sub-healthy state in 2021.③ Human activity density,water production modulus,effective irrigated area,per capita water resources,and domestic water consumption were the main obstacle factors.The obstacle degree of the influence subsystem has been continuously increasing,the obstacle degrees of the driver,state and response subsystems remain unchanged,and the obstacle degree of pressure subsystem continues to decrease.
Key words:
ecological health evaluation; obstacle factor; DPSIR model; Shanxi Provi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