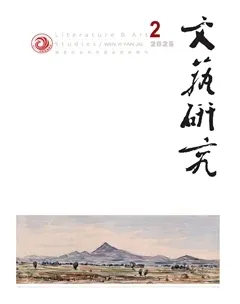公正的記憶何以可能:重釋保羅·利科“記憶的責任”概念
摘要 “記憶的責任”概念在戰后的法國知識界受到廣泛關注,它迎合了受害者在道德層面占據主導地位的趨勢。然而,這一概念的模糊性導致的記憶濫用現象也引發了眾多批評。在此背景下,保羅·利科從關于記憶的責任的爭論出發,建構起公正的記憶的三重平衡。他以弗洛伊德的“哀悼的工作”為基礎提出“記憶的工作”,試圖從認識論層面的迂回來規避記憶的責任在實踐層面的風險,從而在忠實再現過去與償還倫理債務之間實現平衡。同時,他用“作為記憶的過去”取代“作為歷史的過去”,通過改變過去的他者性來促進個體與集體的溝通,力圖在個體見證與歷史書寫之間達到平衡。他也提出在“去-集體記憶”和世界主義的視角下平衡記憶與遺忘的關系,由此轉向一種開放的未來現象學,實現過度記憶與積極遺忘之間的平衡。
作為“二戰”后的倫理反思浪潮的核心人物,保羅·利科在《記憶,歷史,遺忘》一書的開篇便表達了對戰后社會記憶現狀的深切擔憂:“我仍然對某一地方過多的記憶和其他地方過多的遺忘所構成的令人不安的景象感到困擾,更不用說各種紀念活動以及記憶和遺忘的濫用所造成的影響了。”記憶的濫用現象與20世紀90年代以來“記憶的責任”(devoir de mémoire) 概念的泛化密切相關,這也引起了法國、德國等思想家的關注和反思。一方面,以托多羅夫為代表的學者公開批評記憶的濫用現象,反對那些曾經的受害者無限制地擴展“記憶的責任”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乃至從道德高地為自己索取權益;另一方面,利科與楊科列維奇(Vladimir Jankélévitch)、列維納斯等人則堅持保留這一概念,他們認為“記憶的責任”不僅是反思歷史創傷的認識論要求,更是重建戰后社會倫理秩序的重要基石。
關鍵問題在于,利科在對“二戰”記憶的單一性及其引發的濫用現象深感憂慮的同時,為何堅持保留“記憶的責任”這一備受爭議的概念?他又如何以此為切入點,試圖建構一種公正的記憶(juste mémoire)?本文首先從記憶的責任的起源和爭論出發,分析其合理性及問題所在,探究利科如何通過語法解構對其進行再闡釋,論述他在此基礎上提出的補充性概念“記憶的工作”(travail de mémoire),以探索忠實再現過去與償還倫理債務之間可能的平衡;然后討論記憶的工作在精神分析領域的適用性和在歷史學層面的有效性,從而進一步分析利科在個體見證與歷史書寫之間尋求的動態平衡;最后聚焦于利科對記憶與遺忘兩種極端狀態采取的調和策略,探討他在建構公正的記憶的過程中追求的過度記憶與積極遺忘之間的平衡。利科對這三重平衡的深入探討,不僅回應了記憶濫用的倫理困境,也構建了通向公正的記憶的重要理論路徑。同時,本文結合《波斯語課》《美麗人生》《索爾之子》《鋼琴家》等電影對極端歷史事件的敘述與重現,展現公正的記憶的倫理實踐可能性,凸顯利科思想在戰后記憶文化中的理論貢獻與實踐意義。
一、“記憶的責任”:起源與爭論
“記憶的責任”在“二戰”后風靡歐洲,并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成為一種共識性的社會指稱,但這一概念實則擁有悠久的歷史,包括宗教、政治、文化等多個維度。追溯其詞源可以發現,法語中的“責任”(devoir) 與“債務”(dette) 享有相同的拉丁語詞根dēbēre,意指“當我虧欠某人某物時,我就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在這個意義上,記憶的責任指涉的是對過去債務的償還,承擔因歷史負累而產生的義務。它自誕生之初便是多義的,關聯于“強制的記憶”(mémoire obligée)、“被要求的記憶”(mémoirecommandée) 等。“二戰”后,“記憶的責任”成為一種強迫性、神經質的甚至具有道德約束力的口號,“當個人或群體所經歷的事件具有特殊性或悲劇性時,這種記憶的權利就變成了一種責任:記住,見證”。在戰后社會,這種責任被理解為對歷史真相的銘記,對歷史事件的受害者給予道德上的優先性,主動承擔和償還對過去的負債,擔負起道德、倫理和社會的責任。
記憶的責任的合法性主要體現于兩點。一是記憶的責任作為道德承諾,從實踐層面宣布不再重蹈歷史的覆轍,它要求將歷史事件的意義納入當下的考量,以防止此類事件在現在乃至將來再度發生。正如對戰爭的見證構成了現代性建設的“絕對必要”,在此意義上談論記憶的責任及其強制性要求是避免負面的歷史事件再次發生的唯一可能。二是記憶的責任試圖以道德義務的形式重新關聯過去與現在,通過將“記憶”視作道德符號,過去的“過去性”以被命令的形式重新被放置于現在的“現在性”中。記憶的責任重視對過去的傳承,致力于維系群體的同一性與完整性,從這個層面來說,其合法性基于歷史完整性這一前提:承認某些奠基性、變革性乃至破壞性的事件對現在和未來的影響,這反映的是對歷史整全性的要求,“我們對過去所負擔的債務反映了我們對于完整性的關注:通過努力將我們的生活植根于集體性的過去,我們渴望生存在一種完整性中”。這種進步的線性歷史觀將過去、現在與將來視為一個有機整體,通過對缺席者的回憶、再現、表述和重構,記憶的責任與對過去的見證、講述以及杜絕悲劇再次發生的雄心壯志相關聯,一種強大的個體歸屬感將歷史的諸多時刻統一起來。這使得對過去的真實性的探究逐漸被弱化,記憶研究的重點轉向對受害者倫理債務的償還。在這個層面上,“記憶的責任”這一具有強制性的表述使我們感到安心而非焦慮,“只要我們保持對過去的記憶,就可以避免惡的回歸”。
對缺席者的回憶、再現與重構不僅是為了保留對逝者的記憶,更是為了承擔歷史事件的道德債務。這種對記憶的責任的追求在《波斯語課》的結尾得以充分展現,并達到情感與敘事的高潮。影片講述了比利時猶太人吉爾斯為了在集中營里生存,謊稱自己是波斯人,因此被納粹軍官科赫選中,后者計劃在“二戰”結束后前往德黑蘭開餐館,吉爾斯被要求在兩年內教會科赫波斯語。對波斯語一無所知的吉爾斯偶然間獲得了抄寫猶太囚犯名冊的機會,于是他以這些囚犯的名字為詞根虛構出一門語言,借此蒙騙科赫。影片結尾呈現了兩次高潮:一次是在伊朗邊境,科赫用自認為已經掌握的“波斯語”回答海關人員的問題,殊不知他實際上復述的是那些被他迫害的猶太人的名字;另一次是吉爾斯成功脫險后,面對盟軍的詢問,他逐一回憶起2840個猶太人的名字,當這些名字被低聲念出時,逝去的生命仿佛再次出現在歷史舞臺上。吉爾斯以獨特的經歷完成了一種別樣的歷史見證,而科赫則通過陰差陽錯的語言習得,意外記錄并傳遞了人生中最羞恥的罪行。這種雙重見證傳遞了受害者和施害者雙方的倫理責任,也為記憶的責任的合法性提供了有力辯護。
記憶的責任在戰后風靡的主要原因是它迎合了受害者在道德層面占據主導地位的趨勢,但其含義的模糊性以及由此導致的記憶被操控、被濫用等問題引發了廣泛批評。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以皮埃爾·諾拉、讓-皮埃爾·克萊羅、阿爾弗雷德·格羅斯、茨維坦·托多羅夫、亨利·羅素、喬治·本蘇桑、讓-米歇爾·肖蒙、艾瑞克·柯南等為代表的學者開始公開反對“記憶的責任”概念的泛濫,他們提出一系列觀點,如“ 紀念性的迷戀”(obsession commémorative)、“ 記憶的病理學”(pathologie demémoire)、“ 受害者競爭”(concurrence des victimes)、“ 記憶的濫用”(abus de lamémoire)、“被操控的記憶”(mémoire contr?lée),以此反對記憶的責任帶來的消極影響,他們的批評立場也逐漸成為當代法國思想界的主流。記憶的責任遭受眾多批評的主要原因在于,它跳躍性地指向道德的要求而非認識論的工作。相較于記憶的內在性、表象的不徹底性等特征,記憶的責任首先從道德層面、倫理層面提出要求,甚至成為更加強硬的由意識形態主導的政治命令。事實上,如果以一種強制性的命令來要求記憶,那么如何實現從記憶現象學到歷史認識論的過渡?在這個層面上,具有排他性的“記憶的責任”概念構成了對歷史研究的自由表達的威脅。對此,有些歷史學家提出“歷史的責任”(devoir d’histoire)這一新的表述來與記憶的責任相抗衡,其目的是使認識論層面的歷史研究優先于倫理學層面的記憶命令。
利科也曾揭露記憶的責任的問題,“今天,人們常常援引‘記憶的責任’的概念,其目的是縮短歷史批判性分析工作的時間,冒著將特定歷史群體的記憶封閉起來的風險,將記憶凝固在受害者的情緒中,使其失去正義感和對公平的追求”,“對于記憶的要求可能會被理解為一種邀請,邀請記憶繞過歷史研究的工作”。對此,多斯進一步指出:“利科區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追求:歷史追求真實性,記憶追求忠實性。他同時強調,對于記憶的多疑會導致歷史研究的神圣化;然而,如果歷史完全被記憶覆蓋,就會忽略解釋和理解這一至關重要的認知層面。”因此,當我們以“責任”為要求挾制記憶從而使倫理要求占據主導地位時,就有可能將過去凝固在一個封閉的模式中,而忽略歷史方法可能帶來的細微差別和復雜解釋。利科認為,強制性的記憶雖然可以引導出對記憶的善用,但也會不可避免地出現對記憶的濫用。他在《記憶,歷史,遺忘》中詳細分析了多種記憶濫用的形式,包括“受阻的記憶”(mémoire empêchée)、“被操控的記憶”(mémoire manipulée) 以及“被過度要求的記憶”(mémoire abusive?ment commandée)。
托多羅夫在著作《記憶的濫用》(Les abus de la mémoire) 中也指出記憶濫用的后果:“過分沉溺于過去的原因在于它可以讓我們將注意力從當下移開,同時為我們提供問心無愧的滿足。”這種尚未被反思的重復使歷史群體的記憶被禁錮在受害者的憤怒和痛苦中,也使某個群體的復雜經歷被單一化,以維護他們作為受害者的地位,賦予他們某種特權: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曾經是受害者……因為成為受害者賦予了你抱怨、抗議和索賠的權利;除非與你斷絕一切關系,否則其他人必須對你的要求做出回應。與接受賠償不同,保持受害者的身份更有利:與短暫的滿足感相比,你保持了永久的特權,確保了他人的關注,因此也得到了他人的承認。
受害者身份不僅帶來話語權,也在社會共識層面形成相應的道德義務,因為他人一旦承認某群體為受害者,就必須回應受害者的需求。這種權利與義務的不對稱性,使受害者身份成為一種具有優勢地位的社會資源。托多羅夫質疑,“記憶的責任”概念可能在無意中削弱了對歷史復雜性的深入探討,將多維的歷史研究簡化為單一的受害者敘事,并可能演變成重新分配權利和利益的工具。
不僅如此,記憶的責任在表述上的多義性和含混性使“每個人都可以從中看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從而讓人懷疑這一概念可能是偽造的”,這體現出語言的表演性特質,而該表述隨后也逐漸發展成政治話語的一部分。在當代法國,那些依然談論“二戰”、高喊“銘記歷史責任”的人通常會遭受巨大的敵意,這種情況可見于克萊羅對利科在《記憶,歷史,遺忘》中堅持談論“記憶的責任”概念的嘲諷:“盡管他(利科——引者注) 在書中意識到這一概念在認識論和實踐維度所遇到的困難,但是他仍然保留這一概念,堅持這一令人尷尬的立場。”實際上,克萊羅對利科、楊科列維奇、列維納斯等強調償還過去負債的學者的負面態度并不奇怪,因為在戰后社會,媒體宣傳、政治競演以及宗教演講使記憶的責任成為廉價且實用的口號,本蘇桑將其類比為一種“新的公民宗教”。記憶的責任作為紀念“二戰”猶太人大屠殺這一特定歷史事件的產物,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偏離了最初的所指,演變為一種“政治武器”,更何況“出于各種不同的原因而使死者復活是世界上最廣泛的和共同的誘惑”。“記憶的責任”概念的泛化造成了它在實踐層面的偏差,過度政治化的記憶引發了理論與實踐中的諸多問題,“去-政治化”由此成為眾多思想家反思的主題。
概言之,“記憶的責任”概念的合理性及其潛在的風險,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忠實于歷史真實與償還過去負債之間的張力以及可能引發的理論困境。在這一框架下,記憶的責任更傾向于優先償還歷史負債,進而在倫理訴求與認識論要求之間制造了緊張關系,因為這種偏向直接觸及了歷史研究的核心問題,可能弱化對歷史復雜性和事實真相的探究,甚至可能動搖認識論基礎。因此,記憶的責任遭到法、德歷史學家等多方的批評和質疑。利科對于記憶的責任的態度顯得尤為復雜,他在肯定其倫理意味的同時,也對可能造成的濫用保持警惕。這種復雜態度耐人尋味:為何像利科這樣頗為強調倫理重要性的哲學家會對具有強烈道德訴求的“記憶的責任”概念持保留意見?他又如何調和倫理學與認識論,從而提出自己的應對之道?這些問題不僅是理解利科思想的關鍵,也關涉更廣泛的記憶與歷史研究的范式轉向。
二、“記憶的工作”:一種補充性方案
在法國思想界,談及記憶的責任時必然會提及利科《記憶,歷史,遺忘》,他最早提出“將記憶變成一種責任是否合法”的問題。相較于托多羅夫對記憶的責任引發的濫用的批判,利科作為對記憶的責任的“倫理-詩學”批判的代表,在一定程度上承認其合法性。利科認為,在正義的觀念的指導下,記憶的工作可以通達公正的記憶,開啟現象學反思的可能性,同時他也警惕“記憶的責任”概念可能被過度意識形態化或工具化。這種矛盾的立場反映了利科在批判性反思和回應倫理訴求之間的搖擺。
利科關于記憶的責任的曖昧態度招致了眾多批評。比如,米里亞姆·比恩奈斯托克(Myriam Bienenstock) 曾公開質問:“今天,一些法國哲學家和知識分子在面對‘記憶的責任’這一問題時會表現出反對甚至蔑視的態度,利科的這本書(《記憶,歷史,遺忘》——引者注) 是否應該對此負責?哪怕只是負部分責任?”與之類似,讓-克勞德·莫諾(Jean?Claude Monod) 也指出利科的矛盾態度:“一方面,利科探求如何滿足‘記憶的責任’的要求(同時對這一表達方式持保留意見),尤其是對于大規模犯罪的受害者償還債務的要求;另一方面,他想知道如何跳出對過去傷痛的執念,這種執念表現為一種‘揮之不去’或‘癡迷’,甚至是被過去‘俘獲’和意識形態的工具化。”莫諾和比恩奈斯托克的批評都源自對利科模糊立場的不滿,尤其是利科在提到記憶的責任時表現出的搖擺態度。筆者認為,這實際上與利科一貫的調和迂回的哲學思想密切相關。盡管利科對記憶的責任持批判態度,但他并未完全否定其合理性,相反,他在此基礎上提出“記憶的工作”這一補充性方案,旨在彌補記憶的責任在認識論層面的不足。通過這種互補關系,利科試圖在忠實再現過去的認識論要求與償還歷史債務的倫理要求之間建構一種動態平衡。
利科認為,記憶的責任作為一種強制性的命令,實則在語法層面存在悖論:
首先,我們應當對“記住”這一命令所構成的語法悖論感到驚訝。如何理解“你將記住”這一表述?也就是說,如何能以未來時態表達記憶這一被視為過去守護者的行為?更為嚴峻的問題是:如何能夠說“你必須記住”這一命令?你必須以命令式來調動記憶,但記憶應當像亞里士多德在《論記憶》中所說的那樣,以一種自發的情感浮現的方式重現。
此處,利科從兩個方面探討了記憶的責任在語法層面的悖論。一方面,從時態來看,自亞里士多德以來,記憶就與過去有著內在的聯系,而記憶的責任雖然與過去密切關聯,但同時以一種強勢的未來時態呈現出來,“說‘你要記住’(tu te souviendras),這同樣是說‘你不要忘記’(tu n’oublieras pas) ”。這一源自過去的道德命令表述的卻是對未來的要求,其中隱藏著一種矛盾,“我們強加給自己一個記憶的道德命令,以便使我們復活那遙遠的、我們不再認同的過去。我們援引這段歷史不是為了從中獲得靈感,相反,它是一種排斥物,是不公正和犯罪的代表。我們尋求接近過去以便拒絕它們。我們把過去刻在我們的意識之中,只是為了與它們保持距離”。這一將來時態與過去記憶的矛盾也在《摩西五經》中有所體現,尤其是在《申命記》中,記憶的責任通過將來時表達了對記憶的持續的倫理召喚,例如,“你也要記念你在埃及地作過奴仆”,這一命令通過將來時的記住來陳述銘記過去的要求,這種時態上的變化揭示了過去與未來之間的倫理張力。
另一方面,利科提問,自發性的個體記憶如何能被集體的強制命令規訓?這一問題基于一種傳統的記憶共識:個體記憶是自發的、情感的、想象的和難以控制的,而集體記憶是社會的、客觀的和可控的。值得注意的是,利科對“集體記憶”概念表現出一種頗為謹慎的態度。他承認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 等人倡導的集體記憶的必要性,記憶的責任與哈布瓦赫所謂的“社會框架”有關,并且調整社會框架時必然也需要調整強制記憶的內容,這些非私人性質、非個體的記憶在引起公眾關注和實現特定政治目的上發揮了積極作用。然而,他也認為集體記憶在實踐層面容易導致記憶的濫用和誤用,它會遮蓋個體記憶的多樣性,以同質化、單一的道德要求或政治命令來規訓紛繁復雜的個體記憶。而記憶的責任正存在這樣的風險,即用同質化、集體、強制性的道德命令來規訓多元、自發的個體記憶。利科對“記憶的責任”的雙重語法解構經常被誤解為是對這一概念的徹底否定,“伯納德-亨利·萊維(Ber?nard?Henri Lévy) 和巴迪歐等人認為,利科同歷史學家合謀,主張用‘記憶的工作’來替代記憶的責任”。然而,筆者認為,利科對記憶的責任的語法解構實際上是為提出記憶的工作奠定基礎,他將后者視為前者的補充性方案,旨在彌補記憶的責任在認識論層面的不足,從而尋求一種更加合理的概念框架來均衡記憶在認識論維度和倫理學維度的雙重要求。
利科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討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經由80年代的《時間與敘事》第二卷《虛構敘事中時間的塑形》、90年代的《作為一個他者的自身》和21世紀初的《記憶,歷史,遺忘》,他持續探索并深化對精神分析的興趣。記憶的工作實則基于弗洛伊德的“哀悼的工作”(travail du deuil)概念,后者旨在揭示個體在失去所愛之物后借由心理活動應對悲痛的機制。哀悼的核心在于解除對失去對象的情感依附并撤回力比多,其中盡管伴隨著痛苦和沖突,卻是個體為了恢復心理平衡必須付出的主觀努力。在哀悼的工作的過程中,個體逐漸接受失去對象不再存在的現實,轉而將力比多投入新的關系或目標,從而適應新的現實。與此相似,記憶的工作試圖借助歷史學批判,使過去的痛苦記憶從當下的情境中解脫出來,將過去的事件置于實踐性反思的客體位置上,從而中和回憶者對苦難的創傷情感,如痛苦、怨恨、不甘、憂郁,以實現他們關于創傷事件的平和的記憶,這是一種始終處于動態過程中的未完成狀態。
《美麗人生》以溫情的敘事方式揭示了記憶的工作對極端歷史創傷的緩和作用,塑造了一種平和而深刻的回憶機制。猶太青年圭多以自己的幽默與機智贏得了多拉的愛情,兩人克服階層阻力組建了幸福的家庭。然而,“二戰”爆發后,圭多一家被送入集中營,在這個極端環境中,圭多通過謊言將恐怖的集中營生活偽裝成一場冒險,為兒子構建了“游戲”的世界和相對安全的心理環境。他將集中營的暴行重新編碼為游戲規則,掩蓋了毒氣室、苦役和死亡的真實意義,使兒子在最殘酷的環境中依然保持童真的笑容。這種敘事策略不僅是父愛的體現,更是一種對創傷記憶的主動調適,將現實中無法承受的痛苦轉化為更容易被接受的虛構經歷。影片通過這種敘事重構,展現了個體記憶與歷史創傷的復雜關系,正如利科以記憶的工作來強調記憶的敘事化可以為主體提供重新理解創傷的路徑。圭多的敘事實踐并非簡單的逃避,而是有意識的介入:它將不可直面的苦難包裹在溫情的外殼中,在情感層面緩和創傷。這種介入不僅使兒子免于心理上被摧毀,也賦予他對父愛和人性力量的深刻記憶。通過這種創造性的記憶實踐,《美麗人生》可以被視作記憶的工作在藝術中的經典例證,它超越了對戰爭暴行的直接控訴,轉而以柔化創傷記憶的敘事方式來展現人類在最絕望的環境中重新找到生命意義的能力。這種敘事的迂回為觀眾提供了另一種反思歷史的視角,彰顯了藝術在處理歷史創傷時的深遠力量:銘記并非必須直面痛苦,重構記憶也是一種治愈的途徑。
“記憶的工作”試圖將記憶置于反思的距離中,調和個體的脆弱情感,以喚起回憶并加以批判性地審視,“這一概念包含認識論的要求、精神分析的工作和歷史學批判的警醒”。一方面,它突破了將記憶的責任局限于忠實再現過去的框架,避免了“責任”中隱含的正義、公平等強制性的道德律令,旨在消解記憶的濫用和操控等對歷史真實性的扭曲;另一方面,它致力于尋找一種平衡,在歷史的真相和對受害者的倫理關懷之間尋找一種協調的方式,從而將對過去的痛苦記憶沉淀為平和的記憶,“平和的記憶的目的不在于消除過去的張力,而是解決怨恨的邏輯并終止暴力的傳承”。在這個層面上,平和的記憶代表一種理想狀態,即終止暴力的傳承、繼承過去的遺產、償還歷史的負債,并在沉痛的過去和現實間建立一種連續性的關系。多斯認為,利科試圖以認識論層面的記憶的工作來進行必要的迂回,在這一框架下,被記憶的責任忽視的認識論維度通過記憶的工作得到補充,利科也由此在忠實再現過去與償還倫理債務之間建構起一種平衡。
公正的記憶指向具體的歷史事件,而事件的單一性、特殊性使得對公正的記憶的討論既不能被簡化至單純的歷史維度,也不能被完全剝離道德維度。在討論公正的記憶時,應在歷史認識論的基礎上構建一種記憶的倫理學,從而規避記憶濫用的風險。在這一語境下,利科通過兩個對比來實現忠實再現過去與償還倫理債務之間的平衡。首先,在實踐維度上,利科通過對比“劑量”(dosage) 的過量與不足來尋求相對準確的記憶:公正的記憶是相對于托多羅夫所說的記憶的濫用而言的,而公正與精準的“劑量”密切相關。“這種精確性也可以從準音樂的或者準美學的角度來理解:公正的記憶就是聽起來準確的記憶,它避免了夸夸其談、媚俗、惡趣味、陳詞濫調……避免虛假的因素。”與之相對的則是不準確或病態的記憶,包括對記憶的操控、涂抹、篡改。其次,公正的記憶在倫理維度上指向對過去的承認和負責,在道德維度上則指向對他異性的考量,包括償還對逝者的負債、給予受害者以道德上的優先性。考慮到托多羅夫談及的受害者利用自身倫理身份過度索取的情況,利科主張從一種積極的主體性出發,“將主體從自我中心中解脫出來,從對現在和未來的擔憂中解脫出來”,堅持給予受害者道德上的優先性,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在利科看來,記憶的責任是個體對他者的責任,這種責任不能要求他者給予同等的回饋,這也是利科否認存在遺忘的責任的原因。
利科提出記憶的工作,將其作為對記憶的責任的補充性方案,二者在語言層面處于雙重運動的過程中,“一方面是將過去代入現在,另一方面是將現在代入歷史”。在此基礎上,一種交互性平衡被建構起來:在認識論層面上,記憶的工作旨在療愈創傷以實現準確的記憶,而這種記憶的表象力圖忠實于過去的事件;在實踐層面上,利科試圖在記憶的濫用與善用之間尋找平衡,以引導出均衡的記憶;在倫理層面上,記憶的責任賦予他異性的受害者道德上的優先性,為受害者主持公道并償還過去的負債,“記憶的責任就是通過記憶,公正地對待每一位異于自身的他者的責任”。通過記憶的責任和記憶的工作的交互作用,利科在認識論、實踐和倫理三個層面實現了某種平衡,這構成了實現公正的記憶的必要條件。
三、記憶的敘事:見證與歷史
之所以對公正的記憶、記憶的責任、過去的債務等方面的討論總是被置于宏大的敘事框架中,是因為對多元化的個體記憶而言,缺乏明確的標準來證明某人的記憶比其他人更公正,公正必然指向他異性、多元和復數。歷史學家在研究創傷性事件時,經常面臨著將歷史研究與精神分析相聯系的巨大誘惑。對此,雅克·勒高夫(JacquesLe Goff) 曾警示應對這種誘惑保持謹慎。他認為,雖然精神分析在解釋個體創傷時具有積極作用,但其概念未必適用于集體,若是直接將這種框架應用于集體性的歷史研究,可能會忽視歷史與集體經驗的復雜性與多維性。上文提及記憶的工作基于哀悼的工作,如何在集體領域中保持個體相關概念的有效性,成為利科面臨的主要挑戰。利科對這個問題的回應不僅是對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記憶與歷史之間的張力關系的回應,也體現了他在個體見證與歷史書寫之間尋求平衡的努力。
在精神分析理論中,創傷記憶或被壓抑的記憶只有經由漫長的敘述才能轉化為鮮活、真實的記憶。然而,這一轉化有時難以進行,尤其是在面對像“二戰”這樣的歷史創傷時,幸存者的回憶常常受到復雜歷史事件和個體創傷情感的影響,形成一種無法敘述的創傷。利科在《哲學人類學》(Anthropologie philosophique)一書中指出,曾經存在但現已不再存在的事件使回憶者產生對當下世界的陌異感,這種痛苦的感覺導致他們的個體經驗無法被交流和溝通,因而無法成為宏大敘事的一部分。他認為,這一狀況的根源在于回憶者無法區分多重時間層次,導致在他們的回憶過程中,過去似乎仍處于當下的“在場”狀態,這種創傷狀態源自一種時間上的混亂。在這種情況下,精神分析治療不能僅是情感的疏導,還必須納入時間因素,尤其應穿越過去、現在、將來三重時間。通過時間的分層與轉換,個體能夠逐漸釋放被壓抑的記憶,過去的創傷不再直接占據當下的情感經驗,而是在時間的框架中得到重新構建和理解。在這個意義上,利科將精神分析的范疇還原為一種時間本體論。
利科在某種程度上和海德格爾持有相似的時間觀,他們都認同時間性對于此在在世界中存在的重要性,“時間性不僅構成我們作為存在者的主要特征,而且是最能表明存在者與存在本身之間關系的特征”。利科認為,相較于奧古斯丁的三重離散的時間結構,海德格爾將過去、當下和將來的三重時間結構連接起來,“把將來性置于‘向死而在’的標志下,從而將自然和歷史的無限時間置于死亡有限性的殘酷法則之中”。然而,利科也指出這一時間結構的內在問題,“由于‘向死而在’的標志性特征,未來從一開始便獲得了優先地位,這種優先性將影響時間三個維度的統一”,同時他反對將歷史局限于對過去的回溯性特征,“一種把過去作為一種‘完結的’(fertig) 客體和死亡的時間來看待的歷史認識論對于一種侵擾集體歷史性的體驗也是不合適的”。
利科承認三重時間維度的同等源初性,相較于海德格爾的封閉的時間結構,他主張向一種開放的將來性的現象學過渡。他認為,與其關注死亡,不如關注人類在時間中的負債狀態。“債務”不僅是物質上的欠債,更是歷史、道德和記憶上的責任。他提出“向債務而在”(être?en?dette) 概念,將其作為過去性與未來性之間可能的聯系。過去仍然存在于現在的“分層”時間中,過去的事件和責任并沒有隨著當下的不在場而完全消失,而是在現在的時間中存在,并且通過多層次的時間結構影響著現在和未來。希伯來語的《圣經》在語法上沒有區分過去、現在和未來,而是區分“完成的”和“未完成的”兩種狀態,前者指向過去,后者指向現在和將來。債務作為“未完成的”任務并非負擔,而是可以成為意義的源泉,成為重新審視和理解過去的多元記憶的重要路徑。這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解人類存在和時間關系的視角,“時間性構成了記憶和歷史指涉過去的生存論前提”,“債務”則成為記憶與歷史指涉將來的倫理關鍵詞。作為一位“債務哲學家”,利科試圖將古希臘的邏各斯哲學傳統同猶太教-基督教傳統相結合,即將哲學的真理性同記憶的忠實性相結合,從而勾勒出實踐智慧的道路。
利科以“作為記憶的過去”替代“作為歷史的過去”,這一概念轉換使過去的他者性發生變化,過去從歷史的客觀存在轉變為主體化過程中具象化的“肉身”(chair),“這一‘肉身’的范疇意味著,在‘此在’的解釋學中,需要跨越一種邏輯鴻溝,這一鴻溝存在于‘操心’的存在維度與事物的存在方式之間,而事物的存在方式涉及一切已知且可操控的事物范疇”。利科為“肉身”這種特殊化的生存論范疇開辟了新的空間,使“過去”不再是抽象的概念或他者,而是具體、有形的主體。這種視角轉變也順應了20世紀90年代的“記憶轉向”潮流,記憶研究將注意力從宏大敘事轉向“見證”(témoignage)、從記憶符合論轉向承諾-信任的互動關系,具有明顯主體性色彩的“證詞”成為從歷史向記憶過渡的中間結構。《索爾之子》即為“見證電影”的杰出代表。影片伊始,索爾發現了一具年輕男孩的尸體,并執意認為這是自己的兒子。盡管身心瀕臨崩潰,他仍不顧一切地堅持為男孩舉行一場完整的猶太葬禮。這一信念驅使他冒著極大風險尋找一位拉比以完成葬禮儀式,甚至因此放棄了同胞的反抗計劃和自己的生存機會。影片采用緊湊的單一視角,鏡頭始終緊隨索爾,以長鏡頭的形式將觀眾牢牢嵌入索爾的處境。這種局限性的敘事策略不僅制造出強烈的壓迫感,也讓觀眾如索爾的同伴般切身體會到集中營的殘酷現實與無盡的死亡威脅。通過這種沉浸式體驗,觀眾不僅見證了索爾面對的外在暴力,還深入感受到他的內心掙扎與情感困境。更為重要的是,影片通過細膩的敘事和強烈的視覺表達,將那些被歷史遺忘的個體與事件重新拉回公共記憶的場域。索爾為男孩舉辦葬禮的執念不僅象征了對生命尊嚴的堅持,也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一種見證行為:在試圖抹去生命痕跡的暴力機制中,他以個人的行動為無數無名者留下記憶的印記。影片中交織的見證片段通過索爾的單一視角被串聯起來,完成了對集中營歷史的重新詮釋與構建。
見證同時裹挾著個體記憶與集體敘事,利科以此為基礎思考記憶與歷史的雙重關系:一方面,證詞使相似關系問題被信任關系問題取代,記憶通過對證詞的參照成為歷史的母體;另一方面,證詞被檔案化之后,過去不再“被體驗”,歷史因其批判功能而在記憶研究中被賦予優先地位。但歷史并沒有擺脫想象對真實性的負面影響,“歷史學的批判活動沒有消除人們可能被錯誤的證據所欺騙的嫌疑。歷史學里的真相因此仍然無法確定,它一直都處于改寫的過程當中”。歷史學成為不斷被建構的開放領域,它指向的并非絕對的定義或完全的客觀存在,而是更廣泛的共享的經驗。利科以彼得·斯特勞森(Peter F. Strawson) 的“個體”(individuel) 概念為基礎,提倡“預先敞開向所有語法人稱(甚至不定人稱:我們on,任何人quiconque,每個人chacun) 歸因的空間”,從語言歸因的角度發展出記憶的多重歸因,“記憶是過去的事物在精神中的存在及對這種存在的探尋,它原則上可以歸屬于所有的語法人稱:我、她/他、我們、他們等等”。這一多重歸因的立場對于歷史事件的見證以及歷史撰寫至關重要,隨著宏大敘事的瓦解,碎片化的記憶書寫相互碰撞,復數的記憶相互沖突,而不必服務于特定的歷史群體或意識形態。同一個事件可以有多個不同的回憶者,他們相互交流和補充,從不同角度打開一個開放、論辯、公共的空間。
莫諾在利科思想的基礎上主張一種去中心化、去邊界感的記憶,“只有在不將‘集體記憶’與我們立即想到的形象聯系在一起的前提下,才可能存在‘公正的記憶’,也就是說,不將這種記憶與一個統一的集體主體(sujet collectif unifié) 相聯系,在政治上也是如此”。為了修正托多羅夫對集體記憶的批評,“去-集體記憶”顯得尤為必要。莫諾提倡將對公正的記憶的反思與世界主義的關切(considération cosmopolite)相結合,只有在不與特定的集體記憶相關聯的情況下、在去中心化的世界主義的視角下,我們才能思考公正的記憶。多元、開放、復數的個體見證與單一、宏觀的歷史書寫之間的張力,構成了記憶研究的核心議題。個體見證常常呈現出不同的視角和情感色彩,而歷史書寫則試圖通過統一的敘述來構建連貫的過去,二者的矛盾與交織揭示了公正的記憶面臨的挑戰。利科通過三重時間觀的轉換,確立了記憶的工作在集體層面的合法性。他將時間性作為記憶和歷史指涉過去的生存論前提,并通過“向債務而在”將“作為記憶的過去”轉變為面對具體他者的責任,順應了記憶研究的“見證”轉向。
綜上,利科進一步探討實現公正的記憶所要達到的個體見證與集體書寫之間的平衡。他主張在“去-集體化”“去-政治化”的視角下,重新審視個體與集體、記憶與歷史的關系,從而在沖突和對話中尋找平衡。通過這一努力,公正的記憶不僅能避免集體敘事的片面性,也能尊重歷史中個體記憶的復雜性,這種平衡使公正的記憶成為一種倫理實踐,既反映了個體的創傷經驗,又滿足了集體的歷史書寫需求,為記憶與歷史之間的張力提供了和解的可能性。
四、過度記憶與積極遺忘
在烏托邦的設想中,公正的記憶基于一種純粹量化的正義觀,通過對記憶的全面保留來完整再現歷史與經驗。“遺忘被視為禁忌,甚至被視為是一種錯誤”,這種記憶模式假定,唯有無差別、無選擇地保留每一段記憶,才能確保對歷史的忠實再現與再分配,從而彌補歷史的斷裂與空缺。然而,利科認為,公正的記憶實際上必須在記憶與遺忘之間找到動態平衡。杜絕遺忘不僅從人的生理構造而言難以實現,甚至可能導致記憶的病態化。在《記憶,歷史,遺忘》中,利科借用博爾赫斯的短篇小說《博聞強記的富內斯》(Funes, the Memorious),批判了這種“記住一切”的幻想。博爾赫斯生動描繪了一個不會遺忘的個體如何被無法承受的記憶壓垮,最終喪失正常的生活能力。富內斯在遭受意外后,記憶能力變得非常強大,以至于能夠記住每一片樹葉、每一絲風的吹動,甚至是事物腐爛的具體過程。富內斯的大腦如同巨大的數據庫,存儲著無盡的信息,但他無法從中概括和抽象出有意義的模式或概念。歸納能力的匱乏使富內斯的生活陷入瘋狂和愚昧,“他不費多少力氣就學會了英語、法語、葡萄牙語、拉丁語。但我認為他思維的能力不是很強。思維是忘卻差異,是歸納,是抽象化。在富內斯的滿坑滿谷的世界里有的只是伸手可及的細節”。無用的記憶堆積成無序的混沌,它們既無法被遺忘的篩網過濾,也無法被思維的工藝塑造。這些記憶無法被組織成有序的體系,最終使富內斯變成一個被動、機械化的記憶存儲器,只有當他的生命終結時,這些記憶才會消散。富內斯的記憶是一種百科全書式的靜止記憶,其特征是記憶主體無法參與對記憶內容的選擇、詮釋與重構,這種記憶形式展現出一種僵化的“死的記憶”(mémoire morte),缺乏靈活性和創造性。
自柏拉圖以來,記憶被分為“回憶”(anamnèse) 和“憶技”(hypomnésie) 兩類,前者指靈魂通過回憶獲取知識的能力,強調記憶主體的主動性和對意義的內化;后者則涵蓋所有幫助記憶的外在工具、技術和物質手段,表現為一種被動、機械的記憶方式,重在儲存與提取,服務于實用性目標。這種外化于靈魂的記憶形式因其機械性和重復性,常被視為對創造性記憶的壓制。憶技在弗朗西斯·耶茨(Frances A. Yates) 的經典著作《記憶之術》(The Art of Memory)中得到了系統闡述。耶茨通過探討歷史上的各種記憶技巧,揭示出人類為了對抗遺忘而設計的記憶體系,這些體系往往通過視覺化和結構化的方式來強化記憶。然而,這種方法雖然能夠顯著增強記憶的容量,卻也具有一定的強制性,迫使個體不得不機械地記住大量信息,進而削弱了記憶的自然性和靈活性,甚至剝奪了個體對記憶內容進行選擇和重構的自由。
在現代社會中,對遺忘的恐懼時常被轉化為對記憶的強烈執著,這不僅體現在個人的記憶訓練中,也體現在社會集體記憶的塑造上。在《記憶之場》(Les lieux demémoire) 中,諾拉從文化記憶的角度討論了因記憶外化而產生的記憶過剩的現象。他指出,在現代社會,記憶的記錄與保存已經演變為一種過度膨脹的文化現象。檔案、紀念碑、博物館等記憶場所的數量激增,記憶日益被外化為物質符號,從而失去其內在的活力和延續性,妨礙了記憶作為動態敘事的功能。這種物化的記憶文化加劇了記憶碎片化與僵化的趨勢,反而無法為個體和社會提供應有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指引。因此,記憶的過剩并非僅是個體的心理現象,也涉及社會、歷史、政治等多重維度的復雜問題。如何在記憶與遺忘之間找到平衡進而通達公正的記憶,已然成為當代社會亟須解決的核心問題。
利科從記憶倫理的角度批判了機械記憶對主體性的壓制, 強調“ 活的記憶”(mémoire vive) 的重要性。他認為,記憶不應僅是對過去的機械保存,更應成為主體與過去之間的對話。在這一過程中,主體在對記憶的選擇與重構中賦予過去新的意義,避免僵化和被動的存儲方式。記憶和遺忘之間的張力體現了記憶主體的批判性反思,促使主體在回憶過程中重新理解并公正對待歷史。由此,記憶不僅能夠避免被簡化為靜態的事實復述,還能成為歷史再現的主動參與者,反思過去的同時推動個體和集體的倫理轉向。因此,記憶的選擇本質上就是一種遺忘的選擇,記憶的建構不可避免地依賴于遺忘的篩選。
利科在“痕跡”的問題域層面將遺忘分為“因痕跡消失而產生的終極遺忘”和“保留的可逆遺忘”兩類,前者“在內化和掌握客觀知識的路徑展開”,后者“從認識的核心體驗出發,沿著回溯的路徑展開”。在此基礎上,他區分了消極遺忘和積極遺忘。消極遺忘主要涉及遺忘的政治學,它作為一種逃避現實的策略,試圖通過操控遺忘來掌控當下的政治形勢,“當最高權力通過恫嚇或誘惑、恐懼或奉承的方式強加一套規范敘事時,敘事資源也就成為陷阱。在這里,一種狡猾的遺忘形式正在發揮作用,這種遺忘源于社會行動者被剝奪了他們原本講述自身故事的權力”。遺忘作為逃避策略被無限排列和重組,成為記憶政治的重要部分,“過去的縈繞是當下政治象征的核心”。“作為回避、躲避、逃避的策略,這種模棱兩可的遺忘形式,既是主動的,又是被動的。作為主動的遺忘,它帶來了與疏忽、遺漏、輕率、短視等行為相同類型的責任。”遺忘引發的群體失憶表明,被遺忘的并非過去的事件、罪惡的行徑本身,而是它們的意義及其在歷史意識辯證法中的地位,其始作俑者的責任亦被轉移。
積極遺忘則是對記憶過剩的回應,它并不意味著完全抹除過去,而是在過去和未來之間找到恰當的平衡,幫助個體和社會從創傷性記憶中解脫出來。這種治愈將創傷記憶重新融入時間的敘事,使其逐漸轉變為可承受的過去。在這個意義上,“遺忘和記憶,都是歷史的條件的一部分”。尼采在《論道德的譜系:一本論戰著作》中也凸顯了遺忘的價值,積極健忘“仿佛一位守門人,靈魂秩序、安寧和禮節的一位維護者:由此立刻可以想見,在何種程度上,沒有健忘便可能沒有幸福,沒有明朗,沒有希望,沒有自豪,沒有當前”。他認為,龐大的集體記憶實為對生命的積極力量的威脅,這種過度的歷史存在削弱了個體制定未來計劃的創造性能力。通過反對社會公認的價值觀,尼采將遺忘視為一種積極的能力,一項建立人類的時間平衡的必要條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記憶的一個條件就是遺忘”。記憶的意義不在于完全復原過去,而在于為當下賦予意義、為未來注入希望。《鋼琴家》探討了記憶與遺忘的復雜關系,結尾部分更是突出了緬懷過去與建設未來之間的平衡與張力。影片主人公斯皮爾曼在經歷了戰火與磨難后被引導回波蘭國家廣播電臺,他演奏了肖邦的《第一敘事曲》,這既是對肖邦的致敬,更是對過去不堪回首的戰爭歷史的藝術性銘刻。影片結尾,斯皮爾曼演奏完最后一個音符,鏡頭定格在他的面龐上,表現出他內心的平靜和對過去的淡然。這一刻,過去與未來的邊界變得模糊。對斯皮爾曼而言,音樂不僅是記憶的載體,也是走出創傷的通道。他的鋼琴聲既傳達了對過去的緬懷,也指向面向未來的力量。遺忘在這里體現為一種必要的適應機制,它為承受深重苦難的個體和社會提供了繼續前行的路徑。通過這種平衡,影片表達了一個深刻的主題:銘記過去的苦難是為了避免重蹈覆轍,而選擇性地遺忘部分創傷則是為了給予未來以生機。《鋼琴家》由此成為對人類在戰爭與和平、記憶與遺忘、承認痛苦與放眼未來之間艱難抉擇的詩意詮釋。
為了實現公正的記憶,利科試圖在過度記憶與積極遺忘之間協商出一種共識性的平衡,“根據古代智慧的箴言,在人類記憶的使用中,存在一個尺度,即‘萬事切記過分’。因此,遺忘并不是在所有情況下都是記憶的敵人,并且為了摸索著尋找公正尺度以保持記憶和遺忘的平衡,它們應該進行協商”。這種協商的終極目的是尋求共識的平衡,既不讓過剩的記憶壓倒一切,也不使遺忘成為遮蔽真相的工具。利科致力于在自我與他者、過去與未來、個體與集體的多重關系中保持動態的張力,這種張力是不斷互動、調整和尋求對話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遺忘并非對過去的消解,而是為未來的建構提供空間。通過積極遺忘,個體和群體可以從歷史的重負中解脫出來,利科在此建構起記憶和遺忘之間的平衡。在此基礎上,積極遺忘為寬恕提供了可能。寬恕作為一種倫理實踐,既不掩飾過去的罪責,也不執著于怨恨的報復,它成為記憶的工作和哀悼的工作之間的橋梁,為我們提供了反思過去與建構未來的可能性。
結語
法國學界對“記憶的責任”概念的批評主要在于其越過記憶現象學,強制性地提出倫理要求。在這一背景下,利科試圖開辟新的空間,與指示性和規范性保持同等距離,以充滿希望的未來視角,同時借助精神分析理論,解除創傷記憶對個體乃至集體的束縛,恢復遺忘的合法地位,在記憶與遺忘之間尋求平衡,包容性地看待過去的復雜性,從而還原“真實”的歷史。利科并不追求實現具有共識性的普遍的記憶,而是強調在差異性解釋中找到前進的方式,建構一種共享的記憶,即通過對過去的關注和理解,創造出能夠包容不同觀點和經歷的共同的文化和社會空間。
公正的記憶問題涉及多個方面,包括過去的債務、記憶的濫用、見證的可信度、歷史的分歧、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沖突、遺忘的影響、寬恕的可能性。利科分別從認識論、實踐和倫理維度建構起三重平衡:忠實再現過去與償還倫理債務之間的平衡、個體見證與歷史書寫之間的平衡、過度記憶和積極遺忘之間的平衡。在這三重平衡中,自我與他者、過去與未來、責任與寬恕相互交織,構成了不斷尋求公正的動態平衡。利科不僅為個體與集體的歷史創傷提供了療愈的可能性,也為建構具有未來視野的包容的共同文化提供了理論依據。然而,現實社會中的力量與利益沖突使公正的記憶面臨諸多障礙和不確定性,這也表明記憶的工作尚未徹底完成。利科的記憶理論具有明確的實踐價值,但在現實中仍需要集體的勇氣與意愿以及相應的制度和機制支持,才能釋放出更多建設未來的力量。
作者單位 華東師范大學外語學院
責任編輯 吳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