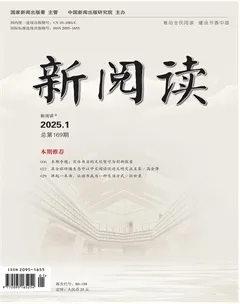《西行漫記》:用春水般清澈言辭書寫不可征服的精神




埃德加·斯諾(1905年7月19日—1972年2月15日),生于美國密蘇里州,美國記者,代表作紀實文學作品《西行漫記》(又名《紅星照耀中國》)。斯諾于1928年來華,曾任歐美幾家報社駐華記者、通訊員。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諾同時兼任北平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1936年6月,斯諾訪問陜北蘇區,寫了大量通訊報道,成為第一個采訪蘇區的西方記者。故而,斯諾被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縱觀“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對華友好的各國政要是比例最大的群體,如基辛格、尼克松等。對于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中國政府往往極為重視,高度禮遇,這些友好的老朋友也尤為珍視這一稱號。基辛格曾表示:“中國人民所說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指的是一種非常重要的關系,我以這個稱謂為榮。”
為有犧牲多壯志
1936年6月,埃德加·斯諾不懼戰火紛飛、不畏艱險,毅然決然深入紅都保安(今陜西志丹縣,1936年12月紅軍才占領延安)、預旺堡及周邊地區,歷時4個月,實地大量采訪了當時英勇奮戰的中國共產黨人和群眾,通過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以及廣大紅軍戰士、農民、工人、知識分子的交往交談,親眼見證了革命根據地的斗爭、生產和生活,真實記錄和整理了大量珍貴歷史資料和照片,客觀公正地傳達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紅色中國的生機活力,塑造了在革命圣地上戰斗的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氣質。當時,斯諾已經30歲了,風華正茂,是個富有雄心、經驗豐富的新聞記者。出于新聞記者的職業敏感,他意識到沒有任何一個非共產黨員的觀察家對共產黨人有準確的、一線調查的報道,只有對被國民黨當局稱為“赤匪”的充滿偏見的報道。但是,如何通過重重關卡和封鎖進行蘇區的報道,這簡直就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斯諾不輕言放棄,輾轉通過宋慶齡,秘密聯絡到了毛澤東,并同意接受采訪。怎么到達蘇區見到毛澤東又是一個難題。還是宋慶齡的真誠相助,伸出援手,通過當時在西安所謂剿匪前線的張學良的秘密支持到達保安。苦心人天不負,有志者事竟成。當時一同趕赴保安的,還有名醫馬海德。這也是宋慶齡對共產黨人的信任和支持。宋慶齡的所作所為,展現了她對國家和人民深沉的愛,救國救民的滿腔熱忱。正如她所言:“我們今天紀念過去,但也展望將來;我們今天正在建設著明天,為了所有的人民。”
了解了斯諾的成書過程和時代背景,再來品讀《西行漫記》(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8)講述的“紅色中國”的故事,心生敬佩,為之動容,感同身受作者在第一版序言中的斷言:“從字面上講起來,這本書是我寫的,這是真的。可是從最實際主義的意義來講,這些故事卻是中國革命青年們所創造的,所寫下的……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辭,解釋中國革命的原因和目的……從這些對話里面,讀者可以約略窺知使他們成為不可征服的那種精神……”《西行漫記》以80多個問題的設置和90天的詳細采訪,用富有感染力的傳播話語和情感共融的話語方式,形象傳播和建構中國共產黨的建黨精神、長征精神和延安精神。
敢教日月換新天
《西行漫記》生動地刻畫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及普通紅軍的正面形象和人格魅力,讓建黨精神變得具象直觀。斯諾用西方視角來描述他在蘇區的所見所得、所思所想。在表達自己對共產黨人的印象時,毛澤東是一個“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頗有天才的軍事和政治戰略家”;朱德在游擊戰中“為革命化的中國軍隊培養起了令人生畏的作戰能力”;周恩來是頭腦冷靜、神情冷峻的“紅色中國的頭號外交家”;賀龍讓他懂得了“共產黨人為什么這樣長期地、這樣毫不妥協地、這樣不像中國人地進行戰斗”;徐海東是個紅色窯工出身,“嘴里露出掉了兩個門牙的大窟窿,使他有了一種頑皮的孩子相”,“羞怯地長在一對寬闊的孩子氣肩膀上的,卻是南京的懸賞不下于彭德懷的腦袋”;劉志丹則是個“現代俠盜羅賓漢”,“在窮人中間,他的名字帶來了希望,可是在地主和老財中間,他成了懲奸除惡的天鞭”。斯諾形象逼真、細膩生動的文字,使紅軍領導人的形象栩栩如生,躍然紙上,讓世界各地的讀者,特別是西方讀者看到了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人為了中國的獨立自主,民族的解放復興所做的杰出努力。斯諾細致地描述了共產黨人對革命理論的學習,在理論學習中,建黨精神從而生根發芽。毛澤東認為《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著)、《階級斗爭》(考茨基著)和《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三本書建立起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其中的《共產黨宣言》他讀了不下一百遍;朱德在德國留學時閱讀了《共產主義》和列寧的著作;周恩來閱讀了《共產黨宣言》《階級斗爭》《十月革命》;彭德懷閱讀了《共產黨宣言》《新社會》《階級斗爭》等唯物主義文章和小冊子。斯諾還多處描寫了普通紅軍戰士的日常生活景象:“深入蘇區以后,我就會在這些臉頰紅彤彤的‘紅小鬼’的身上發現一種令人驚異的青年運動所表現的生氣勃勃的精神。”斯諾發現,紅軍普通士兵平均年齡是19歲,農民占紅軍的大部分,“他們堅忍卓絕,任勞任怨,是無法打敗的”。
斯諾的《西行漫記》橫空出世,刻畫了革命根據地人民群眾對“紅色中國”的愛戴擁護,破除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造謠抹黑,認為中國共產黨代表了中國的進步力量,描寫了中國共產黨偉大建黨精神的開篇圖景,展現了中國共產黨與生俱來的紅色基因。斯諾別具一格地把毛澤東比作林肯,并拍攝了著名的“八角帽照片”,顯現了毛澤東在民族解放和國家危難中沉著睿智的領袖形象,贏得了世界人民和中國的好感和信任。
《西行漫記》傳播了中國共產黨人堅韌不拔和艱苦創業的作風,延安精神從而熠熠閃光、光芒四射。斯諾細致地描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居住的環境:毛澤東住的地方,天花板、墻壁和窗戶都是“從巖石中鑿出來的”,窗簾是布做的,僅有的一張桌子是“一張沒有上油漆的方桌”;周恩來的辦公室里唯一的奢侈品是一頂蚊帳;彭德懷的辦公室僅有桌子和板凳、兩個文件箱、一張地圖、一臺野戰電話、一條毛巾和一個臉盆。他也寫實了抗日軍政大學的辦學條件:“以窯洞為教室,石頭磚塊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墻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轟炸的這種‘高等學府’,全世界恐怕只有這么一家。”毛澤東曾對學員詼諧地說:“你們是過著石器時代的生活,學習當代最先進的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抗大精神的底色就是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和艱苦奮斗的政治本色,也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內容。1938年,毛澤東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回答“在抗大應當學習什么”時指出,“首先是學一個政治方向”。斯諾在書中專門記錄和介紹了陜北蘇區人民在極其艱苦條件下創建工業的情況,他仍然采取慣用的類比英美的筆觸寫到吳起鎮是陜西蘇區的一個工業中心,它的突出“并不是由于在工藝學方面有什么成就使底特律或曼徹斯特不能等閑視之,而是因為它居然存在。”顯然,斯諾是個中國通,他非常清楚共產黨在江西的時候,確實建立了不少繁榮的工業,包括年產100多萬鎊的鎢礦、800人規模的中央蘇區印刷廠,還有紡紗廠、織布廠等。但是,在偏僻窮困的西北,共產黨人仍然艱苦奮斗建立了織布廠、被服廠等手工業(注:沒有電力),甚至有永平煤礦、延長油井以及臨近寧夏的鹽池。條件如此艱苦卓絕,斯諾記錄里提到了當時的經濟人民委員毛澤民的想法,工業計劃的目標就是要使得紅色中國在經濟上自主,其含義就是蘇區能夠有不怕國民黨封鎖而維持下去的能力。
《西行漫記》廣泛傳播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理念和長征經歷,讓長征精神傳遍世界、深入人心。斯諾是向全世界介紹紅軍長征的第一人。在《西行漫記》寫作時,專門在第五篇寫了長征,并把長征英譯為“Long March”,從此成為長征的標準英譯。斯諾最初曾用“Expedition”來翻譯長征。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的斯諾特藏(Edgar Snow Collection)保存了一份紅軍總政治部1936年7月21日發的《征文啟事》。斯諾在此《征文啟事》反面用英文寫道:Notice for collecting materi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of the R A July 21(紅軍遠征史征稿啟事)。但是由于形勢的變化和戰爭年代的動蕩,《長征記》的出版直到1942才塵埃落定。斯諾應該是參考了《長征記》前期收集整理的資料才完成“長征”一章。2002年初,國內曾發布一條引人注目的新聞: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發現了一部朱德簽名贈給埃德加·斯諾的延安1942年版《紅軍長征記》。斯諾在書中對長征的艱難多有記錄,比如,“長征的統計數字是觸目驚心的。幾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戰,發生在路上某個地方,總共有15個整天用在打大決戰上”。斯諾對紅軍的長征多次不厭其煩地贊美稱奇,譬如,“他們的長征是軍事史上偉大的業績之一”,“紅軍終于到達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無損,其軍心士氣和政治意志顯然一如往昔”,“是歷史上最盛大的武裝巡回宣傳”。事實上,斯諾對長征的認識與毛澤東對長征的歷史定位近乎一致。長征勝利結束后,毛澤東高度評價長征精神的意義,提出長征不僅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更是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并用詩意盎然的語言創作了七律《長征》。長征精神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長征永遠在路上。
踏遍青山人未老
斯諾的《西行漫記》首次刻畫了中國共產黨的重要人物,首次描述了他們的生活方式、信念和精神狀態,首次向全世界報道了中國紅軍英勇的長征。斯諾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事業給予了充分報道,對20世紀30年代那些懼怕抗擊法西斯的人們是一個強有力的鼓舞。80多年過去了,撫今追昔,無論是對歷史的記錄還是對歷史趨勢的預見,斯諾的《西行漫記》都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是“講好中國故事”的極佳案例。這也充分說明,那些蘊含著先進文化、先進理念、先進思想的偉大精神,才能建構健康繁榮、積極向上的社會,才能塑造國家未來發展的主方向。
作者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