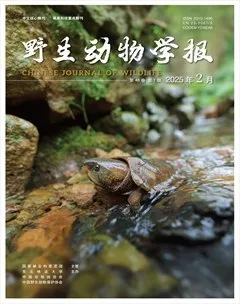基于mtDNA D-loop的河南某地引入獼猴群體遺傳背景分析




關鍵詞:獼猴;物種引入;種群;遺傳多樣性;系統發育
野生動物旅游是以野生動物為主要消費對象的一種生態旅游活動,而獼猴(Macaca mulatta)則是最為常見的目標動物之一[1]。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基于野生動物的生態旅游快速發展,并取得了可觀的經濟利益[2]。在此背景下,一些地區通過引入(introduction)或重引入(re-introduction)方式,使獼猴(或其他野生動物)擴散到其自然分布區以外的地方[3]。然而,引入來源不清、遺傳背景不明的動物,可能導致不同進化譜系之間產生遺傳同質化、遺傳污染等現象,進而擾動局部地區的動物區系組成,甚至引發嚴重的生態后果[4]。如棕樹蛇(Boiga ir?regularis)[5]、褐家鼠(Rattus norvegicus)[6]和溫室蟾(Eleutherodactylus planirostris)[7?8]等動物,借由交通運輸和貿易等人類介導的方式擴散到新的地區。被引入物種一旦定殖成功,其種群數量往往迅速增長[9?11],并通過競爭、捕食和疾病傳播等方式,嚴重威脅本土物種與生態系統穩定,最終成為入侵物種。美洲牛蛙(Rana catesbeiana)導致全球多個入侵地區的本土兩棲類快速下降甚至滅絕[12];緬甸蟒(Pythonbivittatus)入侵北美地區后,造成當地小型獸類種群的快速下降、瀕臨滅絕[13];褐家鼠等入侵鼠類導致鼠疫、鼠傷寒在全球范圍內傳播[14]等。
遺傳多樣性常用于評估物種對環境的適應能力和抵御疾病的能力[15?18]。在物種滅絕后的重引入過程中,遺傳多樣性水平被作為重要的參考指標[16,19?20]。如對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21?22]、普氏野馬(Equus ferus przewalskii)[23]和大熊貓(Ailu?ropoda melanoleuca)[24]等物種的研究結果,無不展示了遺傳多樣性在珍稀瀕危物種保護中的重要作用。較高的遺傳多樣性有助于物種快速響應環境變化、減少近交,也是入侵物種成功定殖的主因[25?27]。因此,評估引入物種的遺傳多樣性水平、追溯其原始產地,對建立規范、可行和有效的監管措施極為必要[28]。
獼猴是世界上分布最廣泛的非人靈長類物種[29?30],在我國的分布范圍從熱帶雨林到溫帶雪山[31?32]。筆者在野外調查期間,于河南省滎陽市環翠峪風景名勝區(34°64′ N,113°27′ E)發現一群自由活動的引入獼猴群體,遂予以重點關注。迄今為止,關于該獼猴群體的數量現狀、遺傳背景等尚未見有研究報道。為此,本研究擬以mtDNA D-loop部分序列為分子標記,分析環翠峪獼猴群體的遺傳多樣性現狀,探討其可能的原始產地等,以期為該獼猴種群的科學管理和可持續利用提供可靠信息。
1 研究方法
1. 1 種群現狀調查
1996年,河南滎陽市環翠峪風景名勝區開發者引入獼猴約40 只,以建立種群、開展生態旅游。2020年3—12月,采用訪問調查法、直接計數法統計該獼猴群體的數量。
1. 2 樣品采集、DNA 提取和序列擴增
采集14只環翠峪(Huancuiyu,HCY)地理單元獼猴個體的糞便樣品。為避免同一個體的重復采樣,首先對獼猴行為進行觀察以鎖定目標個體,繼而基于糞便的大小、形狀和顏色,并將間距lt; 2 m的糞便作為一個獨立樣品收集。然后,使用一次性滅菌手套,將新鮮糞便樣品放入10 mL 的樣品收集管中。記錄采樣點的海拔和經緯度等信息。最后,按照樣品采集順序編號,放入干冰保存。
糞便樣品DNA的提取使用PowerFecal DNA Kit(QIAGEN, Germany),并參考已發表的mtDNA Dloop序列引物[33]:dloop-F(5′-TCCGAGGGCAATCAGAAAGAAA-3′)和dloop-R(5′-GCCTTGAGGTAAGAACCAGATGC-3′),進行PCR擴增。采用25. 0 μL反應體系,包括2. 0 μL 模板DNA、1. 5 μL 上游引物(10 μmol/L)、1. 5 μL下游引物(10 μmol/L)和20. 0 μL1. 1 × T3 Super PCR Mix(北京擎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反應條件:98 ℃預變性3 min;8 ℃變性10 s,55 ℃退火10 s,72 ℃延伸12 s,循環35次;最后72 ℃延伸5 min。將質量合格的PCR產物送至北京擎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測序。
1. 3 數據分析
結合本課題組已發表的、分布于河南濟源王屋地區(Wangwu,WW)太行山獼猴的19 條mtDNA Dloop序列[34],以及NCBI 數據庫中來自國內11 省份(河南、安徽、福建、浙江、湖北、湖南、貴州、廣西、海南、四川和云南)的125條獼猴相關序列,進行后續分析。
采用DNASTAR 軟件包的SEQMAN 模塊[35],查看并組裝序列。為確保所測DNA序列為目的片段,將組裝序列結果在NCBI數據庫中與目標物種的同源序列進行比對。采用DnaSP v6. 12軟件[36]統計變異位點(variable sites)、簡約信息位點(parsimony informativesites)和單倍型數(haplotype number),計算群體的單倍型多樣性(haplotype diversity,Hd)和核苷酸多樣性(nucleotide diversity,π)。基于最大似然法(maximum likelihood,ML)和貝葉斯法(Bayesian inference,BI)構建系統發育樹,以食蟹猴(Macaca fas?cicularis)為外群(GenBank登錄號:FJ906803和NC_012670)。使用PhyloSuite v1. 2. 2[37]構建mtDNA Dloop單倍型的系統發育樹。(1)序列比對:將“fasta”格式文件導入MAFFT進行序列比對。(2)ModelFinder:將比對完成的序列導入,“Criterion”選擇Bayesian informationcriterion(BIC),“model for”選擇MrBayes,其余均為默認參數,運行后可得到貝葉斯最佳模型。(3)構建貝葉斯樹:運行設置為2 × 106代,每運行100次抽樣一次,舍棄前25%的老化樣本。(4)構建似然樹:使用ModelFinder 選擇最佳模型,BootStrap 選擇Ultrafast,自舉值設置為5 000。運行后使用FigTreev1. 4. 3[38]讀取樹結果文件,并進行可視化處理。使用PopART v1. 7軟件[39]構建單倍型網絡結構圖。使用MEGA X軟件[40]對序列進行比對,基于Kimura 2-parameter模型計算群體間遺傳距離。使用Arlequinv3. 5軟件[41]進行群體分子方差分析(analysis of molecularvariance,AMOVA),以估算遺傳變異在不同地理單元獼猴群體間的分布。
2 結果
2. 1 種群數量
環翠峪獼猴群體自1996年引入,約40只。至調查結束時,計有4群約300只個體,其中約200只較為常見。
2. 2 序列特征和單倍型分布
環翠峪(HCY)地區14 只獼猴個體的D-loop 區序列(502 bp),存在25個單變異位點(5. 0%),且所有變異位點均為轉換位點。D-loop序列堿基組成分析顯示,A、T、C 和G 的平均含量分別為31. 1%、29. 8%、26. 5% 和12. 6%,其中A+T含量(60. 9%)明顯高于G+C含量(39. 1%),表現出AT偏倚性。
結合河南王屋(n = 19)以及NCBI 數據庫(n =125)中獼猴D-loop序列,共定義86個單倍型(表1)。其中,Hap1在環翠峪和浙江獼猴群體間共享;湖南獼猴群體單倍型Hap35與云南獼猴群體共享;Hap38是海南和四川獼猴群體的共享單倍型。Hap2為環翠峪獼猴群體特有單倍型;河南、安徽、福建、廣西、貴州和湖北獼猴群體間無共享單倍型。
2. 3 群體遺傳多樣性
各獼猴群體均表現出高的單倍型多樣性[Hd: 0 ~(1. 000 ± 0. 500)]和低的核苷酸多樣性[π: 0 ~(0. 065 20 ± 0. 019 36)](表2)。與其他地區相比,環翠峪獼猴群體核苷酸多樣性水平(π: 0. 007 11 ±0. 005 92)明顯高于河南獼猴群體,但低于除安徽和湖北之外的其他地理單元獼猴群體;另外,環翠峪地理單元獼猴群體單倍型多樣性(Hd: 0. 143 ± 0. 119)低于上述獼猴群體,表明該獼猴群體單倍型類型較單一。
2. 4 系統發育和遺傳結構
基于158條獼猴mtDNA D-loop序列所定義的86個單倍型,構建的ML 和BI 系統發育拓撲結構一致(圖1)。系統發育分析結果表明,來自中國西部省份(云南和四川)和東部省份(河南、安徽、福建、浙江、湖北、湖南、貴州、廣西和海南)的獼猴個體,分別聚為西部(West)和東部(East)遺傳組(BI/PP = 0. 85/97)。東部遺傳組又被劃分為5個遺傳支(Clade1~5),并得到較高的支持度。河南獼猴個體單倍型聚于Clade3支(BI/PP = 1/100)。環翠峪獼猴特有的單倍型Hap1和Hap2分別聚于Clade1和Clade5支內,且2個單倍型均與浙江獼猴個體表現出較近的親緣關系(BI/PP = 1/100;BI/PP = 0. 76/99)。
單倍型網絡分析結果顯示,所有獼猴個體的86個單倍型可劃分為2個單倍型簇,西部(West)和東部(East),并且2個單倍型簇間存在19個突變步數(圖2)。環翠峪和河南獼猴群體均位于東部單倍型簇內,并得到系統發育結果的支持(圖1)。其中,環翠峪獼猴群體單倍型Hap1與浙江獼猴群體共享;單倍型Hap2與浙江獼猴群體間雖然存在較多的突變步數和未知單倍型的遺傳變異,但與其他獼猴群體相比,依然顯示較近的親緣關系。另外,環翠峪獼猴群體的2個特有單倍型(Hap1和Hap2)間也存在較高的突變步數,表明該獼猴群體的個體間存在較大的遺傳差異(圖2)。
2. 5 群體間遺傳差異
群體間遺傳距離分析表明,環翠峪獼猴群體與其他獼猴群體間的遺傳距離為0. 034 8 ~ 0. 070 5(表3)。其中,環翠峪獼猴群體與浙江獼猴群體間的遺傳距離最小(0. 034 8),而與海南獼猴群體存在較大的遺傳差異(0. 070 5)。值得注意的是,環翠峪獼猴群體與河南獼猴群體間的遺傳距離,均大于該獼猴群體與其他地區獼猴群體(海南群體除外)間的遺傳距離(表3)。
環翠峪獼猴群體與東部組(河南、安徽、福建、廣西、貴州、湖北、海南和浙江)內其他地區獼猴群體間的分子方差分析結果顯示(表4),群體間和群體內的方差分別占總變異的63. 10%和36. 90%,表明遺傳變異主要發生在群體間。
3 討論
本研究基于獼猴158條mtDNA D-loop部分序列(502 bp)定義的86個單倍型,評估了河南滎陽環翠峪獼猴群體的遺傳多樣性水平,進而構建系統發育和單倍型網絡。結果表明,環翠峪獼猴群體表現出低的核苷酸多樣性和高的單倍型多樣性;該獼猴群體與浙江獼猴的親緣關系較近,與其他地區獼猴群體存在較大的遺傳差異。
環翠峪獼猴群體存在低的遺傳多樣性水平,但明顯高于河南獼猴群體遺傳多樣性。該現象或有兩種解釋:其一,具有多個遺傳背景的獼猴群體遺傳多樣性水平明顯高于野生獼猴群體[33];其二,不同遺傳背景獼猴個體間的基因流共同促進了群體內遺傳變異水平[34,42]。由于該獼猴群體建群時間短,且獼猴具有較長的世代間隔(10. 4 a)和較低的核苷酸突變率(0. 77 × 10-8)[43],故遺傳漂變對該獼猴群體的遺傳多樣性水平影響較小。
環翠峪獼猴的初始種群可能來自浙江地區。獼猴自上新世期間橫穿青藏高原東南緣橫斷山脈進入中國,并在更新世期間沿著東部和西部兩條路線快速輻射到中國的大部分地區[44?45]。本研究發現,系統發育揭示中國獼猴可分為東部和西部兩大遺傳譜系,與基于分子標記[45]和基因組[46?47]的研究結果相一致。環翠峪獼猴群體聚于東部支,表明該獼猴群體源自中國東部地區。值得注意的是,環翠峪獼猴群體與其臨近地理單元(如河南太行山地區、安徽和湖北)獼猴群體間存在較大的遺傳差異,而與浙江獼猴群體存在較近的親緣關系。
綜上所述,環翠峪獼猴群體遺傳多樣性高于已知的國內其他野生獼猴群體,且為跨省份引入群體,為非自然分布,其原始種群分布區應為浙江地區。從中國獼猴的分類與分布來看[31],環翠峪獼猴與河南地區的太行山獼猴(獼猴華北亞種)分屬于不同亞種。鑒于該獼猴群體發展迅速,一旦出現種群逃逸,將對華北地區野生太行山獼猴種群或有潛在的負面影響。因此,本研究建議,不應盲目引入動物用于生態旅游活動;在野生動物管理部門指導下,應對環翠峪獼猴群體采取嚴格的管控措施,限定其活動范圍,以防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