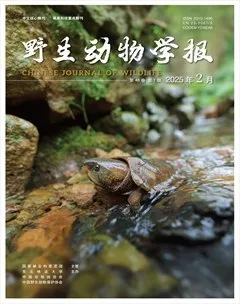基于物種監(jiān)測(cè)數(shù)據(jù)的卡拉麥里國(guó)家公園野生動(dòng)物觀賞路線設(shè)計(jì)






關(guān)鍵詞:卡拉麥里國(guó)家公園;水源地;紅外相機(jī)監(jiān)測(cè);野生動(dòng)物旅游;觀賞點(diǎn)
國(guó)家公園因特有的生物多樣性及其對(duì)自然和文化遺產(chǎn)的綜合保護(hù),而成為具有國(guó)家代表性的重要區(qū)域,依托其豐富的自然資源,在國(guó)家公園內(nèi)開(kāi)展的生態(tài)旅游是全民公益性的重要體現(xiàn)[1]。野生動(dòng)物旅游指在自然環(huán)境或圈養(yǎng)環(huán)境下以野生動(dòng)物為主要觀賞對(duì)象的特定游憩方式[2],在國(guó)家公園、自然保護(hù)區(qū)等區(qū)域開(kāi)展的野生動(dòng)物旅游,不僅能為管理機(jī)構(gòu)提供物種保護(hù)的資金來(lái)源,增強(qiáng)自養(yǎng)能力,還可以帶動(dòng)當(dāng)?shù)叵嚓P(guān)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使社區(qū)獲得經(jīng)濟(jì)收益。隨著我國(guó)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和環(huán)境保護(hù)意識(shí)的提高,近年來(lái)野生動(dòng)物旅游受到廣泛關(guān)注。相比于其他生態(tài)旅游形式,野生動(dòng)物觀賞為人們提供了回歸自然、接觸野生動(dòng)物的機(jī)會(huì),將禁錮于城市的人們與自然重新建立聯(lián)結(jié),滿(mǎn)足了人們想要親近自然的需求。
在過(guò)去的幾十年間,國(guó)家公園等各類(lèi)保護(hù)地?cái)?shù)量成倍增長(zhǎng),目前這類(lèi)包含了野生動(dòng)物棲息地的受法律保護(hù)區(qū)域占地球陸地面積的17%,其中一部分自然保護(hù)區(qū)域是重要的野生動(dòng)物旅游目的地[3?4]。在全球范圍內(nèi),野生動(dòng)物旅游創(chuàng)造的價(jià)值為450億美元,年增長(zhǎng)率為10%,預(yù)計(jì)隨著教育水平和收入的增加,未來(lái)價(jià)值會(huì)繼續(xù)擴(kuò)大,在全球旅游業(yè)中發(fā)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5]。不僅如此,作為人類(lèi)與野生動(dòng)物互動(dòng)的主要途徑之一,野生動(dòng)物旅游增加了人們接觸動(dòng)物及其棲息地的機(jī)會(huì),在旅游過(guò)程中既可以使人的身心沉浸于自然,產(chǎn)生幸福感[6],又可以起到戶(hù)外鍛煉的作用。同時(shí)開(kāi)展野生動(dòng)物旅游還可以促進(jìn)人們對(duì)保護(hù)生態(tài)環(huán)境的認(rèn)知,加強(qiáng)生態(tài)責(zé)任,有效推動(dòng)當(dāng)?shù)亟?jīng)濟(jì)發(fā)展和文化傳承。但是,如管理不當(dāng),野生動(dòng)物旅游活動(dòng)也會(huì)對(duì)當(dāng)?shù)貏?dòng)物種群產(chǎn)生不利影響,過(guò)多的人類(lèi)干擾會(huì)改變動(dòng)物的生存環(huán)境,增加動(dòng)物的警戒性,減少動(dòng)物的出現(xiàn)頻率,壓縮動(dòng)物的生存空間,即使是“良性”的人類(lèi)活動(dòng)也會(huì)影響動(dòng)物的生物學(xué)和個(gè)體行為[7]。因此,如何做到既滿(mǎn)足游客的觀賞需求,又最大限度地降低對(duì)動(dòng)物群落的影響成為野生動(dòng)物旅游項(xiàng)目規(guī)劃的一大難題。
本研究通過(guò)分析卡拉麥里國(guó)家公園動(dòng)物資源數(shù)量和分布特征,基于沿道路觀賞的旅游形式,在不干擾野生動(dòng)物的前提下,提出野生動(dòng)物觀賞路線的規(guī)劃設(shè)計(jì)建議,以期最大限度地提高游客觀賞體驗(yàn),使人們更關(guān)注卡拉麥里國(guó)家公園的動(dòng)物資源保護(hù),為國(guó)家公園野生動(dòng)物旅游的可持續(xù)管理提供科學(xué)參考。
1 研究區(qū)概況
卡拉麥里國(guó)家公園于2022年4月經(jīng)國(guó)家公園管理局批復(fù)同意創(chuàng)建,前身為1982年成立的新疆卡拉麥里山有蹄類(lèi)野生動(dòng)物自然保護(hù)區(qū),創(chuàng)建面積14 951 km2,其中核心保護(hù)區(qū)7 883 km2,一般控制區(qū)7 068 km2。位于新疆準(zhǔn)噶爾盆地的卡拉麥里,是我國(guó)低海拔唯一的荒漠有蹄類(lèi)野生動(dòng)物超大型國(guó)家公園,國(guó)家公園東部為礫石戈壁,中部為卡拉麥里山,西部為沙漠。卡拉麥里山東高西低,北面為低山丘陵,坡度較緩,相對(duì)高差僅幾十米。山嶺以南為將軍戈壁,個(gè)別地段形成沙丘。國(guó)家公園西部沙漠是古爾班通古特沙漠的一部分,有6條大的中速流動(dòng)沙垅和大面積的格狀沙丘鏈。山地丘陵、風(fēng)蝕臺(tái)原與沙漠的交界處形成大的泥漠,俗稱(chēng)“黃泥灘”。
卡拉麥里位于戈壁荒漠,氣候干旱,年均氣溫3. 4 ℃,年均降水量191. 7 mm,而蒸發(fā)量高達(dá)2 090. 4 mm。依據(jù)卡拉麥里國(guó)家公園綜合科學(xué)考察報(bào)告記錄,該區(qū)共有維管植物46科196屬393種,組成簡(jiǎn)單、分布稀疏,主要由超旱生、旱生灌木、小半灌木及旱生一年生灌木、多年生草本和短命植物等組成;共有脊椎動(dòng)物69科260種,其中哺乳動(dòng)物15科47種,鳥(niǎo)類(lèi)45科192種,爬行類(lèi)8科20種,兩棲類(lèi)1科1種。由于特定的生態(tài)條件,國(guó)家公園的動(dòng)物群落具有明顯的適應(yīng)特征,兩棲類(lèi)種類(lèi)很少,爬行類(lèi)和嚙齒類(lèi)豐富,有蹄類(lèi)數(shù)量較多。
國(guó)家公園境內(nèi)有國(guó)道216線由南至北縱貫,長(zhǎng)約164 km。省道228線經(jīng)將軍廟、紅柳溝、野馬泉到二臺(tái),是國(guó)家公園的東部界限。南部邊界以準(zhǔn)東工業(yè)園區(qū)規(guī)劃邊界,結(jié)合巡護(hù)道路劃定。新疆石油管理局準(zhǔn)東勘探開(kāi)發(fā)公司修建一條火燒山—彩南油田公路,其中在國(guó)家公園境內(nèi)約40 km。國(guó)家公園內(nèi)有124 km鐵路:大黃山—將軍廟鐵路,在五彩灣地區(qū)設(shè)有準(zhǔn)東北站[1]。
2 研究方法
2. 1 紅外相機(jī)布設(shè)位點(diǎn)
在卡拉麥里國(guó)家公園干旱少水的自然條件下,水源地成為大量野生動(dòng)物的聚集點(diǎn),因此管理站工作人員在水源地附近進(jìn)行紅外相機(jī)監(jiān)測(cè),收集動(dòng)物數(shù)據(jù)。每處水源地布設(shè)2臺(tái)紅外相機(jī),使拍攝范圍盡量覆蓋整個(gè)區(qū)域。2019—2023年卡拉麥里全域設(shè)置了24處紅外相機(jī)位點(diǎn)。因?yàn)閲?guó)家公園核心保護(hù)區(qū)不能開(kāi)展生態(tài)旅游活動(dòng),本研究只選取了一般控制區(qū)道路附近的10處紅外相機(jī)位點(diǎn),其中月牙灣和12號(hào)水源地照片數(shù)量較少,故未統(tǒng)計(jì)這2處水源地的物種空間分布情況(圖1)。
對(duì)紅外相機(jī)動(dòng)物數(shù)據(jù)進(jìn)行篩選,發(fā)現(xiàn)該區(qū)域內(nèi)野生動(dòng)物主要出現(xiàn)于7—10月,冬季和春季(11月—次年6月)能記錄到的野生動(dòng)物數(shù)量較少,所以將數(shù)據(jù)劃分為不同季節(jié)進(jìn)行統(tǒng)計(jì)整理,7—8月為夏季,9—10月為秋季。
2. 2 物種監(jiān)測(cè)數(shù)據(jù)統(tǒng)計(jì)分析
將紅外相機(jī)獲取的照片數(shù)據(jù)錄入Excel,排除夜間活動(dòng)的動(dòng)物照片。因數(shù)據(jù)分析目的是評(píng)價(jià)野生動(dòng)物的觀賞重要性,動(dòng)物在一段時(shí)間內(nèi)的集中分布數(shù)量也具有統(tǒng)計(jì)價(jià)值,所以未使用有效照片法(30 min內(nèi)出現(xiàn)則不計(jì)入有效照片),而是計(jì)算動(dòng)物出現(xiàn)的出現(xiàn)指數(shù)。計(jì)算每個(gè)點(diǎn)位每種動(dòng)物的照片數(shù)量(Ni )及該位點(diǎn)所有野生動(dòng)物物種的照片數(shù)量總和(N),即可計(jì)算出物種相對(duì)頻率(Pi = Ni/N),即某一物種在某一水源地出現(xiàn)的百分比,Pi值高即意味著動(dòng)物單獨(dú)出現(xiàn)的頻率增加,在該位點(diǎn)物種的觀賞重要值較高。
照片拍攝次數(shù)可反映野生動(dòng)物的種群數(shù)量以及動(dòng)物在相機(jī)監(jiān)測(cè)位點(diǎn)的停留時(shí)間,單位時(shí)間內(nèi)拍攝次數(shù)越多則代表動(dòng)物數(shù)量越多、在相機(jī)監(jiān)測(cè)位點(diǎn)停留的時(shí)間越長(zhǎng)。計(jì)算相機(jī)拍攝時(shí)長(zhǎng)(總拍攝日,t),根據(jù)Ni即可得出物種的出現(xiàn)指數(shù)Qi (Qi = Ni/t),即單位時(shí)間(1 d)內(nèi)記錄到某種動(dòng)物的平均照片數(shù)。
2. 3 野生動(dòng)物觀賞路線設(shè)計(jì)
根據(jù)國(guó)家公園對(duì)游客的管理規(guī)定,核心保護(hù)區(qū)禁止外部人員進(jìn)入,因此將觀賞路線設(shè)計(jì)在一般控制區(qū)內(nèi),路線以公園西南端臨近月牙灣水源地的觀賞點(diǎn)為起點(diǎn),以北部10號(hào)水源地的觀賞點(diǎn)為終點(diǎn),斜跨整個(gè)國(guó)家公園。水源地基本分布在道路主線和支線附近,根據(jù)不同季節(jié)每個(gè)水源地的監(jiān)測(cè)數(shù)據(jù)挑選出優(yōu)質(zhì)觀賞點(diǎn),再利用現(xiàn)有道路將觀賞點(diǎn)串聯(lián)起來(lái),從而規(guī)劃出夏季和秋季2條不同的路線。
每個(gè)水源地出現(xiàn)的主要物種不同,動(dòng)物出現(xiàn)頻率不同,綜合考量每個(gè)水源地野生動(dòng)物的相對(duì)頻率與出現(xiàn)指數(shù),確定不同動(dòng)物的最佳觀賞地點(diǎn)。有研究顯示,蒙古野驢(Equus hemionus)、野馬(E. ferus)等大型有蹄類(lèi)動(dòng)物的警戒距離一般在2 000 m以?xún)?nèi),因此以2 000 m為回避距離設(shè)定緩沖范圍,將觀賞點(diǎn)設(shè)置在緩沖范圍以外的位置,且盡量靠近公路,使得在此區(qū)域停留的游客不會(huì)對(duì)野生動(dòng)物行為造成干擾[8?11]。
在每個(gè)觀賞點(diǎn)設(shè)置2或3個(gè)簡(jiǎn)易觀賞平臺(tái),游客可以在此停車(chē)觀看。為最大限度地滿(mǎn)足游客的觀賞體驗(yàn),需配備相應(yīng)引導(dǎo)設(shè)施,例如:繪制觀賞路線和觀賞點(diǎn)位置的導(dǎo)覽牌,設(shè)置帶有動(dòng)物照片和文字說(shuō)明的觀賞解說(shuō)牌,提供單筒或雙筒望遠(yuǎn)鏡,以及布設(shè)垃圾桶和節(jié)水公廁等環(huán)保設(shè)施。
3 結(jié)果
3. 1 紅外相機(jī)監(jiān)測(cè)情況
共拍攝31 362張動(dòng)物日間活動(dòng)照片,記錄到9種哺乳動(dòng)物,即蒙古野驢、野馬、鵝喉羚(Gazella sub?gutturosa)、狼(Canis lupus)、盤(pán)羊(Ovis ammon)、赤狐(Vulpes vulpes)、沙狐(Vulpes corsac)、猞猁(Lynx lynx)和蒙古兔(Lepus tolai);10種鳥(niǎo)類(lèi),即禿鷲(Aegypiusmonachus)、草原雕(Aquila nipalensis)、棕尾鵟(Buteorufinus)、獵隼(Falco cherrug)、灰鶴(Grus grus)、毛腿沙雞(Syrrhaptes paradoxus)、赤麻鴨(Tadorna ferru?ginea)、綠頭鴨(Anas platyrhynchos)、大白鷺(Ardeaalba)和黑翅長(zhǎng)腳鷸(Himantopus himantopus),共19個(gè)物種。其中國(guó)家一級(jí)重點(diǎn)保護(hù)野生動(dòng)物有蒙古野驢、野馬、草原雕、禿鷲和獵隼5 種,國(guó)家二級(jí)重點(diǎn)保護(hù)野生動(dòng)物有鵝喉羚、狼、盤(pán)羊、赤狐、沙狐、猞猁、灰鶴和棕尾鵟8種。從種群數(shù)量上看,卡拉麥里國(guó)家公園內(nèi)有蹄類(lèi)動(dòng)物數(shù)量占比最大,照片總數(shù)最多的為蒙古野驢,其后依次為野馬、鵝喉羚(表1)。
3. 2 觀賞物種的時(shí)空分布
卡拉麥里國(guó)家公園一般控制區(qū)內(nèi)野生動(dòng)物集中分布于33號(hào)水源地和32號(hào)水源地,31號(hào)水源地動(dòng)物數(shù)量相對(duì)較少。31、32、33 號(hào)、庫(kù)木西克水源地的7—8月動(dòng)物出現(xiàn)指數(shù)高于9—10月,其余水源地則是9—10月動(dòng)物的出現(xiàn)指數(shù)更高(圖2)。7—8月33號(hào)水源地的動(dòng)物數(shù)量最多,主要由于野馬在此時(shí)間段聚集分布,出現(xiàn)指數(shù)為371. 54,高于其他水源地。因406號(hào)路邊水源地缺少7—8月相機(jī)數(shù)據(jù),未作季節(jié)間的比較。
蒙古野驢照片數(shù)量最多,占總照片數(shù)量的45. 41%,分布位點(diǎn)也最多,僅31號(hào)水源地在7—8月未記錄到。蒙古野驢7—8月在32號(hào)水源地的出現(xiàn)指數(shù)是全年最高的;9—10月在五彩城南和33號(hào)水源地的出現(xiàn)指數(shù)也非常高(圖3)。從分布數(shù)量和季節(jié)性活動(dòng)特征上看,蒙古野驢可作為卡拉麥里國(guó)家公園的最主要觀賞物種。
野馬照片數(shù)量?jī)H次于蒙古野驢,共拍攝10 086張,占總照片數(shù)量的32. 16%,主要集中分布于公園中部的喬木希拜區(qū)域,出現(xiàn)高峰是7—8 月的33 號(hào)水源地,出現(xiàn)指數(shù)338. 00(圖4)。這說(shuō)明野馬有特定的活動(dòng)地點(diǎn)和時(shí)間,可將此水源地設(shè)立為重要的野馬觀賞點(diǎn)。
鵝喉羚的照片數(shù)量為3 974張,也是卡拉麥里廣泛分布的主要觀賞有蹄類(lèi)之一,在6個(gè)水源地有記錄,但活動(dòng)頻率相對(duì)較低。鵝喉羚具有相對(duì)集中分布的特征,9—10月的出現(xiàn)指數(shù)相比7—8月的更高,其活動(dòng)高峰出現(xiàn)在9—10月的10號(hào)水源地,7—8月在32號(hào)水源地的出現(xiàn)指數(shù)也較高(圖5)。
其他出現(xiàn)頻率較高的物種還有狼、盤(pán)羊、禿鷲、赤麻鴨、毛腿沙雞和草原雕。狼7—8月在31號(hào)水源地的出現(xiàn)指數(shù)最高,為16. 92;盤(pán)羊7—8月主要出現(xiàn)在32 號(hào)水源地,出現(xiàn)指數(shù)為7. 60;禿鷲9—10 月在32號(hào)水源地出現(xiàn)指數(shù)最高,為3. 33,其次為406號(hào)路邊水源地,為2. 27;赤麻鴨、毛腿沙雞和草原雕主要分布在庫(kù)木西克水源地,出現(xiàn)指數(shù)分別是7. 67、7. 17和3. 24。
3. 3 觀賞路線與觀賞點(diǎn)設(shè)計(jì)
根據(jù)監(jiān)測(cè)數(shù)據(jù)結(jié)果,卡拉麥里國(guó)家公園一般控制區(qū)內(nèi)野生動(dòng)物的分布有明顯的空間和季節(jié)差異,且有5處水源地(31、32、33號(hào)水源地、五彩城南水源地和37號(hào)水源地)不在主干道路上,不能一次全部經(jīng)過(guò),需要設(shè)計(jì)分支路線,所以在設(shè)計(jì)觀賞路線時(shí)分2個(gè)時(shí)間段:夏季(7—8月)和秋季(9—10月)。31、32、33號(hào)和五彩城南水源地在一條支線上,7—8月的動(dòng)物出現(xiàn)指數(shù)相對(duì)較高,因此將其規(guī)劃在夏季觀賞路線中;而37號(hào)水源地則是9—10月動(dòng)物出現(xiàn)指數(shù)更高,將其規(guī)劃在秋季觀賞路線中。
將各觀賞點(diǎn)中的物種根據(jù)出現(xiàn)頻率由高到低進(jìn)行排序,選取前4個(gè)作為目標(biāo)觀賞物種;為保證每個(gè)物種都有觀賞點(diǎn),根據(jù)每個(gè)物種的最大出現(xiàn)指數(shù)固定其第一觀賞點(diǎn)后再進(jìn)行排序(表2)。夏季觀賞路線中設(shè)置4個(gè)觀賞點(diǎn),31、32、33號(hào)水源地和五彩城南水源地距離較近,所以共用一個(gè)觀賞點(diǎn)(圖6)。秋季觀賞路線設(shè)置5個(gè)觀賞點(diǎn),其中2號(hào)觀賞點(diǎn)(37號(hào)水源地)只有蒙古野驢和野馬2 個(gè)物種,且出現(xiàn)指數(shù)較低,所以將其設(shè)置為補(bǔ)充觀察點(diǎn)選擇性觀賞(圖7)。
4 討論
4. 1 野生動(dòng)物觀賞路線設(shè)計(jì)考慮因素
視覺(jué)質(zhì)量在自然旅游中一直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13],在野生動(dòng)物旅游中,野生動(dòng)物可視度則是衡量視覺(jué)質(zhì)量最重要的因素,所以本研究?jī)?yōu)先考慮野生動(dòng)物在道路或水源地附近出現(xiàn)的時(shí)間、地點(diǎn)和數(shù)量,在對(duì)野生動(dòng)物不造成影響的情況下,設(shè)計(jì)動(dòng)物可視度最高的旅游路線。
為保證繁殖成功率,動(dòng)物在繁殖期會(huì)表現(xiàn)出更強(qiáng)烈的警戒行為[14],一旦受到驚擾,則要花費(fèi)更長(zhǎng)的時(shí)間來(lái)恢復(fù)到正常狀態(tài)[15]。卡拉麥里國(guó)家公園是新疆有蹄類(lèi)野生動(dòng)物主要活動(dòng)區(qū)域,蒙古野驢、野馬等有蹄類(lèi)野生動(dòng)物繁殖期集中在3—6 月[16?17],選擇7—10月作為旅游時(shí)間可以有效確保野生動(dòng)物正常繁育,減小人類(lèi)活動(dòng)造成的干擾。卡拉麥里國(guó)家公園冬季寒冷漫長(zhǎng),春夏季炎熱干旱,秋季溫涼,冬季極其嚴(yán)寒[18],將7—10月作為旅游時(shí)間也可以避開(kāi)極端溫度,增加旅游舒適度。
水是荒漠地區(qū)野生動(dòng)物生存所必需的因素之一,對(duì)野生動(dòng)物分布起著決定性作用[19],許多對(duì)卡拉麥里國(guó)家公園內(nèi)野生動(dòng)物生境適宜性評(píng)價(jià)的結(jié)果都顯示貢獻(xiàn)率最大的環(huán)境變量為距水源地距離,并且大于距人類(lèi)活動(dòng)區(qū)距離的貢獻(xiàn)率[16,20?21],所以將水源地作為觀賞點(diǎn)可以觀察到最大數(shù)量的野生動(dòng)物。數(shù)據(jù)顯示,7—10月相機(jī)拍攝到的野生動(dòng)物明顯比其他時(shí)間段多,且有研究表明夏季高溫以及秋季干燥會(huì)增加動(dòng)物在夏、秋兩季對(duì)水源地的利用率[22],導(dǎo)致動(dòng)物在水源地的聚集,還有可能是7—10月狼因?yàn)樗磫?wèn)題向核心區(qū)集中[23],迫使有蹄類(lèi)動(dòng)物向控制區(qū)遷移。在考慮到水源地對(duì)野生動(dòng)物重要性的前提下,結(jié)合距道路距離以確定適宜的觀賞點(diǎn)位置,本研究將觀賞點(diǎn)設(shè)置在距水源地2 000 m外的道路附近,在確保觀賞質(zhì)量的同時(shí),最大限度地降低對(duì)野生動(dòng)物及其棲息地的干擾[24]。
相較于傳統(tǒng)旅游,生態(tài)旅游的游客承載量小,過(guò)多人的出現(xiàn)會(huì)影響野生動(dòng)物的生活習(xí)性、分布情況,同時(shí)游客體驗(yàn)也會(huì)隨游客數(shù)量的增加而受到負(fù)面影響[25],在設(shè)計(jì)觀賞點(diǎn)時(shí)要盡可能將參觀游客平均地分配到各個(gè)觀賞點(diǎn),這有助于減少游客所帶來(lái)的壓力,如本研究將2號(hào)觀賞點(diǎn)設(shè)置為補(bǔ)充觀賞點(diǎn)有助于緩解游客在單一水源點(diǎn)聚集。當(dāng)然,保護(hù)區(qū)和國(guó)家公園也可以通過(guò)限制游客進(jìn)入特定地點(diǎn)或限定游客量來(lái)降低旅游活動(dòng)對(duì)野生動(dòng)物的影響[26]。
4. 2 國(guó)家公園野生動(dòng)物觀賞旅游管理
國(guó)家公園的戶(hù)外游憩和旅游活動(dòng)必須符合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原則。卡拉麥里國(guó)家公園生態(tài)旅游管理最核心的目標(biāo)是對(duì)野生動(dòng)物的可持續(xù)觀賞利用[27],所以在開(kāi)展旅游過(guò)程中減少對(duì)野生動(dòng)物的干擾,保護(hù)野生動(dòng)物不被侵害成為旅游管理中的關(guān)鍵一環(huán)。
長(zhǎng)時(shí)間的人類(lèi)活動(dòng)會(huì)對(duì)野生動(dòng)物的出現(xiàn)率造成影響,加拿大一研究發(fā)現(xiàn),在道路關(guān)閉期間野生動(dòng)物出現(xiàn)率比開(kāi)放期多了一倍[28],所以在野生動(dòng)物旅游開(kāi)展期間,可以通過(guò)適當(dāng)暫停觀賞點(diǎn),提供緩沖時(shí)間,提高野生動(dòng)物復(fù)現(xiàn)率。與此同時(shí),野生動(dòng)物旅游項(xiàng)目的實(shí)施,會(huì)導(dǎo)致國(guó)家公園外來(lái)人員和車(chē)流量的增加,可通過(guò)限定入園人數(shù),限時(shí)封閉公園內(nèi)車(chē)輛行駛路段和停放區(qū)域的方式,來(lái)緩解人類(lèi)活動(dòng)激增給野生動(dòng)物帶來(lái)的干擾。
不同旅游活動(dòng)類(lèi)型也會(huì)對(duì)動(dòng)物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有研究發(fā)現(xiàn),車(chē)輛的通過(guò)提高了野生動(dòng)物的警惕和躲避行為,減少了覓食時(shí)間[29],但靜止觀察卻可以使觀察者與動(dòng)物保持較近的距離[8],所以本研究基于動(dòng)物警戒距離將觀賞點(diǎn)設(shè)置在2 000 m以外的位置,未來(lái)可以考慮修建步行道路實(shí)現(xiàn)游客對(duì)野生動(dòng)物更近距離地觀察。
噪聲同樣也是影響野生動(dòng)物行為的重要因素,動(dòng)物在車(chē)輛接近時(shí),對(duì)噪聲更大的車(chē)輛表現(xiàn)出更遠(yuǎn)距離的逃避行為[30],甚至還會(huì)增加野生動(dòng)物接觸到寄生蟲(chóng)的概率,提高患病概率[31],因此可以設(shè)立“禁止鳴笛”警示牌減少對(duì)動(dòng)物的驚嚇,還可以在國(guó)家公園外部設(shè)置臨時(shí)停車(chē)場(chǎng)并配備電動(dòng)觀光車(chē),減少?lài)?guó)家公園內(nèi)部車(chē)流量,降低車(chē)輛噪聲對(duì)野生動(dòng)物的干擾。
道路在為人類(lèi)交通提供便捷的同時(shí),對(duì)野生動(dòng)物種群構(gòu)成了嚴(yán)重的負(fù)面影響。卡拉麥里國(guó)家公園南北由S11 高速公路、阿富準(zhǔn)鐵路以及國(guó)道216 線3條道路穿過(guò),導(dǎo)致野生動(dòng)物出現(xiàn)了明顯的回避行為,阻礙國(guó)家公園內(nèi)野生動(dòng)物東西向的遷移擴(kuò)散,加劇國(guó)家公園東西部蒙古野驢的生境隔離,可能進(jìn)一步影響蒙古野驢對(duì)生境的季節(jié)性利用和種群基因交流[20]。根據(jù)不同野生動(dòng)物的習(xí)性在旅游道路上修建不同類(lèi)型的遷移廊道,可有效保護(hù)野生動(dòng)物種群并擴(kuò)展其棲息地。